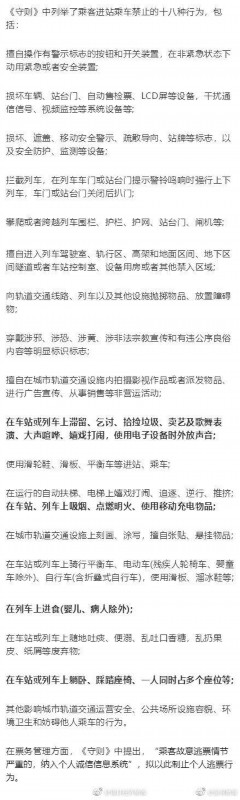文帝十二年(前168)三月,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文帝十三年(前167)五月,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吾甚自愧……《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其除肉刑。”
文帝十四年(前166)春,诏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文帝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上列诏令,应该是由文帝自作。表面的证据是,诏令中自称用“吾”,人臣草诏不敢这样。深层的证据是,皇帝下诏示以谦卑之态,说“朕既不德”、“朕甚自丑”、“朕甚自愧”云云,后世虽屡见不鲜,文帝之前其实并没有先例。既无先例,人臣草诏就不敢轻易用,以免干犯忌讳。汉帝诏令称引《五经》,也是从文帝开始的,如上举十三年诏,就引了《诗经》。汉初,黄老思想是主流,儒学地位并不尊显,诏令之中引《五经》,应属政治思想上的大事,人臣草诏是不敢这样造次的。
文帝作诏,具体是口授,还是亲笔?这不易确定,只能推测。简单浅显些的诏令,应是口授,侍御史在旁笔录。精致文雅些的诏令,可能是亲笔草拟。拟成之后,由侍御史按格式誊抄,然后加盖玺印,发送御史大夫颁下。此外,联系到当时书写不易的情形,文辞考究的诏令,不乏历经以下程序的可能:侍御史先将文帝口授的意旨笔录在简牍上,然后将简牍奉上,请文帝审定,待文帝润色完毕后,侍御史再按格式誊抄,进而送御史大夫颁下。总体来说,不论是哪种情形,诏令都由皇帝自作,御史只负责将其制作成正规的文书。
由高祖和文帝的情形来看,西汉初期,皇帝自作诏令应属常态,人臣草诏之制仍未形成,人臣负责的其实仍是“记王言”。
前辈学者受东汉以后历史的影响,觉得设专官来掌草诏,应是皇权时代始终都有的现象,于是逆推汉初的草诏之官,认为御史庶几近之。然而,说汉初由御史草诏,并无直接证据,反倒是皇帝自作诏令的例证,很容易发现。既然有这种矛盾,我们就要问个问题:什么历史条件下,人臣才可能有权“代王言”?简单来说,皇帝能让近臣草拟诏令,而自己只需授意即可,这得有个前提,即诏令怎样写,已经形成了较固定的套路,哪些话可用,哪些话不能用,能用的该怎样用,大体有一定之规。用当下流行的话讲,就是诏令已经形成一套话语体系。没有这个前提,人臣要“代王言”,说多了,说偏了,都是件大事。那么,汉初诏令怎样写,是否已经有了固定的套路?显然没有。话语体系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形成的,得有个过程。在话语体系没有形成之前,近臣所作的,是“记王言”而不是“代王言”,皇帝才是诏令的真正作者。
四、“代王言”与东汉人臣草诏之制的确立
相较于初期,西汉中期的诏令特点有所变化。《文心雕龙》说:“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确实,汉武帝诏令力求古雅,远离当时的口语。公孙弘任丞相时,曾上奏说:“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当时的“小吏”,能识字写字,却读不懂武帝的诏令,为什么?因为武帝诏令,喜欢引经典,用古语,要想读懂,得有经学素养。“小吏”文化素养不高,自然难以完全理解武帝的诏令。
推荐阅读
- 盘点不同朝代汉服特点:秦汉曲裾繁琐,魏晋宽衫飘逸,你喜欢哪种
- 中国古代的“战斗民族”,从建国打到灭亡没停过,并非秦汉和蒙元
- “粪土当年万户侯”:浅谈秦汉时期的爵位制度
- 秦汉历史剧中的那些娱乐项目,不能乱编,两千年出土文物都有实证
- 听名校名师 讲中国史
- 幽冥世界其实是与秦汉帝国同步形成的
- 秦封泥:跨越秦汉的封缄“密钥”
- 考古证实秦汉建筑文明始于秦栎阳城
-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打通文化科技融合“最后一公里”
- 一代人|中国史上最强大的一代人,百家争鸣,秦汉唐宋,根本就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