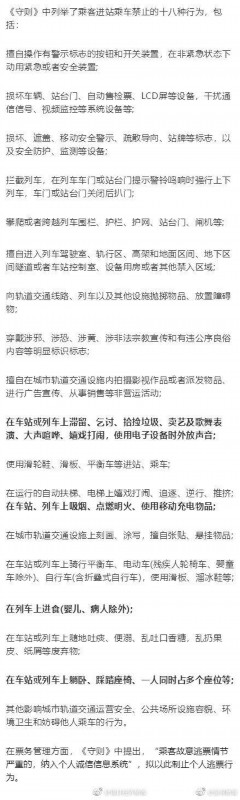三、战国至汉初的人臣“记王言”之制
战国时期,由于文书行政机制的确立,君命已广泛用文书来发布。不过,君主的命令文书未必是由人臣起草的。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一时期命书的形成过程应该是这样:君主口授,近臣书写于简牍之上并制成规范文书。近臣负责的是“记王言”。战国时期,君主左右有御史一官,掌管文书之事。《战国策·韩策一》曰:“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是故秦王使使臣献书于大王御史。’”《战国策·赵策二》载:“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献书于大王御史。’”两条史料说明,御史负责将文书转呈给君主。不过,御史职责不止于此,他还负责书记录君主之言。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渑池之会,秦国御史与赵国御史记录两国君主的言行。又如《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之言:“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御史近侍左右,大约有记言之责。再如《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此“侍史”类似于国君左右的“御史”,职掌记言。此类材料说明战国之时设有专官掌记君主之言,此官即御史。由于战国御史还兼司文书的上达,可知其属于行政官员,性质不同于隋唐之起居舍人,起居舍人实际上是史官。御史既为行政官员,其所记之言,应该就是君主的政令。其过程大约就是君主口授命令,御史书于简牍,然后下达于有司。
《周礼》有五史之名,御史为其一。《周礼》的成书年代,学界有多种看法。综括传世文献与金文材料来看,《周礼》的问世,应该不会早于战国。彭林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着眼,断定其书成于西汉之初。此说有一定的道理。至于《周礼》的性质,学界的看法已趋同,认为此书虽非某个时代官制的实录,但很多内容都是有历史根据的。而《周礼》对御史的某些描述,比较符合战国时期的情形。
《周礼·春官·御史》曰:“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郑玄注“凡治者授法令焉”曰:“为书写其治之法令,来受则授之。”注“掌赞书”曰:“王有命,当以书致之,则赞为辞,若今尚书作诏文。”孙诒让疏曰:“王有诏命,当书之简册,宣布内外,则赞为辞,若今尚书作诏文。”郑玄、孙诒让看到御史的职掌与东汉尚书有联系,这是其独到处。不妥之处在于其将“赞书”转换成“赞为辞”。“书”、“辞”虽一字之异,相差甚远。东汉尚书郎主起文书草,负责“代王言”,属于“赞为辞”无疑。但《周礼》御史“赞书”,实际上是“记王言”。赞者,助也。赞书,就是帮助书写。战国之时,书写的材料主要是简牍,书写的工具主要是刀笔。书写远不如后世方便,文书的制成也比后世复杂。故君主设专官负责帮助他书写,而自己口授即可,这样可以省去了不少时间和麻烦。御史“掌赞书”,就是将君主之言记于简牍之上。“赞书”,要求忠实记录,不应润色修饰。“赞为辞”则不同,就是要起草诏文,这是后世尚书、中书之事,战国御史并不承担此任。《周礼》言“御史掌赞书”,恰恰印证了战国时期命书形成的过程。
御史因为掌记君命,遂有“主法”之责。法令出自君主,御史掌记之于策,等于手持法令。《周礼》所谓“凡治者受法令焉”,大约就是指御史抄写法令下发“治者”。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中的《尉杂》曰:“岁雠辟律于御史。”“雠”是校对、核对之意。这是由于君主所宣法令,御史记于简册,犹如持法令之正本,故廷尉要到御史处核对法令。可见,御史能掌管法令,缘于其书记王言。盖御史本以文字立业也。
秦代诏令的形成过程与战国相似,大约还是由皇帝口授,近臣书写,然后发付有司,人臣草诏之制并未确立。《史记·李斯列传》载:“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所谓“令赵高为书”,应指始皇口述,赵高书记。又,睡虎地秦简中,南郡守腾下达给本郡各县、道的文告,名曰“语书”。整理小组据韦昭注《国语》之言,释为“教戒的文告”。这种说法似乎还可以商榷。其实,所谓“语书”,也有可能指此“书”的来源是“语”,是记录“语”的。西汉有些地方文告就是这样形成的。如《汉书·朱博传》载,朱博为琅琊太守,“阁下书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贼发不得,有书。檄到,令、丞就职,游徼王卿力有余,如律令!’王卿得敕惶怖。”这一檄文是由朱博口授、阁下书佐书记而成的。睡虎地秦简《语书》的形成过程可能与此类似。秦律《内史杂》有条律文曰:“下吏能书者,毋敢从史之事。”“史”掌书记,且有资格限制,恐与其参与命令文书的制成有关。综括上述的证据,我们认为,秦代的诏令应该是皇帝自作的,近臣一般只负责将其记录于简册之上。人臣依旧是“记王言”,而非“代王言”。
推荐阅读
- 盘点不同朝代汉服特点:秦汉曲裾繁琐,魏晋宽衫飘逸,你喜欢哪种
- 中国古代的“战斗民族”,从建国打到灭亡没停过,并非秦汉和蒙元
- “粪土当年万户侯”:浅谈秦汉时期的爵位制度
- 秦汉历史剧中的那些娱乐项目,不能乱编,两千年出土文物都有实证
- 听名校名师 讲中国史
- 幽冥世界其实是与秦汉帝国同步形成的
- 秦封泥:跨越秦汉的封缄“密钥”
- 考古证实秦汉建筑文明始于秦栎阳城
-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打通文化科技融合“最后一公里”
- 一代人|中国史上最强大的一代人,百家争鸣,秦汉唐宋,根本就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