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西汉,诏令大多由皇帝自作,侍御史或尚书负责将皇帝的诏令制成正规的文书,然后发送御史大夫颁下。终乎西汉,人臣草诏之制仍未确立。
东汉施行三公之制,制书的制作、颁下之权转而归于尚书。而人臣草诏之制完全确立,就是在东汉。
《汉官仪》载:“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夜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所谓“文书起草”,应指草诏。据《后汉书·周荣传》,安帝时,尚书陈忠上疏说:“诸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才,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辞多鄙固。”这条材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汉安帝时,人臣草诏之制已经完全确立。诏令一般由尚书郎起草,皇帝不必自作诏令。一是制度确立,时间还不太久。如果尚书郎“代王言”早已属定制,选任其人之时,肯定会取才学之士,还不至于出现“转相求请”、“辞多鄙固”的窘态。陈忠的上疏表明,草诏应是尚书郎的新增职责,他们对此还不熟悉,正在适应之中。因此,我们推断,人臣草诏之制完全确立,可能是在章帝或和帝之时。
把人臣草诏之制的完全确立定在这个时间,同时也是考虑到光武帝和明帝还有自作诏令的习惯。光武帝自作诏令之例,清人赵翼已指出了一些,此处再举三个。建武六年(30)十月丁丑,诏曰:“吾德薄不明,寇贼为害,强弱相陵,元元失所。”建武七年(31)三月癸亥,日有食之。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这些诏令只能出自光武帝之手。由此推测,光武帝自作诏令,应属常态。又《后汉书·钟离意传》载,明帝时,“诏赐降胡子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帝见司农上簿,大怒,召郎将笞之。意因人叩头曰:‘过误之失,常人所容。’”所谓“尚书案事”,极有可能指明帝口授,尚书代笔,所以才会出现“以十为百”的过失。如果诏文由尚书郎草拟而成,理应经明帝审定才可下发,还不至于等到司农上簿,皇帝才觉察其误。同《传》又载:“帝性褊察……朝廷莫不悚慄,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解救之。”钟离意时任尚书仆射,他“封还诏书”就表明,诏令应出自明帝。综括来说,光武帝和明帝时,重要诏令大约还是由皇帝自作,尚书台主要负责将皇帝草拟的诏令制成规范的制书,然后再将制书颁下。尚书郎“代王言”之制完全确立,应该是章帝或和帝时的事情了。
东汉确立尚书郎“代王言”的制度之后,皇帝自作诏令的现象并未就此消失。尤其是东汉末期,皇帝动辄自作诏令以任命官员。此类诏令称为“尺一”,应该是皇帝临时口授,由近臣写就的,而且不经尚书台就颁布执行。如桓帝时,李云上疏说:“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灵帝时,杨政为老师范升诉冤,“乃肉袒,以箭贯耳,抱升子潜伏道旁,候车驾,而持章叩头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适三岁,孤之可哀。’武骑虎贲惧惊乘舆,举弓射之,犹不肯去;旄头又以戟叉政,伤胸,政犹不退。哀泣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即尺一出升”。桓、灵二帝屡屡下达“尺一”任命官员,几成泛滥之势。但是,用“尺一”来命官,频受大臣非议。桓帝延熹年间,时任光禄勋的陈蕃上疏说:“陛下宜采求失得,择从忠善。尺一选举,委尚书三公,使褒责诛赏,各有所归,岂不幸甚!”灵帝元和年间,光禄大夫杨赐上疏说:“惟陛下慎经典之诫,图变复之道,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内亲张仲,外任山甫,断绝尺一,抑止盘游,留思庶政。”可见,皇帝用“尺一”来命官,是违反了正常程序的。一般而言,诏令要由尚书台起草、颁下。
五、结语
由上可知,人臣草诏之制是东汉初期才完全确立的。春秋以前,王命一般用口头方式发布、下达,所以不存在人臣为王起文书草的问题。到战国时期,由于文字的广泛传播和官僚体制的确立,文书行政机制正式确立,形成了人臣“记王言”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大一统帝国建立之后,仍持续了一段时间,等到帝国体制发展到特定阶段,才被人臣“代王言”的制度所取代。
推荐阅读
- 盘点不同朝代汉服特点:秦汉曲裾繁琐,魏晋宽衫飘逸,你喜欢哪种
- 中国古代的“战斗民族”,从建国打到灭亡没停过,并非秦汉和蒙元
- “粪土当年万户侯”:浅谈秦汉时期的爵位制度
- 秦汉历史剧中的那些娱乐项目,不能乱编,两千年出土文物都有实证
- 听名校名师 讲中国史
- 幽冥世界其实是与秦汉帝国同步形成的
- 秦封泥:跨越秦汉的封缄“密钥”
- 考古证实秦汉建筑文明始于秦栎阳城
-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打通文化科技融合“最后一公里”
- 一代人|中国史上最强大的一代人,百家争鸣,秦汉唐宋,根本就比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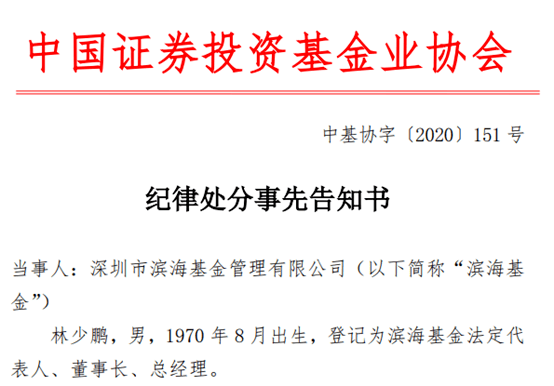







![人民网|[网连中国]乡音唱新风、定约除陋习,文明实践最后"一公里"通了](https://mz.eastday.com/1840376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