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御史和尚书,都还只是“刀笔吏”,诏令不会出自他们之手。武帝文化素养很高,有自作诏令的习惯。他每赐淮南王玺书,“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表明玺书由他自拟。武帝诏令,要论文辞最讲究者,莫过于封三王策,而策文正出自武帝之手。西汉末期的褚少孙言及策文,说:“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唐司马贞根据当时的传世文献,指出:“三王策皆武帝手制。”都说明了这一点。由此类推,武帝诏令,大约还是以他自拟为主。不过,武帝好辞章,任用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文学之士为郎,这些词臣常侍左右,可能也承担着草拟部分诏令的职责。
汉武帝的诏令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文辞,追求典雅古奥之美。一是推重五经,凡事喜欢寻求经典上的依据。这两点有着深远影响,是后世诏令的基调。有这个基调,才有人臣草诏之事。不过,这还是得有个过程。从皇帝自拟诏令,到人臣草诏之制完全确立,中间应该还有个过渡期。事实上,西汉中后期,甚至还包括东汉初,正处于这个过渡期。这一时期,皇帝自作诏令仍属常态,但有些诏令已交由近臣起草。
汉宣帝的有些诏令,由他口授,侍御史笔录。东汉胡广说:“孝宣感路温舒言,秋季后请谳。时帝幸宣室,斋居而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书。”两位侍御史是书记官,掌“记王言”。元帝也自作诏令。元帝侍中曾评价元帝说:“元帝多材艺,善史书。……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所谓“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评价的应是元帝自作的诏令。哀帝策立董贤为大司马,用“允执其中”一语,赵翼已经指出,策文应出自哀帝之手。综括种种迹象,我们认为,西汉中后期,重要诏令还是以皇帝自作为主。
同时,有证据表明,这一时期已逐渐有人臣草诏之事。《汉书·贾捐之传》载,元帝时,长安令杨兴上书说:“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使君房为尚书令,胜五鹿充宗远甚。”由此来看,尚书令似乎偶尔代草诏令。尚书令草诏,是很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方面,这表明人臣草诏之制正在逐渐确立。武帝时虽有近臣草诏的情形,但草诏者不是因官而得职,人臣能不能草诏,要看他有没有文学才能,受不受皇帝赏识,和他任什么官职没有直接关系。元帝时不同,人臣能不能草诏,要看他是不是尚书令,不是尚书令就不能草诏。草诏之权在官而不在人,意味着人臣草诏之制正在逐渐形成。另一方面,这说明人臣草诏之制还未正式确立。此时由尚书令草诏,先要看他是否有文学才能,表明草诏依然具有临时差遣的味道,还未彻底成为尚书台这个机构的职责。这与重要诏令主要由皇帝自作,是一致的。
西汉中后期,皇帝口宣的诏令,由谁来笔录呢?皇帝及词臣草拟好的诏令,由谁按格式誊抄,最终制成正规的制书呢?从敦煌悬泉出土的“传信简”来看,主要还是由侍御史负责。如简(Ⅱ0214③:73):“甘露二年十一月丙戌,富平侯臣延寿、光禄勋臣显承制诏侍御史:闻治渠军猥候丞承万年汉光王充诣校属作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一各人,轺传二乘。”简(Ⅰ0112②:18):“建平四年五月壬子,御史中丞臣宪,承制诏侍御史:敦煌玉门都尉忠之官,为驾一封轺传,载从者。”两者皆系中朝臣代宣王言,由侍御史笔录并制成规范的文书。不过,随着尚书台的日渐壮大,尚书也开始染指这一事宜。《汉书·郑崇传》载,建平四年(前3),哀帝要封傅太后的堂弟傅商为侯,尚书仆射郑崇“谏曰:‘孝成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今无故欲复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愿以身命当国咎。’崇因持诏书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为天子乃反为一臣所颛制邪!’”上遂下诏曰:“朕幼而孤,皇太后躬自养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礼,至于成人,惠泽茂焉。……其封商为汝昌侯。”所谓“诏书案”,颜师古说:“案者,即写诏之文。”可以看出,哀帝下诏封傅商,程序是这样的:他口授诏令,尚书仆射郑崇笔录成文书。则西汉中后期尚书偶尔也负责“记王言”。这和汉初纯由侍御史负责的情形已有所区别。但始终未变的是,侍御史或尚书将皇帝的诏令制成正规的制书后,依然要交付御史大夫,由御史大夫最终颁下。
推荐阅读
- 盘点不同朝代汉服特点:秦汉曲裾繁琐,魏晋宽衫飘逸,你喜欢哪种
- 中国古代的“战斗民族”,从建国打到灭亡没停过,并非秦汉和蒙元
- “粪土当年万户侯”:浅谈秦汉时期的爵位制度
- 秦汉历史剧中的那些娱乐项目,不能乱编,两千年出土文物都有实证
- 听名校名师 讲中国史
- 幽冥世界其实是与秦汉帝国同步形成的
- 秦封泥:跨越秦汉的封缄“密钥”
- 考古证实秦汉建筑文明始于秦栎阳城
-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打通文化科技融合“最后一公里”
- 一代人|中国史上最强大的一代人,百家争鸣,秦汉唐宋,根本就比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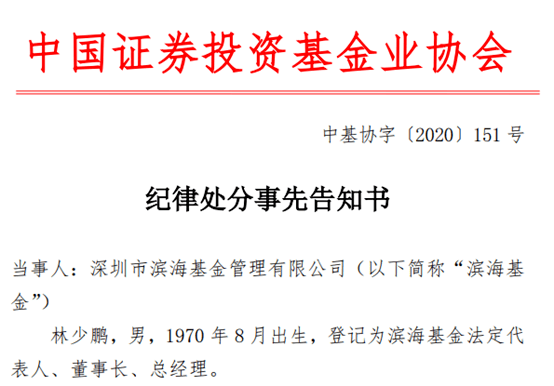







![人民网|[网连中国]乡音唱新风、定约除陋习,文明实践最后"一公里"通了](https://mz.eastday.com/1840376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