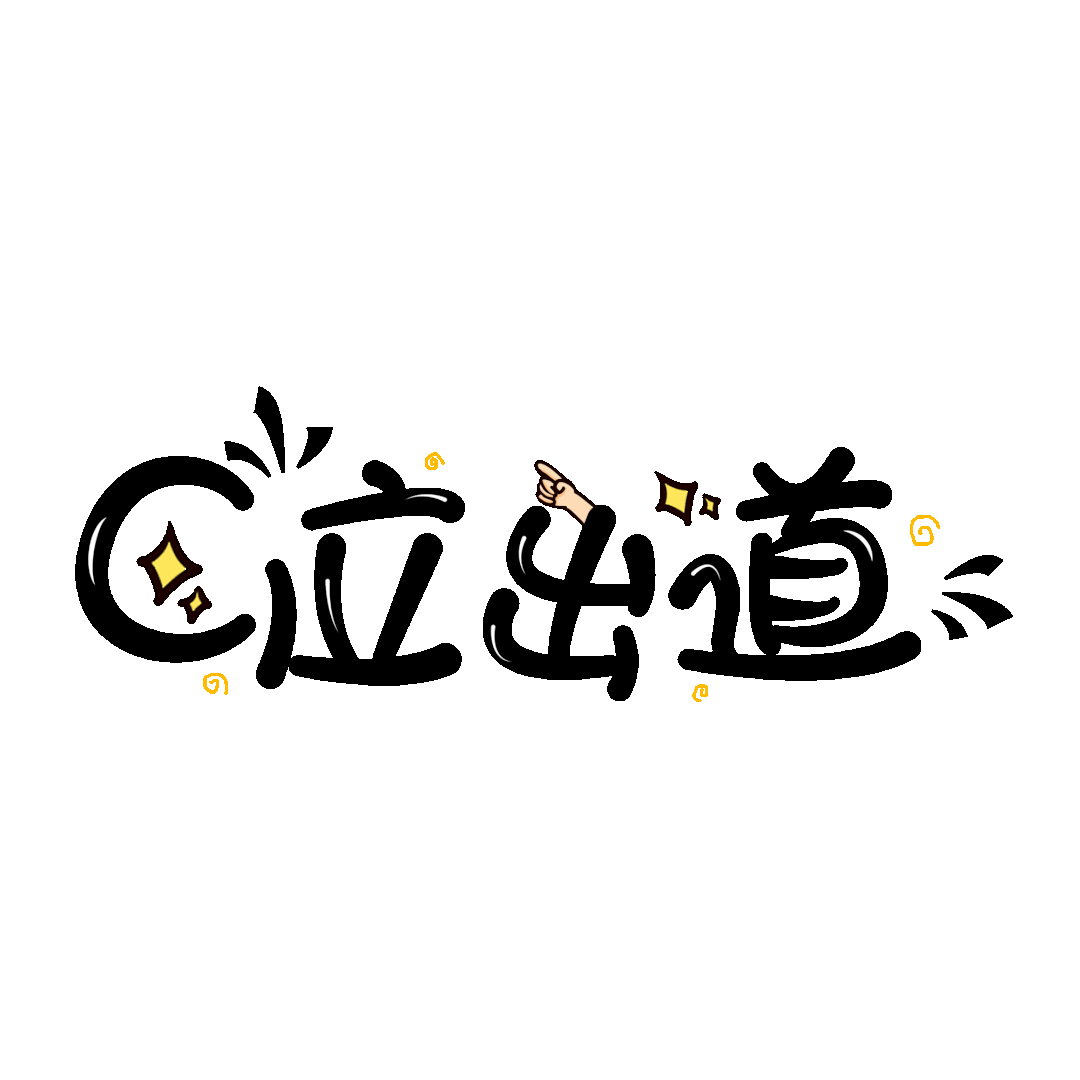жҜ•еҠ зҙўдёҺжҠҪиұЎ|гҖҢжҜ”иҫғгҖҚ| иҝӘ科尔жӣј( е…ӯ )
зҺ°еңЁпјҢжҲ‘еёҢжңӣеӨ§е®¶иғҪеҺҹи°…жҲ‘иҝҷж¬Ўе…ідәҺи’ҷеҫ·йҮҢе®үзҡ„зҰ»йўҳгҖӮжҲ‘жң¬еҸҜд»Ҙз”Ёе…¶д»–зҡ„дҫӢеӯҗжқҘеӣһзӯ”вҖңеҰӮжһңвҖқзҡ„й—®йўҳ вҖ”вҖ” дҫӢеҰӮпјҢеҸҰеӨ–дёӨдҪҚиүәжңҜ家пјҢеҰӮ马еҲ—з»ҙеҘҮе’ҢеЎ”зү№жһ—пјҢд№ҹз»ҸеҺҶдәҶз”ұжҜ•еҠ зҙўзӣҙжҺҘеҗҜеҸ‘зҡ„з«ӢдҪ“жҙҫйҳ¶ж®өпјҢ他们и®ӨдёәиҮӘе·ұжҳҜзңҹжӯЈзҡ„жҜ•еҠ зҙўзҡ„继жүҝдәәгҖӮдёӨдәәз»•иҝҮдәҶеңЁи’ҷеҫ·йҮҢе®үйӮЈйҮҢеҫҲйҮҚиҰҒзҡ„вҖңе°Ҷжҹҗзү©жҠҪиұЎвҖқзҡ„йҳ¶ж®өпјҢд»ҺиҖҢиҜҒжҳҺжҲ‘дёҖејҖе§Ӣе°ұжҸҗеҲ°зҡ„пјҢйҷӨдәҶе°ҶиҮӘ然жҜҚйўҳдёҚж–ӯжҸҗзӮјд№ӢеӨ–пјҢиҝҳеӯҳеңЁзқҖе…¶д»–ж–№ејҸзҡ„жҠҪиұЎгҖӮ然иҖҢпјҢж— и®әи’ҷеҫ·йҮҢе®үгҖҒ马еҲ—з»ҙеҘҮжҲ–еЎ”зү№жһ—жүҖиө°зҡ„и·ҜзәҝжңүеӨҡд№ҲдёҚеҗҢпјҢе®ғ们йғҪиө·жәҗдәҺжҜ•еҠ зҙўзҡ„з«ӢдҪ“жҙҫгҖӮжҖ»д№ӢпјҢз«ӢдҪ“жҙҫжҳҜдёҖдёӘжҠҪиұЎзҡ„и·іжқҝпјҢжҳҜжҜ•еҠ зҙўиҮӘе·ұжӢ’з»қи·іи·ғзҡ„и·іжқҝгҖӮ
иҮідәҺд»–дёәд»Җд№ҲжІЎжңүи·іпјҢжҲ‘们еӨ§еҸҜз®ҖеҚ•ең°е°Ҷе®ғеҪ’еӣ дәҺжҒҗжғ§пјҢе°ұеғҸиҝӘ科尔жӣје’ҢжҲ‘еңЁдёҺеЎһжӢүзҡ„еҜ№иҜқдёӯжүҖз»ҷеҮәзҡ„дҝ®иҫһдёҖж ·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үжҳҜжҺЁжөӢеҺҹеӣ пјҢе’ҢеҺҶеҸІеӯҰ家зҡ„иҒҢиҙЈжҳҜзӣёиҝқиғҢзҡ„пјҢе°ұеҰӮеҗҢеҺҶеҸІеӯҰ家дёҚеә”иҜҘй—®вҖңеҒҮеҰӮжҖҺж ·еҸҲдјҡжҖҺж ·вҖқзҡ„й—®йўҳгҖӮжүҖд»ҘпјҢжҺҘдёӢжқҘжҲ‘дјҡйӣҶдёӯиҜҙжҳҺпјҢе°Ҫз®ЎжҜ•еҠ зҙўдјјд№Һе·Із»ҸеңЁиҘҝзҸӯзүҷеҚЎиҫҫе…Ӣж–ҜдёӢе®ҡдәҶеҶіеҝғпјҢдҪҶжҳҜеңЁе…¶д№ӢеҗҺзҡ„ж•ҙдёӘиҒҢдёҡз”ҹж¶ҜдёӯпјҢд»–йғҪдјҡдёҚж—¶ең°йҮҚж–°жҺўзҙўжҠҪиұЎзҡ„еҸҜиғҪпјҢиҝҷдјјд№ҺжҳҜдёәдәҶе®үжҠҡиҮӘе·ұпјҢд№ҹеҸҜиғҪжҳҜдёәдәҶеҸ–笑他иҮӘе·ұгҖӮ
иҝҷз§ҚдәӢжғ…еҸ‘з”ҹеңЁи®ёеӨҡж—¶еҲ»пјҢ第дёҖж¬ЎеҸ‘з”ҹеңЁеҚЎиҫҫе…Ӣж–ҜеӨұиҙҘдәӢ件еҗҺдёҚд№…гҖӮжҲ‘иҜҙзҡ„жҳҜ1913е№ҙзҡ„жҳҘеӨ© вҖ”вҖ” иҝҷжҳҜжҜ•еҠ зҙўеҲӣдҪңдёӯзҡ„йҮҚиҰҒеүҚиҝӣйҳ¶ж®өпјҢжҲ‘е°ҶеҶҚдёҖж¬Ўз®Җзҹӯең°иҜҙжҳҺиҝҷдёҖзӮ№пјҢеӣ дёәжҲ‘е·Із»ҸеҶҷиҝҮеҫҲеӨҡдәҶгҖӮ
иҝҷдёҖж—¶жңҹжӯЈжҳҜжүҖи°“зҡ„з»јеҗҲз«ӢдҪ“дё»д№үзҡ„е…Ёзӣӣж—¶жңҹгҖӮжҜ•еҠ зҙўе·Із»Ҹз»ҸеҺҶдәҶеүҚдёӨдёӘйҮҚиҰҒзҡ„жӢјиҙҙзі»еҲ—еҲӣдҪңж—¶жңҹпјҲиҝҷдёҖйҳ¶ж®өд»Һ1912е№ҙз§ӢеӨ©ејҖе§ӢпјҢе°ұеңЁд»–еҸ‘иЎЁж—·дё–еҘҮдҪңгҖҠеҗүд»–гҖӢд№ӢеҗҺдёҚд№…пјҢд»ҘеҸҠд»Һ1912е№ҙеҶ¬еӨ©еҲ°1913е№ҙеҲӣдҪңжӣҙеӨ§зҡ„зі»еҲ—з»ҳз”»ејҖе§Ӣ)гҖӮеҪ“д»–жӯЈиҮҙеҠӣдәҺжӢјиҙҙз”»зҡ„ж—¶еҖҷпјҢжҜ•еҠ зҙўеҒ¶з„¶еҸ‘зҺ°дәҶдёҖдёӘй—®йўҳпјҢ并дёәд№ӢзқҖиҝ· вҖ”вҖ” жҲ–иҖ…еҸҜд»ҘиҜҙпјҢиҝҷжҳҜд»–еҶҚж¬ЎйҒҮеҲ°зҡ„й—®йўҳпјҢеӣ дёәе®ғеҸҜд»ҘиҝҪжәҜеҲ°з”»е®¶еҜ№вҖңз¬ҰеҸ·зҡ„з»ҹдёҖзі»з»ҹвҖқзҡ„еҜ»жүҫпјҢиҝҷз§ҚеҜ»и§…дё»еҜјзқҖд»–еӨҡе№ҙжҠ•е…Ҙзҡ„жүҖи°“еҲҶжһҗз«ӢдҪ“дё»д№үж—¶жңҹпјҲиҜ·еӨ§е®¶и®°дҪҸпјҡеҗҢдёҖдёӘдёүи§’еҪўеҸҜд»ҘиЎЁзӨәеӨ§и…ҝгҖҒд№іжҲҝгҖҒиҶқзӣ–зӯүеӨҡз§ҚдәӢзү©пјүгҖӮ
й—®йўҳе°ұеңЁдәҺз¬ҰеҸ·зҡ„еӨҡд№үжҖ§пјҢд»ҘеҸҠдёҺд№Ӣзӣёдјҙзҡ„пјҢж„Ҹд№үз”ұиҜӯеўғеҶіе®ҡиҝҷдёӘжҖ§иҙЁгҖӮз®ҖеҚ•зҡ„иҜҙпјҢиҝҷеңЁ1912-1913е№ҙеҶ¬еӯЈзҡ„зі»еҲ—дҪңе“Ғдёӯе°ӨдёәжҳҺжҳҫпјҢжҜ•еҠ зҙўз—ҙиҝ·дәҺдёҖдёӘз¬ҰеҸ·иў«з ҙиҜ‘зҡ„жңҖдҪҺиҰҒжұӮпјҢдҫӢеҰӮеңЁз»„жҲҗеҗүд»–гҖҒеӨҙжҲ–瓶еӯҗзҡ„з¬ҰеҸ·дёӯпјҢжңҖз»Ҷеҫ®зҡ„еҢәеҲ«жҳҜд»Җд№ҲгҖӮжҜ•еҠ зҙўзҡ„з»“и®әжҳҜпјҢиҝҷз§ҚеҢәеҲ«е®Ңе…ЁжҳҜвҖңеұһжҖ§вҖқзҡ„й—®йўҳ:жҠҠж ҮзӯҫвҖңзҷҪе…°ең°вҖқж”ҫеңЁдёҖдёӘеҪўзҠ¶дёҠпјҢе®ғе°ұеҸҳжҲҗдәҶдёҖ瓶зҷҪе…°ең°пјҢжҠҠиҝҷдёӘеҪўзҠ¶йў еҖ’иҝҮжқҘпјҢз»ҷзңјзқӣеҠ дёҠдёӨдёӘзӮ№пјҢе°ұеҸҳжҲҗдәҶдёҖеј и„ёгҖӮ
жҜ•еҠ зҙўеңЁ1913е№ҙеҲӣдҪңзҡ„еӨҙе’Ңеҗүд»–зі»еҲ—жҲ–иҖ…иҜҙеҗүд»–е’ҢеӨҙзі»еҲ—жҳҜдёҖдёӘеҫҲеӨ§зҡ„дҪңе“ҒйӣҶпјҢе…¶дёӯиҮіе°‘жңү12е№…жІ№з”»пјҢиҝҳжңүдёҠзҷҫе№…зҙ жҸҸе’ҢжӢјиҙҙз”»гҖӮеҫҲжҳҫ然пјҢзҺ°еңЁжҲ‘们没жңүж—¶й—ҙдёӘдёӘд»”з»Ҷз ”з©¶гҖӮжҲ‘еҸӘжғіиҜҙпјҢдёҖж—ҰжҜ•еҠ зҙўеҸ‘зҺ°дәҶдёҖдёӘеҸҜд»ҘеҗҢж—¶д»ЈиЎЁеҗүд»–е’ҢеӨҙйғЁзҡ„жңҖе°Ҹз¬ҰеҸ·пјҢиҖҢиҝҷдёӘз¬ҰеҸ·е·Із»Ҹи¶ҠиҝҮдәҶжҠҪиұЎзҡ„з•ҢйҷҗпјҢд»–е°ұеҝғж»Ўж„Ҹи¶іең°зҰ»ејҖдәҶгҖӮ
жҲ‘д№ӢжүҖд»Ҙз®ҖиҰҒең°жҸҗеҲ°иҝҷдёӘж—¶жңҹпјҢжҳҜеӣ дёәжҲ‘и§үеҫ—е®ғе’Ңд№ӢеҗҺзҡ„жүҖжңүж—¶жңҹйғҪжңүдёҖзӮ№дёҚеҗҢ вҖ”вҖ” еңЁжҹҗз§Қж„Ҹд№үдёҠпјҢе®ғзҡ„еҸ‘з”ҹдјјд№Һ并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еӣһеә”д»»дҪ•е…·дҪ“дәӢ件гҖӮжҚўеҸҘиҜқиҜҙпјҢеӨҙе’Ңеҗүд»–зі»еҲ—дјјд№Һе®Ңе…ЁжҳҜз”ұжҜ•еҠ зҙўдёҚж–ӯең°з”Ёз»ҳз”»иүәжңҜеҺ»и§ЈеҶіз¬ҰеҸ·еӯҰеҲҶжһҗзҡ„еҶ…еңЁйңҖиҰҒиҖҢдә§з”ҹзҡ„гҖӮжҲ‘ж„ҹи§үпјҢеңЁд»–жј«й•ҝзҡ„иҒҢдёҡз”ҹж¶ҜдёӯпјҢжҜ•еҠ зҙўе…¶д»–зҡ„жҠҪиұЎз»ҳз”»еҲӣдҪң并дёҚе®Ңе…ЁжҳҜиҝҷж ·гҖӮ
дҪ еҸҜиғҪзҹҘйҒ“пјҢжҜ•еҠ зҙўжҳҜдёҖдёӘйқһеёёжҙ»жіјзҡ„иүәжңҜ家гҖӮ15е№ҙеүҚпјҢжҲ‘(еңЁзҫҺеӣҪеҫ·е·һеқҺе§Ҷиҙқе°”еҚҡзү©йҰҶ)зӯ–еҲ’дәҶдёҖеңәе…ідәҺд»–дёҺ马и’Ӯж–Ҝзҡ„еҜ№иҜқеұ•пјҢж¶үеҸҠзҡ„дҪңе“ҒжҳҜд»Һ20дё–зәӘ30е№ҙд»Јж—©жңҹд№ӢеҗҺеҲӣдҪңзҡ„пјҢзӣҙеҲ°йӮЈж—¶жҲ‘жүҚж„ҸиҜҶеҲ°д»–жңүеӨҡд№Ҳжҙ»жіјгҖӮеҪ“ж—¶з ”з©¶иҝҷдёҖдё»йўҳзҡ„ж—¶еҖҷпјҢжҲ‘дёҖзӣҙеҜ№з¬¬дәҢж¬Ўдё–з•ҢеӨ§жҲҳйғЁеҲҶж„ҹеҲ°зү№еҲ«з„Ұиҷ‘пјҡиҝҷжҳҜеӣ дёәпјҢжӯӨж—¶дёӨдёӘиүәжңҜ家第дёҖж¬Ўз»ҸеҺҶдәҶй•ҝе№ҙзҡ„еҲҶзҰ»пјҢйӮЈд№Ҳ他们жҖҺд№Ҳеұ•ејҖеҜ№иҜқе‘ўпјҢеӣ дёәд»–д»¬ж №жң¬дёҚзҹҘйҒ“еҜ№ж–№еңЁеҒҡд»Җд№ҲгҖӮ
жҲ‘зӣ®зһӘеҸЈе‘Ҷең°еҸ‘зҺ°пјҢжҜҸж¬ЎжҜ•еҠ зҙўд»Һ马и’Ӯж–Ҝзҡ„з”өиҜқжҲ–иҖ…дҝЎд»¶йӮЈйҮҢ收еҲ°дёҖдәӣж–°й—»зҡ„ж—¶еҖҷпјҢжҲ–иҖ…жҳҜеңЁеұ•и§ҲдёӯзңӢеҲ°й©¬и’Ӯж–Ҝзҡ„дҪңе“Ғж—¶пјҲ马и’Ӯж–ҜдёҺжҜ•еҠ зҙўжңүжүҖдёҚеҗҢпјҢд»–еңЁеҫ·еӣҪеҚ йўҶе…¶д»–ең°ж–№ж—¶иў«е…Ғи®ёеұ•еҮәпјүпјҢд»–дјҡз«ӢеҚіеңЁеҪ“еӨ©жҲ–иҖ…第дәҢеӨ©з”»дёҖдәӣеҲ»ж„ҸеёҰжңү马и’Ӯж–Ҝзү№иүІзҡ„дҪңе“ҒпјҢ然еҗҺ继з»ӯеүҚиҝӣгҖӮ
жҲ‘зӣёдҝЎпјҢиҝҷз§ҚжЁЎејҸз»ҸеёёеҮәзҺ°еңЁжҜ•еҠ зҙўж—¶дёҚж—¶еҲӣдҪңзҡ„е°ҸеһӢй«ҳйҡҫеәҰвҖңжҠҪиұЎвҖқдҪңе“ҒдёӯгҖӮжҲ‘们и°Ҳзҡ„并дёҚжҳҜдёҖз§Қеҝ«йҖҹзҡ„й’Ҳй”ӢзӣёеҜ№ вҖ”вҖ” д»–еҜ№жҠҪиұЎзҡ„жҠ•е…ҘдёҺ马и’Ӯж–ҜжңүзқҖжң¬иҙЁзҡ„дёҚеҗҢпјҢ马и’Ӯж–ҜеёҰзқҖи®ёеӨҡжғ…ж„ҹеҢ…иўұгҖӮеӣ жӯӨпјҢ马и’Ӯж–ҜеҜ№еҲәжҝҖеҒҡеҮәеҸҚеә”зҡ„иҠӮеҘҸдёҚжҳҜйӮЈд№Ҳеҝ«пјҢеҸҜиғҪдјҡжңүдёҖдәӣ延иҝҹгҖӮдҪҶжҳҜпјҢеңЁжҜ•еҠ зҙўе·Із»Ҹж•…ж„Ҹе°ҶжҠҪиұЎ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ӯ»иғЎеҗҢиҖҢжҗҒзҪ®зҡ„ж—¶еҖҷпјҢжҠҪиұЎзҡ„дёҚжҳҺйЈһиЎҢзү©еҸҲзӘҒ然еңЁд»–зҡ„дҪңе“ҒдёӯйҷҚдёҙпјҢйӮЈд№ҲпјҢжҲ‘们е°ұеә”иҜҘжҠҠиҝҷз§Қж—¶й—ҙзңӢдҪңжҳҜ他们еҜ№еҗ„иҮӘйқўеҜ№зҡ„е…·дҪ“дәӢ件е’ҢзҺҜеўғеҒҡеҮәзҡ„зӣҙжҺҘеҸҚеә”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вҖңзҘһд»ҷд№ҹжңүжү“е·ҘйӯӮвҖқпјҹдёӯеӣҪзҡ„зҘһд»ҷдёәе•ҘжҜ”иҫғиҙҹиҙЈд»»пјҹ
- зәёеёҒ收и—Ҹе’ҢеҗҚ酒收и—Ҹе“ӘдёҖз§ҚжҜ”иҫғеҘҪе‘ўпјҹ
- иүәеұ•еӣһйЎҫпјҡгҖҠеҪўејҸзҡ„и§ӮеҝөпјҡжҠҪиұЎиүәжңҜзҡ„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ҺзҫҺеӯҰиЎЁиҫҫгҖӢеұ•
- еҸӨд»ЈйҖҡзјүд»ӨеҰӮжӯӨжҠҪиұЎзңҹиғҪжҠ“еҲ°зҠҜдәәпјҹе®ҳе·®пјҡдҪ зңӢжңҖеҗҺдёҖеҸҘиҜқпјҢи·‘дёҚдәҶ
- еҸӨд»ЈеҘіеӯҗиҝҳжІЎеҸ‘иӮІжҲҗзҶҹпјҢдёәдҪ•еҚҒдёүеӣӣеІҒе°ұиҰҒе«ҒдәәеҺҹеӣ е…¶е®һжҜ”иҫғз®ҖеҚ•пјҒ
- гҖҠиҜҙе”җе…Ёдј гҖӢдёӯжүҖеҶҷйҡӢжң«еҚҒе…«жқЎеҘҪжұүдёҺжӯЈеҸІжҜ”иҫғпјҒ
- зӣҳзӮ№дёӯеӣҪеҺҶеҸІдёҠпјҢжҜ”иҫғжңүеҗҚзҡ„еҶ·зҹҘиҜҶпјҢ专家йғҪдёҚдјҡи®І
- д»–еҲӣйҖ дәҶвҖңжҠҪиұЎиҷ«д№ҰвҖқпјҢиүәеқӣдјҡдёҚдјҡиў«вҖңеҷҺзқҖвҖқпјҹ
- жҳҺжңқ|еҺҶеҸІдёҠеҸ—еҲ°дё“е® зҡ„еҰғеӯҗеҫҲеӨҡпјҢдёәд»Җд№ҲиҜҙжҳҺжңқзҡ„дёҮиҙһе„ҝзҡ„жғ…еҶөжҜ”иҫғзҰ»еҘҮе‘ўпјҹ
- иҝҷж ·жқҘз”»и·іж Ҹзҡ„е°Ҹз”·еӯ©пјҢеҘҪеӯҰеҸҲеҘҪзң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