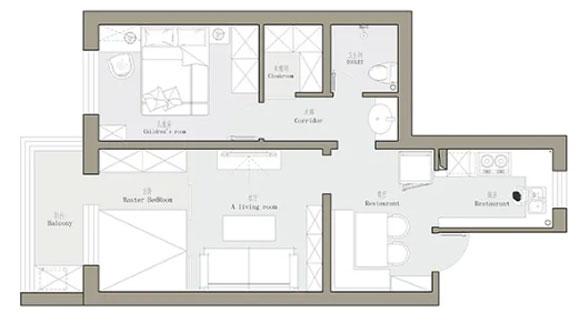林宜生|王鸿生:从《隐身衣》到《月落荒寺》,格非让小说成为一种例外( 五 )
世界的白日化 , 小说的日常化 , 使现代故事普遍丧失了诗性魅力 。 这是神话思维退化的结果 , 也是文学的真正悲剧 。 作为一个抵抗者 , 一个气质上更倾向于诗的小说家 , 格非必须在白天与黑夜、日常与非常、叙事与抒情上寻求新的平衡 。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 , 音乐与神话存在结构相似性 , 它们是语言孕育的同胞姊妹 。 如果是这样 , 赎回神话思维能力 , 音乐不啻是一条邻近通道 。 我想 , 让小说向音乐学习 , 让音乐不是作为素材而是作为结构、调性、意境融入自己的语言 , 一定是许多作家梦牵魂绕的理想 。 但不能看 , 只能听 , 这是音乐的特权 , 小说却是需要阅读的 。 因此 , 如何不依赖汉语小说的“声口”传统而能够凸显听觉的意义 , 便成了现代中国小说的艺术标识之一 。 我们知道 , 希腊思维一向注重“看” , 对光、对视觉的依赖几乎是整个西方哲学、美学之基础;而中国古代智慧 , 一直隐伏着“听” , 强调耳目相济 , 见闻并重 , 又因“道”是看不见的 , 只能用耳朵来听 , 所以在形上层面 , “听”比“看”更具本源性优势 , 所谓“朝闻道 , 夕死可矣” 。 20世纪后 , 西方人也开始重视“听”了 , 象海德格尔 , 还有里尔克、帕斯这些诗哲 , 晚年都发现了听觉的价值 , 帕斯甚至写下这样的诗句:“眼睛闭上 , 世界睁开”!
那么 , 从《隐身衣》到《月落荒寺》 , 是否可视为一场集中的、蓄谋已久的小说音乐化尝试?对此 , 格非本人是否定的 。 尽管作者说过 , 《月落荒寺》的构思灵感来自一场音乐会 , 但不久前在深圳罗湖书城接受专访时 , 他公开声称“音乐欣赏和创作无关” 。 然而 , 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两部作品中感受到文学思维与音乐思维的默契:如“对位” , 恋人/夫妻、母女/父子、同学/朋友圈等多条叙事线构成了复调;如“和声” , 人物设置、声部层次、收尾方式的对称感或对立统一性;如“板式” , 节奏快慢、间隔和叙述速度、章节详略;如“再现” , 动机、细节重复出现;如“变奏” , 主题在往返、分蘖中丰富、深化、陡转 , 等等 。 有时 , 读《月落荒寺》的感觉 , 的确很像听一首乐曲 , 好比用简洁的音符直接构成句子 , 格非以文字给情绪编码时 , 删除了任何冗赘 , 使各章节接口行云流水;他不追求情节丰饶 , 也不让叙述者与故事靠得太近或离得太远 , 更不对杂多人事、对话作什么评价或引申;只是让联想迅疾穿过人物境遇 , 让变幻逻辑显示模糊轮廓 , 让命运的叩击声在静寂中顿然响起;这一切 , 不是为了谛听无以终结又深不可测的生活世界的回声 , 又是为了什么呢?当音乐启示已转化为无意识的叙述旋律 , 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那种状态就出现了 ,“随着这星云播散开来 , 它的内核凝聚起来 , 形成组织 。 散乱的线索彼此串联 , 空隙弥合 , 联系形成 , 混沌中显露出秩序般的东西 。 ”
一层雾裹着世界 , 裹着格非营造的意象、意境、氛围 。 “混沌”之“秩序” , 在理智与情绪、意识与无意识、可说与不可说的交界处 , 掐住了命运的咽喉 。 命运的秘密 , 则闪现为一系列令人惊悚或让人释然的“意外” 。 一个意外 , 又一个意外 , 超出预期 , 无法把控 , 既像《月落荒寺》开头 , 十字路口刚刚发生了一场“车祸” , 又像《月落荒寺》结尾 , 林宜生与楚云分别七年后在林间小道上出乎意料地“相遇” 。 日常生活本身蕴含的神秘性比一切想象都要深邃 。 巴迪欧曾把电影看作一种哲学情境 , 认为电影哲学就是照亮 , 照亮“选择、距离和例外这三点之间的关联” 。 那么 , 格非小说的哲学情境呢?却是“百感交集 , 竟一时找不到话说” 。《月落荒寺》尝试了某种日常叙述的极限:它徘徊于精神世界的边缘地带 , 在日常中打破日常 , 在终结时取消终结 , 在时间中否定时间 。 当故事不断被“意外”抛出原有轨道 , 落入有常与无常、偶然与必然的轮回 , 寻常人生忽然变得惊心动魄 , 玻璃般透明的日子一下子就无以辨认了 。 先以“听觉”入主“视觉” , 再以“无声”了却“有声” , 格非悄悄进行的一场由“西”向“东”的美学位移 , 进入了更深层次 , 东方气息开始从骨子里透出来 。 一如中秋音乐会结束 , 那台“借来”的斯坦威钢琴刚运走 , 林宜生“忽听得一阵锣鼓响 , 湖边的露台上 , 传来了京剧《霸王别姬》那著名的十字句唱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