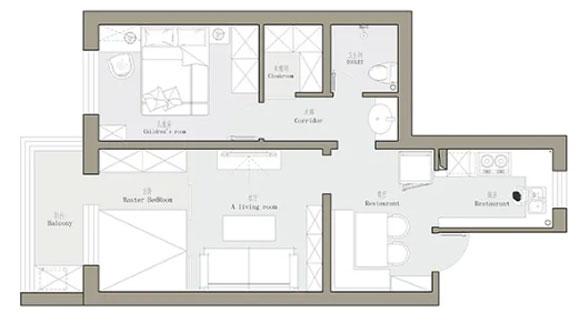林宜生|王鸿生:从《隐身衣》到《月落荒寺》,格非让小说成为一种例外( 二 )
这回出手 , 格非写得很快也很顺 。 我不免惊讶 , 他怎么就忽发奇想 , 把以往惯用的留白、空缺、悬疑、重复等修辞手段加以整合、推进 , 创构了一种罕见的同故事文法呢?像环节动物断体再生 , 又像锔匠用金刚钻揽瓷器活 , 通过这一文法 , 生活世界的多处断面竟奇迹般复原了 。 说《月落荒寺》和《隐身衣》具有同故事性 , 依据无疑是充分的 。
其一 , 虽然倒叙中某些情节可跨几十年 , 但两书主体部分的故事时间却是同步的、接续的 。 《月落荒寺》开始于四月初的一个下午 , 楚云神秘失踪 , 到半年后的中秋音乐会 , 小说已近尾声 。 正是在这场音乐会上 , 丁采臣委托服装厂老板蒋颂平搞一套全世界最好的音响 , 蒋说您可找对人了 。 回头一看 , 在《隐身衣》里 , 蒋老板立马把这单生意介绍给了发小“胆机王”崔 。 即将流离失所的崔师傅接单后抓紧赶制、交货、上门安装 , 不惜舍出了一对自己心爱不已的极品扬声器 。 《隐身衣》开头第二段第一句话就是“秋已渐深” , 待再度登门索要尾款时 , 季节已到初冬 。 《月落荒寺》从春到秋 , 《隐身衣》从秋到冬 , 两部小说的故事时间显然发生、衔接于一年之内 。 但这一年究竟是哪一年?按《月落荒寺》第41节 , 林宜生儿子伯远携女友蓝婉希去加拿大探母(林宜生前妻白薇) , 闻着白薇身上飘来的劣质香水味 , 蓝婉希曾不无自豪地提到了正在建造的“鸟巢”和“水立方” 。 按《隐身人》 , 当崔被姐姐、姐夫逼着交出住房 , 寻思买农家院急用钱时 , 求助于蒋颂平却遭到拒绝、羞辱 , 遂想起25年前(小说明示为1984年)帮蒋度过一劫时蒋曾发誓报答 。 两个细节趁人不经意间披露 , 两书的同故事时间是2008年 , 应不出北京夏季奥运会前后八、九个月内 。
其二 , 在布局上 , 楚云及其非血缘哥哥辉哥(化名丁采臣)是两书的关键连线 。 他们先构成《隐身衣》故事的落点 , 又倒转为《月落荒寺》故事的起点 , 两兄妹扑朔迷离的身世遭际 , 在故事中占有极大比重 , 其不断由暗入明、由明入暗的行动方式 , 不仅构成了小说的诡秘氛围 , 而且作为叙事动力 , 直接支配了情节变轨和整个故事的逻辑走向 。
其三 , 《月落荒寺》和《隐身衣》的交汇点和重心其实就是楚云 。 作为辉哥“生意”的人质被绑架后 , 两部小说先后出现了各自的“高光时刻”:林宜生服了抗抑郁药伏案打个盹 , 似梦非梦中 , 楚云“凄然一笑” , 就消失不见了;林宜生苦寻楚云不得而逼其黑道哥哥露面 , 两人居然还聊了聊如何有效对抗资本主义;约定的中秋音乐会 , 楚云隔着白色纱幔 , 听完德彪西的《月光》就提前走了 , 辉哥一字一顿地告诉林宜生 , “她让你忘了她 。 就当是做了一场梦 。 她还说 ,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更改的行程和死亡”;失神、酸楚、落泪 , 林宜生“一时不知身在何处”;而后便到了12月 , 走投无路的崔师傅只剩一个念头 , 必须找到丁采臣 , 要回那套顶级音响器材的26万余款;当冒雨驱车来到远离京城的盘龙谷 , 他听见勃拉姆斯《第二钢琴演奏曲》正从自己亲手组装的音响中播放出来 , 却被一个蒙面女人告知 , 丁采臣“死了”;在令人头皮发麻的惊悸中 , 那女人迟疑一下 , 偏身掀开那块蒙面头巾 , 猛地转过身来 , 崔看到 , 一张被钢刀划过的脸与白皙、细长的脖子连在一起 , “横七竖八的伤口已经结痂 , 在她脸上布微微隆起、纵横交错的疤痕 。 ”
作为叙事枢纽 , 楚云兄妹与林宜生、崔师傅先后交会 , 使三个本不相干的平行世界被勾连起来了 。 不仅如此 , 楚云还分担了这两部小说的重心 。 这重心有爱、有情义、有担当 , 但飘忽、冷峻、不稳定 。 小说里 , 楚云是个弃婴 , 被辉哥捡回家 , 养父母视如己出 , 成年后一度去芝加哥留学 , 一直见不到哥哥却总受到暗中保护 。 她懂音乐 , 对帕斯卡尔概率论也能娓娓道来 , 她喜欢《源氏物语》 , 引用白居易诗句“假使如今不是梦 , 能长于梦几多时” , 以致哲学教授林宜生心中 , “蝶化庄生”的意象永远和楚云联系在一起 。 失踪两个月生还 , 她在手机里向人推荐了麦尔维尔的小说《抄写员巴托比》 。 巴托比是个安静且固执得出奇的文学形象 , 关于他的来龙去脉 , 人们一无所知 。 这是一个无法写传的人 , 一个永远温柔地、不动声色地用“我不愿意”来解除世界武装的人 , 仿佛一个消弭了生死界限的幽灵 。 消弭生死界限 , 可视为楚云幽灵般来去自如的奥秘 , 也不妨看作一个向下超越的隐喻 。 楚云式的“向下超越” , 就是在苦难中把自己埋得更深 , 更远离尘嚣 , 更能够凭直觉触碰自己的心跳 。 那么 , 楚云就是一个女版巴托比?又不尽然 。 《月落荒寺》里 , 楚云还是一个剔透而善解人意 , 随和又不乏决绝的女子 , 她亡灵般活在生死界面上 , 却能不断给世界送来意外、震荡和惊奇 , 这是一种怎样坚韧而灵性的存在啊 , 其隐忍的活力 , 在巴托比身上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