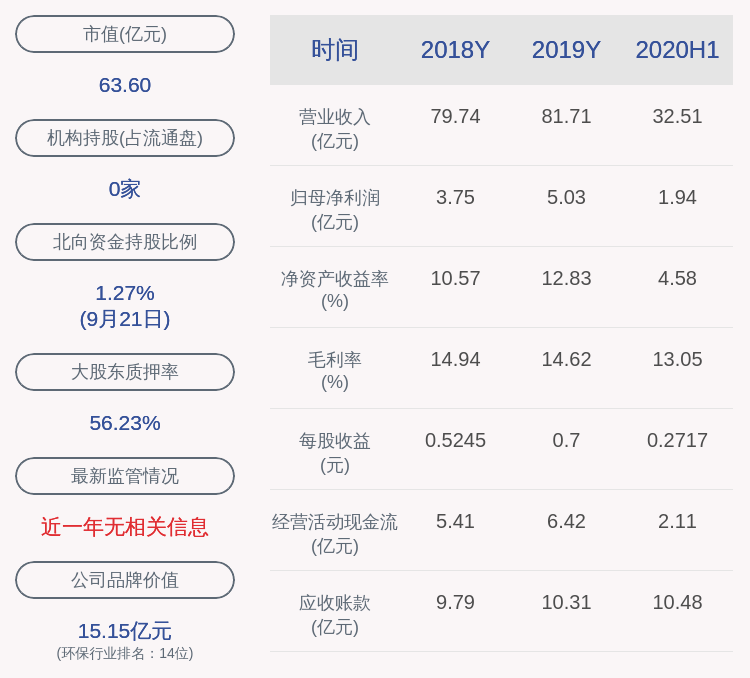“人啊,谁不苦呢?”( 三 )

从那天起 , 蓝姨和我之间结成了某种同谋 。 我不曾想自己和蓝姨会走得这样近 。 她做了好吃的 , 会第一时间留给我 , 不让我帮她做家务 , 说我是客人 , 轮不到我来做 。 不得不说 , 蓝姨做的菜和母亲做的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 母亲做的菜味道偏淡 , 蓝姨的偏咸 。 蓝姨的口头禅是“咸才香” , 她和大部分从农村到城里的妇人一样 , 将口味从老家原封不动地照搬来 , 用的食材虽没有老家新鲜 , 但总能做出地道的风味 。一个星期过后 , 我租到房子了 , 和蓝姨说我要搬走 , 蓝姨问我:“怎么不多住几天?”我说:“这段时间实在太麻烦蓝姨了 。 ”蓝姨说:“没什么麻烦的 , 我当你自家人 , 自家人怎么会麻烦呢?”我告诉蓝姨 , 租房合同签了 , 下午就得搬过去 , 蓝姨脸上掠过一阵失望 。 她说:“你走了 , 就没人陪我说话了 。 ”我望着蓝姨说:“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 。 ”但说实在的 , 我也不知以后会不会来 。 一想到这些 , 我的鼻头一酸 , 突然难过起来 。过了一阵 , 蓝姨说:“要不今天加菜吧 , 给你做顿好的!”那天中午 , 蓝姨提着大袋小袋从菜市场回来 。 天气热 , 她的上衣湿了大半 。 她像过节一般 , 精心准备饭菜 。 这一次 , 我帮忙打下手 。 她让我到客厅择菜 , 我就搬了凳子 , 在客厅坐下 , 一边择菜 , 一边和淑君姐闲聊 。 厨房里 , 传来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 , 锅碗瓢盆 , 发出悦耳的节奏 , 砧板上 , 咔嗒咔嗒 , 是刀起起落落的声音 。 蓝姨忙进忙出 , 表情是活泛的 , 自如的 , 她许久未曾这样开心 , 好像这顿菜 , 她必须使出全部气力才能做好 。我看着蓝姨的身影往返于厨房和饭桌之间 , 不禁有些感动 。淑君姐老公外出谈生意了 , 那天饭桌上就我们三个 。 一张玻璃餐桌 , 摆得满满当当 , 蓝姨特地做了一大盘白灼虾 , 倒了一碟梅酱搁在旁边 。 蓝姨说:“也不知你喜不喜欢 , 这罐梅酱是我从家里带来的 , 蘸虾肉最好吃 。 ”我想起蓝姨第一次去我家 , 带的是一樽青梅酒 。 我问蓝姨:“是不是酿酒的青竹梅做的?”蓝姨笑笑:“是啊是啊 , 青梅可以腌酱 , 也可以制酒 。 ”我尝了尝 , 酱是加白糖和盐腌制的 , 青竹梅本身有酸性 , 尝起来甜中带咸酸 , 不但没有减弱虾的鲜 , 反而将它的味带了出来 。 剥开虾壳 , 蘸一点 , 吃进嘴里 , 甜酸咸香 , 再美味不过 。淑君姐说:“这么一大桌菜 , 三个人估计吃不完 , 都不许浪费啊 。 ”吃到一半 , 蓝姨又说:“我给你们做拍黄瓜 。 ”我和淑君姐的第一反应都是 , 吃不下啦 , 不用做 。 蓝姨说:“拍黄瓜开胃 , 你们一定会喜欢 。 ”说罢 , 蓝姨拉开椅子 , 走到厨房 。 很快 , 厨房就传来丁零当啷的声音 。我和淑君姐继续闲聊着 , 就在这时 , 厨房突然传来刀具落地的哐当声 , 震天价响 。 我和淑君姐吓了一跳 。 淑君姐拍下碗筷冲到厨房 , 我踉踉跄跄地跟在她身后 。 只见蓝姨脸色煞白 , 捂着手 , 手上满是血 , 赤红赤红的血 , 沾得手心手背全是 。 蓝姨立在原地 , 浑身哆嗦 。 她的眼神涣散 , 是空的 , 看不见她的泪 , 只听到她语无伦次地说:“手、手指……”抽油烟机呼呼作响 , 钢刀落地的地方 , 躺着一截粗短的手指 , 黑乎乎 , 一道血迹 , 横在那里 。淑君姐从喉咙深处发出尖叫声 。 我靠在门边 , 心跳到嗓子眼 , 差点吓晕过去 。
那件事过后 , 很长一段时间 , 我都不敢进到厨房 。 厨房仿佛成了一个受诅咒的地方 。 我接连好几天做噩梦 , 梦见蓝姨出事那天的场景 , 醒来 , 像被人扔进一只大冰柜 , 胸口汗涔涔的一片凉 。 我害怕一切尖利的东西:刀叉、碎玻璃、竹签……看见它们 , 就会想起蓝姨被刀切掉的半截手指 , 它留在记忆中的印象太过深刻 , 血迹、形状 , 连接着肉体的痛感 , 还有蓝姨脸上的恐惧 。 她在一天中经历了情绪的两个极端 , 从山峰到谷底 , 兜一圈 , 跌下去 , 再也没能起来 。那天我和淑君姐急得团团转 , 慌乱中用毛巾将蓝姨受伤的手包好 。 血还在流 , 浸透包了几层的毛巾 , 透着红色 。 那半截手指 , 我用另一条干净的毛巾小心裹起来 , 捂在怀里 , 扶蓝姨下楼 。 淑君姐抱了孩子 , 跑在前面 。 孩子一直哭 。 因为失血过多 , 蓝姨的嘴唇和脸色苍白得像纸 。 我们打车到福田医院 。 一路上 , 淑君姐情绪很坏 , 不停地催司机开快点 。蓝姨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 半个身子倚向我 , 一直重复念叨着:“都怪我 , 都怪我……”我伸手搂住蓝姨 。 裹在毛巾里的半截指头 , 好像在跳动 , 挣扎着要逃出来 。蓝姨断的 , 是左手食指 , 沿着指关节处的半截断掉了 。 血管被切开了 , 所以才会流那么多血 。 所幸送医及时 , 断指缺血的时间短 , 动过手术 , 接上了 。 事后 , 主刀医生气急败坏地抱怨道:“怎么一点急救知识也没有 , 应该先放塑料袋 , 再用冰冻起来的!”我们愚蠢无知的处理方式 , 给手术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 淑君姐抱着孩子 , 向医生连连致歉 。我守在蓝姨床边 , 麻醉药过后 , 蓝姨望着包扎着绷带的手发呆 。 护士给她打抗生素 , 吃止痛药 , 例行检查伤口的渗血情况 , 以免感染 。 这一次 , 蓝姨反过来安慰我:“没事的 , 死不了 。 ”说完 , 她嘴角挤出一丝苦笑 , 眼角的鱼尾纹更明显了 。 我头一回见到蓝姨这样 , 没有了大嗓门 , 没有了喋喋不休 , 她虚弱得像只随时会碎掉的瓷器 。溽热的七月 , 窗外是白花花的日光 , 光线穿透树木 , 滑过繁枝 , 落向昏暗的病房 。我在医院守了蓝姨几天 。 蓝姨受伤 , 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 如果不是因为要给我做饭 , 她不会切到指头 。 想到这些 , 我心生愧疚 , 但我别无他法 , 只能尽己所能陪着蓝姨 。 那几天 , 蓝姨和我说了很多话 , 从她年幼说到现在 。 在自己的讲述里 , 她又重活了一遍—好像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 蓝姨不让淑君姐带孩子来看她 , 说是医院晦气 , 少让外孙接触 。 蓝姨女婿来看她 , 给她提了一篮水果 , 蓝姨和他说不上几句话 。蓝姨术后恢复得很好 , 拆完线 , 左手食指那里只留下淡淡的一道疤 。后来我忙学业 , 忙着备考雅思、申请学校 , 从淑君姐家搬离之后 , 再也没见过蓝姨 。听母亲说 , 手指痊愈后 , 蓝姨就回老家了 。母亲去看她 , 两个人合伙做了一顿饭 , 边吃边聊 。 母亲说那天她感觉又回到了以前 ,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难熬 , 不知道世事和人情多复杂 , 日子照旧流转 。 蓝姨丈夫不赌六合彩了 , 老老实实耕种养家;蓝姨的儿子阿楷 , 毕业后没去造火箭 , 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工程师 , 听说混得不错 。一年之后 , 我顺利申请到香港的一所大学 , 读工商管理 , 这一次 , 是个光鲜的专业 。 得知录取结果那天 , 我打电话给母亲 , 母亲终于“扬眉吐气” , 轮到她向蓝姨报喜了 。 母亲说:“蓝姨又胖回来了 , 精神气足 。 ”那天发生的事谁也不愿提及 ,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 刀子又怎么切断了指头 , 蓝姨始终没说 。动身去香港之前 , 我回了一趟清平镇 。母亲做了一桌好菜 。 一家三口吃饭 , 吃到一半 , 父亲一个激灵 , 突然想到什么 , 说:“你们等等 。 ”说完 , 父亲在楼梯间翻找一番 , 母亲问他找什么 , 他说:“等下就知道了 。 ”是那樽青梅酒 。 十年过去了 , 人世变幻 , 风雨流转 , 酒还在 。这樽青梅酒不知什么时候落在家里 , 被人忽略 。 酒樽落满灰尘 , 盖子脏得很 。 父亲拿抹布仔细擦干净 。 他倒两杯 , 推到我和母亲面前 , 又给自己斟上一杯 。酒樽里的青梅明显老了 , 皮肉绽开 , 只剩下果核 , 在一片混浊中 , 晃悠悠地浮动 。父亲迫不及待地呷一口 , 咂巴嘴唇 , 皱着眉头说:“唉 , 酒都不好喝了 , 真苦啊——”母亲抢过酒杯 , 仰头饮尽 , 望着父亲说:“人啊 , 谁不苦呢?”本文节选自林培源小说《青梅》 , 收录进《小镇生活指南》一书 。
推荐阅读
- 大场面,谁不想看?
- 谁不说咱家乡美
- 去哪玩|公务员基层成“女儿国”, 女公务员显著变多, 福利这么好谁不想来
- 菌落总数|再馋也要忍!这一家的3种牛肉都出问题,大几率的“致病菌”谁不怕!
- 美西追光1|中国请求好兄弟帮忙,却吃了闭门羹?靠谁不如靠自己
- 蓬佩奥恼羞成怒:谁不制裁伊朗,美国就制裁谁!
- 蓬佩奥:谁不制裁伊朗,美国就制裁谁!
- 古人:“冰激凌”,谁不爱呢?
- “怎么全世界都是中国敌人啊”?胡锡进作出解释
- 有人抱怨怎么全世界都是中国敌人啊?胡锡进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