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е№ҙеүҚзҡ„дёӯеӣҪз•ҷеӯҰз”ҹвҖңй„ҷи§Ҷй“ҫвҖқ( дәҢ )

йҷҲеҜ…жҒӘзҘ–зҲ¶йҷҲе®қз®ҙдёҺиҜёеӯҷгҖҒжӣҫеӯҷеҗҲеҪұеҗҙе®“зҡ„еҘіе…¬еӯҗеҗҙеӯҰжҳӯжӣҫеңЁгҖҠеҗҙе®“дёҺйҷҲеҜ…жҒӘгҖӢдёҖд№ҰдёӯеҶҷйҒ“пјҡвҖңеҗ¬зҲ¶дәІиҜҙ пјҢ жҳ”е№ҙеңЁе“ҲдҪӣ пјҢ еҝ—еҗҢйҒ“еҗҲ пјҢ жғ…и¶ЈзӣёжҠ• пјҢ еҫҖжқҘеҜҶеҲҮзҡ„еҗҢзӘ—еҘҪеҸӢ пјҢ йҷӨдәҶеҜ…жҒӘгҖҒй”ЎдәҲдјҜзҲ¶ пјҢ жў…е…үиҝӘе’ҢдҝһеӨ§з»ҙе…Ҳз”ҹ пјҢ иҝҳжңүеј й‘«жө·гҖҒжҘје…үжқҘе’ҢйЎҫжі°жқҘзӯүеҗӣ гҖӮ вҖҰвҖҰзҲ¶дәІиҜҙ пјҢ иҜёеҗӣеӨҡе…·жңүж·ұеҺҡзҡ„еӣҪеӯҰеҹәзЎҖ пјҢ еҜ№иҘҝж–№ж–ҮеҢ–д№ҹзӣёеҪ“дәҶи§Ј пјҢ еңЁеҜ№еҫ…зҘ–еӣҪдј з»ҹж–ҮеҢ–зҡ„й—®йўҳдёҠ пјҢ дёҚиөһжҲҗиғЎйҖӮгҖҒйҷҲзӢ¬з§Җзӯүзҡ„е…ЁйқўжҠЁеҮ»гҖҒеҪ»еә•еҗҰе®ҡгҖҒз ҙж—§з«Ӣж–° пјҢ иҖҢдё»еј жҳҢжҳҺеӣҪзІ№ пјҢ иһҚеҢ–ж–°зҹҘ пјҢ йҮҚи§Ҷдј з»ҹдёҺзҺ°д»Јд№Ӣй—ҙзҡ„继жүҝжҖ§ пјҢ еңЁзҺ°жңүзҡ„еҹәзЎҖдёҠе®Ңе–„ж”№иҝӣ гҖӮ еҸҲиҜҙеҪ“ж—¶еңЁе“ҲдҪӣд№ ж–ҮеӯҰиҜёеҗӣ пјҢ еӯҰж·ұиҖҢе“ҒзІ№иҖ… пјҢ еқҮиҺ«дёҚз—ӣжҒЁиғЎгҖҒйҷҲ гҖӮ вҖқ еҰӮжӯӨжғ…жҖҖ пјҢ дәҰеҸҜзҗҶи§Ј пјҢ еҸ—зҷҪз’§еҫ·еҪұе“ҚиҖҢеҜ№дёӯеӣҪж–ҮеҢ–дј з»ҹж·ұжҖҖ敬ж„ҸдёҺжё©жғ… пјҢ иҜ•еӣҫжҳҢжҳҺеӣҪзІ№ пјҢ иһҚеҢ–ж–°зҹҘ пјҢ иҖҢиҝңеңЁеӨ§жҙӢеҪјеІёзҡ„ж•…еӣҪеҚҙ已然йҷ·жәәеңЁж¬§йЈҺзҫҺйӣЁеҜ№дј з»ҹзҡ„摧жҠҳд№Ӣдёӯ пјҢ ж”Ҝж’‘дёӯеӣҪж–ҮжҳҺзҡ„е„’е®¶дј з»ҹж‘Үж‘Үж¬Іеқ пјҢ иҝ‘д№ҺдёӨеӨҙдёҚеҲ°еІёзҡ„еӯӨиҲҹжёёйӯӮ гҖӮиҝҷз§ҚжӮІжғ…ж„ҸиҜҶдёҺж–ҮеҢ–жүҳе‘Ҫзҡ„иҮӘжҲ‘и®ӨеҗҢ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з§Қејәеӣәзҡ„еҝғзҒөз»“жһ„ пјҢ ж—ўжңүе…ұеҗҢзҡ„ж•Ңдәә пјҢ еҸҲжңүеҪјжӯӨжҠұеӣў еҸ–жҡ–зҡ„зҹҘе·ұ пјҢ 并且жңүжқҘиҮӘзҷҪз’§еҫ·зӯүе“ҲдҪӣеҗҚеёҲзҡ„еҠ жҢҒ пјҢ д№ҹе°ұдёҚйҡҫзҗҶи§Јеҗҙе®“жӯӨж—¶жӯӨеҲ»зҡ„еҝғеҝ—гҖӮжңүи¶Јзҡ„жҳҜ пјҢ иҝҷжҳҺжҳҺжҳҜдёҖдёӘжҠұеӣўеҸ–жҡ–зҡ„з•ҷеӯҰз”ҹзҫӨдҪ“ пјҢ еҗҙе®“еҚҙеёёеёёејәи°ғиҮӘиә«дёҚиӮҜдёәдё»д№үжҲ–жөҒжҙҫжүҖ规е®ҡзҡ„иҮӘз”ұеҝғеҝ— пјҢ иҝҷд№ҹжҒ°жҒ°иҜҙжҳҺдәҶеҗҙе®“жһҒе…¶зҹӣзӣҫзҡ„еҝғжҖҒ гҖӮеҗҙе®“еңЁз•ҷеӯҰе“ҲдҪӣж—Ҙи®°дёӯжӣҫеҶҷйҒ“пјҡеҗҫиҮӘжҠұе®ҡе®—ж—Ё пјҢ ж— и®әдҪ•дәә пјҢ зҡҶеҸҜдёҺе‘Ёж—Ӣе…ұдәӢ пјҢ 然еҗҫеҶідёҚиғҪдёәдёҖе…ҡжҙҫдёҖжҪ®жөҒжүҖжәәйҷ„гҖҒжүҖзүөз»Ҡ гҖӮиӢҘи®әзІҫзҘһзҗҶжғідёҖж–№ пјҢ еҗҫиҮӘз¬ғдҝЎеӨ©дәәе®ҡи®әгҖҒеӯҰйҒ“дёҖиҙҜд№Ӣд№ү пјҢ иҖҢеҗҺ兼蓄并收 пјҢ ж—ҒеҫҒеҚҡи§Ҳ пјҢ жү§дёӯжқғиЎЎ пјҢ еҗҲиҰҶеҲҶж ё пјҢ иҖҢеҶідёҚдёәдёҖеӯҰжҙҫгҖҒдёҖж•ҷе®—гҖҒдёҖ科门гҖҒдёҖж—¶д»ЈжүҖжқҹзјҡгҖҒжүҖиҝ·жғ‘пјӣеә¶еҮ еӯҰиғҪеҫ—е…¶зңҹзҗҶ пјҢ ж’·е…¶иҸҒеҚҺ пјҢ иҖҢдёәиҮҙз”Ё гҖӮеҗҫе№ҙжқҘеҸ—еӯҰдәҺе·ҙеёҲ пјҢ иҜ»иҘҝеӣҪеҗҚиҙӨд№Ӣд№Ұ пјҢ еҸҲдёҺйҷҲгҖҒжў…иҜёеҗӣиҝҪд»ҺиҜ·зӣҠ пјҢ д№ғдәҺеӯҰй—®зЁҚзӘҘй—Ёеҫ„ пјҢ ж–№зҹҘдёӯиҘҝеҸӨд»Ҡ пјҢ зҡҶеҸҜдёҖиҙҜ гҖӮ еӨ©зҗҶдәәжғ… пјҢ жӣҙж— ејӮж ·д№ҹ гҖӮ жӯӨвҖңж— жүҖйҷ„дёҪвҖқд№ӢеҸҲдёҖи§Јд№ҹ гҖӮ жҖ»д№Ӣ пјҢ еҗҫдҪҶжұӮеҝғд№Ӣе®ү пјҢ йҖғдәҺеҝ§жӮЈ гҖӮ еҮЎжӯӨз§Қз§Қ пјҢ зҡҶжҡӮдёҚејғдё–иҖҢеӣҫиҮӘж•‘д№ӢжңҜиҖі гҖӮе…¶ж—¶зҡ„еҗҙе®“ пјҢ йқўдёҙзқҖдёҘеі»зҡ„зІҫзҘһеҚұжңә пјҢ жӣҫиҜ•еӣҫеҲ°жҹҘе°”ж–ҜжІіиҮӘз»қдәҺдё– пјҢ еҜ№иҮӘжҲ‘дёҘиӢӣзҡ„иҰҒжұӮ пјҢ иҝ‘дјјдәҺдёҖз§ҚйҒ“еҫ·еңЈеҫ’зҡ„еўғең° пјҢ еҗҢж—¶еҜ№иҮӘжҲ‘еӯҰжңҜдёҠд№ҹжңүжһҒдёәеҙҮй«ҳзҡ„жңҹи®ё пјҢ иҖҢж—Ҙеёёз”ҹжҙ»дёӯзҡ„еҗҙе®“еҚҙеёёеёёиў«дё–дҝ—зҗҗдәӢз”ҡиҮійҡҗи”Ҫзҡ„жғ…ж¬ІжүҖзүөз»ҠпјҢ иҜ»е…¶ж—Ҙи®°ж„ҹи§үд»–жҜҸеӨ©йғҪеңЁз–ІдәҺеҘ”е‘Ҫ пјҢ 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дёҚдјҡжӢ’з»қеҲ«дәәзҡ„иҪҜејұзҡ„дәәпјҢ жҜ”еҰӮдёәдәҶе©ҡдәӢеёёдёҺ家дәәд»ҘеҸҠжңӘе©ҡеҰ»йҷҲеҝғдёҖзҡ„дәІдәәеҸҚеӨҚйҖҡдҝЎжІҹйҖҡ пјҢ жҜ”еҰӮжҺҘеҫ…д»Һеҗ„з§ҚйҖ”еҫ„еҲ°и®ҝжіўеЈ«йЎҝзҡ„еёҲеҸӢ пјҢ иҝҺжқҘйҖҒеҫҖ пјҢ еҸӮдёҺзј–иҫ‘зәҰзЁҝе’Ңе“ҲдҪӣдёӯеӣҪеӯҰз”ҹдјҡзҡ„жҙ»еҠЁзӯүзӯү пјҢ иҜёеҰӮжӯӨзұ» пјҢ еҚ з”ЁдәҶд»–еҫҲеӨҡж—¶й—ҙдёҺзІҫеҠӣ гҖ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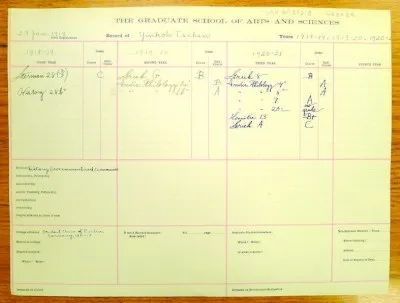
еҗҙе®“еңЁе“ҲдҪӣзҡ„жҲҗз»©еҚ•е°ӨжңүиҝӣиҖ… пјҢ иҮӘйқ’е№ҙж—¶д»Јиө· пјҢ д»–ж—ўеҫ—зӣҠдәҺдёҺжў…е…үиҝӘгҖҒйҷҲеҜ…жҒӘгҖҒжұӨз”ЁеҪӨзӯүдёҖжөҒеӯҰдәәзҡ„и°ҲеҸІи®әеӯҰ пјҢ ејҖжӢ“дәҶзңјз•Ң пјҢ еҹ№е…»дәҶи§ҒиҜҶ пјҢ еҸҜд№ҹиў«з¬јзҪ©еңЁжў…гҖҒйҷҲзӯүе·Ёжҳҹд№ӢдёӢ пјҢ е°Өе…¶еҜ№йҷҲеҜ…жҒӘ пјҢ иҝ‘д№ҺеӯҰжңҜзІүдёқеҝғжҖҒ пјҢ иҮӘжҲҗдёҖ家зҡ„еӯҰжңҜдё»дҪ“жҖ§е№¶жңӘеҫ—д»ҘзЎ®з«Ӣ пјҢ жүҖи°“жҲҗд№ҹиҗ§дҪ•иҙҘд№ҹиҗ§дҪ•пјҒ03з•ҸеҸӢйҷҲеҜ…жҒӘгҖҒжұӨз”ЁеҪӨзҡ„жү№иҜ„жҲ–и®ёжӯЈеӣ дёәжӯӨ пјҢ з•ҸеҸӢйҷҲеҜ…жҒӘжҲ–жұӨз”ЁеҪӨеңЁе“ҲдҪӣеҗҢеӯҰж—¶еҜ№еҗҙе®“зҡ„жү№иҜ„ пјҢ жҜҸжҜҸи®©е…¶ж—ўиӯҰ йҶ’ пјҢ еҸҲиҗҰжҖҖиҖҝиҖҝиҖҢж¬ІиҮӘиҫ©жҠӨ гҖӮйҷҲеҜ…жҒӘиЁҖеҸҠе©ҡ姻дёҺдәәз”ҹд№Ӣе…ізі»дәӢ пјҢ еҸ–иұҒиҫҫиҮӘ然йҖҡйҖҸд№ӢжҖҒеәҰ пјҢиҖҢжҜҸжү№иҜ„еҗҙе®“д№ӢжіҘи¶іж·ұйҷ·йҡҫд»ҘиҮӘжӢ”д№ӢдҪңиҢ§иҮӘзјҡ пјҢ иҖҢеҜ№дәҺеӯҰжңҜиҮӘз”ұдёҺдәәж јзӢ¬з«Ӣд№Ӣе…ізі» пјҢ йҷҲжӣҙжҳҜжңүзқҖжё…йҶ’зҡ„и®ӨзҹҘ пјҢ жІЎжңүеҗҙе®“иә«дёҠйӮЈдёҖз§ҚеӨ№зј дёҚжё…зҡ„д№Ұе‘Ҷеӯҗж°” гҖӮ1919е№ҙ6жңҲ3ж—Ҙ пјҢ еҗҙе®“еңЁж—Ҙи®°дёӯи®°иҪҪйҷҲеҜ…жҒӘзҡ„иҜқпјҡеӯҰеҫ·дёҚеҰӮдәә пјҢ жӯӨе®һеҗҫд№ӢеӨ§иҖ» гҖӮ еЁ¶еҰ»дёҚеҰӮдәә пјҢ еҸҲдҪ•иҖ»д№ӢжңүпјҹвҖҰвҖҰеЁ¶еҰ»д»…з”ҹж¶Ҝдёӯд№ӢдёҖдәӢ пјҢ е°Ҹд№ӢеҸҲе°ҸиҖ…иҖі гҖӮ иҪ»жҸҸж·ЎеҶҷ пјҢ еҫ—дҫҝдәҶд№ӢеҸҜд№ҹ гҖӮ дёҚеҝ—дәҺеӯҰеҝ—д№ӢеӨ§ пјҢ иҖҢз«һз«һжғҹжұӮеҫ—зҫҺеҰ» пјҢ жҳҜи°“ж„ҡи°¬ гҖӮ д»Ҡд№Ӣз•ҷеӯҰз”ҹ пјҢ е…¶з«ӢиЁҖиЎҢдәӢ пјҢ зҡҶеҠЁеӨұе…¶е№іиҖ…д№ҹ гҖӮиҝҷеҸҜиғҪжҳҜй’ҲеҜ№з•ҷеӯҰз”ҹзҫӨдҪ“д№ жҹ“欧йЈҺзҫҺйӣЁ пјҢ еҖЎеҜјжҒӢзҲұзҘһеңЈд№ӢиҜҙ пјҢ жҜҸжҜҸеҚ•ж–№йқўж’•жҜҒдёҺж•…еӣҪз”ұзҲ¶жҜҚд№Ӣе‘ҪеӘ’еҰҒд№ӢиЁҖжүҖйў„е®ҡд№Ӣе©ҡзәҰ пјҢ иҖҢж¬ІеңЁеҘіз•ҷеӯҰз”ҹдёӯйҖүжӢ©ж–°ејҸеҘіеӯҗд№ӢйЈҺж°” гҖӮиҖҢеҜ№дәҺз»ҸжөҺзӢ¬з«ӢдёҺеӯҰжңҜиҮӘз”ұд№Ӣе…ізі» пјҢ йҷҲеҜ…жҒӘд№ҹжңүж·ұеҲ»зҡ„и®әж–ӯ гҖӮеҗҙе®“еңЁ1919е№ҙ9жңҲ8ж—Ҙзҡ„ж—Ҙи®°йҮҢи®°иҪҪйҷҲеҜ…жҒӘзҡ„иЁҖиҜҙпјҡжҲ‘дҫӘиҷҪдәӢеӯҰй—® пјҢ иҖҢеҶідёҚеҸҜеҖҡеӯҰй—®д»Ҙи°Ӣз”ҹ пјҢ йҒ“еҫ·е°ӨдёҚжөҺйҘҘеҜ’ гҖӮ иҰҒеҪ“дәҺеӯҰй—®йҒ“еҫ·д»ҘеӨ– пјҢ еҸҰжұӮи°Ӣз”ҹд№Ӣең° гҖӮ з»Ҹе•ҶжңҖеҰҷ гҖӮ Honest means of living гҖӮ иӢҘдҪңе®ҳд»ҘеҸҠдҪңж•ҷе‘ҳзӯү пјҢ еҶідёҚиғҪз”ЁжҲ‘жүҖеӯҰ пјҢ еҸӘиғҪйҡҸдәәж•·иЎҚ пјҢ иҮӘдҫӘдәҺй«ҳзӯүжөҒж°“ пјҢ иҜҜе·ұиҜҜдәә пјҢ й—®еҝғдёҚе®ү гҖӮ иҮіиӢҘеј„жқғзӘғжҹ„ пјҢ ж•ӣиҙўз§°е…ө пјҢ жҲ–еҰ„еҖЎйӮӘиҜҙ пјҢ еҫ’иЁҖз ҙеқҸ пјҢ з…Ҫжғ‘дј—еҝ— пјҢ ж•ҷзҢұеҚҮжңЁ пјҢ еҚ’иҮійў еҚұе®—зӨҫ пјҢ иҙ»е®ійӮҰ家 пјҢ жҳҜжӣҙжңүдәәеҝғиҖ…жүҖдёҚеҝҚдёәзҹЈ гҖӮеӯҰй—®дёҚи¶ід»Ҙи°Ӣз”ҹ пјҢ иҖҢз»ҸжөҺзӢ¬з«ӢжүҚжҳҜдәәж јзӢ¬з«Ӣзҡ„еүҚжҸҗд№ӢдёҖпјҢ иҝҷи®әж–ӯж”ҫеңЁеҪ“д»ҠдёӯеӣҪд№ӢеӯҰз•Ң пјҢ д№ҹеҗҢж ·йҖӮз”Ё гҖӮж— зӢ¬жңүеҒ¶ пјҢ еҗҢеұ…дёҖе®Өзҡ„еӯҰеҸӢжұӨз”ЁеҪӨеҜ№еҗҙе®“д№ҹеҒ¶жңүдёҘиӢӣд№Ӣжү№иҜ„ пјҢ з»ҷеҗҙе®“йҖ жҲҗдәҶе·ЁеӨ§зҡ„еҝғзҗҶеҺӢеҠӣ пјҢ е°Өе…¶жҳҜеҜ№еҗҙе®“зғӯиЎ·дәӨйҷ…иҚ’з–ҸеӯҰй—®зҡ„жҢҮжҺ§ пјҢ и®©еҗҙе®“д№…д№…йҡҫд»ҘйҮҠжҖҖ гҖӮеҗҙе®“е…¶е®һе№¶ж— й•ҝиў–е–„иҲһд№ӢжҪңиҙЁ пјҢ еҚҙеҸҲи·ғи·ғж¬ІиҜ•дәҺдәӨйҷ…еңәеҗҲ пјҢ зңҹжҳҜжңүзӮ№з”ЁйқһжүҖй•ҝ гҖӮ жҚ®еҗҙе®“ж—Ҙи®°пјҲ1919е№ҙ12жңҲ29ж—Ҙпјү пјҢ д»–иҮӘиҫ©дёәж¬ІеҖҹжӯӨдёҖж”№дёӯеӣҪиҜ»д№Ұдәәеӣәжңүзҡ„д№Ұе‘Ҷеӯҗж°” пјҢ еҚҙеҫ—дёҚеҒҝеӨұ пјҢ еҸҚиҖҢдёәеҸӢдәәжүҖи®Ҙ笑 пјҢ д»Ҙдёәд»–зғӯиЎ·дәҺдҝ—еҠЎеҖҫеҝғдәҺеә”й…¬ пјҢ е°ұжӯӨиҖҢиЁҖ пјҢ жҲ–и®ёжүҚиғҪзҗҶи§Јеҗҙе®“д»ҘиҜ»д№ҰжқҘиҮӘжҲ‘ж•‘иөҺиҺ·еҸ–еҶ…еҝғе®үе®Ғзҡ„вҖңиҜ»д№Ұж•ҷвҖқд№ӢжүҖз”ұжқҘ гҖӮиҜ»д№ҰеҶҷж—Ҙи®°е°ұжҲҗдәҶеҗҙе®“зҡ„дёҖз§Қе…·жңүе®—ж•ҷд»ӘејҸж„ҹзҡ„иЎҢдёәдәҶ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Ҳ‘з»ҷдёӯеӣҪд№іе“ҒиҙЁйҮҸжҙ—дёӘең°
- еңЁвҖңй»„йҮ‘жө·еІёвҖқдёӯеӣҪиҝҷж ·е®һзҺ°дәәе·ҘжёҜеҸЈдёҺжө·йҫҹе…ұз”ҹ
- еҪ“ж ёиҒҡеҸҳйҒҮдёҠ3Dжү“еҚ°дёӯеӣҪдҪҝвҖңдәәйҖ еӨӘйҳівҖқжӣҙиҝ‘дёҖжӯҘ
- ж¬әдәәеӨӘз”ҡпјҒиҝ‘дёӨдёӘжңҲзҫҺеӣҪе…ЁйқўеӣҙеүҝдёӯеӣҪе®һеҪ•
- еҚҒеӨҡе№ҙеүҚиҝҷйғЁеҲ·ж–°дёүи§Ӯзҡ„з”өи§Ҷеү§пјҢз«ҹеҗҜи’ҷдәҶдёҖд»Јдәә
- зәёиҖҒиҷҺпјҹдҝ„еӘ’пјҡзҫҺеӣҪдёҚж•ўдёҺдёӯеӣҪеңЁеҚ—жө·еҸ‘з”ҹзӣҙжҺҘеҶІзӘҒ
- дёӯеӣҪдәәдёҚеӯҰиҘҝж–№зҡ„еҘҪ
- ж—Ҙжң¬еӣҪеҶ…ж–°еҶ жӯ»дәЎдәәж•°иҫҫеҲ°1000дәә
- дёӯеӣҪз»“
- е№іеҺҹе…¬еӯҗпјҡи°ҒжҳҜиҝ‘д»ЈдёӯеӣҪжңҖдјҹеӨ§зҡ„дә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