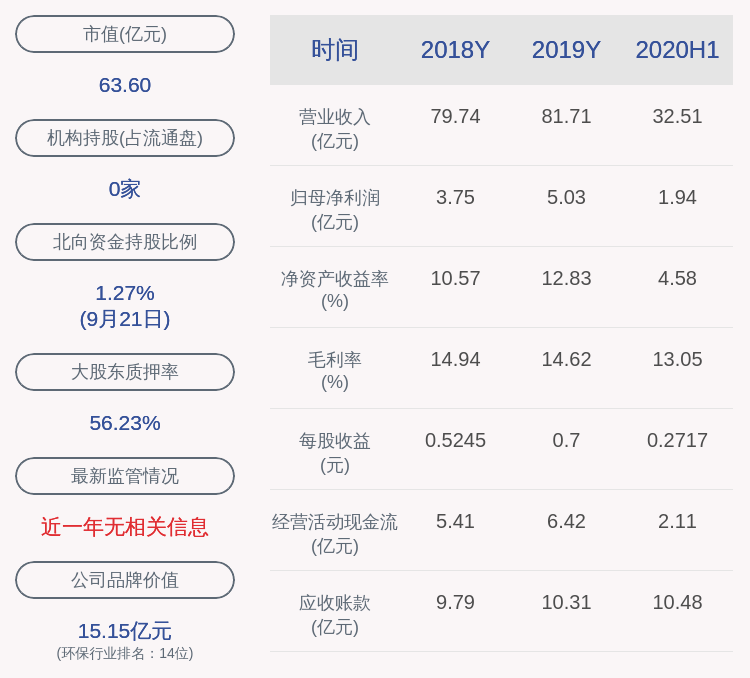『文学教育』小说家如何制礼作乐 | 胥志强( 二 )
当然 , 儒家的伟大之处 , 在于它对人性的基本尊重 , 在于它对天下为公的不懈追求 , 这使得儒家的礼乐堪称文明 , 虽然不乏历史的局限性 。 儒家制礼作乐的局限性 , 不仅表现在它的宗旨始终在于维护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支配关系 , 还表现在由于对礼仪的过分执着而衍生的教条化倾向 , 即礼仪可能脱离人性而成桎梏 。 而礼教要想不成教条 , 就得时刻谨记制礼的要点 , 是“因人之情” 。 这一点“先圣”是有自觉的 , 不过具体执行起来很不易 。 因为要因人之情 , 就先要懂得人情 , 那么问题来了:儒家的圣人和后学懂人情吗?今时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懂人情吗?不见得 。 话又说回来 , 如果谁懂得人情谁就更有资格制礼作乐 , 这下恐怕就要轮到小说家们窃笑了 。 因为 , 就像古代那位最伟大的小说家所说的 , “世事洞明皆学问 , 人情练到即文章” , 小说家其实正是人情的专家 。
三
本文插图
实际上 , 无论是儒家圣人后学 , 还是原始部落首领 , 抑或芸芸凡夫俗子 , 一旦涉及如何设计礼俗 , 他们都会面临一些根本性的难题 。 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 小说家或者小说式思维 , 正能为此一难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启发、补充以及矫正 。
古人说 , 诗言志 , 实际上礼仪也是心志的表达 , 无论是礼容(神情)、礼仪(动作)还是礼器(礼物) , 都是表达内在之心意的外在载体 。 既是载体 , 就免不了会有“异化”的时候 , 即外在与内在不能相符 , 或者东西不能代表“心意” , 或者礼虽到而情未到 , 也可能是有心而无力表示 。 礼崩乐坏 , 自然是“人心不古”的征兆 , 但礼仪隆盛 , 也不见得一定有多少真情流露;甚至过份的繁文缛节 , 恰恰是对礼义匮乏的掩饰 。 所以孔子会无可奈何地悲叹:“礼云礼云 , 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 , 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甚至有时候也不得不舍弃对形式的要求——“礼 , 与其奢也 , 宁俭;丧 , 与其易也 , 宁戚” 。 (论语·八佾)
概括一下 , 礼之内在与外在的脱节 , 或古话所说的心与迹之间的张力 , 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相互缠绕的维度 。
其一 , 公共的仪式如何表达个人的情感?礼仪的本质和语言很相似 , 都涉及一个公共符号如何表达个人情感的难题 , 由于礼仪所用载体的局限 , 这一难题甚至更为棘手 。 比如 , 父慈子孝应该是亲子之间的伦理要求 , 但如何以礼俗表达这一要求 , 却很难一概而论 。 比如 , 《礼记》里讲 , “凡为人子之礼 , 冬温而夏凊, 昏定而晨省 , 在丑夷不争” , 这能否看作屡试不爽的通则?
实际上并不见得 。 如何做父母 , 如何做子女 , 不一定只有一套通行的规则 , 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往往是极为个人化的个例和细节 。 晓苏先生非常赞赏的小说《上边》(作者:王祥夫)里有个细节 , 令人过目难忘 。 住在乡下的母亲 , 好不容易盼来了城里上班的儿子回家小住 , 但不久儿子又要走了 , 临走前儿子在院子里像小时候一样撒了泡尿 。 儿子走后心情失落的母亲 , 用个盆子扣住这滩尿迹 。 也许只有最敏感的心灵才能想像出这等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 , 而这恐怕是古板的礼俗专家们轻易看不见的 。
如何做子女 , 也是一样的道理 。 晓苏先生写自己的父亲、母亲 , 显得很真实 , 不虚伪 。 在散文《读父》中也有一个细节令人难忘 。 文章写自己在一个雪天跑去父亲工作的地方玩 , 没想到父亲忙于打牌 , 根本没有问自己是否吃饭 , 还立刻打发他回了家 。 但也许这种爱恨交织才是亲情的真相 。 正如作家自己说的 , “父亲也是个凡人 , 他也有自己的兴趣 , 也有自己的个性 , 也有自己的脾气 , 偶尔的疏忽、偶尔的暴躁 , 偶尔的失误 , 都是可以理解的 , 也是可以原谅的” 。 小说《父亲的相好》则更是一个更能让礼学专家惊掉大牙的话题 。 小说以一个人到中年的女儿的口吻 , 讲述了她对父亲出轨行为的谅解:父亲年轻时那么帅 , 他的相好那么漂亮 , 又那么善良 , 这段故事又那么美好 , 怎么让人忍心去破坏和否认呢?毫无疑问 , 故事里有受害者 , 但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 没有完美的生活 。 人既不纯粹是天使 , 也不纯粹是魔鬼 , 善恶交织、即圣即俗才是生活的真相 , 以非黑即白、“人人皆可为尧舜”思维搞人性大清洗才是最可怕的罪恶 。
推荐阅读
- [考易达教育]中小学必读书籍《简爱》必考知识点汇总!建议收藏!
- 【王玉秀细说教育】他是“不老童星”,35岁却演了17年小朋友,娶娇妻还被说像母子
- #希赛教育#那些让人惊悚的减肥方式还在用?学了护理才知道多可怕!
- 「倚数」杜贵晨:“倚数”称名和“倚数”谋篇(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二)
- 女子文学■如君训,作别善良
- 『金凤泛论教育』吴尊女儿8岁打耳洞被赞勇敢,黄磊女儿被批成熟,差距咋就这么大
- 『草儿聊教育』周冬雨替身不算啥,吴京替身才叫“吓人”,这简直是复制粘贴
- 「」孩子近视的原因和误区
- 「小红聊教育」同样演富二代,佟丽娅和王子文为什么差那么多
- 「艳艳聊教育」原相机到底多真切?看杨紫跟郑爽同节目路透,颜值高低一眼便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