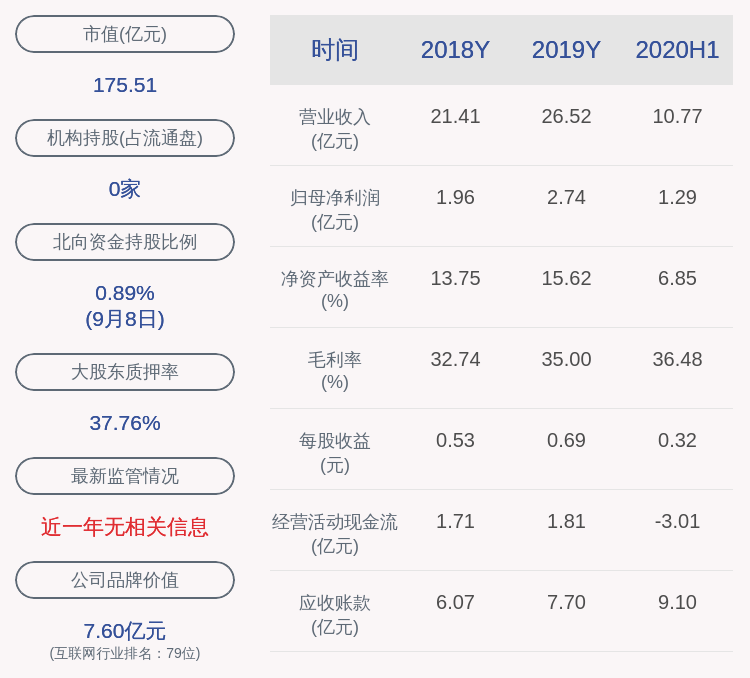文章插图
因此,要更准确地理解雍正的“十二美人屏”我们必须将其置于清宫艺术的语境中,并与其他产于清宫的女性图像作比较。
杨伯达在研究清宫档案之后指出,乾隆皇帝对宫廷画师的控制相当严格,这种控制在绘制皇家成员肖像时——包括女性成员如皇太后、皇后、嫔妃、公主等的肖像——尤其明显。宫廷画师必须严格依照一系列例行标准,并且只有在初稿被审査、通过之后才能正式绘制。
乾隆以前的清帝应该也实行了类似的控制,因为康熙、雍正朝的帝王与后妃肖像展现出相当一致的严格模式。若将此类画像与雍正“十美人"作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强烈反差会令人大吃一惊。此类宫廷画像称为“容”,其地位是正式的,其作用是仪式性的。
这类作品遵循统一的图像风格,全然摈弃对建筑环境、身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的描绘。当然,有些皇室容像更为传神,有些则展现出西欧技法的较深影响,但它们全都没有逾越此种画类的基本规则:作为正式的仪式肖像,“容”像必须在空白的背景下以完全正面的角度表现帝王与后妃。女性皇室成员被简化为近似同一的偶人,其主要角色在于展现象征其民族与政治身份的满族皮帽和龙袍。
这些容像中对正式礼服的着重强调显示出清帝王对其身份的深刻关注。清朝伊始,满族的统治者就极为强调其民族服裝的重要性,拒绝接受改换汉服以显示其天授皇权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满族服装显示了其起源及民族优越性。
实际上,如果说清朝统治者非常情愿地汲取了大量汉文化因素,有三件事——姓氏、发式和服装——则是例外。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大批17世纪以来的清官女性服装,但就我所知,其中没有一件汉族式样的衣服。
这个缺失不难理解:自清朝奠基者皇太极开始,每个帝王都颁布法令,严格禁止各旗成员(不论是满、蒙或汉旗)穿戴汉族服饰。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在讨论清宫女性题材绘画的篇文章中引用了嘉庆皇帝于1804年颁布的法令,清楚地证明了这种禁戒在清代建国一个半世纪后仍在强令实行。
了解了这个背景,雍正十二美人及其他清宫美人画就显示出了一种深刻的反讽性:画中仕女全都着汉装,而且被源自传统中国文化的象征物及视觉隐喻所环绕——画中所表现的正是被严令禁止的情境。
真实的情况是:严格的法规似乎更激起法规设立者在私下里对其所公开禁止之事物的兴趣。在我看来,清宫中美人画风行的原因,正是这种对“汉族性”及“汉装美人”所代表的异域风情的私下兴趣。也正是因为这种兴趣和推崇来自最高统治者,汉族美人画在清代宫廷艺术中才能发展成一个强有力的画类,对异族女性空间的幻想也オ能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
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中,美人画与江南名妓文化之间的原本联系并没有被忽略,不过这种关系滋养了另一种想象。雍正美人屏及其他清官美人画所表现的女性空间被赋予了更宽泛的象征意义,代表了满族统治者想象中的江南(亦即中国)以及它所有的魅力、异域风情、文学艺术、美人名园,以及由过度的精致带来的脆弱。
满族征服者来自北方并定都北方,在他们眼中,中国文化的魅力——其精致与柔顺——使它成为一个扩大的、寓意性的女性空间,激起幻想和征服的欲望。雍正的十二美人屏并不是头一件将中国文化表现成女性空间的作品。他的父皇康熙就已经建立起这种象征性的联系: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一架画屏上描绘了在梦境般的江南园林中冶游的中国仕女,屏风背后是康熙亲笔书写的张协帝(活跃于295年)的《洛禊赋》,描述了古代贵族和仕女在洛阳附近的洛水之畔的冶游。

文章插图
《乾隆皇帝宫中行乐图轴》
清金廷标
绢本设色
168*20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也不是最后一位将政治意义赋予汉装美人形象的清代帝王。其嗣位者乾隆恭顺地继承了这一传统。在一幅《宫中行乐图》中,乾隆皇帝坐在亭阁之中,遥遥俯视五位身着传统汉族服装的美人,皇家侍从正护送这五位美人过桥。乾隆在此画上的题跋中有这样几句:
推荐阅读
- 14个城市空间的阅读指南
- “小舟独棹烟波间”:关于出行工具,宋代女性真的只独爱舟船吗?
- 梁山中哪一位好汉最受女性欢迎没有背景,却人尽皆知!
- 眉山市东坡区:拓展服务空间 共享文化盛宴
- 此人发明了一个汉字,被未婚女性谩骂了3年,如今人人都在用
- 西游最另类的三位女性:她们选的老公都很奇葩
- 大秦帝国:苏子&亚圣思辨之美
- 为什么能革大清的命,却革不掉女性的裹脚布?不缠足是奇耻大辱
- 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的帝国,有太多相似之处!
- 《大秦帝国》违背了多少历史事实,为美化秦朝撒了多少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