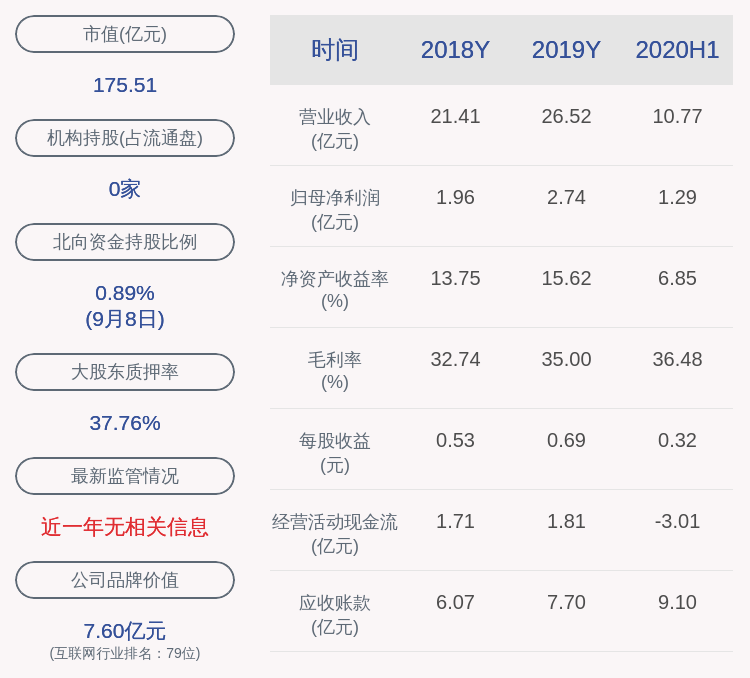这两种方式也反映在雍正美人屏的创作中:每幅画的构图都以位无名佳人为中心,她周边的物质环境凸显了其女性气质。在某几幅图中,雍正的诗作和美人屏甚至构成了相互指涉的“对偶”。如前文所引的《竹子院》一诗中,挺立于岁寒之中的竹子影射着一个娟秀、孤寂的美人。

文章插图
而在美人屏上的一幅画中,几竿郁郁苍苍的修竹半掩门洞,门后是幽深的庭院,一位美人正从门洞后探出半个身子。修竹充当了画面的右侧边框,细长的美人则框住了画面左侧。二者对称的布局及相互呼应的关系暗示着其间的语义互换性。
类似的美人和植物的对等性在其他几幅屏画中也可见到。其中一幅表现一位美人坐在梧桐树下,茂盛的树叶宛若华盖。从她身后的月门可以窥见满架的书卷及更远处的另一扇方门。这两扇门都有其他画屏中所没有的月蓝色边框。从这些特征看来,此画屏似乎可与《园景十二咏》的第三首《梧桐院》联系起来。诗中写道:“吟风过翠屋,待月坐桐轩。”
在另一幅屏画里,正在房内补衣的美人出神地望着窗外的一枝象征同心之好的并蒂莲。此一有关爱情的主题亦是雍正《莲花池》一诗的主题:“浅深分照水,馥郁共飄香。……折花休采叶,留使荫鸳鸯。”类似的关联性在其他诗作和画屏之间也可以见到。
如在《桃花坞》一诗中,雍正将桃花比作“绛雪”:“绛雪侵衣艳,霞绕屋低。”而一幅画屏所描绘的正是细雪之后、恻侧清塞之中,竹叶上覆着一层薄雪,戴着毛皮的美人坐在炭炉边取暖,一枝桃花昭示着春之降临。粉中泛白地从屋檐上垂下,令人联想到的正是“绛雪”这个词的意味。

文章插图
另一幅描绘夏景的画屏中,花栏的六边形大窗将美人与观众隔开。美人倚在层层叠叠的假山石畔,正凝视着窗外,其眼神指向画面前景中绽放的牡丹。白色、粉色、紫色的牡丹花与假山石相伴,呼应着美人的面庞与衣裳。整幅图像描绘的似乎就是雍正的《牡丹台》:
叠云层石秀,曲水绕台斜。
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
艳宜金谷赏,名重洛阳夸。
国色谁堪并,仙裳锦作霞。
我在这里进行的比对并不只是为了显示一般意义上的诗与画的共同主题与图像,而是希望说明《园景十二咏》和十二美人屏都展现出构建女性空间的特殊意图。
二者都将美人表现为男性注视的对象,她们也都属于(或融入了)一个女性化的空间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花草和树木映现美人的相貌和优雅,铜镜和画屏暗示其孤独及忧伤。当然,这种类型化的文学和艺术的联系可以追溯到美人文学和艺术的起点。

文章插图
简言之,中国文学和艺术在想象和建构女性空间的过程中以两类主要美人形象为中心。早期类型为宫廷女子(有时也以神女的形象出现),徐陵(507—583年)于545年编成的《玉台新咏》中所收的诗歌不厌其烦地吟咏这种女性的寂寞深闰,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可感知的寂寥。
以英国翻译家白安妮(AnneBirrell)的话来说,深闰在这些诗里总是被描写为“封闭的情色世界。一个女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元素,如侍女、孩子友人、其他家庭成员,尤其重要的夫君或情郎,全都从诗中的情景里消失了。在这一时期(指六朝)繁盛的宫体诗中,身处锦绣香国中的女人囿于符号化的孤寂”。
尽管如此,诗人游移的目光仍能穿透这个闭锁的空间,以细密的心思窥伺无名宫姫的体貌及器物之细节。

文章插图

推荐阅读
- 14个城市空间的阅读指南
- “小舟独棹烟波间”:关于出行工具,宋代女性真的只独爱舟船吗?
- 梁山中哪一位好汉最受女性欢迎没有背景,却人尽皆知!
- 眉山市东坡区:拓展服务空间 共享文化盛宴
- 此人发明了一个汉字,被未婚女性谩骂了3年,如今人人都在用
- 西游最另类的三位女性:她们选的老公都很奇葩
- 大秦帝国:苏子&亚圣思辨之美
- 为什么能革大清的命,却革不掉女性的裹脚布?不缠足是奇耻大辱
- 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的帝国,有太多相似之处!
- 《大秦帝国》违背了多少历史事实,为美化秦朝撒了多少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