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出版四十周年。此书虽是当代著作,但出版不久即无可争议地成了经典。我们甚至可以说,启蒙时代之后,最重要的自然法著作有且只有两本,一本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另一本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第二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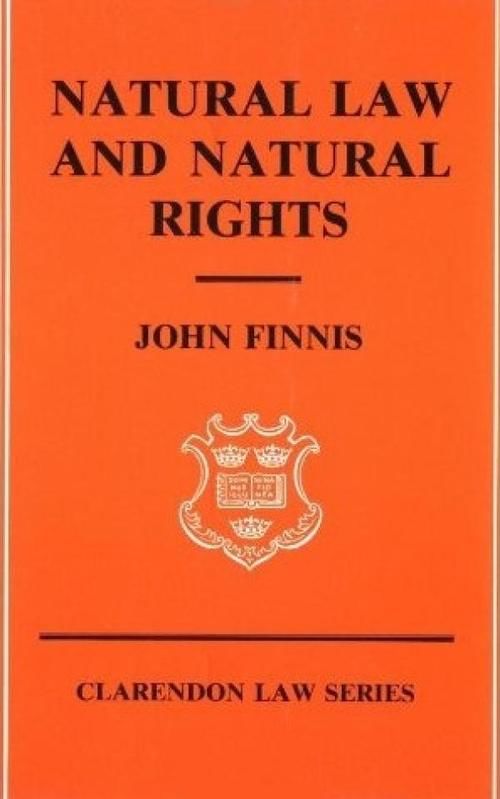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第一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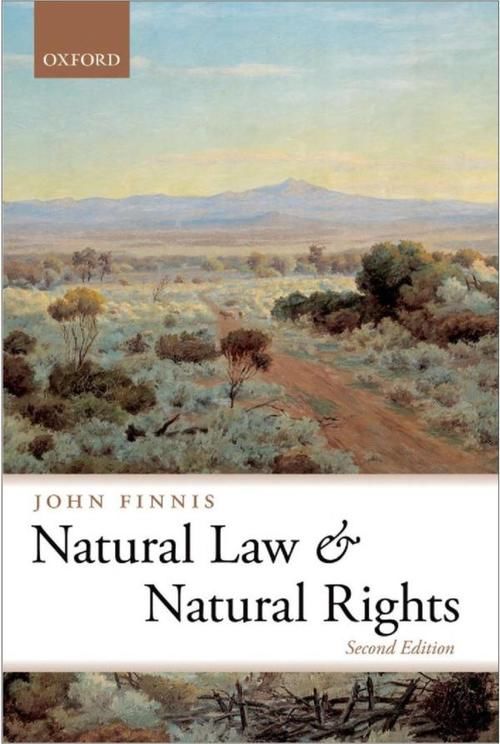
文章插图
《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第二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菲尼斯vs.施特劳斯有些读者可能会对上述论断产生困惑乃至有所不满:说到自然法,最重要的当代著作难道不是列奥·施特劳斯那本《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菲尼斯本人对施特劳斯的态度。
菲尼斯是少见的对施特劳斯、沃格林等非分析传统内部的思想家抱有强烈兴趣的英美哲学家,但与此同时,他明确把自己归入分析哲学阵营。在《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中,施特劳斯的名字仅在前言和第一章出现过几次。菲尼斯还专门写了个长注批评施特劳斯,认为他根本没有证明古典意义上的自然正当依赖于目的论宇宙观这一“重要但含糊”的主张。
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从哲学和思想史的区别入手,来理解菲尼斯和施特劳斯的差异。
菲尼斯明确区分了对自然法的研究和对自然法理论的研究:自然法理论是相关学者对自然法的看法,对自然法理论的研究是史学而非哲学研究 (参见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4)。《自然法与自然权利》是对自然法而非自然法理论的研究,这一点和《自然权利与历史》大不一样,后者基本就是对自然法理论发展史(毋宁说是崩坏史)的梳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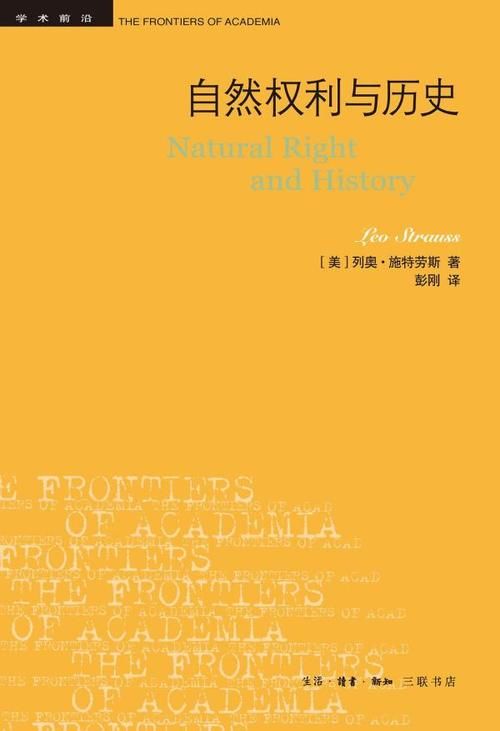
文章插图
三联书店分别在2003、2006、2016年出过三个版本的《自然权利与历史》
不过施特劳斯的独特性在于,虽然做的基本都是思想史研究,但对他来说,思想史只是传递哲学教诲的恰当手段。也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施特劳斯是政治哲人,而非单纯的政治思想家。不过施特劳斯似乎一直停留于“走向哲学”——准确说是“返回哲学”——途中,《自然权利与历史》并没有挑战真正的哲学问题:证明自然法的真理性(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页)。相比之下,《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不仅给出了相关论证,而且水准不俗。如果施特劳斯能活到《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出版那天,他也许会像之前对待富勒(Lon L. Fuller)那样,写信给菲尼斯说:“你的论证要比哈特高明。”(关于施特劳斯和富勒的通信参见[美]罗伯特·萨默斯:《大师学述:富勒》,马驰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17页)下面我简单介绍下自然法面临的理论困境,并对菲尼斯之前的当代自然法理论作整体性评估。
自然法复兴?一场虚假繁荣
在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知识体系形成之后,人们的历史感、相对主义意识越来越强烈,从“事实”推不出“价值”也被普遍认为是一项基本的学术法则。而自然法是亘古不变、普遍必然的应然法则,且据说是从关于人之本性的“事实知识”中推导出来的。因此在现代世界,自然法似乎注定沦为明日黄花。霍姆斯的刻薄话很好地展现了有现实感和智识自信的现代人对自然法的轻蔑态度:“那些相信自然法的法学家们,在我看来心智状态十分幼稚,他们把那些耳熟能详且为自己及周围人所采信的东西接受下来,视之为必被天下所有人采信的东西。” ([美]霍姆斯:《自然法》,载《法学论文集》,姚远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274-275页)
推荐阅读
- 朗诵:顺其自然,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 赵孟頫《大元敕藏御服之碑》,秀媚爽朗,灵动自然!
- 从木格栅窥见自然禅韵!印尼现代风雅泳池别墅
- 在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中,诗人对自然大地敞开胸怀汲取慰藉
- 修行要顺其自然!原来,这样退步就是向前?
- 《衣尚中国》山水取形、草木采色 藏在衣服中的自然与诗意
- 展览预告|“运河晨曦 自然淮安”——朱传宏书画作品展
- 2021年去寺庙烧香,牢记2句话,好运自然来
- 新书上架|诺奖作家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 动物复仇案反思人和自然
- 软陶最美的玩法,把大自然搬到耳上,太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