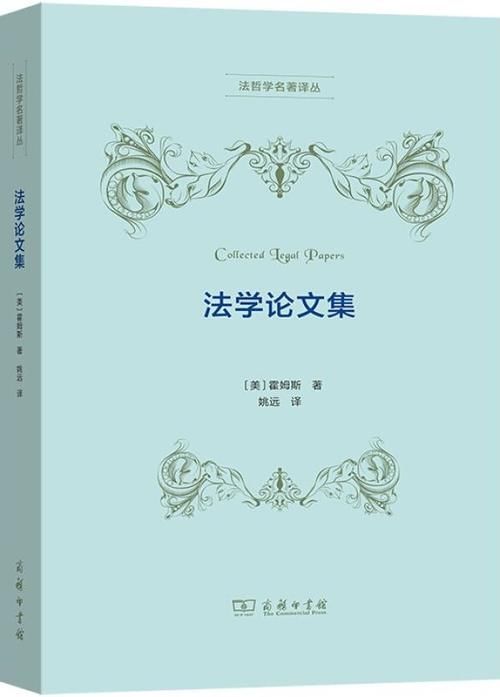
文章插图
霍姆斯著《法学论文集》
在菲尼斯之前,当代自然法学家虽然给出了种种辩护方案,但对自然法之真理性所作的证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很难让人满意。自然法的复兴完全要“归功于”纳粹统治的历史教训及战后审判的现实需要。这些历史情势使自然法学家提出的“实践必要性”论证有了强大的说服力。【 对自然|钱一栋︱菲尼斯改变了什么:《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出版四十年】实践必要性论证的基本套路如下:如果不接受自然法,我们面对恶法就会毫无抵抗力,就会陷入极权统治,乃至走向虚无主义,因此有必要拥抱自然法。
但这种说法其实站不住脚。不少学者都曾敏锐地指出,“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但它是恶的”这两个理论命题落到实践中并没什么差别,接受法律实证主义并不妨碍人们抵抗暴政。这里的关键在于,“恶法亦法”仅仅是一项概念主张,它并没有附加任何违反常识的守法义务。回顾历史,自然法学说不见得比别的理论更能激发人们抵抗暴政的决心。事实上,只有在君权神授的背景下,诉诸自然法才是抵抗暴政的必要手段。总体而言,自然法思想宣扬的是服从权威,而非奋起反抗。明确鼓舞了反抗行为的只有自然权利论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自然法理论 (参见Judith N. Shklar,Legalism: Law, Morals, and Political Trial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70-77)。
更重要的是,哪怕在经验层面无懈可击,实践必要性论证也依然是一种糟糕的推理,容易陷入“诉诸后果谬误”。一种科学理论不会因为导致了可怕的技术灾难而被证伪,自然法同样不会因为能带来可欲的实践效果而变成真理。施特劳斯对此作了极为精彩的说明:“愿望并不等于事实。即便是证明了某种特定的观念对于幸福生活来说必不可少,那也只不过是证明这种观念乃是人们理当崇敬的神话:人们并没有证明它是真确的。效用和真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自然权利与历史》,第7页)
敏锐的读者也许会反驳道,实践必要性论证仅致力于说明我们有理由接受自然法,而非证明自然法确实是真理;即便不能证明自然法揭示了价值真理,我们也可以根据其实践效用来接受它。在前面引的那段话里,施特劳斯也认为,只要证明自然法确实有用,那它就是“人们理当崇敬的神话”。
问题是,在科学领域,效用和真理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价值领域则否(也因此,前文将自然法和科学真理作类比是非常粗糙的)。原因在于,效用是工具属性,“有用”是对工具、手段的评价,而手段总是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目的是否合理则要诉诸价值才能得到证明。简言之,价值真理与效用内在关联,谈论效用必须预设价值。因此,只有当我们已经获得价值真理,且这套真理并非自然法,但离开自然法又无法实现由这套真理定义的幸福生活时,我们才能逻辑一贯地将自然法视作必要的神话。但现实却是,许多学者一方面不相信自己还能证明任何价值真理,另一方面却不断作出诸如“现代性病入膏肓”“虚无主义糟糕透顶”之类的价值判断,进而以这些判断为依据为自然法招魂。
总之,实践必要性论证存在极为严重的问题。之所以有那么多自然法学家放弃真正的理论努力,停留于实践必要性论证,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两种意义上缺乏智识勇气:不相信自己能为自然法提供可靠的哲学辩护;不愿面对自己在理智层面倾向于接受的虚无主义“现实”。
当然也有少数自然法学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比如耶夫·西蒙(Yves R. Simon)、杰曼·格里塞茨(Germain Grisez)等。但这些学者的理论调子一般比较低,不会大喊“回到自然法”的口号,学术影响力也相对较小。此外,不少教材会给德沃金乃至罗尔斯贴上“新自然法学家”这一标签。他们两位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头脑,但将他们归入自然法阵营只会使自然法这一概念变得无比空泛,从而带来不必要的混乱。与之类似的还有富勒,虽然富勒的自然法学家身份早已写入教材、深入人心,他本人也不拒绝这一标签,但他基本是独立于自然法传统发展出了一套和典型的自然法理论只有局部相似性的学说。称他为新自然法学家本质上和称馒头为中国面包差不多:虽然不无道理,但也实在没有太大意思。
推荐阅读
- 朗诵:顺其自然,是生命的最高境界
- 赵孟頫《大元敕藏御服之碑》,秀媚爽朗,灵动自然!
- 从木格栅窥见自然禅韵!印尼现代风雅泳池别墅
- 在无家可归的漂泊感中,诗人对自然大地敞开胸怀汲取慰藉
- 修行要顺其自然!原来,这样退步就是向前?
- 《衣尚中国》山水取形、草木采色 藏在衣服中的自然与诗意
- 展览预告|“运河晨曦 自然淮安”——朱传宏书画作品展
- 2021年去寺庙烧香,牢记2句话,好运自然来
- 新书上架|诺奖作家托卡尔丘克《糜骨之壤》: 动物复仇案反思人和自然
- 软陶最美的玩法,把大自然搬到耳上,太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