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桐|《红豆》2020.07:【散文空间】幽深之花 |洪放( 二 )
若干年后 , 再来读卡佛这诗 , 依然还能想象悬铃木的美好 。 即使我早已知晓一切 , 梦仍未醒 。 我甚至有种挂念:倘若将来老去 , 能在挂满悬铃木的树下安憩 , 也是一种“回到大地”吧!
青 桐
南方大地上村庄星罗棋布 , 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旗 。 我们村的旗便是庄子东头的那棵青桐 。 一出庄子口 , 除了太阳 , 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青桐 。 它独立于高冈之上 , 四周全是水田 。 蛙鸣 , 鸟语 , 水稻拔节之声 , 蛇吐信子之声 , 野狐求偶之声 , 大雁临时休憩之声……当然还有人声 。 人声从出了庄子便开始 。 先是一声短叹:“那青桐又长高了呢 。 ”再是一声长叹:“好像还是从前那样 。 从我记事时就那么高了 。 ”
后来沿着田埂 , 一直走到高冈之下 , 再望一眼青桐 , 释然道:“树哪像人?人生年不满百 , 树可上千年呢?它当然长得慢 。 ”
村子里的人将时间也固化成了青桐 。 八九时 , 说“日头到青桐半腰了” 。 十二时说“日子正在青桐顶上呢” 。 黄昏时说“日子到青桐脚跟了” 。 夜里还是青桐说“青桐整个都在黑里了” 。
人生一世 , 草木一秋 。 青桐见证了村庄的漫长岁月 。 青桐树下的高冈上 , 埋下了无数的胞衣罐 。 老年人要走了 , 便常常立在村口 , 望着青桐说:“最后看一眼了 。 ”家里人便劝道:“慢慢看 。 那边也有的 。 一模一样 。 ”老人点了点头 , 混浊的目光却一下子澄澈了 。
青桐是村庄的旗 。 老远赶路的人看见青桐 , 便知道洪庄近了 。 倘若不识路 , 便问:“那青桐的庄子还有多远?”被问的人答曰:“三里地 , 快了 。 ”
确实是快 。 六年前 , 庄子没了 。 四年前 , 问同样迁进城的同村人 , 他们说:“青桐也没了 。 ”我问:“什么时候没的?”答曰:“不知道 。 反正是没了 。 ”我说:“那以后怎么回村子呢?”他们不再回答……
响 堂
合安路从桐城大关开始 , 就一直贴着龙眠山行进 。 龙眠山是大别山的余脉 , 因此 , 山的气势 , 就有些温婉 , 但极灵秀 。 公路到了吕亭 , 向西北便有岔路 , 往里走十来里 , 见一中空之山 。 山洞深百米 , 宽五六十米 , 高亦百米 。 据说这是未能完工的飞机跑道 。 六十年前 , 这个叫双龙的山野之地 , 被完全军事化 。 三线工厂和军用电台进驻此地 。 只是它们并不在明处 。 这里大大小小的七八座山头都被掏空 , 工厂和电台都藏在里面 。 平时 , 除了军用车辆出入 , 这双龙湾里 , 竟是出奇的安静 。 天空有时会压下来 , 大片的云朵与随之而来的雨水 , 从山坡上流过 。 在隐蔽的山洞门前 , 或许也能形成一道道瀑布 。 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 这瀑布也被烙上了神秘气息 。
再往里走 , 是响堂 。 这是个古老的村子 。 三十年前 , 我去这村子时 , 村庄的人早已全部搬走了 , 那里仅仅剩下了四排营房 。 红砖、大瓦 , 背对青山、面对小河 , 但却是一派荒凉 。 军队、电台以及三线厂 , 都已撤走 , 山洞被封死 , 未完工的机场跑道 , 成了蝙蝠们的天堂 。
我沿着响堂那四排营房走了一圈 。 我想问问当地人当年的故事 。 没人说得出来 , 也没人记得起来 。 这双龙湾只在某一个时段 , 被军事化 , 而后全然静寂 , 除了封死的洞口、广大的跑道、破旧的营房 , 再无痕迹 。 新修的《桐城县志》也对其语焉不详 。 一个时代的印记 , 比一丛蒿草的消失还要迅疾 。
总有一些事物记载着过去 , 只是我们浑然不知 。 同样 , 总有一些地方埋藏着过去 , 只是它从一开始便已选择了拒绝 。
双龙湾 , 响堂 , 从前的桃花源成了这荒凉地 , 据说还将一直荒凉下去 。 在不远处的合安公路上 , 车辆如流 , 却没有一辆为之停下 , 陪伴它成为亘古的 , 也唯有龙眠山 。
临淮镇与野秋葵
更多时候 , 废弃成了一种让人难以遏制的美 , 这或许是人性深处的阴暗 。 当然 , 明亮是花开的部分 , 享受花香、烛照花颜看似怡情 , 但随之而来的 , 也许还是最后的寂灭 。 万物了了 , 一旦想到或懂得此意 , 人性最深处的阴暗——对废弃也即死亡、消逝的尊崇 , 便油然而生 。
推荐阅读
- 网红美食|网红豆角做法最近真火,3斤也不够吃,不炒不炖,出锅比肉都要香
- 星座|九月初,红豆相思,一往情深,四星座如胶似漆,百年好合
- 养生杨医师|红豆和此物一起煮,常食滋养皮肤,皱纹消失了,子宫也干净!
- 烹饪|面粉和红豆就能做好吃的,外酥里甜,满满红豆香
- 烹饪|白芸豆搭配红豆馅,动手做一碟芸豆卷,健康美味小朋友吃得乐开花
- 食疗食补|立秋后多喝莲子红豆汤,香甜软糯还健脾,多加一味它,清香更开胃
- 红豆杂志|《红豆》2020.07:【小说长廊】飞机上有Wifi吗?(微篇小说)|田鑫
- Array|王维诗词中的红豆,曾经参加过拍卖,为何卖21万也有人买
- 烹饪|酥松香甜的红豆酥
- 诗刊|《红豆》2020.07:【诗歌部落】我与神近了八千米(组诗)? | 龚学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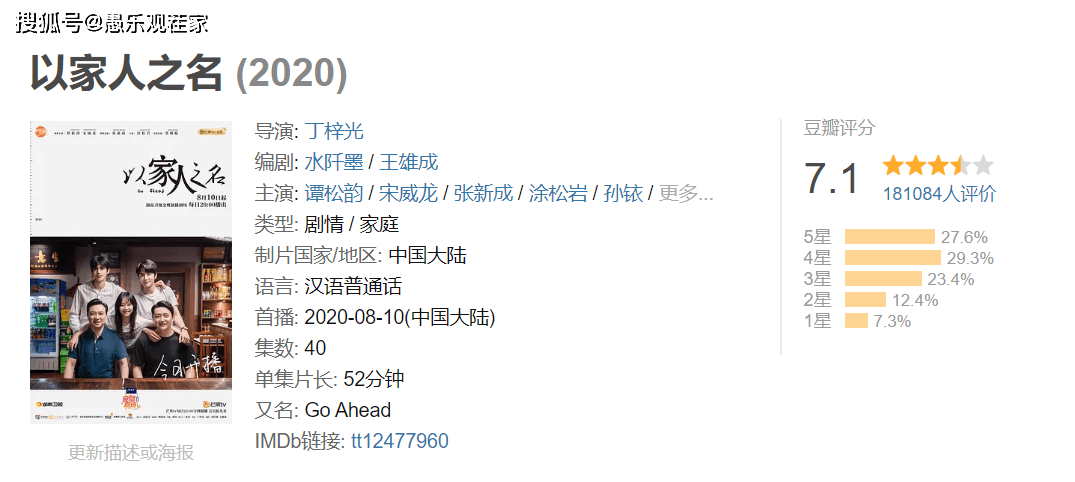









![[商务部]商务部:中国没有也不会出现大规模外资撤离情况](http://aqimg.010lm.com/img.php?https://pic.bbanp.com/img/5080851962419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