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游牧生产活动:传统蒙古包性别文化的影响因素
在传统蒙古包性别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游牧生产活动起着基础性作用。不管是“东西对称”的性别特征,还是“互补协作”的性别秩序,都与蒙古族游牧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生产关系在生活领域、居住空间上的特殊体现。例如,在蒙古包的西侧放置马具,这与男性从事养马、牧马、训马、医马等活动密切相关。因为马的驯服为游牧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质的飞跃。有了马,蒙古族才能够管理数量和种类众多的家畜,才能够大范围地游牧和迁徙,所以马与男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札奇斯钦在《蒙古文化与社会》中指出,蒙古族的马、牛、骆驼、山羊等家畜,其排列次序永远不变,好像在它们中间划有阶级一样,马永远排在第一位。 [13](PP.20~21)女性在游牧生产体系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们不仅是养羊、养牛的能手,也承担着制作奶制品、饭菜、缝制衣服、靴子等重要的劳动任务。《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中记载,蒙古族妇女从事各种劳动,如缝制皮袄、衣服、鞋、马靴,等等,而且在这些劳动中她们非常敏捷和迅速。 [9](PP.44~45)除此以外,蒙古族的一些传统习俗也在明确、强化、延续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例如,蒙古族新娘在第一次煮奶茶时,婆婆会赠送一柄拴着哈达的勺子。 [10](P.122)游牧生产对蒙古族传统的性别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性别关系是劳动关系在性别领域的特殊体现。
传统蒙古包的性别文化还受到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在这里,性别秩序、政治秩序、宗教秩序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互相促进性。王公贵族、高层喇嘛的蒙古包不仅体积大,而且有特殊的装饰。他们一般使用八片、十片、十二片、十五片哈纳搭建的大型蒙古包,而平民百姓一般居住在用四片、五片哈纳搭建的小型蒙古包中。而且,王公贵族还使用蓝色的顶饰装饰蒙古包,高层喇嘛使用红色的顶饰装饰蒙古包,而平民百姓则没有顶饰。 [8](PP.108~109)在蒙古包内外的空间分割上,政治秩序与性别秩序相互一致,即都有“西尊东卑”的特点。例如,在同时搭建两个蒙古包时,王公贵族的蒙古包需要位于西侧;而搭建多个蒙古包时,王公贵族的蒙古包需要位于中间。在进入蒙古包(毡子做的门)时,王公贵族、高层喇嘛可以走西侧,而普通百姓只能走东侧。落座时,王公贵族、高层喇嘛可以在蒙古包的正北或西侧盘腿大坐,男主人一般坐在下方,而女性基本上都是蹲坐。 [5](P.241)在古代宫廷生活中,这种政治秩序、性别秩序已经非常明显。《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记载,蒙古拔都汗坐在高高的宝座,旁边有一位王妃陪同;他的兄弟、儿子等人的座位较低,其他人则在他们后面席地而坐,而且宫廷内都分男西女东。 [9](P.95)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社会中,蒙古族政治权力与男性权利存在一定的相互重叠、互相关联、互相推动的关系。以往蒙古族的王公贵族、大小官员基本上都是男性,而且传统道德也认为男主人兴盛则家庭兴盛,家庭兴盛则国家兴盛,男性与国家兴衰、社会发展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 [10](P.4)在宗教方面,不管是喇嘛教还是萨满教,宗教工作者几乎都是男性,而且家庭祭祀活动也主要由男性来主持。在这里,宗教权力和男性权利存在一定的相互重叠、互相关联、互相推动关系。但是,与游牧生产活动相比,宗教、政治因素在蒙古族传统性别文化中都属于较次要的因素。
四、从女性中心到男性中心:传统蒙古包性别文化的历史演变
性别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从现有的资料看,传统蒙古包的性别文化经历了从女性中心到男性中心的发展过程。而且这一转变至少在上千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完成,直到13世纪建立蒙古汗国时,男性在社会文化各领域已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例如,13世纪的《蒙古秘史》在开篇追溯成吉思汗祖先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男性血脉联系为主。“巴塔赤罕之子塔马察,塔马察之子豁里察儿篾儿干,豁里察儿篾儿干之子阿兀站孛罗温勒,阿兀站孛罗温勒之子撒里合察兀,撒里合察兀之子也客你敦,也客你敦之子挦锁赤,挦锁赤之子合儿出。” [13](P.1)这种男性血脉观念说明当时男性在社会文化领域占据了明显优势。但是,我们从一些古老的神话故事、流传下来的诗歌赞颂词、残存的风俗习惯中,可以推测女性曾占据过重要的社会地位。例如,在蒙古族传统习俗中,一般把蒙古包的西侧视为尊贵,东侧视为卑微。但是在更早的历史时期,蒙古包的东西位置却有着完全相反的涵义。 [8](P.79)这与古代蒙古族崇拜太阳、崇拜太阳升起的位置有关。又比如,蒙古包的火撑子一般代表着男性血脉或者男性权利,但是在更早的时期,火撑子的神灵却是女性,称之为“灶火之母”(蒙古语称“噶拉·额可”)。 [14](PP.56~57)古代蒙古族认为,火神位于东南方,是一位身穿白衣,一只手拿念珠,另一只手拿圣水,骑坐在山羊上的女性“腾格里”神。 [8](P.283)但是随着时代变迁,火神的名称、性别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另外,蒙古族把佛像供奉于蒙古包的西北侧,这里属于男性区域,展现着宗教权力与男性权利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在更早的萨满教中,不仅有专属于女性的偶像神灵,还有专门的女性神职人员。《鲁布鲁克东行纪》记载,当时蒙古包的西侧总有一尊用毡制成的偶像神灵,他们称之为男主人的兄弟;而蒙古包的东侧也有类似的偶像神灵,他们称之为女主人的姐妹;另外它们之间,更高地挂着一个细小的偶像神灵,它算是全屋的保护者。 [9](P.211)可见,在古代萨满教中,神灵并不仅仅局限于男性区域(蒙古包的西北面),祭祀神灵也不只是男性专有的事情。这些都说明蒙古族传统文化经历了从女性中心到男性中心的发展过程,也说明性别文化是一个不断演变、不断建构的体系。
推荐阅读
- 经工集团党委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 史林︱何谓“靖康耻”:性暴力对宋代社会性别观的影响(下)
- 《天天向上》戏曲扮相太惊艳,致敬经典,传播传统文化
- 对话非遗人:赫哲族传统服饰
- 非遗年画进社区 传统文化迎新年
- 安庆师大团委:让青年学子做传统文化传播者
- 读传统文化??讲廉洁故事
- 【文化讲堂】开讲啦!传统修身哲学的当代价值
- 大荔印象:传统文化艺术“跑竹马”
- 王云强教授荣膺中国传统文化品牌“年度影响力人物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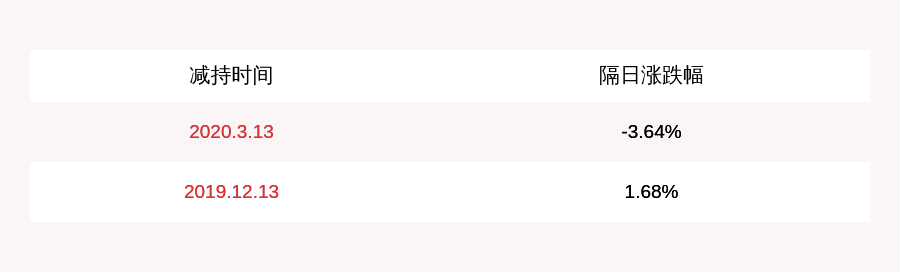
![[澎湃新闻]如何变废为宝,把二氧化碳握在手中?](http://ttbs.guangsuss.com/image/184a5c800afe6c309a05f2e12b53ea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