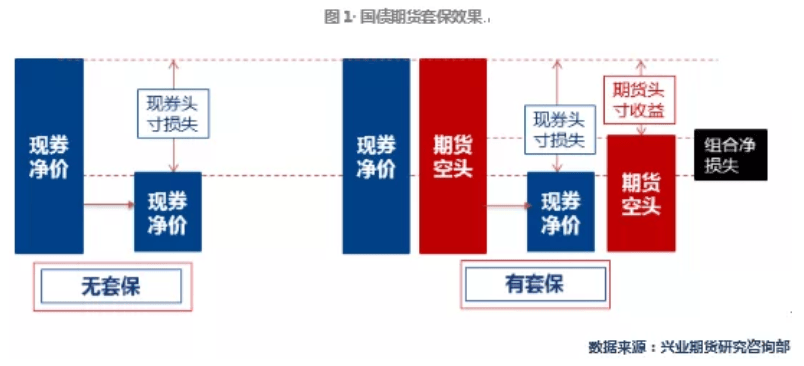еӯҰжңҜ|дјҠиҺұдј‘В·еҚЎиҢЁдёҺеӨ§дј—дј ж’ӯз ”з©¶пјҡеҚҠдёӘеӨҡдё–зәӘзҡ„еӯҰжңҜжј”еҸҳ( дә” )
дёүгҖҒеҸҳйҖҡпјҡд»Һж¶Ӯе°”е№ІеҲ°еЎ”е°”еҫ·
дёҠж»‘
еӯҰжңҜж №жҚ®ж—¶д»ЈеҸҳеҢ–иҖҢеҸҳеҢ–гҖӮеҚідҪҝеҚЎиҢЁе’ҢжӢүжүҺж–ҜиҸІе°”еҫ·еңЁ1950е№ҙд»Јж„ҸиҜҶеҲ°вҖңдёҚеә”иҜҘдёўжҺүе…¶д»–еӨ§дј—еӘ’д»Ӣж•Ҳжһңзҡ„зұ»еҲ«вҖқпјҢеҪ“ж—¶зҡ„дј ж’ӯз ”з©¶дҫқ然вҖңе°ұжҳҜе…ідәҺж•ҲжһңгҖӮе®ғжң¬жқҘеҸҜиғҪжҳҜеҲ«зҡ„ж ·еӯҗпјҢдҪҶжҳҜе®ғжІЎжңүвҖқгҖӮ1960е№ҙд»Јд»ҘеҗҺпјҢдјҙйҡҸзқҖдј ж’ӯз ”з©¶вҖңжһҜиҗҺвҖқзҡ„е®үйӯӮжӣІпјҢеӨ§еӨҡж•°зӨҫдјҡеӯҰ家们йҖүжӢ©дәҶзҰ»ејҖпјҢиҖҢеҚЎиҢЁд№ӢжүҖд»Ҙз•ҷдёӢпјҢжҳҜеӣ дёәд»–и®Өдёәдј ж’ӯз ”з©¶дҫқ然иғҪеҜ№зӨҫдјҡйҮҚиҰҒй—®йўҳдҪңеҮәеӣһеә”пјҢдёҚиҝҮеүҚжҸҗжҳҜиҰҒе…ҲеҜ№еҲҶжһҗе·Ҙе…·иҝӣиЎҢж”№йҖ гҖӮ
йЎәжҺҘвҖңдҪҝз”ЁдёҺж»Ўи¶із ”з©¶вҖқиҜ•еӣҫеӢҫиҝһзҹӯжңҹж•Ҳжһңз ”з©¶дёҺж–ҮеҢ–з ”з©¶зҡ„вҖңжҗӯжЎҘвҖқи·Ҝеҫ„пјҢеҚЎиҢЁеңЁ1980е№ҙд»ЈеҗҺжӣҙеҠ еҒҸеҗ‘иһҚе…ҘзӨҫдјҡз»“жһ„зҡ„ж–ҮеҢ–з ”з©¶ж–№жі•пјӣй»ҳйЎҝдёҺжҙӣж–ҮеЎ”е°”зҡ„еҪұе“ҚејҖе§ӢеҮёжҳҫгҖӮд»ҺгҖҠж„Ҹд№үзҡ„иҫ“еҮәгҖӢпјҲ1990е№ҙпјүдёҺгҖҠеӘ’д»ӢдәӢ件гҖӢпјҲ1992е№ҙпјүејҖе§ӢпјҢеҚЎиҢЁеҶҚж¬ЎйҖҡиҝҮвҖңжҗӯжЎҘвҖқеҜ№еҲҶжһҗе·Ҙе…·иҝӣиЎҢдәҶдёүдёӘдё»иҰҒеҸҳеҠЁпјҡ1гҖҒжҠҠзӨҫдјҡеӯҰе®һиҜҒж–№жі•дёҺж–ҮеҢ–з ”з©¶гҖҒдәәзұ»еӯҰзҗҶи®әе…ұеҗҢеә”з”ЁеҲ°еӘ’д»Ӣз ”з©¶дёӯгҖӮеҰӮгҖҠж„Ҹд№үзҡ„иҫ“еҮәгҖӢдёӯпјҢдҪҝз”ЁдёҺж»Ўи¶ізҗҶи®әеҖҹеҠ©ж–Ҝеӣҫе°”зү№В·йңҚе°”пјҲStuart Hallпјүзӯүдәәзҡ„ж–ҮеҢ–з ”з©¶и·Ҝеҫ„пјҢиөӢдәҲжү№еҲӨжҖ§и§Јз ҒдёҺдҪҝз”Ёд»ҘжӣҙеӨҡзҡ„з©әй—ҙпјӣгҖҠеӘ’д»ӢдәӢ件гҖӢдёәд»ЈиЎЁзҡ„з”өи§Ҷз ”з©¶еҲҷеҗёж”¶дәҶд»ӘејҸдәәзұ»еӯҰ家еҰӮз»ҙе…ӢеӨҡВ·зү№зәіпјҲVictor Turnerпјүзӯүзҡ„з¬ҰеҸ·еӯҰз ”з©¶ж–№жі•пјӣ2гҖҒжҠҠж•Ҳжһңз ”з©¶дёҺи·Ёж–ҮеҢ–жҜ”иҫғзӣёз»“еҗҲпјҢе°ҶжӨҚж №дәҺеҺҶеҸІзҡ„ж–ҮеҢ–жғ…еўғдҪңдёәеҸҳйҮҸеј•е…Ҙж•Ҳжһңз ”з©¶пјӣ3гҖҒйҮҮз”Ёжӣҙе№ҝйҳ”зҡ„зӨҫдјҡгҖҒжңәжһ„дёҺеҲ¶еәҰи§Ҷи§’пјҢиҝӣиҖҢиҖғиҷ‘еӘ’д»ӢеңЁж•ҙеҗҲзӨҫдјҡдёҺеј•еҸ‘зӨҫдјҡеҸҳйқ©дёӯзҡ„дҪңз”ЁгҖӮ
иҰҒиҝӣдёҖжӯҘзҗҶи§ЈиҝҷдёҖеҸҳйҖҡиҝҮзЁӢиғҢеҗҺзҡ„еҠЁеҠӣпјҢйЎ»и·іеҮәеҚЎиҢЁдј ж’ӯз»ҸйӘҢз ”з©¶зҡ„и§Ҷи§’пјҢиҝӣе…ҘзӨҫдјҡзҗҶи®әзҡ„еҸҳиҝҒеұӮйқўе®Ўи§ҶгҖӮеңЁд»Ҙз»“жһ„еҠҹиғҪдё»д№үдёәеҶ…ж ёзҡ„еӨ§дј—дј ж’ӯж•Ҳжһңз ”з©¶е…ҙиө·зҡ„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з»ҸиҝҮ塔尔科зү№В·её•жЈ®ж–ҜпјҲTalcott Parsonsпјүе’Ңй»ҳйЎҝи§ЈйҮҠзҡ„ж¶Ӯе°”е№ІпјҲГ©mile DurkheimпјүеӯҰиҜҙиө·еҲ°дәҶе…ій”®дҪңз”ЁгҖӮеҰӮзҪ—жқ°ж–ҜжүҖиҜҙпјҢеҰӮжһңжңүдёҖдёӘвҖңдё»еҜјиҢғејҸвҖқзҡ„иҜқпјҢйӮЈд№ҲиҝҷдёӘдё»еҜјиҢғејҸеә”иҜҘеҢ…жӢ¬е·Ҙдёҡйқ©е‘ҪгҖҒиө„жң¬еҜҶйӣҶжҠҖжңҜгҖҒз»ҸжөҺеҸ‘еұ•дёҺе®ҡйҮҸжөӢйҮҸпјҢ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ж•ҙеҗҲзҡ„зі»з»ҹеӯҳеңЁгҖӮдјҙйҡҸзқҖ1920е№ҙд»Јд»ҘеҗҺеҮҜжҒ©ж–ҜеҜ№дёҚзЎ®е®ҡжҖ§еңЁз»ҸжөҺз”ҹжҙ»дёӯзҡ„ејәи°ғпјҢзӨҫдјҡеӯҰвҖңйҖҗжёҗиҰҒжұӮзү№ж®Ҡзҡ„зЎ®е®ҡ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жҷ®йҒҚзҡ„жј”з»ҺвҖқгҖӮз»ҸжөҺеҚұжңәдёӯзӨҫдјҡи®ЎеҲ’еӯҰиҜҙзҡ„й«ҳж¶ЁдёҺз»“жһ„еҠҹиғҪдё»д№үеӯҰиҜҙејҖе§ӢеҪўжҲҗдёҖз§ҚеҗҲеҠӣгҖӮе…¶дёӯпјҢеё•жЈ®ж–Ҝд»Ҙзі»з»ҹеҢ–зҗҶи®әе»әз«ӢеҜ№дәҺиЎҢеҠЁзҡ„规иҢғе’ҢеҜ№дәҺзӨҫдјҡзҡ„ж•ҙеҗҲпјҢе…¶зӨҫдјҡеӯҰиҜҙдёӯвҖң秩еәҸвҖқзҡ„ж ёеҝғең°дҪҚйҖҗжёҗзЎ®з«Ӣиө·жқҘпјҢд»Ҙеӣһеә”ж¶Ӯе°”е№ІжҸҗеҮәзҡ„вҖңеӨұиҢғвҖқй—®йўҳгҖӮй»ҳйЎҝеңЁ1951е№ҙзңӢеҲ°её•жЈ®ж–ҜгҖҠзӨҫдјҡзі»з»ҹгҖӢдёҖд№Ұж—¶пјҢеҚіеҫҲе…ҙеҘӢең°е°ҶжӯӨдҪңдёәжңӘжқҘзӨҫдјҡеӯҰзҡ„зҗҶи®әжҢҮеҜјпјҢ并д»ҘдёӯеұӮзҗҶи®әеҜ№ж¶Ӯе°”е№Ізҡ„з»“жһ„дё»д№үе’Ңеё•жЈ®ж–Ҝзҡ„е®ҸеӨ§зҗҶи®әиҝӣиЎҢдҝ®жӯЈпјҢеј•з”іеҮәвҖңз»“жһ„еҪұе“ҚеҠҹиғҪпјҢеҠҹиғҪеҪұе“Қз»“жһ„вҖқгҖӮдёҺжӯӨеҗҢж—¶пјҢд»–еҜ№дәҺж¶Ӯе°”е№ІиҜ•еӣҫж №йҷӨж¶үеҸҠдёӘдәәдё»и§ӮзҠ¶жҖҒдёҺеҝҪз•ҘзӨҫдјҡеҝғзҗҶеӯҰзҡ„еҖҫеҗ‘дёҚж»ЎпјҢиҖҢеҜ№дёӘдәәжҖҒеәҰдёҺиЎҢдёәзҡ„з»ҸйӘҢз ”з©¶жҢҒжҺҘеҸ—жҖҒеәҰпјҢд»ҘдёӯеұӮзҗҶи®әз»“еҗҲе®ҸеӨ§зҗҶи®әдёҺз»ҸйӘҢз ”з©¶йқўеҗ‘гҖӮе…¶дёӯжңҖе…ёеһӢзҡ„иЎЁзҺ°е°ұжҳҜй»ҳйЎҝеҜ№вҖңеӨұиҢғвҖқпјҲanomiaпјүжҰӮеҝөзҡ„дҝ®жӯЈвҖ”вҖ”вҖңж¶Ӯе°”е№ІжҳҺзЎ®жҢҮеҮәеӨұиҢғе®һйҷ…дёҠжҳҜдёҖз§ҚзӨҫдјҡзҠ¶жҖҒпјҢиҖҢй»ҳйЎҝеҚҙе§Ӣз»ҲеңЁиЎҢеҠЁдёҺз»“жһ„д№Ӣй—ҙ游移дёҚе®ҡгҖӮвҖқиҝҷж ·пјҢй»ҳйЎҝд»Ҙе…іжіЁдёӘдәәжҖҒеәҰдёҺиЎҢдёәзҡ„з»ҸйӘҢз ”з©¶жҢҮеҜјеӨ§дј—дј ж’ӯж•Ҳжһңз ”з©¶иҝӣе…Ҙдј з»ҹзҡ„зӨҫдјҡеӯҰвҖңеӨұиҢғвҖқи®®йўҳдёӯгҖӮ
дҪҶжҳҜпјҢйҡҸзқҖ1960е№ҙд»Јд№ӢеҗҺз»“жһ„еҠҹиғҪдё»д№үж— жі•еӣ еә”зӨҫдјҡеҪўжҖҒзҡ„еҸҳеҢ–иҖҢеҸ—еҲ°жү№еҲӨпјҢзӨҫдјҡ科еӯҰдёӯзЁіе®ҡзҡ„зӨҫдјҡ秩еәҸжһ„жғід№ҹеҸ—еҲ°жҢ‘жҲҳпјҢдҪңдёәеӨ§дј—дј ж’ӯж•Ҳжһңз ”з©¶иө–д»ҘеӯҳеңЁзҡ„е“ІеӯҰеҹәзЎҖпјҢвҖңиӮҜи®ӨжҖ§вҖқзҡ„ж„ҸиұЎдёҚеӨҚеӯҳеңЁгҖӮиҮӘж¶Ӯе°”е№Іе°ұжңӘи§ЈеҶізҡ„вҖңзӨҫдјҡеҸҳиҝҒзҡ„ж №жң¬й—®йўҳвҖқпјҢеҚівҖңеңЁжңүжңәзҡ„гҖҒеҠҹиғҪеҚҸи°ғзҡ„зӨҫдјҡж•ҙдҪ“дёӯзӨҫдјҡжј”еҸҳзҡ„еҠЁеҠӣд»ҺдҪ•иҖҢжқҘпјҢд»ҘеҸҠеҺҹжңүзҡ„йӣҶдҪ“ж„ҸиҜҶеҰӮдҪ•иҪ¬еҸҳгҖҒ移зҪ®е’ҢйҮҚжһ„зҡ„й—®йўҳвҖқеңЁвҖңйҒҮеҲ°зӨҫдјҡжҖҘеү§еҸҳеҢ–гҖҒйӣҶдҪ“ж„ҸиҜҶеҢ®д№Ҹе’ҢзӨҫдјҡзәҪеёҰжқҫејӣзҡ„жғ…еҶөвҖқж—¶пјҢжҳҫзҺ°еҮәдәҶзҗҶи®әзҡ„ж №жң¬з—Үз»“гҖӮзӣёеә”зҡ„пјҢвҖңеӨ§дј—дј ж’ӯзҡ„ж•Ҳжһңз ”з©¶е°ұжӣҙе°‘е…іжіЁзӣҙжҺҘзҡ„иҜҙжңҚгҖҒи§ӮеҝөиҪ¬еҸҳе’ҢеҚіж—¶дёӘдәәиЎҢдёәпјҢиҖҢиҪ¬еҗ‘е…іжіЁзҹҘиҜҶиҺ·еҸ–гҖҒдәә们зҡ„зӨҫдјҡе®һдҪ“и§ӮеҝөпјҢд»ҘеҸҠжӣҙе№ҝзҡ„зӨҫдјҡе’Ңж–ҮеҢ–еұӮж¬Ўж•ҲжһңвҖқпјҢвҖңзӘ„ж’ӯжңүзәҝз”өи§ҶгҖҒеҲ©еҹәеёӮеңәе’ҢзҪ‘з»ңжҠҖжңҜе°ҶеҺҹжқҘзҡ„еӨ§дј—йҳ…еҗ¬дәәеҲҶеүІпјӣдёҚеҶҚжөҒиЎҢдҪҝз”ЁжңҜиҜӯвҖҳеӨ§дј—вҖҷжқҘжҢҮж¶үдәәзҫӨпјӣеӘ’д»ӢдёҺж–ҮеҢ–з ”з©¶зҡ„ж–°йўҶеҹҹе…ҙиө·пјҢ并且йҖҡеёёе°ҶиҮӘе·ұдёҺеӨ§дј—дј ж’ӯз ”з©¶зі»з»ҹеҢ–ең°еҲҶејҖвҖқгҖӮ
еҪ“зҗҶи®әеҹәзЎҖеҸ—еҲ°еЁҒиғҒж—¶пјҢеҚЎиҢЁеҸӘиғҪеҜ»жұӮе…¶д»–зҡ„жӣҝд»Јзү©гҖӮеЎ”е°”еҫ·пјҲGabriel TardeпјүиҮӘ1960е№ҙд»ЈеҗҺйҖҗжёҗеҮәзҺ°еңЁд»–зҡ„дј ж’ӯзҗҶи®әи§ҶйҮҺдёӯпјҢеҚідҪҝеЎ”е°”еҫ·дёҺж¶Ӯе°”е№Іе Әз§°зӨҫдјҡеӯҰзҗҶи®әдёҠзҡ„жӯ»ж•ҢгҖӮ继жүҝй»ҳйЎҝеҜ№ж¶Ӯе°”е№Ізҡ„иҜ„д»·пјҢеҚЎиҢЁиҝҷж ·зҗҶи§Јж¶Ӯе°”е№ІдёҺеЎ”е°”еҫ·пјҡвҖңж¶Ӯе°”е№Іи®ӨдёәзӨҫдјҡеӯҰеә”иҜҘеңЁе…¶иҮӘиә«зҡ„ж°ҙе№ідёҠи§ӮеҝөеҢ–пјҢйҒҝе…ҚйҷҚж јеҲ°дёӘдәәж°ҙе№ідёҠзҡ„еҝғзҗҶеӯҰгҖӮеЎ”е°”еҫ·еҲҷи®ӨдёәзӨҫдјҡз”ұдёӘдәәз»„жҲҗпјҢдәә们дә’еҠЁзҡ„зӨҫдјҡеҝғзҗҶеӯҰеј•еҸ‘дәҶзӨҫдјҡз»“жһ„е’ҢеҸҳиҝҒгҖӮж¶Ӯе°”е№Іе…іжіЁзәҰжқҹиЎҢдёәзҡ„ж ҮеҮҶпјҢе°ұеғҸејәеҠ иҮӘвҖҳеӨ–жқҘвҖҷд№ӢеӨ„пјӣиҖҢеЎ”е°”еҫ·е°Ҷиҝҷдәӣж ҮеҮҶзңӢдҪңжҳҜдә’еҠЁзҡ„дә§зү©вҖқгҖӮеҶҚдёҖж¬ЎпјҢеҚЎиҢЁдҪҝз”ЁдәҶвҖңжҗӯжЎҘвҖқзҡ„жҠҖе·§пјҢи®Өдёәж¶Ӯе°”е№ІдёҺеЎ”е°”еҫ·зҡ„и§ӮзӮ№е№¶йқһдёҚеҸҜи°ғе’ҢпјҢз”ҡиҮіеЎ”е°”еҫ·еңЁд»ҠеӨ©зңӢдјјд№Һд№ҹжІЎжңүиҫ“жҺүиҝҷеңәи®әжҲҳпјҡвҖңж„ҹи°ўеҫ®и§ӮзӨҫдјҡеӯҰзҗҶи®әдёҺз”өи„‘дә’иҒ”зҪ‘пјҢжӯЈиў«еҲ°еӨ„еҸ‘зҺ°зҡ„зӨҫдјҡзҪ‘з»ңзҺ°еңЁз”ҡиҮіжӣҙеҠ жҳҺжҳҫгҖӮвҖқпјҢиҝҳвҖңеҸ‘зҺ°вҖқдәҶеЎ”е°”еҫ·дҪңе“Ғдёӯйҡҗеҗ«зҡ„зӨҫдјҡзҪ‘з»ңгҖҒдәәйҷ…еҪұе“ҚгҖҒеҲӣж–°жү©ж•ЈдёҺеӨ§дј—иҲҶи®әз©әй—ҙзӯүжҖқжғіпјҢз”ҡиҮіеҶҚж¬ЎжӢҝеҮәвҖңжҢ–жҺҳвҖқеҺҶеҸІйҒ—иҝ№зҡ„жң¬дәӢпјҢејәи°ғеӨ§дј—дј ж’ӯе…Ҳй©ұжӢүжүҺж–ҜиҸІе°”еҫ·д№ҹзңӢеҲ°дәҶеЎ”е°”еҫ·зҡ„зӣёе…іжҖ§пјҢе…¶дәҢзә§дј ж’ӯжЁЎејҸжң¬е°ұдёҺеЎ”е°”еҫ·зӨҫдјҡеҝғзҗҶеӯҰз ”з©¶жңүиҜёеӨҡзӣёдјјд№ӢеӨ„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ўҒжҖқжҲҗзҡ„дәҢе©ҡеҰ»еӯҗпјҡеӯҰжңҜжҲҗе°ұдёҠжҜ”дёҚиҝҮжһ—еҫҪеӣ пјҢйӮЈе°ұзј–ж•…дәӢжҠ№й»‘еҘ№
- еҗҙз§Ӣиҫүпјҡд№…иў«еҹӢжІЎзҡ„еӯҰжңҜеӨ§е®¶ йҰ–еұҠе…ЁеӣҪеҗҙз§ӢиҫүеӯҰжңҜз ”и®ЁдјҡжҰӮиҝ°
- вҖңдәІж°‘вҖқпјҡзҺӢеӯҰиҰҒд№үжүҖеңЁ
- жҹіеҗ‘жҳҘпёұйҷҲйёҝжЈ®е…Ҳз”ҹзҡ„жё…д»ЈеӯҰжңҜеҸІз ”究
- еңЁ2020пјҢжҸӯйңІдёҚз«ҜгҖҒеҸҚжҖқвҖңе”Ҝи®әж–Үи®әвҖқпҪңе№ҙз»ҲеӯҰжңҜдәӢ件зӣҳзӮ№
- дёӯеӣҪеҪ“д»ЈжңҖе…·еӯҰжңҜд»·еҖјдёҺ收и—ҸжҠ•иө„жҪңеҠӣиүәжңҜ家вҖ”вҖ”еҲҳй•ҝе…ө
- йғ‘йҮ‘йӣЁвҖ”вҖ”дёӯеӣҪеҪ“д»ЈжңҖе…·еӯҰжңҜд»·еҖјдёҺ收и—ҸжҠ•иө„жҪңеҠӣиүәжңҜ家
- дёӯеӣҪеҪ“д»ЈжңҖе…·еӯҰжңҜд»·еҖјдёҺ收и—ҸжҠ•иө„жҪңеҠӣиүәжңҜ家вҖ”вҖ”иғЎе…ҙд№Ұ
- дёӯеӣҪеҪ“д»ЈжңҖе…·еӯҰжңҜд»·еҖјдёҺ收и—ҸжҠ•иө„жҪңеҠӣиүәжңҜ家вҖ”вҖ”з«ҘжӨҚжҳҺ
- вҖңйңңж»ЎйҫӣзәўвҖ”вҖ”еӮ…еұұзҡ„з”ҹе№ігҖҒжҖқжғідёҺеӯҰжңҜеұ•вҖқд»Ҡж—ҘејҖе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