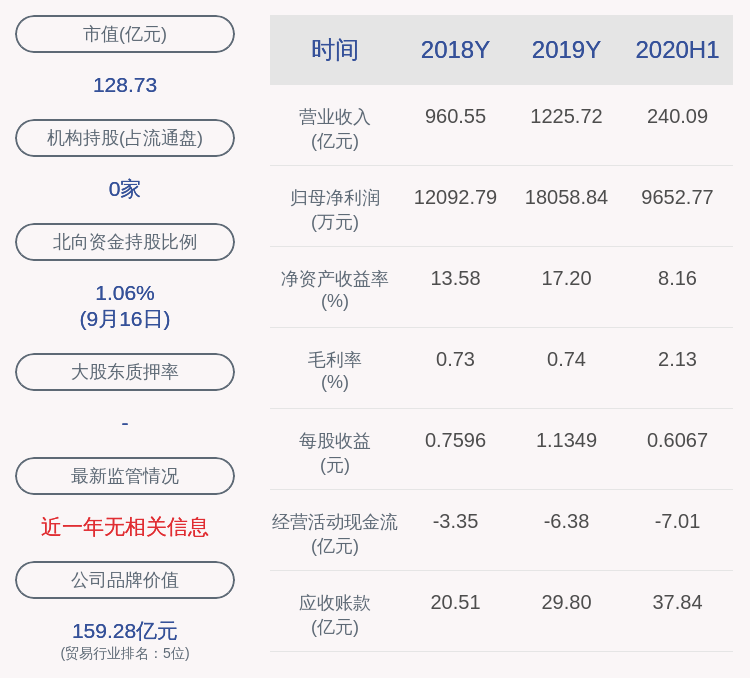实践与文本|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歌( 二 )
本文插图
在策兰于维也纳写作的文本中 , 有一组诗歌为一种全新的风格所标记并因此而脱颖而出 。 它们序列情诗 , 在这些诗中 , 诗人直接对一位女士说话 , 因此也开启了区别于他所有作品的对话体的形式 。 在这些情诗中 , 策兰也宣布放弃后象征主义的修辞和作为他早年诗歌特征的常规意象 。 相反 , 他采纳了一种对现实中锚定的情景和感情的召唤 。 长期以来 , 批评家们一直想知道这些诗歌是否与实际的经验一致或它们是否是一种新的诗歌语言中 , 欧洲抒情诗的传统主题的复兴 。 直到1997年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克里斯蒂娜?克歇尔(Christine Koschel)才发现 , 在德国马尔巴赫策兰档案中 , 策兰在1952年给他的朋友 , 奥地利诗人英博格?巴赫曼的《罂粟与记忆》的副本;(其中的)二十一首诗(也即这些情诗)旁都有“f. D”(意为“为你(而作)”)的手写献词 。 因此关于这些诗歌真实程度以及它们的题献对象的身份的谜也就解开了 。 那时人们已经知道保罗?策兰在抵达维也纳不久后就遇见了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英博格?巴赫曼 , 他们有过一段充满激情的事情 。 当策兰离开维也纳奔赴巴黎的时候 , 他们之间的联系并未中断 , 而巴赫曼甚至还在1950年的时候到巴黎探望策兰 。 这两位诗人一直持续通信 , 直到1961年 。 甚至在这之后 , 同时已经成为用德语写作的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的巴赫曼 , 依然不断地在她的虚构和理论文本中提到保罗?策兰的形象以及她对他的迷恋 。
只有在发现《罂粟与记忆》的情诗中英博格?巴赫曼编码式的在场的情况下 , 这部作品的支配性的主题才变得清楚:那就是 , 记忆与遗忘的对立的两极之间的张力 。 当然 , 这种二元性已经出现在该书的标题之中 , 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 , 它谈论的是一个传统的文学主题 , 那像俄尔甫斯一样必须先下到死者的国度才能把过去从它埋葬其中的阴影中提取的诗人的主题 。 而且 , 语言的极度的音乐性 , 意象的丰富 , 以及诗学话语的多样元素的和谐整合——超越了刻意的不和谐以及精心计算的语调的中断——使《罂粟与记忆》的诗戴上了一种旋律的魅力——这种魅力长期以来一直藏在诗中表达的悲剧和心伤的面具之后 。 交互贯穿整部诗集的两个灵感——一种记忆、苦难和悲伤的诗学 , 以及一种爱、缓和和希望的诗学——试图和解 , 但最终 , 它们之间的分歧看起来是不可能桥接的 。 最初的情诗源于维也纳时期 , 谈论的是一种内部的解放和对新生活的许诺 , 正如《法国记忆》(“Erinnerung an Frankreich”; “Memory of France”)一诗结尾诉说的那样——“我们死去却能够呼吸”(“Wir waren tot und konnten atmen[We were dead and were able to breathe]”)——而诗集中的最后一首诗 , 《数杏仁》(“Z?hle die Mandeln”; “Count the Almonds”) , 则诗歌主体对他以之为言说对象的女人的去魅了的诉求作结:“把我变苦 。 /把我数进杏仁 。 ”(“Mach mich bitter. / Z?hle mich zu den Mandeln[Make me bitter. / Count me among the almonds]”) 。
本文插图
这种快乐与悲伤 , 忘却与记忆的矛盾情感无疑在保罗?策兰和英博格?巴赫曼的爱情中结晶:“我们相爱如罂粟与记忆”(“Wir lieben einander wie Mohn und Ged?chtnis[We love each other like poppy and recollection]”) , 宣告了《花冠》(“Corona”)一诗的核心乐章 。 在爱情的感觉之外 , 这位奇迹般逃过灭绝的犹太诗人与这位自幼在纳粹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国度成长的奥地利女诗人之间的对话只会艰难、紧张而充满了误解 。 然而这种模棱两可本身也反映了保罗?策兰的内部分裂 , 因为他一直为重新学会如何生活的欲望和在他身上依然鲜活的 , 他经历过的个人和集体的灾难留下的印记所撕裂 。 实际上 , 摆在《罂粟与记忆》核心位置的问题在这两位诗人的关系中实现: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诗歌还是否可能?这个由忒奥多尔?阿多诺在《罂粟与记忆》三年后出版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 , 对策兰来说只有一个答案:对他来说 , 除继续写作外不存在其他的解决方案 。 在他的书出版六年之后 , 在他的“不来梅奖演说(Bremen Prize Speech)”中 , 策兰解释了为什么德语 , 尽管根本上为纳粹体制对它的使用所腐蚀 , 依然是他自我表达的媒介:
推荐阅读
- 秀全街|干货满满!秀全街开展摄影知识讲座 | 新时代文明实践
- 孙鹏程|豪洋中学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2020级新生军训汇演暨总结表彰大会
- 七夕|文明实践丨我区举行七夕相亲活动 为青年男女搭桥寻爱
- 知名圈|不实践就想成功 你觉得可能吗
- 满龙江|【志愿服务】铁锋区南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最美七夕 爱满龙江”主题文艺志愿服务活动
- 幸福杨舍|城东暑期大巴车 | 下一站,新时代文明实践!
- 闲暇|新时代文明实践在行动 | 《读书时间》空闲时间,决定你的人生高度
- 手工|新时代文明实践 | 麻涌举办纯银绕线首饰手工培训活动
- 微观鱼台|[新时代文明实践]“浪漫七夕 美在园区”鱼台经济开发区举办青年联谊活动
- 江苏省盐城中学|盐城市高级实验中学暑期社会实践系列活动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