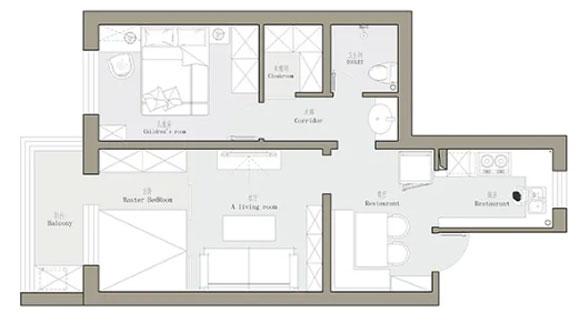梁小曼|梁小曼:正像黄昏之多姿,鸟鸣之声茂,诗让我们在现实中贴地飞行 | 此刻夜读( 二 )
本文插图
这个时期的写作 , 大多是出于一种“为诗而诗”的动机 。 多年视觉与文字训练的缘故 , 我的诗歌写作在视觉和语感方面一开始具有优势 , 例如写于2011年的《阿斯旺》 , 它的视觉与推进的方式很像电影里的摄像机之眼 。
此外 , 我也极力去探索各种风格与形式 , 有一首诗《结核》 , 就在结构上有所发明:它在第一节结束后做出一个迷宫的指示:(转第三节)——旨在破坏 , 同时重建诗歌本来自然的断行与分节 , 强行引入一个博尔赫斯的环形迷宫 。 它不仅像公牛闯入瓷器店一样闯入诗歌的内部时间 , 也像一列脱轨火车 , 在空间上旁逸斜出 。 这是我早期诗歌创作一例 , 以我当下眼光去看 , 诗歌并不成功 , 因此我没有将它放入书中 。
很快 , 我就意识到诗歌必须有所承载 , 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创造或者诗性的生发 。 我从诗歌的“轻”中感受到它的“重” 。
本文插图
这些年 , 个人际遇、情感起伏等因素 , 让我的写作不得不面对一个写作者的诚实问题——写作无法回避现实 , 无法回避自身 , 更无法回避写作本身 。 我意识到要写出真实的、诚实的诗歌 , 必须舍身 。
我并不是信徒 , 但在那几年 , 我常读《圣经》 , 企图获得一种精神力量 , 我也渴求从写作中得到这种力量 , 通过写作 , 感受到自己与某种更高智慧的联系 。 我开始对早期的写作产生不满 , 陷入了一个沉默期——能足以表达个人的声音尚未出现 , 我转向了诗歌的翻译 。
翻译诗歌时 , 需要去揣摩、想象诗人的声音 , 尽量将这种声音的形象配之以相应的汉语 , 为诗歌落实这个声音形象 , 形成诗人的语调和风格 。 我在翻译时比较重视这点 , 也许 , 正是在这样一种密集的声音布置中 , 我个人的声音 , 不知不觉中来到 。
一个诗人 , 当其决定要呈现自身时 , 必然是以一种声音出现 。 这个声音 , 仅属于他个人 。 如同在林中诸多的鸟鸣中辨认出一只鸟 , 读者也在诸多的声音中辨认出一个诗人 。
本文插图
我的声音最先预兆着变化的是2017年的第一首诗《较场尾》 , 抒情与意象的结合被暂时搁置 , 在这首诗里 , 出现了我最早的叙事探索 。 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此要写叙事诗 , 传统诗人往往诸体皆擅 , 我也常想起韦伯被问及专业领域时的发怒:“我又不是驴子 , 哪有固定的领域 。 ”诗人写诗不是占山为王 , 不必非竖什么旗杆不可 , 何妨“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阿多尼斯) , 这座花园 , “从此窗望出去/你知道 , 应有尽有”(陆忆敏的《美国妇女杂志》) 。
于是 , 从一个“乏味无聊”的大海(《较场尾》)开始 , 我以回归的姿态 , 开始向内寻求自身资源 , 在广袤的大地上“母语不断返回声音/如同葡萄籽 , 总落入泥土”(《葡萄》) 。 往往借助于一种必须如此否则别无他法的宿命感去写 , 仿佛接受了神谕——“叙事的乌有乡/被无间奏的鸟语浸洗”(《葡萄》)——而我的鸟 , 一直有着神秘使命 , “你寻觅着一种神秘黑鸟的声音 , 它/经常落在你散步的小径”(《虚拟世界》) , 它是诗人的自我 , 也是诗人的预言者 , 它既是单数 , 也是复数 。
通过书写 , 诗人将其命运与他者融合 , 既写那个特定的鸟儿 , 也写那个被复数的鸟儿——“这趟飞行 , 是所有飞行的其中一次/这只鸟儿 , 是所有鸟儿的其中一只”(《旅行》) 。 鸟儿带领着飞行 , 也是诗歌带领着飞行 。 然而 , 诗歌的飞行并不轻盈 , 要抵达个人的语言宿命 , 不能惧怕粉身碎骨 , 或像精卫徒劳无功——“山雨已经呼之欲出/却在犹豫 , 应否向大海走去/那里一无所有/只有灰白色的时钟 , 它滴答/滴答——曾将你吸进去/那乌有之乡 , 布满血腥海藻”(《春分》) 。
推荐阅读
- 云大|昆明的黄昏和云大宾馆的咖啡吧
- 每日诗词|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
- |冬日黄昏... 1
- 女人的励志说|夏日黄昏(随笔)
- 读睡|诗人戈麦现代诗歌精选七首◎如果种子不死◎没有人看见草生长◎黑夜我在罗德角,静候一个人◎献给黄昏的星◎死后看不见阳光的人◎彗星◎眺望时
- 诗歌|一直向西走,越过黄昏线,越过日界线,回到初始见你的那一天
- 不完美妈妈|65岁外公等了她17年,因这个原因最终分手:异地黄昏恋经不起等待
- 白带异常|令人唏嘘!53岁大妈坠入爱河,上演“黄昏恋”,不料却查出宫颈癌
- 博美神奇|黄昏的黎里,邂逅只是遐想,月上柳枝,却被迷离的小酒挽留
- 品诗|第五届“芙蓉杯”全国文学大赛入围诗歌作品—《???印象的黄昏(外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