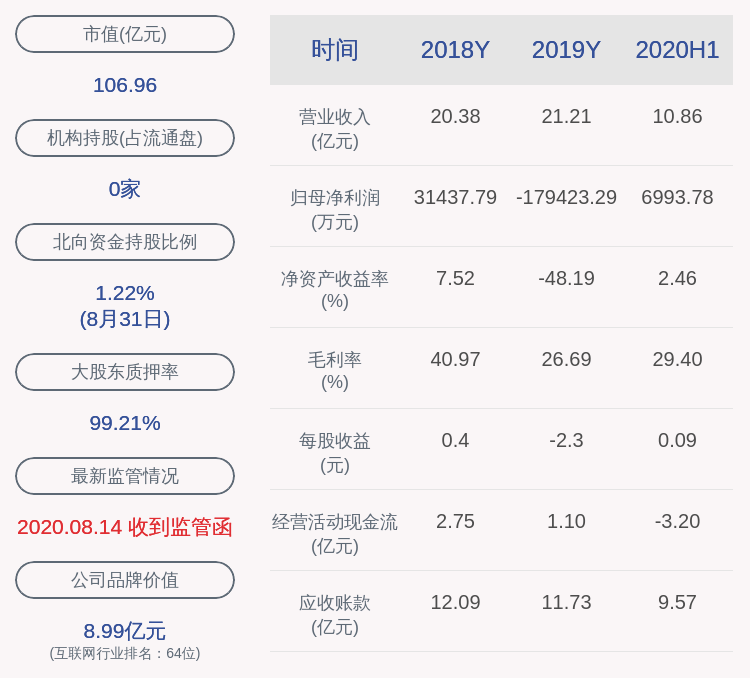我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之死之
1.
一些未完成的文字,它们慢慢地展开,将会变得十分漫长 。
我站在夜晚的操场上哭 。这没有失去窥探的地方,让人觉得安全 。储说你为什么不跑步?把你身体里的水都排出来,便无泪可流 。可是,哭,只是我的习惯 。
花朵盛开在田野,大片大片的 。我没有看见,可是有幻象 。它们在春天的风里轻轻摇曳,一波又一波地缓慢起伏 。但我不是太喜欢 。渴望见到向日葵,那些表情凶残的植物,在夏日毒辣的日光之下纹丝不动,一棵一棵,犹如锋芒,尖锐,没有感情 。它们的生长直接而剧烈,凶猛而迅疾,以强者的姿势暴戾长大,最终必将猛烈地死去 。但这也是习惯 。
习惯是一种可怕的重复 。比如流泪 。比如去爱 。
列车加速,轰隆隆地疾驶 。为达目的地而飞奔 。很多东西从视野里一掠而过,没有清晰的印象 。夜半停靠小站,灯光昏黄或惨白 。有人在半夜下车,走进黑暗中 。走入未知 。很多时候站台给夜晚的旅人带来慰藉,尤其当它们流落荒野之时,尤其成为慰藉 。
格外喜欢火车,或许因为它有分明的轨迹,紧贴大地,有具体的安全感 。
但有一天,祁去工厂接他年轻的妻子时,穿过这铁的路轨,便死了 。列车呼啸而来,不可遏止 。犹如台风呼啸而过,只是很快的事情,什么东西便瞬间消失了 。暮色里有水的凉意 。祁11岁的女儿站在路轨之上,仿佛一切遥远,与己无关 。
我是祁的女儿 。喜欢轨道、列车、站台 。还有旅行 。旅行,只要可以,便选择火车作为去往以及回归的工具 。有些东西尽管给人带来深刻的疼痛,但仍不会影响它在你心底的感觉 。譬如依赖,还有偏爱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不可改变或者迁移 。
2005年的冬天 。南方岛屿温热潮湿 。海的咸味肆无忌惮地流动,不顾掠过之处一些尚未久远的伤口再次产生刀割般的痛感 。那是清醒的记忆!
对海的偏爱有如对火车,但它没有带来安全感 。只是喜欢看那些咆哮而来的浪头,带来巨大的惊悸 。继而是劫后余生的幸运 。幸福的幻觉由此产生,得到满足 。一种周而复始的自我或是安慰!
幼年时祁偶尔带我来海边 。我喜欢踩着浪潮奔跑,一路尖叫,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安静地蹲在海滩上堆沙子 。因为确定我一转身它们便会被海水冲走,不留痕迹 。最终不会存在,便无需一开始就费力去做,以免再回头时望见一片空茫,觉得伤心 。祁说的 。我不懂,但我知道我不希望自己亲手堆砌的城堡消失,内心明了那种失落 。所以我只在海边飞快地奔跑 。那也是我喜欢的事情,日后成为习惯 。
后来祁死了 。
我记得他并不宽阔的额头,正中偏左有一颗小小的痣,鼓出来,丰满的圆 。小而有神的眼睛,深邃至极 。不知什么时候,那颗很显眼的圆痣消失了 。没有痕迹 。不知什么时候的事情,因我总是长久才见他一面 。他只是个陌生男人,在我的生活中时常出现,不与我说话 。或许没人愿意和孩子交谈 。他与我有血缘关系,当然,他也拿出一部分钱抚养我,让我活着、读书 。
但他并不喜爱我 。或许是因为我的孱弱、孤僻、暴戾、歇斯底里 。于是我时常流离于外,过寄居的生活 。我们都不喜欢见到对方 。感情冰冷 。寄居并不是什么凄惨的事情,如果你已经习惯的话 。但会常偷偷地流泪,在一张又一张陌生的不断变换的床上、被褥里,或是房间的角落里,偷偷地哭 。长久以后,哭,成为一种习惯 。
由于幼年时辗转生活,长大后迁徙竟成为一种习惯,但一定携带有自己气味的公仔,抱着,才能在不同的没有自己气味的床上安心睡眠 。
因为没有感受过来自一个父亲的爱、慰藉,及其它,心里也便无从想象 。既是无从想象,也便无从期待 。但知道自己确实有着一个父亲,他是祁 。心里便不觉得缺失 。这大概就是无所求的状态 。不希望,也不失望 。
渐渐成为一个淡漠的孩子,放任而倔强 。在某一个夜晚被刀片划过手臂,暗红的血液顺着翻开的白色皮肤缝隙流出来,细长绵延,似是为了追寻某种根源而出 。只让医生随便用结晶粉敷衍 。每次换需将那些白色的大颗固体从伤口中挖出,再填补,再挖……我是个痛感并不强烈的孩子,三四岁时已不需大人抱着,自己坐在高高的凳子上,父母不在身边,也便强忍着过去了 。后来对痛,日渐麻木 。伤口很久后愈合,留下难看的疤 。我时常抚摸它 。有人问起便只是笑 。它已经不会消失了 。变成一个印记,执拗地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