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插图
《一日谈》EP5
“
恍惚间你有点不知道是美学在先,还是自己的情绪在先。这些作品是先关注作品的美学,还是先关注受众的情绪。
如果是先关注受众的情绪,那么和微信公众号的爆文似乎也没有太大不同,它们不那么直接,只是创作手法更娴熟罢了。
”
文 | 李厚辰
今天想谈谈一个有点滥的词汇——“少年感”。
还记得第一次看《局部》,已经是2015年的事情,第一集《千里江山图》,陈丹青老师未有任何书画技艺的精深分析和理论的构架,只是对王希孟的年轻气盛静静讲述着。
那期的结尾,他说:
“在《千里江山图》中,我分明看见一位美少年,他不可能老,他必须十八岁。再小几岁,再老几岁,不会有《千里江山图》。王希孟好像知道,过几年,他就死了。”
这几句话令人动容且震撼,也一下子抓住了一种时代精神,我们在一个催熟的时代。每次想到催熟,我总是想到尼采对叔本华的一句表述。
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会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
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如此说的话——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罢了。
早熟而幼稚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感受的问题。
01.
催熟时代的两种生活
这是个快速催熟的时代,不必论述太多,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容易年纪轻轻而对世界没有疑惑,全然了解真相。
世界是物质还是精神的,物质。人的意识来自于哪里?神经系统。人与人之间的秩序由什么决定,资源和竞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由他自己还是他人决定?他人。人能够影响和改变他人吗?不能。
这些都是好终极的问题,但大家都懂。
在采访陈丹青老师的前一天,恰逢木心美术馆五周年的节日,从一个读者交流会开始,很多木心读者从全国各地汇聚乌镇。在交流会上,听到最多的词汇是“避难所”与“乌托邦”。
那当然是令很多人开心的一天,但我也得说,那是十分苦涩的一天,很多人哭了,那一半是喜极而泣,一半是生活的苦涩终于获得了一个出口。或多或少的,那是一场群体心理的互助。
诸位也许会想,这有什么不好?生活中有这么一方净土,能够在其中休憩一下,这不是令人羡慕的事吗?为什么要残忍地连这样一块净土也要打扰?
是啊,如果这真是一种可期的平衡生活,在现实中谋生,在文学艺术中休憩,是否也不失为一种现代生活的策略。而且,这岂不是一种理想与现实两全的策略。
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一日谈》这档节目一直以来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张力。
至少我们发现了是什么在催熟我们的精神,“现实不再有别的可能”,“艺术品味可以让我安放自我”。若对这两个结论没有疑惑,我想一个人就早早成熟了吧。
但麻烦之处在于,这样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并不如它看上去那样合理。
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卡伦·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明确指出了一种矛盾的现代生活本身的危险,这本书的第六章被称为“理想化意象”,个体在自己内部构造出一些浪漫的“潜力”,并将其当作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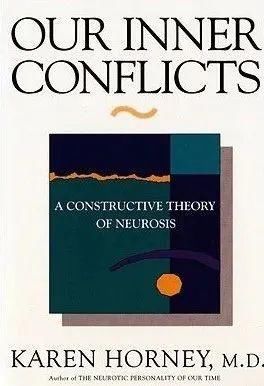
文章插图
《我们内心的冲突》
在霍妮的分析中,这个意象在给予个体巨大安慰时,也不可避免地引起痛苦。因为这种潜力越被当作现实,也就是安放在艺术和品味中的自我越被当作现实,就会让真正的现实越来越变得难以下咽。
因为一个人最终会明白,不管在现实和艺术的幻象中,没有哪一种尝试是可以令人满意的,这都是注定失败的尝试。
过一种充满矛盾的生活,从来都是现代神经症的一种主要来源。
推荐阅读
- 「张忆滨」|丹青追梦 水墨本色-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个人云展览
- 「陈锋」|丹青追梦 水墨本色-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个人云展览
- 翰墨争晖 丹青焕彩 兰州市博物馆“高台县博物馆馆藏明清书画精品交流展”开展
- 云烟浩莽绘丹青 笔墨立空写奇观 ——记著名书画家王诗皓
- 陈丹青:虽然没有读过莫言的书,但我知道他获诺贝尔奖与作品无关
- 古代言情文丹青千卷描眉眼,比翼翩翩何日飞!
- 陈丹青:民国是美好的,是一个童话般的王国
- 陈丹青评价于丹是个“神父”,于丹和易中天真是二三流学者吗
- 壁上丹青斑斓,这样的世相百态!这样的精神世界!
- 「你好,警察节」书画献礼警察节 笔墨丹青写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