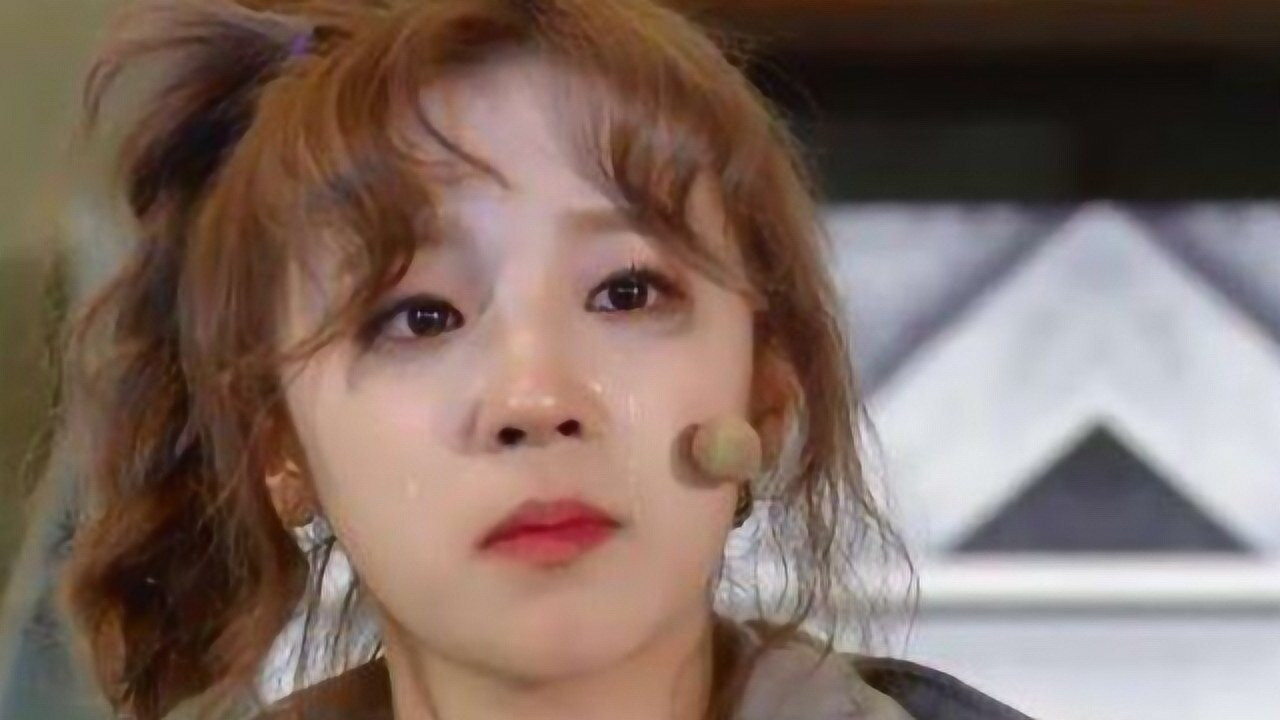|?从巴塞罗那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市政自治主义时刻
?左翼运动正越来越多地寻求在地方层级凝聚力量 。但现在的问题是 , 如何利用市政自治的成果 , 在更大的规模上改造这一体系 。思想市场栏目在2019年的“罗贾瓦危机”系列 , 通过罗贾瓦的社区实践 , 介绍了“自由意志市政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的思潮 , 它重新定义了一种不同于“民族国家”和血缘所界定的公民身份 , 和新的参与式民主框架 。“市政自治主义”这一思潮早有其?源远的历史和失败的教训 , ?却?从未停息过 。本文介绍了当下的两个案例——巴塞罗那市和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市(1960年代美国黑权运动的产物——新非洲共和国[RNA]设立的首府所在地) , 二者都遭受民族主义的外力所困扰 , 却都诞生了各自的崭新政治主体 。这些故事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故事暗示着 , 在城市这一尺度上 , 彻底且急剧的变革的特定轨迹与生俱来 。它们显示了重组社会再生产和日常生活 , 重新设想想象的共同体和新形式民主可能性的潜力 。
马克思在1871年问及巴黎公社:“公社 , 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 , 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这个时代 , 被城市政治逗弄的不仅是资产阶级 , 左翼运动也在越来越多地将地方视为凝聚力量的场所 。我们正活在市政自治主义时刻(municipalist moment) 。
在美国各地 , 城市已经变成了充满进步可能性的岛屿 。“庇护所城市”运动(sanctuary cities movement)迫使市政府为移民和难民提供援助和庇护 。气候运动已赢得市政承诺 , 坚持减排目标和通过绿色新政立法(Green New Deal ) 。在多数情况下 , 劳工运动“为15美元而战”(Fightfor $15)在推动州立法之前 , 成功在市政一级实现了最低工资的增长并促成了对快餐员工的其他新保障措施 。同时 , 工会正在把城市变为为平台工人(设计的)新劳动法框架的实验室 。
这些改革措施由大批选举层面的成功所支撑:西雅图的卡沙马·索瓦特(Kshama Sawant) , 在杰克逊的乔科维·卢蒙巴(Chokwe Lumumba) , 芝加哥的许多社会主义者 , 在费城的拉里·克拉斯纳(Larry Krasner) , 里士满的进步联盟最近每个选举周期都把更多的左派送进了地方政府的办公室 。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美国 。在许多威权主义右翼势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 , 左翼把城市作为巩固、试验和壮大的场所 。去年 , 土耳其东部一个名为通切利(Tunceli)的城镇选举了一位共产党人当选市长 , 他恢复了该镇的库尔德名称 , 并着手创建一个合作社式食品系统 。在智利的雷科莱塔(Recoleta) , 另一位共产党人市长公开违反了智利新自由主义宪法中关于政府与私营部门竞争的禁令 , 他开设了一个合作社式药房网络、免费的成人教育系统、免费的牙科诊所、课后项目、社区保健中心和一家书店 。
城市作为一个政治场所已经在政治光谱上被理论化了 。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在2013的《如果市长统治世界》(If Mayors govern the World)一书中指出 , 民族国家对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而言太小 , 而对于民主来说又太大 。相反 , 巴伯设想 , 由CEO式的市长管理的城市 , 是自由派技术官僚(liberal technocracy)的理想规模 。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在1968年提出了“进入城市权利”(rightto the city) , 这个想法被地理学家大卫·哈维进一步发展;他们把城市的组织看作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斗争领域 。在20世纪80年代 , 墨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提出了“自由意志市政自治主义”(libertarianmunicipalism)的想法 , 呼吁直接民主管理的生态可持续的城市 , 通过合作社的方式为其需求而生产 。
市政自治主义的转向 , 并没有明显地遵循这些理论;更多时候 , 它展示的是一种应急战略(emergent strategy)【这个术语由商业理论家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创造 , 阿德里安娜·马雷·布朗(adrienne maree brown)在其2017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将其用于社会运动语境中】 , 而非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 。我们没想走到这步 , 但我们现在就在这里 。那么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我们能找到一条从市政自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