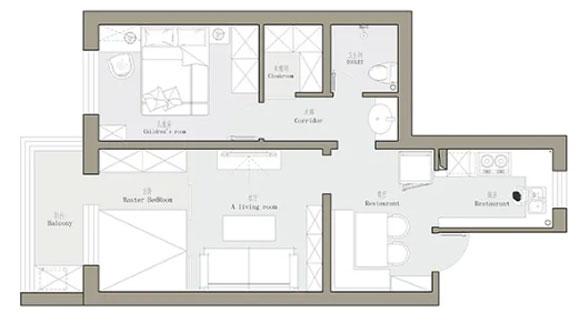дәәй—ҙ|з§ҰеІӯи„ҡдёӢзҡ„е°Ҹй•Үпјҡдё–дәӢжӣҙиҝӯпјҢжӮІе–ңзҡҶеҜ»еёё( дәҢ )

иҝҳиҮӘиЎҢиҪҰзҡ„ж—¶еҖҷе®үе®үдёҚеңЁе®¶ пјҢ жҲ‘жҠҠиҮӘиЎҢиҪҰеҺҹж ·жҺЁеӣһжҲҝдёңзҡ„йёҪжЈҡйҮҢ гҖӮ жҲҝдёңиҜҙе®үе®үжү“е°Ҹйә»е°ҶеҺ»дәҶ пјҢ еңәеӯҗе°ұеңЁж–ҮжӯҰиЎ—зҡ„зүҢеқҠдёӢйқў пјҢ жӯЈжҳҜжҲ‘еҺ»жҗӯе…¬дәӨиҪҰиҰҒи·ҜиҝҮзҡ„ең°ж®ө гҖӮеңЁзүҢеқҠдёӢйқў пјҢ 并没жңүзңӢеҲ°е®үе®үзҡ„йә»е°Ҷж‘Ҡе„ҝ гҖӮ зү§д№Ӣжү“дәҶдёӘз”өиҜқ пјҢ д»–еҢҶеҢҶең°иө°иҝҮжқҘ пјҢ еҚҙдёҚиӮҜи·ҹжҲ‘们еҺ»еҗғйҘӯ пјҢ иҜҙиҮӘе·ұзҡ„жҷҡйҘӯеҫҲз®ҖеҚ• пјҢ е°ұжҳҜдёҖдјҡеӣһеҺ»йҡҸдҫҝдёӢдёӘйқўжқЎ гҖӮ д»–еӨ§дҪ“жҳҜиҮӘе·ұеҒҡдёҖйЎҝ пјҢ дёӯеҚҲеңЁеӨ–иҫ№еҗғдёҖйЎҝиЎҘжІ№ж°ҙ пјҢ и·ҹжҲ‘еңЁеҢ—дә¬зҡ„д№ жғҜдёҖж · гҖӮж–°еҶ з–«жғ…ж¶ҲйҖҖд№ӢеҗҺ пјҢ жҲ‘еҶҚж¬ЎеҺ»еҲ°еёғй•Ү пјҢ жҸҗиө·е®үе®ү пјҢ еҝғжғід»–зҡ„йј“жүӢз”ҹж¶ҜдёҚзҹҘиғҪеҗҰжҢҒз»ӯ гҖӮ иҝҮеҺ»дёҖзңӢ пјҢ е®үе®үжӯЈеңЁз»ҷиҮӘе·ұиЎҘдёҖ件дёӯеұұиЈ…еҸЈиўӢзҡ„зәҝзјқ пјҢ еӨ§зәҰжҳҜжҳҘеӨ©иҰҒдёҠиә«зҡ„ гҖӮ д»–жҲҙзқҖзҹіеӨҙзңјй•ң пјҢ иә«ж—Ғж”ҫзқҖй’ҲзәҝеҢ… пјҢ зңӢдёҠеҺ»еғҸдёҖдёӘиҖҒдәә пјҢ еҸ‘йҷ…дёӢйқўйӮЈдёҖеңҲзҢ©зәўдјјд№Һд№ҹиӨӘдәҶиүІ пјҢ жҳҫеҫ—жё©е’ҢдәҶеҫҲеӨҡ пјҢ жІЎжңүжҸҗиө·зҲ¶дәІж—¶йӮЈз§Қе…ғж°”дәҶ гҖӮжҸҗеҲ°з”ҹи®Ў пјҢ е®үе®үиҜҙиҝҳиғҪз»ҙжҢҒ пјҢ з–«жғ…жңҹй—ҙжІЎдәәеҠһе–ңдәӢдәҶ пјҢ дҪҶзҷҪдәӢ并жңӘеҸ–ж¶Ҳ пјҢ д№җйҳҹйҮҢжңүдёӨдёӘдәәжҖ•дј жҹ“йҖҖеҮәдәҶ пјҢ д»–дёҚз®ЎйӮЈд№ҲеӨҡ пјҢ еҺ»е“Әе„ҝжҲҙдёӘеҸЈзҪ©е°ұеҘҪ гҖӮ ж•Ій”Јзҡ„иө°дәҶ пјҢ д»–дёҖдәәе№ІдәҶдёүдәәзҡ„жҙ»е„ҝ пјҢ д№ҹиғҪеӨҡжӢҝзӮ№е„ҝ гҖӮйә»е°ҶйҰҶдёҚиғҪејҖдёҡ пјҢ еӨҡж•°ж—¶еҖҷд»–е‘ҶеңЁе®¶йҮҢ пјҢ жӯЈеҘҪд№ҹиғҪеҒҡеҒҡйҘӯ гҖӮ зңӢд»–зҡ„жЎҲеӯҗдёҠ пјҢ жЎҲжқҝе’Ңж“Җйқўж§ҢйғҪеёҰзқҖзҷҪзІүзҡ„з—•иҝ№ пјҢ жҳҫ然жҳҜж–°иҝ‘еҒҡиҝҮйҘӯ пјҢ е®үе®үиҜҙд»–д»Җд№ҲйқўйғҪдјҡеҒҡ гҖӮ д»–дјҡиҮӘе·ұжҠ»йқўеҒҡйҘӯиҝҷдёҖдәӢе®һ пјҢ и®©дәәеӨҡе°‘жңүдәӣе®үеҝғ пјҢ дјјд№ҺжңүдәҶе°Ҷж—ҘеӯҗжӢүй•ҝзҡ„еҸҜиғҪжҖ§ пјҢ дёҚеҶҚжҳҜеҸЈеӨҙиҜҙзҡ„йӮЈж ·зҙ§иҝ«дәҶ гҖӮе’Ңе°ҡе’Ңе°ҡдҪҸеңЁеёӮеңәй—ЁйқўжҲҝзҡ„жҘјдёҠ пјҢ д»–е…¶е®һ并дёҚжҳҜе’Ңе°ҡ гҖӮ第дёҖж¬ЎеҺ»еҜ»и®ҝ пјҢ жІЎжңүйҒҮи§Ғд»– пјҢ еӨ§зәҰжҳҜеҮәеҺ»з»ҷдәә家е®үиЈ…йҳІзӣ—й—ЁдәҶ гҖӮ зү§д№ӢиҜҙ пјҢ иҝҷйЎ№иҒҢдёҡз»ҷе’Ңе°ҡеёҰжқҘдәҶжҹҗз§ҚдҫҝеҲ©пјҡиЈ…й—Ёзҡ„家еәӯдёҖиҲ¬з”·дәәеңЁеӨ–жү“е·Ҙ пјҢ еҘідәәй—ЁжҲ·йҳІе«ҢдёҚдёҘ пјҢ иЈ…йҳІзӣ—й—ЁйңҖиҰҒеҘідәәжҗӯжүӢ пјҢ з•ҷдёӢдәҶиҒ”зі»ж–№ејҸ пјҢ дёҖжқҘдәҢеҺ»еҫҖеҫҖе°ұзҷ»е Ӯе…Ҙе®ӨдәҶ гҖӮиҝҷзңӢиө·жқҘжҳҜзҰҸеҲ© пјҢ е…¶е®һд№ҹеҮәдәҺж— еҘҲпјҡе’Ңе°ҡзҡ„иҖҒе©Ҷи·ҹдәәи·‘дәҶ гҖӮ иҷҪ然зҺ°еңЁдәәеҸҲеӣһжқҘдәҶ пјҢ дҪҶе…ізі»еӣһдёҚеҲ°д»ҺеүҚ гҖӮ иө·еӣ жҳҜиҖҒе©ҶеЁҳ家зҡ„дёҖжЎ©иҙўдә§е®ҳеҸё пјҢ иҜ·дәҶдёҖеҗҚеҫӢеёҲ пјҢ е®ҳеҸёжІЎжү“иөў пјҢ еҫӢеёҲеҚҙжӢҗеёҰдәҶе’Ңе°ҡзҡ„иҖҒе©Ҷ гҖӮиҖҒе©ҶеёҰзқҖе„ҝеҘізҰ»ејҖеёғй•Ү пјҢ и·ҹеҫӢеёҲеҗҢеұ…дәҶдёӨе№ҙ пјҢ еҫӢеёҲе§Ӣд№ұз»Ҳејғ пјҢ иҖҒе©ҶеҸӘеҘҪеӣһжқҘ гҖӮ еӣһжқҘд№ӢеҗҺдҪҸеңЁй—ЁйқўжҲҝзҡ„дёҖеұӮ пјҢ дёӨдәәдёҚеҶҚжңүеӨ«еҰ»д№Ӣе®һ пјҢ дҪҶиҖҒе©Ҷиҝҳз»ҷе’Ңе°ҡеҒҡйҘӯ пјҢ е’Ңе°ҡз»ҷж— дёҡзҡ„иҖҒе©ҶжӢҝдёҖдәӣдҫӣе…» гҖӮ иҝҷж®өжӣІжҠҳдҪҝе’Ңе°ҡеңЁеёғй•ҮеҮәдәҶеҗҚ пјҢ д№ҹдҪҝеҫ—д»–жҖ§жғ…еӨ§еҸҳ пјҢ з©ҝдёҠдәҶиҝ‘д№ҺеҮә家дәәзҡ„жңҚиЈ… пјҢ жүӢи…•дёҠз»•зқҖдҪӣзҸ пјҢ йҖўдәәж„ҹеҸ№дё–дәӢзҡҶз©ә гҖӮ вҖңе’Ңе°ҡвҖқзҡ„з§°е‘је°ұжҳҜиҝҷд№ҲжқҘзҡ„ гҖӮе’Ңе°ҡзҡ„иҖҒе©ҶеңЁе®¶ гҖӮ 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зӣёиІҢе№іе№ізҡ„дёӯе№ҙеҰҮеҘі пјҢ е®һеңЁзңӢдёҚеҮәеҘ№иә«дёҠжј”еҮәиҝҮйӮЈж ·зҡ„жғ…иҠӮ гҖӮ жҸҗеҲ°е’Ңе°ҡ пјҢ дјјд№Һ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дёҚзӣёе№Ізҡ„жҲҝе®ў гҖӮ жҲ‘们иө°еҲ°еҗҺйқўйҷўеӯҗйҮҢзңӢдәҶзңӢ пјҢ дәҢжҘјзҡ„й—Ёй—ӯзқҖ пјҢ йҷўең°жңүеҮ зӣҶе°ҸиҠұе’ҢдёҖдёӘж°ҙжұ пјҢ дёҖжқЎе’Ңе°ҡе…»зҡ„й»‘зӢ—жӢҙеңЁйӮЈйҮҢ гҖӮ зӢ—жһҒе…¶з»ҶзҳҰ пјҢ и®©дәәжҖҖз–‘дё»дәәд»ҺжқҘжІЎжңүе–ӮиҝҮе®ғ пјҢ й»Ҹдәәзҡ„жғ…жҖҒ пјҢ еҸҲи®©дәәж„ҹеҲ°е®ғзҡ„еӯӨзӢ¬ гҖӮ зңӢиө·жқҘйӮЈдәӣзӣҶж ҪжҜ”зӢ—еҸ—еҲ°зҡ„з…§йЎҫиҰҒеҘҪеҫ—еӨҡ гҖӮ第дәҢж¬ЎжҲ‘们дёҠеҚҲеҺ»еёӮеңә пјҢ ж—©еёӮе·Із»ҸжӯҮеңә пјҢ е’Ңе°ҡиҝҳеңЁзқЎи§ү пјҢ зү§д№ӢеңЁжҘјдёӢе–ҠдәҶеҚҠеӨ© пјҢ з»ҲдәҺ пјҢ д»–д»ҺдәҢжҘјдёҖеүҜзӘ—еёҳеҗҺжҺўеӨҙ пјҢ зӯүдјҡдёӢжқҘжҺҘжҲ‘们 гҖӮ д»–зҗҶзқҖе…үеӨҙ пјҢ иә«жқҗиғ–еӨ§ пјҢ зңӢдёҠеҺ»зЎ®е®һеғҸдёӘеӨҙйҷҖзҡ„ж ·еӯҗ гҖӮ иҖҒе©ҶдёҚеңЁ пјҢ жҲ‘们и·ҹд»–дёҖиө·еҺ»еҲ°еҗҺйҷў пјҢ дёҠж¬Ўзҡ„е°Ҹй»‘зӢ—е·Із»ҸдёҚеңЁдәҶ гҖӮжҲ‘们и·ҹзқҖд»–дёҠеҲ°дәҢжҘј пјҢ еңҹй»„иүІзӘ—еёҳйҒ®дҪҸдёҖеҚҠе…үзәҝ пјҢ жҲҝй—ҙйҮҢеҫҲеҮҢд№ұ пјҢ еҲ°еӨ„жҳҫйңІиө·дјҸдёҚ规еҲҷзҡ„дәӢзү©иҪ®е»“ пјҢ жҳҜеҙҙжҲҗдёҖеӣўзҡ„иЎЈзү©гҖҒж•ЈиҗҪзҡ„й”…зў—е’Ңе…¶е®ғжқӮзү© пјҢ й”…зў—иҝҳз»“зқҖйЈҹзү©зҡ„з—Ӯ пјҢ зңӢжқҘ他并йқһжҜҸйЎҝйғҪдёӢжҘјеҺ»еҗғйҘӯ гҖӮ жңҖзӘҒеҮәзҡ„家具жҳҜдёҖдёӘйқ еўҷзҡ„д№Ұжһ¶ пјҢ жқҫеһ®жҸ’зқҖдёҖдәӣеҲқдёӯеӯҰз”ҹз”Ёзҡ„ж•ҷжқҗ пјҢ зңӢеҫ—еҮәжқҘжҳҜе„ҝеҘідҪҝз”ЁиҝҮзҡ„ гҖӮжҲҝй—ҙйҮҢеҸӘжңүдёҖеҸӘеҮіеӯҗ пјҢ е’Ңе°ҡеқҗеңЁеәҠдёҠ пјҢ жҲ‘й—®д»–иҝ‘жқҘжҖҺд№Ҳж · пјҢ д»–еҸ№жҒҜиҜҙдёҚжҖҺд№Ҳж · пјҢ дјјд№ҺжҲ‘зҡ„й—®иҜқејҖеҗҜдәҶд»–зҡ„иҜқеҢЈеӯҗ пјҢ ејҖе§Ӣи®Іиө·еҫҲеӨҡдәәз”ҹе“ІзҗҶ пјҢ жңҖдё»иҰҒзҡ„жҳҜдәәз”ҹз©әж— пјҢ еӣ дёәеҫҲеӨҡиҜқйўҳж¬ІиЁҖеҸҲжӯў пјҢ зңӢдёҠеҺ»дёҚеӨ§еғҸе’Ңе°ҡ пјҢ еҖ’иҝ‘дәҺдёҖдҪҚе°ҡжңӘзӮјжҲҗзҡ„е“Ідәә пјҢ еңЁйҡҗеҝҚе’ҢйҖҡи„ұд№Ӣй—ҙйҖЎе·Ў гҖӮжҲҝй—ҙйҮҢеҸҰжңүеҮ еҸӘж¶Ӯж–ҷжЎ¶ пјҢ иЈ…зқҖзҺүзұійқўйҘІж–ҷ пјҢ иҝҳжңүдёҖеҘ—дҝЎеҸ·жҺҘ收жңәдёҖж ·зҡ„иЈ…зҪ® гҖӮ иҝҷжҳҜз”ЁжқҘйҘІе…»е’Ңи®ӯз»ғжҘјйЎ¶е…»ж®–зҡ„дҝЎйёҪзҡ„ гҖӮ иҝҷжҳҜе’Ңе°ҡзҡ„еҸҰдёҖиҒҢдёҡ гҖӮйҷўеққйҮҢжҗӯзқҖдёҖжһ¶зӘ„зӘ„зҡ„й“ҒжўҜ пјҢ еҸҜд»ҘзҲ¬еҲ°еұӢйЎ¶зҡ„йёҪиҲҚ гҖӮ е’Ңе°ҡеңЁеүҚйқўзҲ¬дёҠй“ҒжўҜ пјҢ йўҶжҲ‘们еҺ»зңӢйёҪеӯҗ гҖӮ й“ҒжўҜзҡ„еқЎеәҰеҮ д№ҺеһӮзӣҙ пјҢ и®©дәәжңүдәӣеҸ‘жҷ• гҖӮ жўҜеӯҗйЎ¶з«ҜжңүдёҖжүҮе°Ҹй—Ё пјҢ иө°иҝӣеҺ»д№ӢеҗҺе°ұеҲ°дәҶдёӨе№ўйёҪиҲҚд№Ӣй—ҙ пјҢ жө“зғҲзҡ„ж°”жҒҜжү‘жқҘ пјҢ й“ҒдёқзҪ‘дёҠжІҫж»ЎдәҶиҙҘзө®дёҖж ·зҡ„зҫҪжҜӣ пјҢ е’•е’•зҡ„еЈ°е“Қз¬јзҪ©иҖіиҶң пјҢ иҝҷжҳҜдёҺжҘјдёӢе®Ңе…ЁдёҚеҗҢзҡ„дёҖдёӘдё–з•Ң гҖӮйёҪиҲҚйқўз§ҜдёҚе°Ҹ пјҢ йёҪеӯҗ们жү‘и…ҫжҲ–иҖ…е‘ҶеңЁи§’иҗҪ пјҢ ж•°йҮҸеӨ§зәҰжңүдёҠзҷҫеҸӘ гҖӮ е’Ңе№іж—¶е№ҝеңәдёҠи§ҒеҲ°иў«жҠ•е–Ӯзҡ„йёҪеӯҗдёҚеҗҢ пјҢ иҝҷдәӣйёҪеӯҗзҡ„е§ҝжҖҒжӣҙиҪ»зӣҲдәӣ пјҢ еҮ д№ҺжҜҸеҸӘзҡ„и„–еӯҗдёҠйғҪжңүдәӣж–‘зӮ№иҠұзә№ пјҢ и®©дәәжғіеҲ°зҺӢдё–иҘ„еңЁгҖҠй”ҰзҒ°е ҶгҖӢйҮҢеҶҷзҡ„вҖңзӮ№еӯҗвҖқ гҖӮе’Ңе°ҡжү“ејҖз¬јй—Ё пјҢ дёҖзҫӨйёҪеӯҗе”ҝе“ЁйЈһеҗ‘еӨ©з©ә пјҢ еңЁеёғй•Үй«ҳдҪҺй”ҷй”ҷзҡ„жҲҝеұӢдёҠз©әеҫҳеҫҠ гҖӮ д№ҹжңүдёҖдәӣе‘ҶеңЁйёҪз¬јеҸЈзҡ„ж ҸжқҶдёҠ пјҢ е’Ңе°ҡдјёжүӢжҗӮдҪҸдёҖеҸӘ пјҢ йёҪеӯҗзҡ„и„–еӯҗй—ӘзқҖеҫ®еҰҷзҡ„иҷ№еҪ© пјҢ еңЁд»–жүӢдёӯжҳҫеҫ—еҫҲжё©йЎә гҖӮе’Ңе°ҡе…»дҝЎйёҪзҡ„жҲҗз»©дёҚй”ҷ пјҢ еҫ—иҝҮеҢәйҮҢдҝЎйёҪеӨ§иөӣ500е…¬йҮҢз»„зҡ„еүҚеҮ еҗҚ пјҢ еҘ–йҮ‘дёҚе°‘ гҖӮ иҝҷз§ҚжҜ”иөӣжңүиөҢиөӣзҡ„жҖ§иҙЁ пјҢ еҸӮдёҺиҖ…еҗ„иҮӘеҮәд»Ҫеӯҗй’ұ пјҢ иөўиҖ…еҫ—еҘ– пјҢ еҪ“然иҝҳжңүдјҒдёҡзҡ„иөһеҠ© гҖӮ з»ҷе’Ңе°ҡжҢЈжқҘеҘ–йҮ‘зҡ„йёҪеӯҗ пјҢ дёҚзҹҘйҒ“жҳҜеҗҰд»–жүӢдёӯиҝҷеҸӘ пјҢ дәҢжҘјжҲҝй—ҙйҮҢжңүеёҰзқҖе®ғз…§зүҮзҡ„иҜҒд№Ұ пјҢ дёҚиҝҮеҪ“然 пјҢ еңЁжҲ‘们иҝҷж ·зҡ„еӨ–иЎҢзңјйҮҢ пјҢ жүҖжңүзҡ„йёҪеӯҗйғҪй•ҝеҫ—еҫҲеғҸ гҖӮйёҪз¬јйҮҢйёҪзІӘзҡ„ж°”е‘ійқһеёёжө“зғҲ пјҢ дҪҶе’Ңе°ҡдјјд№ҺжҜ«ж— ж„ҹи§ү гҖӮ д»–жҳҫеҫ—жҜ”еңЁдёӢйқўиҮӘеңЁеҫ—еӨҡ пјҢ з»ҲдәҺжҡӮеҒңдәҶеҜ№йӮЈдәӣдәәз”ҹе“ІзҗҶзҡ„и®Іиҝ° пјҢ зңјзҘһйҮҢзҺ°еҮәдёҖе°ҸзүҮеӨ©з©ә пјҢ иҝҪйҡҸзқҖйёҪеӯҗеңЁеёғй•ҮдёҠз©әеӣһзҝ” гҖӮдёҙиө°зҡ„ж—¶еҖҷ пјҢ е’Ңе°ҡд»ҺеұӢйҮҢд»Җд№Ҳең°ж–№жҺҸеҮәдёӨжһҡй“ңй’ұ пјҢ йҖҒз»ҷжҲ‘е’Ңзү§д№Ӣ пјҢ иҜҙиҝҷжҳҜеҸӨдәәзҡ„дёңиҘҝ гҖӮ й“ңй’ұеӨ–еңҶеҶ…ж–№ пјҢ еёҰзқҖйІңжҳҺзҡ„з»ҝй”Ҳ пјҢ жҲ‘жӢҝеҲ°йқ й—Ёе…үзәҝеҘҪзҡ„ең°ж–№ пјҢ зңӢеҮәдёҠйқўз”ЁзҜҶж–ҮеҲ»зқҖдёӨдёӘеӯ—вҖңдә”й“ўвҖқ гҖӮ жҲ‘еҗғжғҠең°иҜҙиҝҷжҳҜжұүд»Јзҡ„еёҒ пјҢ зү§д№ӢиҜҙдҪ йҖҒжҲ‘们иҝҷд№ҲиҙөйҮҚзҡ„дёңиҘҝ пјҢ е’Ңе°ҡеҫ®еҫ®з¬‘зқҖиҜҙеёҒжҳҜзңҹзҡ„ пјҢ еҖјдёҚдәҶеҮ дёӘй’ұ пјҢ жҳҜеүҚдёҖйҳөеңЁжқңжӣІжҢ–еҮәжқҘзҡ„ пјҢ дҪ 们жӢҝзқҖзҺ©е„ҝ гҖӮжҲ‘дәӢеҗҺзҷҫеәҰдәҶдёҖдёӢ пјҢ зЎ®е®һеҰӮе’Ңе°ҡжүҖиҜҙ пјҢ дә”й“ўй’ұеӣә然е№ҙд»Јд№…иҝң пјҢ дҪҶеӣ дёәеҮәеңҹеӨӘеӨҡ пјҢ дёҖжһҡеҖјдёҚдәҶеӨҡе°‘й’ұ пјҢ дҪҶиҝҷд№ҹиҜҙжҳҺдәҶе®ғдёҚдјҡжҳҜйҖ еҒҮ гҖӮиҝҮдәҶдёҖж®ө пјҢ дёҖдёӘе°ҸйӣӘеӨ©еҚҠеӨң пјҢ е’Ңе°ҡе“ӯзқҖжү“з”өиҜқз»ҷзү§д№Ӣ пјҢ иҜҙд»–еҲҡжҢЁдәҶеҮ дёӘиӯҰеҜҹзҡ„жҸҚ гҖӮ еҺҹ委жҳҜд»–ж·ұеӨңйҶүй…’еӣһжқҘ пјҢ иҖҒе©ҶжҖ•еҶ·дёҚж„ҝиө·еәҠејҖй—Ё гҖӮе’Ңе°ҡејҖе§ӢжҳҜж•Ій—Ё пјҢ еҗҺжқҘејҖе§Ӣз ёй—Ё пјҢ и¶ҒзқҖй…’еҠІеҳҙйҮҢйӘӮеҫ—д№ҹйҡҫеҗ¬ пјҢ жҠҠиҝҮеҺ»зҡ„дәӢйғҪжҗ¬еҮәжқҘ гҖӮ иҖҒе©Ҷд№ҹдёҚжҳҜеҘҪжғ№зҡ„ пјҢ еҗҺжқҘзҙўжҖ§жү“дәҶ110 пјҢ ж—¶еҖјз–«жғ…жңҹй—ҙ пјҢ жҙҫеҮәжүҖеҮәиӯҰиҝ…йҖҹ пјҢ еӣӣеҗҚжҲҙзқҖеҸЈзҪ©зҡ„иӯҰеҜҹиө¶еҲ°зҺ°еңә пјҢ й—®д»–дёәд»Җд№ҲдёҚжңҚз–«жғ…з®ЎеҲ¶д№ұиө° пјҢ дёҚжҲҙеҸЈзҪ©иҝҳж·ұеӨңз ёеҲ«дәәзҡ„й—Ё пјҢ е’Ңе°ҡй…’еҠІеӨ§иҜқжІЎиҜҙжё…жҘҡ пјҢ и·ҹиӯҰеҜҹеҗөиө·жқҘ пјҢ еҳҙйҮҢиҝҳйӘӮйӘӮе’§е’§ пјҢ еҮ дёӘиӯҰеҜҹжҠҠе’Ңе°ҡжҢүеҖ’еңЁйӣӘең° пјҢ жҡҙжҸҚдәҶдёҖйЎҝеҮҶеӨҮеёҰдёҠиҪҰ пјҢ иҝҷж—¶е’Ңе°ҡжүҚиҜҙиҮӘе·ұжҳҜиҝҷ家еҘідәәзҡ„дёҲеӨ« гҖӮиӯҰеҜҹж ёе®һдәҶдёҖз•Ә пјҢ зЎ®е®ҡд»–дёҚжҳҜеҚҠеӨңз ёй—ЁжҠўеҠ«зҡ„ пјҢ ж•ҷиӮІдәҶеҮ еҸҘ пјҢ жҠҠд»–жү”еңЁеҪ“ең°иө°дәҶ гҖӮ еҖ’жҳҜйҡҸжүӢжү”з»ҷд»–дёҖеүҜеҸЈзҪ© пјҢ еӢ’д»Өд»–еёҰдёҠ гҖӮ еҘідәәдҫқж—§дёҚиӮҜејҖй—Ё пјҢ е’Ңе°ҡеңЁй—ЁеӨ–е‘ҶеҲ°еӣӣжӣҙеӨ© пјҢ еҸҲжҳҜеҶ»еҸҲжҳҜж°” пјҢ е“ӯзқҖз»ҷзү§д№Ӣжү“з”өиҜқ пјҢ иҜҙиҮӘе·ұдёҚжғіжҙ»дәҶ гҖӮзү§д№Ӣзҡ„дҪҸеӨ„иҙўзҘһеәҷе’ҢеёӮеңәеҸӘйҡ”зқҖдёӨжқЎиЎ— пјҢ иө¶иҝҮеҺ»жҠҠе’Ңе°ҡжҺҘеҲ°иҮӘ家йҒҝеҜ’ пјҢ е’Ңе°ҡдёҖиҫ№е“ӯдёҖиҫ№ж…ЁеҸ№дәәз”ҹиҷҡж— пјҢ зү§д№ӢеҠқж…°еҲ°еӨ©жҳҺжүҚйҖҒд»–еӣһеҺ» гҖӮз–«жғ…и§ЈйҷӨд№ӢеҗҺ пјҢ жҲ‘еҶҚж¬ЎеҺ»еёғй•Ү пјҢ е’Ңзү§д№ӢеҲ°еёӮеңәиЎ—жүҫе’Ңе°ҡ пјҢ д»–е’ҢиҖҒе©ҶйғҪдёҚеңЁ пјҢ еҚҙеңЁдёҖжҘји§ҒеҲ°дәҶд»–зҡ„еҘіе„ҝ гҖӮ еҘіе„ҝеңЁеӣӣе·қеҝөдёҖжүҖдёӯдё“ пјҢ еӣ дёәз–«жғ…еӣһ家дёҠзҪ‘иҜҫ пјҢ жӯЈеңЁжЎҢеӯҗдёҠеҒҡдҪңдёҡ пјҢ иә«иғҢеЈ®еЈ®е®һе®һзҡ„ пјҢ зңӢдёҠеҺ»е’Ңе’Ңе°ҡжңүдёҖзӮ№жҢӮзӣё гҖӮ й—®иө·зҲ¶дәІ пјҢ еҘ№иҜҙдёҚзҹҘйҒ“еҺ»дәҶе“ӘйҮҢ гҖӮзҰ»ејҖд№ӢеҗҺзү§д№Ӣе‘ҠиҜүжҲ‘ пјҢ еҪ“еҲқе’Ңе°ҡе’ҢиҖҒе©Ҷй—№зҰ»е©ҡзҡ„ж—¶еҖҷ пјҢ еҘіе„ҝеҪ“ж—¶иҝҳеңЁдёҠеҲқдёӯ пјҢ иҜҙвҖңжҲ‘иҰҒдёҠеӯҰ пјҢ и°ҒиғҪеҸ«жҲ‘дёҠеӯҰжҲ‘и·ҹзқҖи°ҒвҖқ пјҢ еҗҺжқҘи·ҹзқҖжҜҚдәІиө°дәҶ пјҢ дёӨе№ҙеҗҺеҸҲеӣһжқҘ гҖӮ иҝҷд№ҹжҳҜе’Ңе°ҡзҡ„дёҖ件дјӨеҝғдәӢ гҖӮ е’Ңе°ҡйҖҒз»ҷжҲ‘зҡ„дә”й“ўй’ұ пјҢ дҫқж—§ж”ҫеңЁжҲ‘зҡ„д№Ұжһ¶дёҠ пјҢ жҳҫзқҖжҙһжҳҺдё–дәӢзҡ„жІ§жЎ‘еҪўзҠ¶ пјҢ еёҰзқҖйІңз»ҝзҡ„й“ңй”Ҳ гҖӮиҖҒеӨӘйӮЈеӨ©жҲ‘йӘ‘зқҖе®үе®үзҡ„з”өеҠЁиҮӘиЎҢиҪҰ пјҢ е’Ңзү§д№ӢеҺ»еЎ¬и„ҡзңӢжңӣдёҖдҪҚиЎЁе“Ҙ пјҢ и·ҜиҝҮдёҖеә§жқ‘еә„ пјҢ е»әзӯ‘дјјд№ҺжңүзӮ№ж–° пјҢ еҚҙеҸҲиҝҮеҝ«ең°жҳҫж—§дәҶ пјҢ ж ·ејҸеҲ’дёҖ пјҢ е’Ңжң¬ең°еҶңж°‘иө·зҡ„жҲҝеӯҗжңүеҢәеҲ« гҖӮ зү§д№ӢиҜҙиҝҷжҳҜ移民жқ‘ пјҢ дәәйғҪжҳҜд»Һз»ҲеҚ—еұұйҮҢжҗ¬еҮәжқҘзҡ„ гҖӮиө°еҲ°жқ‘еӯҗдёӯж®ө пјҢ зү§д№ӢеҒңдёӢиҮӘиЎҢиҪҰ пјҢ иҜҙеҺ»зңӢдёҖдҪҚиҖҒеӨӘеӨӘ гҖӮ иҖҒеӨӘеӨӘжҳҜзү§д№ӢдёҠж¬ЎжқҘеё®иЎЁе“Ҙзҝ»ең°и®ӨиҜҶзҡ„ гҖӮ 移民жқ‘зҡ„ең°е°‘ пјҢ иЎЁе“Ҙзҡ„жІ№иҸңең°е°ұеңЁиҖҒеӨӘеӨӘзҡ„жҲҝеӯҗеқҺдёӢ пјҢ иҖҒеӨӘеӨӘз«ҷеңЁйҷўеққйҮҢзңӢзү§д№Ӣе’ҢиЎЁе“Ҙзҝ»ең° пјҢ дёҖиҫ№и·ҹжӯҮж°”зҡ„зү§д№ӢжҗӯиҜқ гҖӮ еҗҺжқҘеҘ№жҠҠзү§д№ӢеҸ«еҲ°йҷўеққ пјҢ еӣһеұӢз«ҜеҮәдёҖеӨ§зјёеӯҗиңӮиңңж°ҙ пјҢ иҜҙиҝҷжҳҜиҮӘ家еңЁеұұйҮҢе…»зҡ„иңӮиңң пјҢ йҖ’з»ҷзү§д№Ӣ пјҢ зңӢзқҖд»–ж…ўж…ўе–қе®Ң пјҢ дёҖиҫ№и·ҹзү§д№ӢиҒҠеӨ© гҖӮ иҒҠеӨ©зҡ„еҶ…е®№ пјҢ жҳҜеҘ№еҜ№зҶҹдәәдёҚдҫҝеҮәеҸЈзҡ„家дәӢ гҖӮиҖҒеӨӘеӨӘ姓з§Ұ пјҢ 家еңЁз»ҲеҚ—еұұйҮҢзҡ„еӨ§жңЁз“ўжІҹ пјҢ дәәиҖҒеҮ иҫҲдҪҸеңЁйӮЈйҮҢ пјҢ иҮӘд»ҺеҮ е№ҙеүҚжҗ¬еҲ°е№іеҺҹдёҠ пјҢ еҫҲеӨҡдәӢжғ…йғҪеҸҳдәҶ гҖӮ еңҹең°еҮҸе°‘ пјҢ д№ҹжІЎдәҶйқ еұұеҗғеұұзҡ„еүҜдёҡ пјҢ е„ҝеӯҗ们еҮәеӨ–жү“е·Ҙ пјҢ иҖҒеӨӘеӨӘе’ҢеӘіеҰҮз•ҷеңЁе®¶йҮҢ гҖӮ жқ‘йҮҢйғҪжҳҜеҰҮеҘі пјҢ еҸӘеү©дёӢжқ‘й•ҝеҮ дёӘз”·дәә пјҢ дәҢе„ҝеӘіе°ұе’Ңжқ‘й•ҝзӣёеҘҪдёҠдәҶ пјҢ еҘ№е№Іж¶үдёҚдәҶ пјҢ еҸҲжІЎеӨ„иҜҙ гҖӮзү§д№Ӣеҗ¬зқҖеҘ№зө®еҸЁ пјҢ д№ҹдёҚеҘҪжҺҘиҜқ гҖӮ иңңж°ҙзҡ„е‘ійҒ“еҫҲжё…з”ң пјҢ зҡ„зЎ®е’Ңеёғй•ҮиЎ—дёҠеҚ–зҡ„дёҚдёҖж · пјҢ дёҖеҸЈдёӢеҺ»з–Ід№ҸдәҶзҡ„иә«еӯҗйғҪиҲ’жңҚдәҶ гҖӮ е–қе®ҢдәҶдёҖеӨ§жқҜ пјҢ иҖҒеӨӘеӨӘеҸҲжіЎдёҠдёҖжқҜ пјҢ и®©д»–еёҰеҲ°ең°еӨҙ гҖӮжҲ‘们没жңүжүҫеҲ°иҖҒеӨӘеӨӘзҡ„й—Ё пјҢ е…ҲеҺ»дәҶиЎЁе“Ҙ家 гҖӮ иЎЁе“ҘеӣһжғіиҜҙ пјҢ д»–еңЁең°йҮҢе№Іжҙ»зҡ„ж—¶еҖҷ пјҢ е·Із»ҸеҫҲд№…жІЎжңүзңӢи§ҒиҝҮиҖҒеӨӘеӨӘдәҶ гҖӮеӣһзЁӢж—¶з»ҸиҝҮжқ‘еә„ пјҢ еҮ дёӘиҖҒеӨӘеӨӘеңЁе…¬и·ҜжӢҗејҜеӨ„жҷ’еӨӘйҳі гҖӮ еҒңиҪҰеҗ‘他们жү“еҗ¬з§ҰиҖҒеӨӘ пјҢ дёҖдёӘиҖҒе©Ҷе©ҶиҜҙпјҡвҖңеҘ№е‘Җ пјҢ еүҚдёҖйҳөж‘”ж–ӯдәҶи…ҝ пјҢ иәәеңЁеәҠдёҠдәҶ гҖӮ вҖқеҘ№жҢҮз»ҷдәҶжҲ‘们йҷўеӯҗ гҖӮж•ІејҖз§Ұ家зҡ„йҷўеӯҗ пјҢ дёҖжқЎзӢ—еҸ«еҫ—еҫҲеҮ¶ пјҢ еҚҠеӨ©жқҘдәҶдёӘжҠұзқҖеӯ©еӯҗзҡ„еҘідәәжӢҰдҪҸдәҶ пјҢ иҜҙжҳҺжқҘж„ҸеҗҺ пјҢ еҘідәәеёҰжҲ‘们иҝӣдәҶйҷўеӯҗ пјҢ иҝҷжҳҜз§ҰиҖҒеӨӘзҡ„дёүе„ҝеӘі гҖӮиө°иҝӣе®ўеҺ… пјҢ иҖҒдәәиәәеңЁдёҙж—¶ж”Ҝиө·зҡ„дёҖеј еҚ•дәәй“әдҪҚдёҠ пјҢ ж—Ғиҫ№йҷӘзқҖдёҖдёӘзңӢдёҠеҺ»жҜ”иҫғе№ҙиҪ»зҡ„еҘіеӯҗ пјҢ еҗҺжқҘзҹҘйҒ“жҳҜеӯҷеҘі пјҢ еңЁеӨ–ең°дёҠиҒҢдёҡеӯҰйҷў пјҢ еӣ дёәж”ҫжҡ‘еҒҮеӣһ家зҺ©дёҖйҳө гҖӮиҖҒдәәй—ӯзңјиәәзқҖ пјҢ зңӢдёҚеҮәжҳҜзқЎжҳҜйҶ’ пјҢ еӯҷеҘіиҜҙеҘ№иҮӘд»Һи·Ңи·Өд№ӢеҗҺ пјҢ иҜқе°ұи¶ҠжқҘи¶Ҡе°‘ пјҢ еҮ д№ҺдёҚи®ӨиҜҶд»Җд№ҲдәәдәҶ гҖӮ еҪ“зү§д№Ӣи·ҹеҘ№жү“жӢӣе‘ј пјҢ еҘ№зқҒејҖдәҶзңјзқӣ пјҢ еҫ®еҫ®ж¬ дәҶж¬ еҹӢеңЁиў«иӨҘйҮҢзҡ„жүӢ пјҢ ж•ҙдёӘдәәеғҸеҸ—дәҶеҫ®йЈҺзҡ„иҠҰиӢҮжңүдәҶзӮ№жҙ»ж°” гҖӮ еҫҲжҳҫ然 пјҢ еҘ№жҳҜи®ӨиҜҶзү§д№Ӣзҡ„ гҖӮ зү§д№ӢдјёжүӢжҸЎдҪҸдәҶеҘ№зҡ„ пјҢ й—®еҘ№жңҖиҝ‘зҡ„жғ…еҶө пјҢ еҘ№дјјд№ҺжҳҜе—«еҡ…зқҖеӣһзӯ”дәҶдёҖдёӨдёӘиҜҚ гҖӮ дёҖж—ҒжҠұзқҖеӯ©еӯҗзҡ„дёүе„ҝеӘіеёҰзӮ№жҠұжҖЁзҡ„иҜӯж°”иҜҙ пјҢ еҰҲе№іж—¶дёҚжҗӯзҗҶжҲ‘们 пјҢ жңүж—¶еҖҷз«ҜйҘӯз»ҷеҘ№ пјҢ вҖңеҘ№иҝҳзғҰиәҒеҫ—еҫҲ пјҢ жҠҠеӨҙдёҖж‘ҶвҖқ гҖӮе„ҝеӯҗ们常е№ҙеңЁеӨ– пјҢ еӯҷеҘіжІЎжңүж”ҫеҒҮзҡ„ж—Ҙеӯҗ пјҢ иҖҒдәәдё»иҰҒйқ дёүе„ҝеӘіз…§йЎҫ пјҢ дёүе„ҝеӘіеҸҲжңүиҮӘе·ұиҘҒиӨ“зҡ„еӯ©еӯҗ гҖӮ иҮідәҺйӮЈдҪҚдәҢе„ҝеӘі пјҢ дјјд№ҺжҳҜеҲҶ家еұ…дҪҸзҡ„ гҖӮ иҖҒдәәж‘”и·Өд№ӢеҗҺжІЎжңүеҺ»жІ»з–— пјҢ иҜҙжҳҜй«ӢйӘЁи„ұжҰ«жҺҘиө·жқҘеҫҲйә»зғҰ гҖӮ еҜ’еҫҖжҡ‘жқҘ пјҢ еҗғе–қжӢүж’’ пјҢ зҝ»иә«ж“Ұжҙ— пјҢ дёҚзҹҘйҒ“и°ҒиғҪдёҖеҶҚе°Ҫеҝғ пјҢ е°ұеғҸжӯӨеҲ»иҗҪеңЁиӨҘиҫ№е…Ёж— иЎҖиүІзҡ„жүӢ пјҢ ж— дәәжіЁж„Ҹ гҖӮжҲ‘жҸЎдәҶжҸЎиҝҷеҸӘиҝ‘д№Һе№ІжһҜзҡ„жүӢ гҖӮ жІЎжңүдёҖзӮ№жё©еәҰ пјҢ дјјд№ҺжҜ”жғіи§Ғзҡ„иҝҳиҰҒеҶ· пјҢ еҗ«жңүдёҖдёқжғҠ讶 гҖӮ д»Һзү§д№Ӣи§ҒеҲ°зҡ„йӮЈдёӘе” е—‘еҶІиңӮиңңж°ҙзҡ„иҖҒеӨӘ пјҢ еҲ°иҝҷдёӘжІЎжңүжё©еәҰзҡ„иәҜдҪ“ пјҢ е…¶й—ҙд№ҹдёҚиҝҮеҚҠе№ҙж—¶й—ҙ гҖӮ иҮӘд»ҺеңЁе…¬и·ҜдёҠе№іең°и·ҢдәҶдёҖи·Ө пјҢ еҘ№зҡ„ж—Ҙеӯҗе®һйҷ…дёҠе·Із»Ҹз»“жқҹ пјҢ еҸӘеү©дёӢдёҖдёӘеҸҘеҸ·жІЎжңүз”»е®Ң пјҢ жҲ‘жңүдәӣжҖҖз–‘еҘ№зҡ„жӢ’з»қиҜҙиҜқе’ҢеҗғйҘӯ пјҢ жҳҜжңүж„Ҹи®©иҝҷдёӘеҸҘзӮ№е°ҒеҸЈ гҖӮжҲ‘们е‘ҠеҲ«зҡ„ж—¶еҖҷ пјҢ иҜҙдёӢж¬ЎеҶҚжқҘзңӢеҘ№ пјҢ иҖҒеӨӘеӨӘиҝҳеҫ®еҫ®еҮәеЈ°еӣһеә” гҖӮ иө°еҲ°й—ЁеҸЈеӣһеӨҙ пјҢ иҖҒеӨӘеӨӘеҸҲй—ӯдёҠдәҶзңјзқӣ пјҢ жүӢиҮӮе’Ңе‘јеҗёиҗҪеӣһеҲ°иў«иӨҘйҮҢ пјҢ зңӢдёҠеҺ»еғҸжІЎжңүд»»дҪ•ж°”жҒҜ гҖӮ йӮЈйҳөеҗ№еҠЁдәҶе№ІжһҜиҠҰиӢҮзҡ„йЈҺеҒңжӯўдәҶ гҖӮеҗ¬зү§д№ӢиҜҙ пјҢ иҖҒдәәеңЁз§ӢеӨ©иҝҮдё–дәҶ гҖӮжңүдёҖж¬ЎжҲ‘еҸ—жңӢеҸӢйӮҖиҜ· пјҢ еңЁз§ҰеІӯеұұйҮҢдҪҸдәҶдёӨеӨ© пјҢ ең°зӮ№е°ұеңЁеӨ§жңЁз“ўжІҹйЎ¶дёҠ пјҢ иғҪеӨҹдҝҜи§ҒжІҝжІҹеҮ еӨ„жҗ¬з©әзҡ„йҷўиҗҪ пјҢ з•ҷдёӢзҒ°жү‘жү‘зҡ„з“ҰйЎ¶е’Ңеңҹеўҷ пјҢ жҺ©жҳ еңЁй«ҳеӨ§д№”жңЁзҡ„иҚ«и”ҪйҮҢ гҖӮ жәӘж°ҙд»Қж—§зҷҪзҷҪжөҒж·ҢиҝҮйҷўеӯҗ пјҢ ж— дәәдҪҝз”Ё пјҢ и’ҝиҚүж·ұиҝҮдәҶиҶқзӣ– гҖӮ жҲ‘жғіиө·еҺ»дё–зҡ„з§ҰиҖҒеӨӘ пјҢ жҲ–и®ёд»ҺеүҚе°ұдҪҸеңЁжҲ‘и§Ҷзәҝзҡ„йҷўеӯҗйҮҢ пјҢ жҢ‘ж°ҙиҙҹи–Ә пјҢ зҲ¬еқЎдёӢеқҺ пјҢ е…»еӨ§дәҶдёӨеұӮеҗҺдәә пјҢ жІЎжңүеҮәиҝҮеӨ§зҡ„й—ӘеӨұ гҖӮ еҲ°дәҶе№іеҺҹдёҠ пјҢ еҚҙе№ізҷҪж— дәӢең°и·ҢеҖ’дәҶ пјҢ дёҖ蹶дёҚиө· гҖӮеңЁйӮЈзүҮе®Ңе…ЁйҷҢз”ҹзҡ„ең°йқўдёҠ пјҢ еҘ№д»ҺжқҘжІЎжңүжүҫеҲ°иҝҮиҮӘе·ұзҡ„з«Ӣи¶ід№Ӣең° гҖӮдҪҸжҢҒзү§д№Ӣзҡ„йҷўеӯҗзҙ§йӮ»иҙўзҘһеәҷ пјҢ еҸӘйҡ”дёҖжқЎеҫҲзӘ„зҡ„е°Ҹе·· пјҢ дёӨйҷўдәәеЈ°зӣёй—» гҖӮ з«ҷеңЁзү§д№Ӣж–°иө·зҡ„дәҢеұӮе°ҸжҘјдёҠ пјҢ е°ұжңүдёҖеҲҶдҝҜзһ°зҡ„ж„ҸжҖқ гҖӮиҙўзҘһиөөе…¬жҳҺжң¬зұҚе°ұжҳҜз§ҰеІӯи„ҡдёӢзҡ„дәә пјҢ жҲ–и®ёдёҺжӯӨзӣёе…і пјҢ иҙўзҘһеәҷдёҖзӣҙжңүйҰҷзҒ« пјҢ иҷҪ然дёҚз®—ж—ә пјҢ иҝҳжңүжҜҸе№ҙдёҖеәҰзҡ„еәҷдјҡ гҖӮ жңүдәҶиҝҷдёӨе®— пјҢ е°ұдјҡй—ҙжӯҮжңүдәәжқҘдҪҸжҢҒ гҖӮ иҙўзҘһиҷҪ然еңЁдҪӣеҜәйҮҢеҫҖеҫҖжңүдёҖеёӯд№Ӣең° пјҢ дҪҶеҮәиә«жҳҜиөөе…¬жҳҺдҝ®д»ҷеҫ—йҒ“ пјҢ иҝҷеә§дё»дҫӣиҙўзҘһзҡ„еәҷ пјҢ дҪҸжҢҒзҡ„дёҖзӣҙжҳҜйҒ“еЈ« гҖӮ жҲ‘еүҚеҗҺи§ҒиҝҮдёӨдҪҚ гҖӮеүҚйқўжҳҜеј йҒ“й•ҝ гҖӮ жңүдёҖж¬ЎжҲ‘еҺ»зү§д№Ӣзҡ„йҷўеӯҗ пјҢ еҲҡеҘҪйҒҮеҲ°еј йҒ“й•ҝеҮәжқҘйҖҒе®ў пјҢ з”·еҘідёӨдёүдәәйұјиҙҜй’»е…ҘдёҖиҫҶеҘҘиҝӘиҪҰ пјҢ еңЁиҙўзҘһеәҷеүҚйқўзҡ„еңҹеққдёҠеҖ’иҪҰ пјҢ з©ҝиҝҮ并дёҚе®Ҫж•һзҡ„еҗҺиЎ—иө°дәҶ гҖӮ еј йҒ“й•ҝжү¬иө·йҒ“иўҚзҡ„иў–еӯҗ пјҢ еңЁеҫ®еҫ®жү¬иө·зҡ„е°ҳеңҹйҮҢдҪңеҲ« гҖӮеӣһеӨҙд»–еёҰжҲ‘们иҝӣдәҶйҷўеӯҗ пјҢ еңЁйҷўеӯҗеҪ“еҝғж ‘дёӢдёҖеј зҹіжЎҢиҫ№еқҗдёӢ пјҢ жЎҢдёҠж‘ҶзқҖж–№жүҚжӢӣеҫ…е®ўдәәзҡ„иҢ¶ж°ҙ пјҢ еј йҒ“й•ҝеҗ©е’җдёҖдёӘи·ҹд»Һд»–зҡ„еҚҒе…«д№қеІҒзҡ„е°ҸйҒ“еЈ«жҚўжқҜеҖ’ж°ҙ пјҢ и®©д»–вҖңжүӢи„ҡйә»еҲ© пјҢ иҝҺжқҘйҖҒеҫҖеӯҰзқҖзӮ№вҖқ пјҢ дёҖиҫ№и·ҹжҲ‘们иҒҠиө·еҲҡжүҚжқҘзҡ„е®ўдәә гҖӮ иҜҙжқҘеӨҙеҫҲеӨ§ пјҢ жҳҜвҖңеҶӣзә§е№ІйғЁ пјҢ д»ҺеұұдёңдёҖи·Ҝи®ҝй—®иҝҮжқҘзҡ„ пјҢ йҷӘеҗҢд»–зҡ„йҷӨдәҶеӨ«дәә пјҢ 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жҳҜжң¬ең°жӯҰиӯҰйғЁйҳҹзҡ„ж”ҝ委вҖқ пјҢ дәӢеӣ жҳҜ家йҮҢиө·жҲҝеӯҗ пјҢ дёҖзӣҙжңүдәӣдёҚжё…йқҷ пјҢ и®©д»–зңӢзңӢеӣҫзәё пјҢ жҳҜеҗҰеҶІзҠҜдәҶжҹҗж–№зҘһз…һ гҖӮиҝҷжҳҜеј йҒ“й•ҝиЁҖи°Ҳзҡ„дёҖиҙҜйЈҺж ј пјҢ и·ҹд»–йҷ…дјҡзҡ„дёҚжҳҜеӨ§дәәзү© пјҢ е°ұжҳҜжҹҗдёӘеҫҲеҺүе®ізҡ„йӮӘзҘҹ пјҢ зӣёжҜ”дёҖиҲ¬еңЁз»ҲеҚ—еұұдҝ®д»ҷзӮјдё№зҡ„йҒ“еЈ« пјҢ д»–зҡ„зңӢ家жң¬дәӢжҳҜжҚүй¬ј гҖӮи·ҹжҲ‘们е–қзқҖе®ўдәәйҖҒжқҘзҡ„йӣӘеі°еұұдә‘йӣҫиҢ¶ пјҢ еј йҒ“еЈ«е°ұжӯӨиҜҙејҖеҺ» пјҢ иҜҙеҲ°еүҚдёҖж®өеҺ»дәҶдёҖи¶ҹж№ҳиҘҝ пјҢ и·ҹдёҖдёӘжҒ¶й¬јж–—жі• пјҢ йӮЈжҳҜдёҖдёӘзү№еҲ«еҺүе®ізҡ„еҘій¬ј пјҢ еҫҲйҮҚзҡ„жҖЁж°”еҢ–жҲҗзҡ„ пјҢ жү‘йқўжҠҠжҸ’йҰҷзҡ„зұіеҚҮеӯҗжү“зҝ»дәҶ пјҢ зҷҪзұіж’’дәҶдёҖең°дёҖеұӢ пјҢ еј йҒ“еЈ«дёәдәҶ收жңҚеҘ№ пјҢ иә«дёҠиў«еҘ№зҡ„й•ҝжҢҮз”ІжқҘеҫҖжҠ еҮәдәҶеҮ еҚҒжқЎжү‘жЈұ пјҢ иҝҳиў«еҘ№еј„жҺүдәҶдёҖйў—й—Ёзүҷ пјҢ вҖңдҪ 们зңӢвҖқ пјҢ д»–еј ејҖеҳҙе·ҙ пјҢ и®©жҲ‘们жү“йҮҸй—Ёзүҷд»Ҙж—Ғзҡ„зүҷйҫҲдёҠзҡ„дёҖеӨ„з©әзјә пјҢ дјјд№Һд№ҹдёҚеғҸжҳҜж–°йІңз—•иҝ№ гҖӮ иҮідәҺйӮЈдёӘеҘій¬ј пјҢ жңҖз»ҲеҲ°еә•ж”¶жӢўеҲ°дәҶеј йҒ“еЈ«еҒҡжі•зҡ„зў—йҮҢ пјҢ иў«д»–зҝ»и…•зӣ–дҪҸ пјҢ зҝ»зӣ–ж—¶е·Із»Ҹж¶Ҳж•ЈдәҶ гҖӮ еӨҡе№ҙжқҘеј йҒ“й•ҝж–—иҝҮеҫҲеӨҡеҺүе®ізҡ„й¬ј пјҢ иҝҷдёӘеҘій¬јжҳҜжңҖеҺүе®ізҡ„дёҖдёӘ гҖӮиә«ж—Ғзҡ„е°ҸйҒ“еЈ«дёҖиҫ№еҶІиҢ¶жіЎж°ҙ пјҢ дёҖиҫ№е’ҢжҲ‘们дёҖиө·еҗ¬д»–иҒҠзқҖ пјҢ и„ёдёҠ似笑йқһ笑 пјҢ еј йҒ“й•ҝе°ұж•ҷи®ӯд»–вҖңи·ҹзқҖеёҲзҲ¶еҘҪеҘҪеӯҰжі• пјҢ 既然еҮәжқҘдәҶе°ұиҰҒе®үеҝғвҖқ пјҢ дјјд№ҺиҝҷдҪҚеҫ’ејҹеҮә家дёҚд№… пјҢ иҝҳжІЎжңүйӮЈд№ҲиёҸе®һ пјҢ зңӢдёҠеҺ»д№ҹзЎ®е®һжңүзӮ№еҝғдәӢйҮҚйҮҚ пјҢ и„ёдёҠй•ҝзқҖйўңиүІеҸ‘жҡ—зҡ„йқ’жҳҘз—ҳ пјҢ дјјд№ҺжңүдәӣиҗҘе…»дёҚиүҜ пјҢ иҝңиҝңдёҚеҸҠеј йҒ“й•ҝзҡ„ж°”иүІ гҖӮиҙўзҘһеәҷзҡ„е№ҙд»Јд№…иҝң пјҢ дҪҶ规жһ„并дёҚеӨ§ пјҢ еқҗеңЁжЎҢж—Ғе°Ҫ收зңјеә• пјҢ еҸӘжңүдёҖиҝӣжӯЈж®ҝ пјҢ дҫӣзқҖиҙўзҘһе’Ңе…іе…¬ гҖӮ еӨ§зәҰдёәдәҶдҪ“иҙҙйҰҷе®ўзҡ„йңҖжұӮ пјҢ ж—Ғиҫ№д№ҹдёҚеӨұе‘ЁеҲ°ең°дҫӣеҘүдәҶдёҖе°ҠйҖҒеӯҗи§Ӯйҹі гҖӮ зҘһеқӣиЈ…йҘ°дёҚз®—еҜ’й…ё пјҢ дҪҶд№ҹжІЎжңүеҫҲеӨҡеҜәеәҷеӨ§ж®ҝйҮ‘зў§иҫүз…ҢйӮЈз§Қж„ҹи§ү гҖӮеҒҸж®ҝжҳҜеј йҒ“еЈ«зҡ„дҪҸеӨ„ пјҢ дёҖеҸЈзјёйҮҢе ҶзқҖдёҚе°‘йҮ‘зәёе…ғе®қ пјҢ жҜ”иҙўзҘһеқӣдёҠзҡ„е°ҸдёҠеҮ еҸ· пјҢ еӨ§зәҰжҳҜдёәдәҶеҮҶеӨҮдёҚд№…дёҫеҠһзҡ„еәҷдјҡ гҖӮ еўҷдёҠиҝҳжҢӮзқҖдёҖе№…дёҚзҹҘе“ӘжқҘзҡ„еӯ—з”» гҖӮ еҸҰдёҖиҫ№зҡ„еҒҸж®ҝдёҠй”Ғ пјҢ е ҶзқҖдёҖдәӣжқӮзү© гҖӮ еҗҺйҷўе°ұжҳҜиҸңеӣӯ пјҢ дјјд№Һд№ҹжІЎжңүејҖиҫҹз§ҚжӨҚиө·жқҘ гҖӮ еүҚйҷўйқ иЎ—иҝҳжңүдёӨй—ҙжҲҝеӯҗ пјҢ еӨ§зәҰжҳҜеҫ’ејҹдҪҸзҡ„ гҖӮиҷҪз„¶еј йҒ“й•ҝзҘһйҖҡе№ҝеӨ§ пјҢ жҲ‘еҚҙйҡҗйҡҗжңүдёҖз§ҚиҝҷйҮҢйҰҷзҒ«дёҚж—әзҡ„ж„ҹи§ү пјҢ жҲ–и®ёеӣ дёәз§ҰеІӯи„ҡдёӢдҪӣеҜәеҠҝеҠӣеӨӘеӨ§зҡ„зјҳж•… пјҢ иҙўзҘһиҷҪ然е®һжғ пјҢ еҗҚеӨҙзҘһйҖҡжҜ”иө·еҰӮжқҘдҪӣзҘ–жҜ•з«ҹе·®дәҶеҘҪеӨҡ гҖӮејҖжҳҘд»ҘеҗҺеҶҚеҺ»еёғй•Ү пјҢ еј йҒ“й•ҝжӯЈеңЁеҝҷзўҢ пјҢ з»ҷиҙўзҘһеәҷй—ЁжҘЈдёҠжҢӮзҒҜз¬ј пјҢ йҒ“еёҪзҡ„еёҰеӯҗеңЁиҪ»еҜ’зҡ„йЈҺйҮҢеҫ®еҫ®жҠ–зҙў пјҢ иә«ж—Ғеё®еҝҷзҡ„дәәжҚўдәҶ пјҢ еҺҹжқҘзҡ„еҫ’ејҹеӨ§зәҰжү“дәҶйҖҖе Ӯйј“ гҖӮйҷўеӯҗдёҠз©әд№ҹжүҺдәҶеҪ©еёҰ пјҢ дёҖдёӘеё®еҝҷзҡ„з”·дәәжӯЈеңЁж“Ұжҙ— пјҢ зү§д№ӢиҜҙиҝҷжҳҜз»ҷеәҷдјҡеҒҡеҮҶеӨҮ пјҢ еәҷдјҡзҡ„дё»йўҳжҳҜжҳҘиҖ• гҖӮ дҝЎдҪӣзҡ„зү§д№ӢиҜҙ пјҢ е…¶е®һиҝҷдёӘиҠӮж—ҘжқҘиҮӘдәҺеҰӮжқҘдҪӣзҡ„з”ҹж—Ҙ пјҢ и·ҹйҒ“家没关系 пјҢ дҪҶжҳҜжӯЈи·ҹж’ӯйәҰзҡ„иҠӮж°”йҮҚеҗҲ пјҢ иө¶еәҷдјҡзҡ„дәәеӨҡзҡ„иҜқ пјҢ иҙўзҘһеәҷеҸҜд»ҘеҖҹжӯӨиөҡдёҖеӨ§е®—йҰҷзҒ«й’ұ гҖӮиҷҪ然еңЁеә”жҷҜеҝҷзўҢзқҖ пјҢ еҜ№дәҺеәҷдјҡзҡ„еүҚжҷҜ пјҢ еј йҒ“й•ҝжҳҫеҫ—并дёҚд№җи§Ӯ гҖӮ д»–дёҚеҶҚеғҸдёҠж¬Ўи§ҒйқўйӮЈж ·жғ…з»ӘйҘұж»Ў пјҢ иҖҢжҳҜжҠұжҖЁвҖңиҝҷйҮҢзҡ„дәәжІЎжңүдҝЎд»°вҖқ гҖӮ иҜҙеҲ°иҮӘе·ұжү“з®—зҰ»ејҖ пјҢ еҺ»д»–еҪ“е№ҙе…ҘйҒ“дҝ®иЎҢзҡ„зҰҸе»ә пјҢ йӮЈиҫ№зҡ„зҺҜеўғжҜ”иҝҷиҫ№еҘҪеҫ—еӨҡ гҖӮжһң然дёҚд№…д№ӢеҗҺ пјҢ еҗ¬зү§д№ӢиҜҙеј йҒ“й•ҝе·Із»ҸзҰ»ејҖ пјҢ дҪҶ并дёҚжҳҜеӣһзҰҸе»ә пјҢ иҖҢжҳҜеҺ»дәҶжІіеҚ— пјҢ д»ҘеҗҺеҸҲиҫ—иҪ¬еҺ»дәҶз§ҰзҡҮеІӣ гҖӮ йӮЈеңәеәҷдјҡиө¶дёҠж”ҝеәңйҷҗеҲ¶еӨ§еһӢжҙ»еҠЁ пјҢ еңәйқўжңүзӮ№еҶ·жё… пјҢ иҝҷеӨ§зәҰжҳҜеј йҒ“еЈ«еҺ»ж„ҸзЎ®е®ҡзҡ„еҺҹеӣ гҖӮиҙўзҘһеәҷе…ідәҶеҚҠе№ҙеӨҡ пјҢ зӣҙеҲ°е°‘йҷөеЎ¬дёҠзҡ„жқҺйҒ“й•ҝдёӢжқҘжҺҘд»» гҖӮжқҺйҒ“й•ҝжҳҜдёӘйҒ“姑 пјҢ зү§д№ӢиҜҙеҪ“е№ҙе°ұжҳҜиҙўзҘһеәҷзҡ„дҪҸжҢҒ пјҢ еҗҺжқҘеҺ»дәҶеЎ¬дёҠдҪҸжҢҒдёҖжүҖйҒ“и§Ӯ пјҢ еј йҒ“й•ҝжқҘиҙўзҘһеәҷжҳҜеҘ№д»Ӣз»Қзҡ„ пјҢ зҺ°еңЁеӣһжқҘд№ҹз®—йЎәзҗҶжҲҗз« гҖӮжқҺйҒ“й•ҝдёҚй•ҝдәҺзҘһйҖҡ пјҢ дҪҶеңЁжң¬ең°ж №еҹәж·ұеҺҡ пјҢ жҺҘжүӢд№ӢеҗҺиҙўзҘһеәҷжңүж–°ж°”иұЎ пјҢ 第дёҖе®—дәӢжҳҜзҝ»дҝ®еӨ§ж®ҝеұӢйЎ¶ гҖӮ иҝҷд№ҹз®—жҳҜеёғй•Үзҡ„дёҖ件еӨ§дәӢ пјҢ еҫҲеӨҡеұ…ж°‘еҮәдәҶй’ұ пјҢ зү§д№Ӣе°ұеҸ‘ж„ҝеҮәдәҶдёӨеҚғеқ— гҖӮ д»ҘеүҚзҡ„зӘ‘з“ҰеұӢйЎ¶йЈҺеҢ–жјҸйӣЁ пјҢ иҙўзҘһзҡ„е…ғе®қд№°дёҚйҖҡйЈҺдјҜйӣЁеёҲ пјҢ жіҘеЎ‘д№ӢзҘһжңүж—¶йҡҫе…ҚеҸ—зҙҜ пјҢ зҺ°еңЁжҚўжҲҗдәҶеҪ©й’ўз“Ұ пјҢ з“ҰжҘһеҚҮдёҠеҺ»дёӨе°ә пјҢ зӣёеҪ“дәҺеҶҚеҠ дәҶдёҖдёӘеӨ§еұӢйЎ¶ пјҢ иҙўзҘһе’Ңи§ӮйҹіеЁҳеЁҳд»ҺжӯӨй•ҝдҝқж— иҷһ гҖӮеҶҚж¬Ўиө°иҝӣиҙўзҘһеәҷйҷўеӯҗ пјҢ дәәж°”еўһеҠ дәҶдёҚе°‘ пјҢ йҷӨдәҶж–°зҡ„дҪҸжҢҒ пјҢ еӨҡдәҶдёҖдёӘе°ҸйҒ“姑 пјҢ иҝҳжңүдёҖдёӘд»ҺеЎ¬дёҠи·ҹйҡҸиҖҢжқҘзҡ„дёүеҚҒжқҘеІҒзҡ„еҗҺз”ҹ пјҢ ж—¶еёёеңЁеәҷйҮҢеүҚеҗҺеё®еҝҷ пјҢ еҸ«еҒҡдёүе®қ гҖӮ зҹіжЎҢзҡ„йҷҲи®ҫд№ҹж— з”ҡеҸҳеҢ– пјҢ йҷӨдәҶйӮЈжЈөж ‘дёҠиҙҙдәҶдёҖеј зҷҪзәёпјҡвҖңе®қе®қз—…дәҶ пјҢ жІЎй’ұиҫ“ж¶ІвҖқ гҖӮ жҲ‘й—®йҒ“й•ҝжҳҜдёҚжҳҜиҰҒеӢҹжҚҗж•‘ж ‘ пјҢ еҘ№еҫ®з¬‘дёҚиҜӯ гҖӮе№ҙиҪ»зҡ„йҒ“姑и·ҹд»ҘеүҚйӮЈдёӘе°ҸйҒ“еЈ«дёҖж ·й»‘зҳҰ пјҢ зңӢиө·жқҘдјјд№Һжңүз—… гҖӮ жҲ‘жҖҖз–‘дёүе®қд»ҺеЎ¬дёҠи·ҹдёӢжқҘжҳҜдёҚжҳҜж„ҸеңЁе°ҸйҒ“姑 пјҢ зү§д№Ӣе‘ҠиҜүжҲ‘全然зӣёеҸҚ пјҢ дёүе®қе’Ңе°ҸйҒ“姑жҳҜжӯ»еҜ№еӨҙ пјҢ жҠҠеҘ№еҸ«еҒҡвҖңй№…вҖқ пјҢ з»ҸеёёеңЁиғҢеҗҺдјёй•ҝдәҶи„–еӯҗжҜ”еҲ’еҘ№ пјҢ еӣ дёәе°ҸйҒ“姑жңүиғғз—… пјҢ еҗғйҘӯд№ӢеҗҺдјҡеғҸй№…дёҖж ·еҸ‘еҮәвҖңе‘ғе‘ғвҖқзҡ„еЈ°йҹі гҖӮ дёүе®қж•Ңи§Ҷе°ҸйҒ“姑зҡ„еҺҹеӣ жҳҜжңүеҘ№еңЁи·ҹеүҚ пјҢ еҰЁзўҚдәҶд»–жҺҘиҝ‘йҒ“й•ҝеёҲзҲ¶ гҖӮдёүе®қж„ҸеңЁйҒ“й•ҝ пјҢ иҷҪ然жқҺйҒ“й•ҝжҜ”д»–е№ҙй•ҝдәҶдәҢеҚҒеӨҡеІҒ гҖӮ йҒ“й•ҝеҜ№д»–зҡ„жҖҒеәҰжӯЈеғҸдёҖдёӘеҮә家дәәзҡ„дјҳе®№е№іж·Ў пјҢ иҷҪ然дёҚжҺ’ж–Ҙд»–еүҚеҗҺеё®еҝҷ пјҢ жңүж—¶д№ҹз•ҷд»–еҗғдёӯйҘӯ пјҢ еҲ°дәҶдёӢеҚҲеӣӣзӮ№й’ҹ пјҢ е°ұи®©жүҖжңүеӨ–дәәзҰ»ејҖ пјҢ е…ідёҠеәҷй—Ёж—©ж—©йҳІе«Ң гҖӮ дёүе®қиҲҚдёҚеҫ—еӣһеЎ¬дёҠ пјҢ еӣҙзқҖиҙўзҘһеәҷжү“иҪ¬ пјҢ иҪ¬дёҖйҳөеҲ°зү§д№ӢйҷўеӯҗйҮҢжқҘ пјҢ и¶ҙеңЁеӣҙеўҷдёҠиё®и„ҡе°–еҗ‘иҙўзҘһеәҷжү“жңӣ гҖӮ жңӣдёҖдјҡжІЎжңү收иҺ· пјҢ дјҡеҗ‘зү§д№ӢеҖҫиҜү пјҢ д»–жҳҜеҰӮдҪ•жҒӢж…•еёҲзҲ¶ пјҢ ж—Ҙеӯҗд№…дәҶжёҗжёҗеҸ№жҒҜ пјҢ вҖңзңӢжқҘжҲ‘еЁ¶еёҲзҲ¶жҳҜд»Ҡз”ҹж— жңӣдәҶпјҒвҖқжҲ‘и§ҒиҝҮд»–и¶ҙеңЁеӣҙеўҷдёҠиё®и„ҡжү“жңӣзҡ„е§ҝжҖҒ пјҢ д№ҹжӣҫз»Ҹе’Ңд»–жҗӯиҝҮдёҖдёӨеҸҘиҜқ пјҢ зңӢд»–дёҚиҝҮжҳҜдёӘз•Ҙеҫ®жҲҶзӣҙдәӣзҡ„еҜ»еёёйқ’е№ҙ гҖӮ д»–дёәдҪ•еҰӮжӯӨеҺҢе°ҸйҒ“姑иҖҢжҒӢж…•жқҺйҒ“й•ҝ пјҢ жҲ‘жІЎжңүжңәдјҡиҜўй—® гҖӮ зү§д№ӢиҜҙд»–зңӢиө·жқҘжңүдәӣеӮ» пјҢ е…¶е®һиҮӘжңүеҝғи®Ў пјҢ иӯ¬еҰӮд»–её®дәәеҒҡе·ҘжӢҝй’ұе®ҒиӮҜе°‘еҫ—дёҖдёӨеқ— пјҢ дёҖе®ҡиҰҒи®©дәәж¬ зқҖиҮӘе·ұ пјҢ еӣ дёәиҝҷжҳҜеҗғдәҸ пјҢ еҗғдәҸе°ұжҳҜз§Ҝж”’еҠҹеҫ· пјҢ жқҘдё–жңүзҰҸжҠҘ пјҢ дёҖзӮ№е„ҝд№ҹдёҚдәҸ гҖӮ д»–д»Ҡз”ҹзҡ„жү§зқҖжҒӢж…•йҒ“й•ҝ пјҢ дёҚзҹҘжҳҜеҗҰдёәжқҘз”ҹ姻зјҳдҝ®зҡ„зҰҸеҲҶ гҖӮж–°еҶ з–«жғ…жқҘдёҙ пјҢ еёғй•Үзҡ„еҗ„дёӘи·ҜеҸЈйғҪе°Ғе өдәҶ пјҢ иҝһеҗҢиҙўзҘһеәҷе’Ңзү§д№Ӣйҷўеӯҗд№Ӣй—ҙзҡ„е°ҸйҒ“ гҖӮ жқҺйҒ“й•ҝе…ідәҶеәҷй—Ё пјҢ йҷӨдәҶиҝҮеҮ еӨ©д№°дёҖж¬ЎиҸңи¶ідёҚеҮәжҲ· пјҢ и·ҹйҡҸеҘ№зҡ„е°ҸйҒ“姑е’Ңдёүе®қд№ҹеҗ„иҮӘеӣһ家дәҶ гҖӮ жңүдёҖеӨ©жё…жҷЁ пјҢ иҙўзҘһеәҷзҡ„й—Ёж„ҸеӨ–ең°ејҖзқҖ пјҢ йҒ“й•ҝеҺ»жҙҫеҮәжүҖжҠҘжЎҲ пјҢ зңӢдёҠеҺ»еҸ—еҲ°дәҶеҫҲеӨ§жғҠеҗ“ гҖӮеӨҙеӨ©жҷҡдёҠйҒ“й•ҝзқЎзқҖеҗҺ пјҢ жңүдёӘзӘғиҙјзҝ»еўҷж’¬й—ЁжәңиҝӣдәҶиҙўзҘһеәҷ пјҢ еңЁйҷўеӯҗйҮҢеҗ„дёӘжҲҝй—ҙиҪ¬дәҶдёҖйҖҡ пјҢ иҝҳеңЁйҒ“й•ҝзҡ„жҲҝй—ҙеӨ–иҫ№зӘҘжҺўдәҶеҚҠеӨ© пјҢ йҒ“й•ҝзқЎжўҰйҮҢйҡҗзәҰеҗ¬и§ҒдәҶеҠЁйқҷ гҖӮ йҒ“й•ҝжғҠеҗ“зҡ„еҺҹеӣ жҳҜ пјҢ иҙўзҘһеәҷеӨ§й—ЁиЈ…жңүзӣ‘жҺ§жҺўеӨҙ пјҢ д»ҺеҪ•еғҸйҮҢзңӢзӘғиҙјжҲҙзқҖдёҖеүҜйқўе…· пјҢ жғіеҲ°иҝҷеј жҲҙзқҖйқўе…·зҡ„и„ёеңЁзӘ—еӨ–зӘҘи§Ҷ пјҢ д»»жҳҜйҒ“й•ҝдҝ®дёәж·ұеҺҡ пјҢ д№ҹз”ұдёҚеҫ—дёҚеҗҺжҖ• гҖӮеӣ дёә并没жңүдёўеӨұеҖјй’ұзҡ„дёңиҘҝ пјҢ жЎҲеӯҗжңҖз»ҲжІЎжңүз ҙ гҖӮ жҲ‘жңүдёҖз§ҚйҡҗйҡҗзәҰзәҰзҡ„жҖҖз–‘пјҡзӘғиҙјжҲҙзқҖйқўе…·е…ҘеәҷзӘҘжҺў пјҢ жҳҜеҗҰдёәдәҶжҖ•йҒ“й•ҝи®ӨеҮәиҮӘе·ұ пјҢ е°ұжҳҜз»ҸеёёеҫҖжқҘзҡ„зҶҹдәәе‘ўпјҹпјҲеӣ дҝқжҠӨдәәзү©йҡҗз§Ғ пјҢ еёғй•ҮдёәеҢ–еҗҚпјүеҫҒзЁҝж— и®әдё»еҠЁиҝҳжҳҜиў«еҠЁ пјҢ еҹҺеёӮжӯЈжҲҗдёәжҲ‘们жңҖдёәдё»иҰҒзҡ„з”ҹжҙ»з©әй—ҙ гҖӮдёҖд»ЈеҸҲдёҖд»Јзҡ„дәә пјҢ иў«еҹҺеёӮжүҖеЎ‘йҖ зқҖ пјҢ д№ҹеЎ‘йҖ зқҖеҹҺеёӮ пјҢ е®Ўи§ҶзқҖз”ҹжҙ» пјҢ д№ҹиў«з”ҹжҙ»е®Ўи§Ҷ гҖӮ жҲ‘们жҜҸдёӘдәә пјҢ йғҪеӣ дёҚеҗҢзҡ„ж—¶д»ЈдёҺдёӘдәәйҒӯйҷ… пјҢ еңЁеҝғеә•е»әжһ„еҮәеҹҺеёӮзҡ„дёҮиҲ¬жЁЎж · гҖӮ2020жҳҜдёӘиў«иҝ«зҰҒи¶ізҡ„е№ҙд»Ҫ гҖӮ ж— и®әжҲ‘们дәәеңЁдҪ•еӨ„ пјҢ жҳҜж·Ўе®ҡгҖҒжҳҜзғҰиәҒ пјҢ жҳҜдёҖзӯ№иҺ«еұ•гҖҒжҳҜеҝғжңүдҪҷжӮё пјҢ йғҪжҳҜдёҖдёӘйҖӮеҗҲзҡ„жңәдјҡ пјҢ и®©еҫҲеӨҡдәәйҮҚж–°е®Ўи§ҶиҮӘе·ұдёҺвҖңдёҖеә§еҹҺеёӮвҖқзҡ„е…ізі» гҖӮзңјдёӢ пјҢ дәәй—ҙзј–иҫ‘йғЁеӨ§еһӢеҫҒж–ҮеҶҚдёҖж¬ЎејҖеҗҜвҖ”вҖ”гҖҢдәәй—ҙВ· дәәеңЁеҹҺдёӯLiving in CityгҖҚ гҖӮи®°еҪ•дёӢдҪ дёҺиҮӘе·ұзҺ°еңЁжҲ–жӣҫз»ҸжүҖеӨ„еҹҺеёӮзҡ„ж•…дәӢ пјҢ и®°еҪ•дёӢе®ғеҜ№жҲ‘们жҜҸдёҖдёӘдәәжүҖжҸҗеҮәзҡ„ пјҢ е…ідәҺжўҰжғігҖҒзҲұдёҺеёҢжңӣй—®йўҳзҡ„зӯ”еӨҚ пјҢ и®°еҪ•дёӢжүҖжңүдҪ еңЁжӯӨеӨ„еҝөеҝөдёҚеҝҳзҡ„дәәдёҺдәӢ пјҢ и®°еҪ•дёӢе®ғеҸӘеұһдәҺдҪ зҡ„гҖҒзӢ¬дёҖж— дәҢзҡ„жЁЎж ·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иҖҒеӯҗе°ұжҳҜиҖҒеӯҗ
- еј еҪҰжҳҺ|жңҖзҫҺжҠӨжһ—е‘ҳпҪңйҷ•иҘҝеј еҪҰжҳҺпјҡе®ҲжҠӨз§ҰеІӯз”ҹжҖҒ еҘүзҢ®йқ’жҳҘе№ҙеҚҺ
- дәәй—ҙ | 姑姑36е№ҙзҡ„дёӯеӣҪејҸе©ҡ姻пјҢз»ҲдәҺеҲ°еӨҙдәҶ
- ж–°еҝ«жҠҘ|з§ҰеІӯйҮҺз”ҹеҠЁзү©еӣӯзҪ‘з«ҷжҢҮж¶үй»„ еҠЁзү©еӣӯеӣһеә”пјҡиў«жҒ¶ж„ҸзҜЎж”№
- йҷ•и§Ҷж–°й—»|еҲҡеҲҡпјҢжү“ејҖиҘҝе®үз§ҰеІӯйҮҺз”ҹеҠЁзү©еӣӯе®ҳзҪ‘з«ҹи·іиҪ¬ж¶үй»„зҪ‘з«ҷ
- ж°‘й—ҙеҖҹиҙ·|еҲӨдәҶпјҢжҒӢдәәй—ҙзҡ„иҝҷзұ»иҪ¬иҙҰиЎҢдёәпјҢйҡҫд»Ҙи®Өе®ҡдёәеҖҹж¬ҫпјҒ
- гҖҠзәўзҒҜи®°гҖӢж°ёиҝңеңЁдәәй—ҙ
- йқ’е№ҙ|еҘіеӯҗж…Ңеҝҷиө¶еҫҖеҢ»йҷўпјҢзӘҒ然и„ҡдёӢжӢ–зқҖдёҖзү©пјҢзҺ°еңәзҡ„дәәдёҚж·Ўе®ҡдәҶ
- иҖҒеӯҗд№ӢвҖңйҒ“вҖқз»ҲдәҺжҸӯз§ҳпјҢдәәй—ҙзҹӣзӣҫеҝ…然з»ҲжӯўпјҒ
- дёҖдёӘдәәй—ҙзңҹе®һиҙҙпјҢиә«й«ҳдёҚйҮҚиҰҒпјҢй’ұйҮҚиҰ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