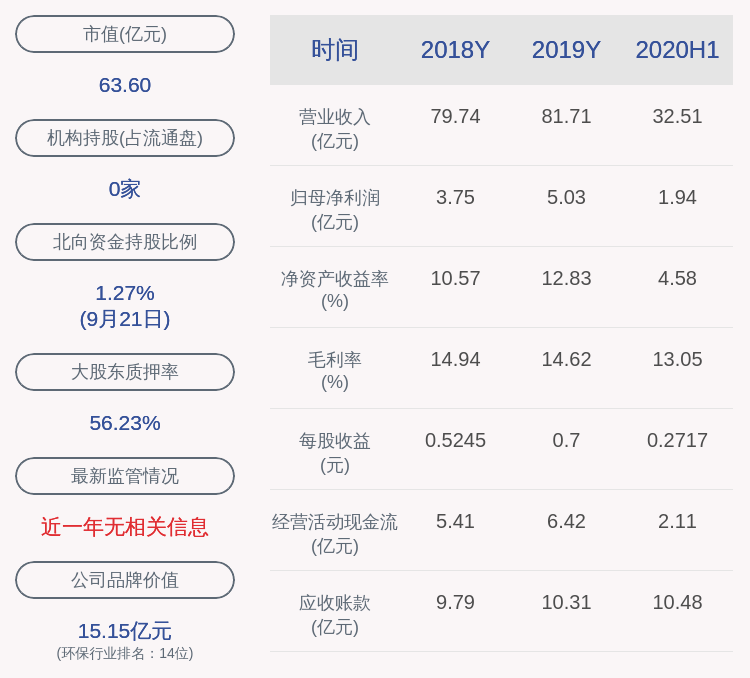дәәй—ҙжңүе‘і|е„ҝж—¶зҡ„еҗғйЈҹиҝҳеңЁпјҢ家乡еҚҙдёҚеҶҚжҳҜж•…д№Ў
жң¬ж–Үзі»зҪ‘жҳ“вҖңдәәй—ҙвҖқе·ҘдҪңе®ӨпјҲthelivingsпјүеҮәе“Ғ гҖӮжң¬ж–ҮдёәвҖң дәәй—ҙжңүе‘і вҖқиҝһиҪҪ第91жңҹ гҖӮ

1и’ёеҮ з¬јвҖңжҺЁжөҶйҪҗвҖқ пјҢ зғӯеҮ еЈ¶зұій…’ пјҢ еҶҚжқҘдәӣдёӢй…’иҸң пјҢ дәІжңӢеҘҪеҸӢеӣҙеқҗеңЁжҹҙзҒ«зҒ¶еүҚе–қй…’иҒҠеӨ© пјҢ иҝҷжӣҫжҳҜиөЈеҚ—客家дәәж—§ж—ҘйҮҢжҠ№дёҚжҺүзҡ„и®°еҝҶ гҖӮиҝҷз§Қж—©е№ҙиў«з»ҹз§°дёәвҖңзіҚзІ‘вҖқзҡ„еҗғйЈҹ пјҢ иүІжіҪйҮ‘й»„ пјҢ еј№зүҷзҲҪеҸЈ пјҢ еёҰзқҖеӨ©з„¶иҚүжңЁзҒ°зҡ„жё…йҰҷ пјҢ еңЁйЈҹзү©зҹӯзјәзҡ„е№ҙд»Ј пјҢ еӨ§е®¶еҸӘжңүйҖўе№ҙиҝҮиҠӮжүҚиҲҚеҫ—еҒҡ гҖӮ еҲ¶дҪңж—¶ пјҢ йңҖиҰҒдёҖ家иҖҒе°ҸйҪҗеҝғеҚҸеҠӣ пјҢ еӨ§дәәжҺЁзЈЁ пјҢ еӯ©еӯҗеҠ ж–ҷ пјҢ ејҖеҗғд№ӢеүҚдҫҝжңүдёҠеә§зҡ„й•ҝиҫҲеҖҹзқҖи°җйҹі пјҢ е°Ҷе®ғеҸ«еҒҡвҖңжҺЁжөҶйҪҗпјҲзіҚпјүвҖқ пјҢ дҪҝиҝҷз§ҚйЈҹзү©жңүдәҶвҖң全家йҪҗеҝғвҖқзҡ„еҜ“ж„Ҹ гҖӮйҡҸзқҖдёҠдёҖиҫҲзҡ„дәәиҖҒеҺ» пјҢ е№ҙиҪ»дәәеӨ–еҮәе®ҡеұ…дёҚеҶҚеҪ’д№Ў пјҢ вҖңжҺЁжөҶйҪҗвҖқд№ҹжҚўдәҶдёӘжҙӢж°”зҡ„еҗҚеӯ—вҖ”вҖ”вҖңзЈЁж–ӢвҖқ пјҢ еҗҚеӯ—иғҢеҗҺзҡ„еҗ«д№үд№ҹйҖҗжёҗжІЎдәәеңЁд№ҺдәҶ гҖӮзЈЁж–Ӣзҡ„еҲ¶дҪңз№ҒзҗҗеӨҚжқӮпјҡжҠҠдҝ—з§°вҖңеҗҠиҢ„еӯҗж ‘вҖқзҡ„ж ‘жһқеҺ»зҡ® пјҢ ж”ҫеңЁй”…йҮҢеҠ ж°ҙзҶ¬жұӨ пјҢ еҶҚз”ЁзЁ»иҚүжҲ–й»„иұҶжқҶзғ§жҲҗзҡ„зҒ° пјҢ дёҺжұӨж°ҙж··еҗҲеңЁдёҖиө·жҗ…жӢҢеқҮеҢҖиҝҮж»Ө пјҢ еҫ…иҝҮж»ӨеҘҪзҡ„зҗҘзҸҖиүІвҖңзҒ°ж°ҙвҖқеҶ·еҚҙеҗҺ пјҢ дҫҝжҠҠзІізұіж”ҫиҝӣеҺ»жөёжіЎвҖ”вҖ”иҝҷзұід№ҹжңү讲究 пјҢ йЎ»йҖүдёҚеҘҪеҗғзҡ„зІізұі пјҢ дёҚ然еҒҡеҘҪзҡ„зЈЁж–ӢдјҡеҫҲзІҳзүҷ пјҢ жІЎжңүйҹ§жҖ§ гҖӮжіЎеҘҪзҡ„зІізұіиҰҒеңЁдёҖ家дәәзҡ„еҗҲдҪңдёӢз”ЁзҹізЈЁзўҫжҲҗзұіжөҶ пјҢ еҶҚжҠҠзұіжөҶеҖ’е…ҘжҹҙзҒ«еӨ§й”… пјҢ е°ҸзҒ«з…ЁдёҠ пјҢ ж…ўж…ўз”Ёй”…й“Ізҝ»еҠЁгҖҒжҢӨеҺӢ пјҢ зұіжөҶзҶ¬е№ІдәҶж°ҙеҲҶ пјҢ дәәж№ҝйҖҸдәҶиЎЈиЎ« гҖӮ зІҳзЁ зҡ„зұізіҠжҚһиө·жқҘ пјҢ ж”ҫеңЁеӨ§з°ёз®•йҮҢ пјҢ жҠ№дәӣеұұиҢ¶жІ№ пјҢ жҗ“жҸүжҲҗйҹ§жҖ§еҚҒи¶ізҡ„й•ҝжқЎ пјҢ жҲ–еҒҡжҲҗеҪўдјјйҘәеӯҗвҖңеүӮеӯҗвҖқзҡ„еҪўзҠ¶ пјҢ еҶҚеҢ…дёҠйҰ…е„ҝ гҖӮз«№и’ёз¬јеә•е„ҝдёҠеһ«дәӣзЁ»иҚү пјҢ жҗ“пјҲеҢ…пјүеҘҪзҡ„зЈЁж–Ӣж”ҫеңЁдёҠйқў пјҢ и’ёдёҠеҚҠе°Ҹж—¶ пјҢ жҺҖејҖзӣ–еӯҗ пјҢ дёҖиӮЎеҲ«ж ·зҡ„йҰҷе‘ідҫҝзӣҙжү‘йј»е°–е„ҝ гҖӮ е°Ҹж—¶еҖҷ пјҢ зЈЁж–ӢдёҖеҮәй”… пјҢ жҲ‘дҫҝеҗөзқҖиҰҒеҗғ пјҢ дёҚз®ЎеӨҡзғ« пјҢ жӢҝзқҖеқҗеңЁй—Ёж§ӣдёҠ пјҢ е°Ҷе®ғеңЁдёӨеҸӘжүӢдёӯдёҚеҒңең°еҖ’жқҘеҖ’еҺ» пјҢ йј“и…®еҗ№ж°” пјҢ иҲҚдёҚеҫ—ж”ҫдёӢ гҖӮзЈЁж–Ӣзҡ„йҰ…е„ҝ пјҢ еёёжҳҜиҗқеҚңгҖҒеҶ¬з¬ӢгҖҒе’ёиҸңзӯүеҒҡзҡ„ пјҢ дёҖеҸЈдёӢеҺ» пјҢ з»өиҪҜи„Ҷе«© пјҢ еӨ№зқҖеӣӣеӯЈзҡ„е‘ійҒ“ гҖӮ жҲ‘家е–ңиҫЈ пјҢ йҰ…е„ҝйҮҢдҫҝеӨ№зқҖдёҚе°‘зәўй»„зҡ„жңқеӨ©жӨ’ пјҢ еҮ дёӘеҗғдёӢеҺ» пјҢ е’§еҳҙжөҒж¶Һ пјҢ йўқеӨҙеҶ’жұ— пјҢ дҪҶеҳҙз»қдёҚиӮҜеҒңжӯўе’Җеҡј гҖӮжҗ“жҲҗй•ҝжқЎеҪўзҡ„зЈЁж–Ӣ пјҢ еҲҷжҳҜеҲҮзүҮеҲҮеқ— пјҢ иҳёй…ұж°ҙеҗғ пјҢ жҲ–зӮ’жҲ–дёӢжұӨ гҖӮ жңқеӨ©жӨ’гҖҒи’ңи“үгҖҒи‘ұиҠұгҖҒй…ұжІ№гҖҒиҠқйә»йҰҷжІ№дҪңеә• пјҢ ејҖж°ҙдёҖеҶІ пјҢ еҗ„з§ҚйҰҷе‘ідёҖзӮ№дёҖзӮ№ж•ЈеңЁз©әж°”еҪ“дёӯ гҖӮ зЈЁж–ӢиҳёдёҠй…ұж°ҙе…ҘеҸЈ пјҢ е…ҲжҳҜй…ұжІ№зҡ„е’ёйҰҷеӨ№зқҖиҚүжңЁзҒ°зҡ„йҰҷж°”ж¶Ңе…Ҙйј»и…” пјҢ зҙ§жҺҘзқҖиҫЈжӨ’и’ңи“үйҰҷжІ№зҡ„е‘ійҒ“жҺҘиёөиҖҢиҮі пјҢ жҢӨж»ЎеҸЈи…” пјҢ еҫ…еҗ„з§Қе‘ійҒ“жҸүеҗҲеңЁдёҖиө· пјҢ еҸҚиҖҢи®©еҳҙйҮҢж„ҹеҲ°з”ңдёқдёқзҡ„ гҖӮиӢҘжҳҜиҰҒзғ№зӮ’еҒҡжұӨ пјҢ е°ұеҺ»з”°ең°йҮҢжҚЎе«©зҡ„иҸңиҠұ пјҢ жҺҗе°–ж”ҫиҝӣжұӨйҮҢжҲ–иҖ…зӮ’зқҖеҗғ пјҢ иҸңиҠұзҡ„зҝ з»ҝжё…йҰҷ пјҢ й…ҚдёҠзЈЁж–Ӣзҡ„зІүй»„еҠІйҒ“ пјҢ иүІйҰҷе‘ідҝұе…Ё гҖӮ2йҷӨйҖўе№ҙиҝҮиҠӮд№ӢеӨ– пјҢ жҜҚдәІжңүж—¶д№ҹдјҡеңЁжҳҘйӣЁж—¶иҠӮеҒҡзЈЁж–Ӣ гҖӮ иҝһз»өзҡ„йӣЁж°ҙи®©дәәж— жі•дёӢз”° пјҢ дҫҝдјҡжңүзӣёзҶҹзҡ„дәәжқҘжүҫжҜҚдәІиҒҠеӨ© пјҢ иҒҠзқҖиҒҠзқҖе°ұдјҡжңүдәәжҸҗи®®еҒҡзЈЁж–Ӣ гҖӮ жҜҚдәІдјҡзғӯдәӣиҮӘй…ҝзҡ„зұій…’ пјҢ еҮ дәәиҫ№е–қиҫ№еҮҶеӨҮеҺҹж–ҷ пјҢ жҲ‘ж—¶еёёи№ІеңЁзҒ¶еүҚ пјҢ жӢҝзқҖеҗ№зҒ«зӯ’е’ҢзҒ«й’іеё®жҜҚдәІзңӢзҒ« пјҢ дёҖиҫ№жҙҘжҙҘжңүе‘іең°еҗ¬еҘідәә们дёң家й•ҝиҘҝ家зҹӯ пјҢ дёҖиҫ№еҗ¬зқҖзӘ—еӨ–йӣЁж°ҙж»ҙзӯ”ж»ҙзӯ”зҡ„еЈ°йҹі гҖӮ жңүж—¶еҗ¬зқҖеҗ¬зқҖ пјҢ е°ұеҖҡзқҖзҒ¶еүҚйқўзқЎзқҖдәҶ пјҢ зӯүжҜҚдәІеҸ«йҶ’жҲ‘зҡ„ж—¶еҖҷ пјҢ зғӯж°”и…ҫи…ҫзҡ„зЈЁж–Ӣе·Із»ҸеҮәз¬јдәҶ гҖӮ家йҮҢ家еӨ– пјҢ жҜҚдәІд»ҺжңӘеҒңдёӢиҝҮеҠідҪңзҡ„иә«еҪұ пјҢ еғҸжҳҜдёҖеӨҙиў«з”ҹжҙ»и’ҷдёҠдәҶзңјзқӣзҡ„й©ҙеӯҗ пјҢ еҸӘдјҡжІҝзқҖз”ҹжҙ»з»ҷзҡ„и·ҜзәҝдёҚеҒңең°з»•зқҖзЈЁзӣҳиҪ¬еңҲ гҖӮ еҒҡжқ‘ж”Ҝд№Ұзҡ„зҲ¶дәІеёёеёёж·ұеӨңжүҚеӣһжқҘ пјҢ иҝ·иҝ·зіҠзіҠдёӯжҲ‘иғҪеҗ¬и§ҒејҖй”Ғзҡ„еЈ°йҹі пјҢ иҖҒж—§зҡ„жңЁй—ЁвҖңеҗұе‘ҖвҖқиў«жҺЁејҖ гҖӮеҖҳиӢҘйҡ”зқҖй—Ёе°ұй—»еҲ°дәҶзЈЁж–Ӣзҡ„е‘ійҒ“ пјҢ зҲ¶дәІдјҡеҡ·еҡ·зқҖе–ҠжҜҚдәІпјҡвҖңе—Ҝпјҹд»ҠеӨ©жҖҺд№ҲеҒҡдәҶжҺЁжөҶйҪҗпјҹеҸҲжөӘиҙ№дёҖеӨ©пјҒиө·жқҘеё®жҲ‘зғӯдёҖдёӢпјҒвҖқиӢҘжҚўдҪңе№іж—Ҙ пјҢ иҝҷд№Ҳжҷҡиҝҳиў«е–Ҡиө·жқҘе№Іжҙ» пјҢ зҙҜдәҶдёҖеӨ©зҡ„жҜҚдәІиӮҜе®ҡдјҡжҒјзҒ« пјҢ дёҖйЎҝдәүеҗөжҳҜе°‘дёҚдәҶзҡ„ пјҢ дҪҶеҒҸеҒҸеңЁзғӯзЈЁж–Ӣиҝҷ件дәӢжғ…дёҠ пјҢ дёҚз®ЎеӨҡжҷҡ пјҢ жҜҚдәІйғҪдјҡдёҖеЈ°дёҚеҗӯең°д»ҺеәҠдёҠзҲ¬иө·жқҘз»ҷзҲ¶дәІеҮҶеӨҮеҘҪ пјҢ 然еҗҺжҠ«зқҖиЎЈжңҚеқҗеңЁзҲ¶дәІж—Ғиҫ№еҫ…д»–еҗғе®ҢгҖҒ收жӢҫе№ІеҮҖдәҶжүҚеҶҚж¬ЎеҺ»зқЎ гҖӮжңүж—¶жҲ‘еӣ дёәиў«зҲ¶дәІеҗөйҶ’иҖҢдҪңжҒј пјҢ и®©жҜҚдәІеҲ«иҝҷд№ҲжғҜзқҖзҲ¶дәІ пјҢ еҘ№жҖ»жҳҜ笑зқҖе—”жҖӘжҲ‘пјҡвҖңдҪ з»Ҷдјўеӯҗз®Ўиҝҷд№ҲеӨҡе№Іеҳӣ гҖӮ вҖқиҝҷе…¶дёӯзҡ„еҺҹеӣ пјҢ еҗҺжқҘжҲ‘жүҚзҹҘйҒ“ гҖӮзҲ¶дәІе°Ҹж—¶еҖҷ пјҢ зҘ–зҲ¶жҜҚй—№зҰ»е©ҡ пјҢ зҘ–зҲ¶еңЁеҲ«зҡ„й•ҮдёҠж•ҷд№Ұ пјҢ еёҰзқҖеҮ дёӘеӯ©еӯҗдёҚеӣһ家 пјҢ зҘ–жҜҚдёҖж°”д№ӢдёӢд№ҹеёҰзқҖеҮ дёӘеӯҗеҘіеӣһдәҶеЁҳ家 пјҢ е”ҜзӢ¬з•ҷдёӢзҲ¶дәІдёҖдёӘдәәеңЁе®¶йҮҢ гҖӮ е№ҙе№јзҡ„зҲ¶дәІжІЎеҠһжі•з…§йЎҫиҮӘе·ұ пјҢ еҸӘиғҪи·ҹзқҖд»–зҡ„зҘ–жҜҚ гҖӮ еӨӘзҘ–жҜҚйқһеёёжҠ й—Ё пјҢ дёҚе–ң欢家йҮҢеҮӯз©әж·»дәҶеј еҳҙ пјҢ йӣҶдҪ“жҢүдәәеӨҙеҲҶз»ҷзҲ¶дәІзҡ„еҸЈзІ®з»Ҹеёёиў«еҘ№и—Ҹиө·жқҘ пјҢ жҜҸеӨ©еҸӘз»ҷжҲ‘зҲ¶дәІдёҖйЎҝйҘӯеҗғ гҖӮ жҲ‘зҲ¶дәІйӮЈж—¶еёёеёёиәәеңЁи·Ҝиҫ№дёҖеҠЁдёҚеҠЁ пјҢ еӣ дёәдёҖеҠЁе°ұзҠҜжҷ• пјҢ жқ‘йҮҢдәәзңӢзқҖд»–и„–еӯҗз»Ҷеҫ—з”ЁжүӢжҺҗдёҖдёӢе°ұиғҪж–ӯзҡ„ж ·еӯҗ пјҢ йғҪи§үеҫ—д»–иҝҹж—©дјҡиў«йҘҝжӯ» гҖӮжңүдёҖе№ҙжқ‘йҮҢзІ®йЈҹ丰收 пјҢ з”ҹдә§йҳҹз ҙеӨ©иҚ’еҒҡдәҶдёҖдәӣвҖңжҺЁжөҶйҪҗвҖқеәҶзҘқ гҖӮ е№ҙе№јзҡ„зҲ¶дәІи¶ҒеӨ§дәәдёҚжіЁж„Ҹ пјҢ еҒ·дәҶдҫҝи·‘ пјҢ еңЁеӣһ家зҡ„и·ҜдёҠеҗғдәҶдёҖдәӣ пјҢ з•ҷдәҶеҮ дёӘеҮҶеӨҮеҪ“дҪңжҷҡйӨҗ пјҢ жІЎжғіеҲ°дёҖеӣһ家 пјҢ зЈЁж–Ӣдҫҝиў«еӨӘзҘ–жҜҚеӨәиө°дәҶ гҖӮзҲ¶дәІй—®пјҡвҖңеҘ¶еҘ¶ пјҢ иҝҷжҳҜжҲ‘зҡ„еӨңйҘӯ пјҢ жҲ‘жҷҡдёҠжҒ°д»Җд№ҲпјҹвҖқеӨӘзҘ–жҜҚиҜҙпјҡвҖңеҝ«зқЎеҗ§ пјҢ зқЎзқҖдәҶе°ұдёҚйҘҝ гҖӮ вҖқдёӯеҚҲеҗғзҡ„йӮЈйЎҝзЈЁж–ӢжҳҜзҲ¶дәІйӮЈеҮ е№ҙдёӯе”ҜдёҖеҗғзҡ„дёҖйЎҝйҘұйҘӯ пјҢ д»ҺжӯӨд»ҘеҗҺ пјҢ йҘҘйҘҝи®°еҝҶдҫҝи®©д»–еҜ№жҺЁжөҶйҪҗжңүдәҶзӢ¬зү№зҡ„жғ…ж„ҹ гҖӮ зҲ¶дәІеӣһеҝҶиө·иҝҷ件дәӢжғ…ж—¶жҖ»жҳҜдёҖи„ёиӢҰ涩пјҡвҖңжҲ‘е°Ҹж—¶еҖҷжІЎжңүеҫ—зқҖзҲ¶жҜҚзҡ„зҲұ пјҢ еӨҡе°‘ж¬Ўе·®зӮ№йҘҝжӯ» пјҢ дҪ дјҜдјҜеҸ”еҸ”们еҫ…йҒҮжҜ”жҲ‘еҘҪеӨҡдәҶ пјҢ еҮ дёӘе…„ејҹжҲ‘е‘ҪжңҖиӢҰ гҖӮ вҖқеҮ е№ҙеҗҺ пјҢ зҘ–зҲ¶жҜҚе’Ңи§Ј пјҢ зҲ¶дәІжүҚеҫ—д»ҘйҮҚж–°еҗғдёҠйҘұйҘӯ гҖӮ дҪҶзҘ–жҜҚдёҚж“…й•ҝеҒҡе°Ҹеҗғ пјҢ зҲ¶дәІйҰӢзЈЁж–ӢдәҶ пјҢ еҸӘиғҪйҒҮи§Ғи°Ғ家еҒҡзҡ„ж—¶еҖҷ пјҢ жүҫдёӘзҗҶз”ұеҺ»вҖңжү“з§ӢйЈҺвҖқ гҖӮиҝҷз§ҚзҠ¶еҶө пјҢ зӣҙеҲ°жҜҚдәІеҮәзҺ°еңЁзҲ¶дәІзҡ„з”ҹжҙ»дёӯж—¶ пјҢ жүҚеҫ—д»Ҙж”№еҸҳ гҖӮжҲ‘еӨ–е…¬еңЁз”ҹдә§йҳҹйҮҢйҘұеҸ—йҳҹй•ҝж¬әиҙҹ пјҢ д»–жҠҠеҺҹеӣ еҪ’з»“дәҺ家йҮҢжІЎжңүвҖңеҗғе…¬зІ®вҖқзҡ„ пјҢ е°Ҫз®ЎзҲ¶дәІй«ҳдёӯжҜ•дёҡеҗҺеҸӘжҳҜжқ‘йҮҢзҡ„е°Ҹдјҡи®Ў пјҢ дҪҶеӨ–е…¬иҝҳжҳҜзӣёдёӯдәҶд»– пјҢ жүҳеӘ’дәәиҜҙдәІ гҖӮ зҘ–зҲ¶жҳҜиҖҒеёҲ пјҢ еӯҗеҘідёӯеҘҪеҮ дёӘйғҪжҳҜеҗғ公家йҘӯзҡ„ пјҢ иҮӘи§Ҷз”ҡй«ҳ пјҢ еҝғйҮҢдёҚеҗҢж„Ҹиҝҷй—ЁдәІдәӢ пјҢ дҪҶдёҚжғіжӢӮдәҶеӘ’дәәзҡ„йқўеӯҗ пјҢ дҫҝзӯ”еә”еёҰзҲ¶дәІдёҠй—ЁзңӢзңӢ гҖӮеӨ–е…¬дёәдәҶиЎЁзҺ°зңӢйҮҚиҝҷй—ЁдәІдәӢ пјҢ жҠҠ家йҮҢз§Ҝж”’дәҶеӨҡе№ҙзҡ„зІізұіжӢҝеҮәжқҘеҒҡдәҶзЈЁж–ӢжӢӣеҫ… пјҢ зҲ¶дәІи·ҹзқҖзҘ–зҲ¶еңЁе®ўеҺ…дёҺеӨ–е…¬иҒҠеӨ© пјҢ жҲ‘жҜҚдәІеҲҷеңЁй©¬и·ҜеҜ№йқўзҡ„еҺЁжҲҝйҮҢеё®иЎ¬еӨ–е©Ҷ гҖӮ дёӯеҚҲеҗғйҘӯзҡ„ж—¶еҖҷ пјҢ зҘ–зҲ¶и§үеҫ—иҝҷйҒ“зЈЁж–ӢеҘҪеҗғ пјҢ дҫҝеӨёжҲ‘жҜҚдәІпјҡвҖңдҪ еҒҡзҡ„жҺЁжөҶйҪҗ пјҢ жҖ•жҳҜзӮүиҝіжқ‘第дёҖдәҶ гҖӮ вҖқвҖ”вҖ”йғҪиҜҙиҝҷ家зҡ„еҘіе„ҝеӢӨеҠіиғҪе№І пјҢ зҷҫй—»дёҚеҰӮдёҖи§Ғ пјҢ зҘ–зҲ¶зӮ№дәҶеӨҙ пјҢ жІЎиҝҮеӨҡд№… пјҢ жҲ‘жҜҚдәІе°ұиҝҮй—ЁдәҶ гҖӮдҪҶе…¶е®һ пјҢ йӮЈж—¶жҲ‘жҜҚдәІиҝҳж №жң¬дёҚдјҡеҒҡзЈЁж–Ӣ пјҢ еЁҳ家зҡ„еҗ„з§Қе°Ҹеҗғ пјҢ е№іж—ҘйҮҢйғҪжҳҜеӨ–е©ҶеҒҡзҡ„ гҖӮ жҲ‘зҲ¶жҜҚ第дёҖж¬ЎвҖңдјҡйқўвҖқзҡ„йӮЈеӨ© пјҢ еқҗеңЁе®ўеҺ…йҮҢзҡ„зҲ¶дәІеҸӘжҳҜиҝңиҝңзһ§и§ҒжҜҚдәІеңЁеҚ–еҠӣең°жҗ“жҸүзқҖзұізіҠ пјҢ 并дёҚзҹҘйҒ“еӨ§йғЁеҲҶе·ҘеәҸйғҪжҳҜз”ұеӨ–е©Ҷе®ҢжҲҗзҡ„вҖ”вҖ”йӮЈеӨ©жҲ‘жҜҚдәІеҸӘжҳҜй—ІдёҚдёӢжқҘ пјҢ йЎәжүӢеё®еӨ–е©ҶжҜ”еҲ’дәҶеҮ дёӢ пјҢ еҒҸе·§е°ұиў«зҲ¶дәІзңӢеҲ°дәҶ гҖӮеҘҪеңЁжҜҚдәІе«ҒиҝҮжқҘеҗҺ пјҢ 家йҮҢзІ®йЈҹзҙ§еј пјҢ зҘ–жҜҚз®Ўеҫ—дёҘ пјҢ еҘ№д№ҹжІЎжңәдјҡжҚЈи…ҫиҝҷдәӣе°Ҹеҗғ гҖӮ зӣҙеҲ°еҮ е№ҙд№ӢеҗҺеҲҶз”°еҲ°жҲ· пјҢ зІ®йЈҹејҖе§ӢжңүдәҶз»“дҪҷ пјҢ иҝҷеұӮзӘ—жҲ·зәёжүҚиў«жҚ…з ҙ гҖӮжҜҚдәІдё“й—ЁеӣһеЁҳ家еҗ‘еӨ–е©ҶжұӮж•ҷжҖҺд№ҲеҒҡзЈЁж–Ӣ пјҢ дҪҶжҳҜзҲ¶дәІдҫқж—§еҜ№зӣёдәІж—¶е°қеҲ°зҡ„е‘ійҒ“еҝөеҝөдёҚеҝҳ гҖӮ жҲ‘е°Ҹж—¶еҖҷеёёеҗ¬зҲ¶дәІиҜҙпјҡвҖңдҪ еҰҲиҝҷд№ҲеӨҡе№ҙжүӢиүәиҝҳжҳҜжІЎжңүй•ҝиҝӣ пјҢ дҪ еӨ–е©ҶеҒҡзҡ„жҺЁжөҶйҪҗеҘҪеҗғеӨҡдәҶ пјҢ еҸӘеҸҜжғңзҺ°еңЁдҪ еӨ–е©Ҷд№ҹдёҚеёёеҒҡдәҶ пјҢ еҒҡдәҶд№ҹдёҚдјҡжүҳдәәйҖҒиҝҮжқҘдәҶ гҖӮ вҖқжҜҸжҜҸиҝҷж—¶ пјҢ жҜҚдәІе°ұд»»з”ұзҲ¶дәІе” еҸЁ пјҢ 笑笑дёҚиҜҙиҜқ гҖӮ жҲ‘еҚҙи®Өдёә пјҢ жҜҚдәІеҒҡзЈЁж–Ӣзҡ„жүӢиүәе·Із»ҸжҳҜйқ’еҮәдәҺи“қдәҶ гҖӮ3жҲ‘еҲқдёӯж—¶ пјҢ жҜҚдәІеқҗйӘЁзҘһз»Ҹз—ӣжҖ»дёҚи§ҒеҘҪ пјҢ зҲ¶дәІжҚўеұҠиҗҪйҖүиөӢй—ІеңЁе®¶ пјҢ еӨ–е…¬жӮЈиӮқзҷҢеҚ§еәҠеҚҠе№ҙеҗҺеҗ«жҒЁеҺ»дё– гҖӮ 家йҮҢз»ҸжөҺеҺӢеҠӣеҫ’еўһ пјҢ зҲ¶дәІдёәдәҶзңҒй’ұ пјҢ еёёеҺ»еҶңз”°йҮҢжҚЎз”°иһәеӣһжқҘ пјҢ з»“жһңжңүж¬ЎеҲ«дәәеҲҡеңЁз”°йҮҢжҙ’иҝҮе‘Ӣе–ғдё№ пјҢ д»–еҗғеҫ—еҶңиҚҜдёӯжҜ’еҚ§еәҠдј‘е…» гҖӮ и§ҒеҘіе„ҝеҘіе©ҝдёӨдёӘеӨ§дәәйғҪеҖ’дёӢдәҶ пјҢ еӨ–е©ҶдҫҝжқҘз…§йЎҫжҲ‘们 пјҢ еҸҳзқҖиҠұж ·з»ҷжҲ‘们еҒҡеҗғзҡ„ гҖӮжҲ‘第дёҖж¬ЎеҗғеҲ°еӨ–е©ҶеҒҡзҡ„зЈЁж–Ӣзҡ„ж—¶еҖҷ пјҢ жңүдәӣеӨұжңӣ пјҢ и§үеҫ—вҖңзӣӣеҗҚд№ӢдёӢ пјҢ е…¶е®һйҡҫеүҜвҖқвҖ”вҖ”еҸЈж„ҹзІ—зіҷ пјҢ жө“жө“зҡ„зЁ»иҚүе‘ізі…жқӮзқҖи®ёеӨҡзҡ„еҺҹжқҗж–ҷе‘ійҒ“ пјҢ и®©жҲ‘и§үеҫ—еҸЈе‘іеҚ•и°ғ пјҢ дҪҶзҲ¶жҜҚеҚҙиөһдёҚз»қеҸЈ гҖӮ еҗҺжқҘйҡҸзқҖе№ҙйҫ„жёҗй•ҝ пјҢ жҲ‘йҖҗжёҗжҳҺзҷҪдәҶе“Ғе°қйЈҹзү©зҡ„иҰҒйўҶ пјҢ д№ҹзҗҶи§ЈдәҶйӮЈдәӣи¶…еҮәйЈҹзү©д№ӢеӨ–зҡ„ж„Ҹд№ү пјҢ дҫҝејҖе§Ӣе–ңж¬ўдёҠеӨ–е©ҶеҒҡзҡ„зЈЁж–ӢдәҶ гҖӮжҜҸе№ҙжҳҘиҠӮ пјҢ д№…жңӘзӣёйҖўзҡ„дәІдәәиҒҡеңЁдёҖжЎҢ пјҢ зғӯй—№ең°еҗғдёҖйЎҝеӨ–е©ҶеҒҡзҡ„зЈЁж–Ӣ пјҢ жҲҗдәҶжҲ‘家зҡ„вҖңдҝқз•ҷиҠӮзӣ®вҖқ пјҢ еҸӘеҸҜжғңиҝҷж ·зҡ„е…¶д№җиһҚиһҚ并жңӘжҢҒз»ӯеӨҡд№… гҖӮ2015е№ҙйӮЈж¬Ў пјҢ жҳҜжҲ‘жңҖеҗҺдёҖж¬ЎеҗғеӨ–е©ҶеҒҡзҡ„зЈЁж–Ӣ гҖӮ жҳҘиҠӮеҗҺжҲ‘еҺ»зңӢеӨ–е©Ҷ пјҢ иҝӣдәҶзҶҹжӮүзҡ„иҖҒжҲҝеӯҗе®ўеҺ…йҮҢ пјҢ еҸ‘зҺ°й»‘жјҶжјҶзҡ„ пјҢ жІЎжңүд»»дҪ•зғҹзҒ«ж°” пјҢ е–ҠдәҶдёҖеЈ°вҖңеӨ–е©ҶвҖқ пјҢ д№ҹжІЎжңүеЈ°е“Қ гҖӮ жҲ‘д»ҘдёәеӨ–е©ҶеҺ»иҲ…иҲ…家дәҶ пјҢ жӯЈжғій—®йҡ”еЈҒйӮ»еұ… пјҢ еҘ№зӘҒ然жӢ„зқҖжӢҗ пјҢ ж‘Үж‘Үжҷғжҷғең°д»Һ马и·ҜеҜ№йқўеҺЁжҲҝеҮәжқҘдәҶпјҡвҖңд№–еҙҪ пјҢ дҪ жқҘзңӢеӨ–е©ҶдәҶ гҖӮ вҖқеӨ–е©Ҷзҡ„и„ёиүІиңЎй»„ пјҢ жӯҘеұҘи№’и·ҡ пјҢ йӮЈдёӨе№ҙеҗ¬жҜҚдәІж–ӯж–ӯз»ӯз»ӯиҜҙиҝҮ пјҢ еҘ№иә«дҪ“дёҚеӨӘеҘҪ пјҢ еҸҲжҖ•еӯҗеҘіеҝғйҮҢжңүжғіжі• пјҢ е®һеңЁж’‘дёҚдёӢеҺ»дәҶжүҚеҺ»дёҖи¶ҹеҢ»йҷў пјҢ иә«дҪ“жҜҸеҶөж„ҲдёӢ гҖӮи§ҒжҲ‘еёҰзқҖеҰ»е„ҝжқҘзңӢеҘ№ пјҢ еӨ–е©ҶеҫҲејҖеҝғ пјҢ жӢүзқҖжҲ‘дёҖзӣҙиҒҠж—§ж—¶еҖҷзҡ„дәӢ гҖӮ еҝ«еҲ°еҚҲйҘӯж—¶ пјҢ жҲ‘иө·иә«еҗ‘еӨ–е©Ҷе‘ҠеҲ«вҖ”вҖ”еӨ–е©Ҷе№ҙиҖҒеҠӣиЎ° пјҢ дёҖдёӘеҜЎеұ… пјҢ жүҖд»ҘйҘӯд№ҹдёҚзғ§дәҶ пјҢ иҪ®жөҒеҺ»еҮ дёӘиҲ…иҲ…家еҗғ пјҢ ж—¶й—ҙдёҖй•ҝ пјҢ е…„ејҹе§җеҰ№дә’зӣёзҢңеҝҢ пјҢ еҗ„з§Қзҹӣзӣҫ пјҢ е…ізі»д№ҹж—Ҙжёҗз”ҹеҲҶ пјҢ жңҖеҗҺеҪўеҗҢйҷҢи·Ҝ гҖӮ жқҘд№ӢеүҚжҜҚдәІе°ұеҸ®еҳұжҲ‘ пјҢ еҝ«еҲ°еҚҲйҘӯзҡ„ж—¶еҖҷе°ұеӣһ家 пјҢ жңҖеҘҪдёҚиҰҒеҺ»иҲ…иҲ…家еҗғйҘӯ гҖӮвҖңдҪ иҝҷз»Ҷдјўеӯҗ пјҢ е“ӘиғҪжқҘеӨ–е©Ҷ家йҘӯйғҪдёҚеҗғе°ұиө°пјҒвҖқеӨ–е©ҶжҖҘдәҶ пјҢ иө·иә«жӢүдҪҸжҲ‘ пјҢ вҖңжҲ‘еҗ¬иҜҙдҪ еӣһжқҘдәҶ пјҢ зҹҘйҒ“дҪ зҲұеҗғжҺЁжөҶйҪҗ пјҢ жқҗж–ҷж—©е°ұеҮҶеӨҮеҘҪдәҶ гҖӮ вҖқеӨ–е©Ҷз»ҷжҲ‘еҒҡзЈЁж–Ӣзҡ„ж—¶еҖҷ пјҢ е°ҸиҲ…иҲ…иҝҮжқҘз»ҷеӨ–е©ҶйҖҒйҘӯ пјҢ жҲ‘и®©е°ҸиҲ…иҲ…з•ҷдёӢжқҘдёҖиө· пјҢ е°ҸиҲ…иҲ…иҜҙжңүдәӢ пјҢ е…Ҳиө°дәҶ гҖӮ д»–иө°еҗҺ пјҢ еӨ–е©ҶеҸ№дәҶдёҖеҸЈж°” пјҢ йўӨйўӨе·Қе·Қең°иҜҙпјҡвҖңзҺ°еңЁеҗ„家жңүеҗ„家зҡ„дәӢ пјҢ еҫҲйҡҫиҒҡеңЁдёҖиө·дәҶ пјҢ иҝҮе№ҙдёҖиө·еҒҡжҺЁжөҶйҪҗд№ҹжҳҜйҷҲе№ҙж—§дәӢдәҶ гҖӮ вҖқ
жҺЁиҚҗйҳ…иҜ»
- иҖҒеӯҗе°ұжҳҜиҖҒеӯҗ
- йқ’е№ҙ|еҘіеӯҗеӣ е„ҝж—¶дёҖдёӘиөҢзәҰжҲҗ"й•ҝеҸ‘е…¬дё»"пјҢеҰӮд»Ҡйқ е®ғж—ҘиөҡеҚғе…ғ
- дәәй—ҙ | 姑姑36е№ҙзҡ„дёӯеӣҪејҸе©ҡ姻пјҢз»ҲдәҺеҲ°еӨҙдәҶ
- ж°‘й—ҙеҖҹиҙ·|еҲӨдәҶпјҢжҒӢдәәй—ҙзҡ„иҝҷзұ»иҪ¬иҙҰиЎҢдёәпјҢйҡҫд»Ҙи®Өе®ҡдёәеҖҹж¬ҫпјҒ
- гҖҠзәўзҒҜи®°гҖӢж°ёиҝңеңЁдәәй—ҙ
- еҚҒдёүдә”|гҖҗеӣһзңёвҖңеҚҒдёүдә”вҖқВ·е–ңзңӢж–°жҲҗе°ұгҖ‘ж№–еҢ—е®ңжҳҢпјҡвҖңе„ҝж—¶зҺ©дјҙвҖқеҸҲеӣһжқҘдәҶ
- е‘ійҒ“|иҝҷдҪҚиҖҒеёҲзҡ„дҪңе“ҒеҸҲеҠЁз”»еҢ–дәҶпјҒдәәзү©и¶ҠзңӢи¶Ҡжңүе‘ійҒ“пјҒ
- иҖҒеӯҗд№ӢвҖңйҒ“вҖқз»ҲдәҺжҸӯз§ҳпјҢдәәй—ҙзҹӣзӣҫеҝ…然з»ҲжӯўпјҒ
- дёҖдёӘдәәй—ҙзңҹе®һиҙҙпјҢиә«й«ҳдёҚйҮҚиҰҒпјҢй’ұйҮҚиҰҒ
- еӣўз»“еҗҲдҪң|гҖҗжҜҸж—ҘдёҖд№ иҜқгҖ‘еӣўз»“еҗҲдҪңжүҚжҳҜдәәй—ҙжӯЈй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