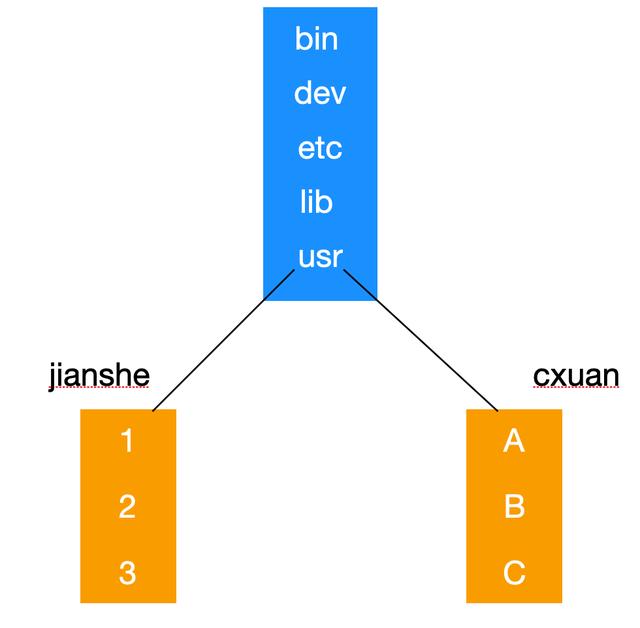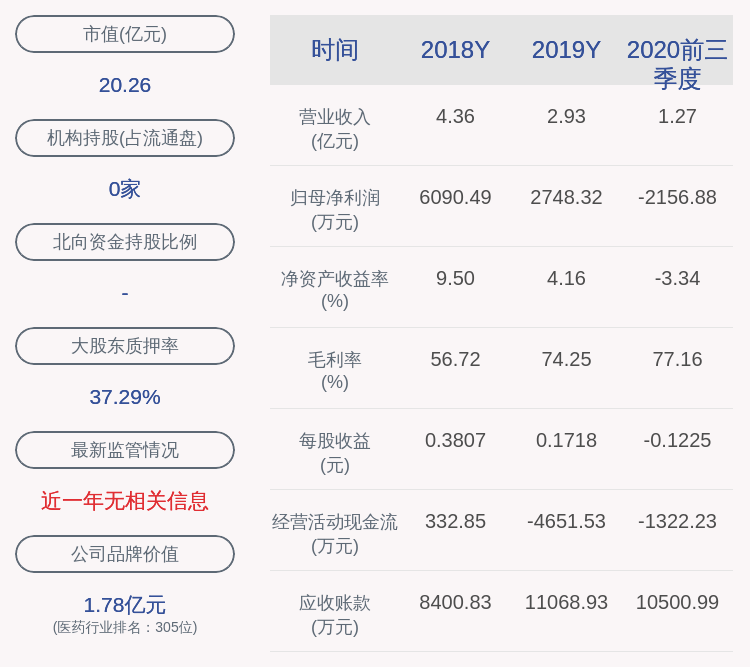许倬云:“致富”是美国文化不能摆脱的诅咒
《不断发展的文化脉络》(本文节选自《许倬云说美国》)任何大的人类共同体 , 其谋生的部分是经济 , 其组织的部分是社会 , 其管理的部分是政治 , 而其理念之所寄、心灵之所依则是文化 。 以个人生命作为比喻 , 文化乃是一个共同体的灵魂 。 本文会从各个时代陈述 , 我们可以体会美国的文化脉络如何不断地转换 。先将中国和美国历史做一比较:中国是一个经历几千年的共同体 , 这庞大共同体的灵魂 , 是数千年来演变而成的 。 美国只有不足三百年的历史 , 其开国之初从欧洲带来的文化 , 就是美国不足三百年来的立国之本 。 他们一切的典章制度、国体之所以如此设计的依据、人情风俗所寄托的理念无不根基于此 。 在中国这一共同体中 , 追溯中国文化的最初理念 , 由于时代久远且演变过程复杂 , 其实已经没有追溯源头的必要 。 美国则不一样 。 近三百年来美国一切的变化 , 万变不离其宗 , 都还多多少少可以从最初的根本理论见其端倪;转变过程 , 也可以从这个端倪作为零点 , 检查变化之关口及其起伏 。01 开疆拓土与“胜者为王”在“五月花”号登陆美国以前 , 欧洲人不是没有在北美大陆立下基地 。 如前所说 , 在今天马里兰州、佛罗里达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的沿河岸上 , 英国人也曾经多次尝试殖民 。 此外 , 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都先后在美国的东岸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 在美国的西岸 , 从墨西哥出发的西班牙拓殖队伍 , 也曾经伸展到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建立若干据点 。 这些不同的个例 , 没能具有“五月花”号在普利茅斯建立基地一样的重要性 , 则是因为“五月花”号带来的移民 , 要以其坚定的信仰在新大陆上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 以落实他们所憧憬的目标 。
“五月花”号从中世纪以来 , 欧洲的居民在战争中占据土地后 , 建立封建制度 , 将人民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 。 这是一个阶级化的社会 。 宗教革命以后经历启蒙时代 , 欧洲各处都卷入反封建的浪潮 。 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光荣革命 , 都提出以平等解除阶级的隔离 , 以个人自由解除封建制度人身的束缚 。 法国革命提出的博爱思想 , 则阐明人与人之间应当如同兄弟手足 , 不应该再有不同的身份区隔 。 相对而言 , 英国的光荣革命肇因于农村大地主争取自己的财产权和人身权 。 英、法两国革命的方式及其理念背景是相当不同的 。“五月花”号上的移民虽然来自英国 , 他们的宗教信仰却是西欧大陆上最激烈的加尔文主义 。 在到达北美之后 , 虽然理论上他们还接受英国王室的统治 , 只是在海外建立英王政府所管辖的殖民地而已 , 但实质上 , 登岸之时他们就已有决心 , 要在这个新的土地上创建一个新的制度:神恩的庇护下 , 落实每个人应有的平等和自由 。这一段开拓的经历 , 无论如何是相当辛苦的过程 。 如果没有清教徒秉持神恩的勇往直前 , 这些殖民者很难在陌生的新大陆上 , 获取坚持开拓的勇气和能力 。 从那时候开始 , 一波一波的新移民进入美国又推向内陆 。 那些新到的人群 , 有的是同一个宗派的教徒 , 有的是基于经济动机的移民 。 这些陆续前来的开拓部队 , 是在欧洲没有发展余地的人群 。 他们宁可抛弃一切进入美国 , 前途未知却勇往直前:他们在颠簸的篷车上 , 翻山越岭、渡河过江 , 在洪荒新世界觅得站定脚头的空间 。 这些开拓者的精神 , 是美国的史家特纳特予强调 , 可以代表美国立国的精神 。 向西开拓的历史 , 即是美国整个历史的定调 。从好的方面说 , 这种精神一方面是承受着神恩 , 要以自己的行为彰显神的恩典:这一种个人主义如此有恃无恐 , 这些开拓者才有勇气和决心一步步往前走 。 可是 ,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 , 这些依仗上帝眷顾的个人 , 自以为是神的选民 , 对他们而言 , “神的选民”四个字 , 就让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其他人有了区隔 。 异教徒不能蒙受神恩 , 乃是异类;那些他们认为是野蛮人的原住民 , 简直是羞以为伍的异类 。 这些自以为蒙受神恩的个人主义者 , 可以理直气壮地任意处置他们眼中的“异类” 。在美国历史上 , 正因为这种不成理由的“理由” , 百万计的原住民被他们驱赶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于以近代的武器对付手持弓箭的原住民 , 对其任意地杀戮和驱赶 。从他们手上夺取的资源和土地 , 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据为己有 。这些错失 , 在今天看来是人类历史上的污点 , 但是在当时那些开拓者的心目中 , 却正是以这种理由毫不留情地将新大陆占为己有 。向西开拓成功还是失败 , 对于当时人而言是机会各半 。 失败者葬身异域 , 成功者却可以自我肯定:神的眷顾 , 就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和才干 。 这种自我肯定 , 是个人主义转变为独占和自私的关键 。 在激烈的竞争考验之中 , 能够生存、能够成功就是一个证明:“我是优越者 , 所以我能成功 。 ”在达尔文提出的自然演化论被当作“真理”的时代 , 从生物演化论引申出来的社会演化论 , 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 , 正如生物界的适者生存一样——成功与失败的差别 , 就在成功者站住了 , 失败者倒下了 。 将生物演化论中弱肉强食的原则 ,引申到社会演化论时 , 个人主义成功者对失败者不会有怜悯 , 更不会同情 。上面两个阶段的推论 , 演变为美国社会上弥漫着的无情竞争 , 整个社会信奉“胜者为王”的观念 。 一方面是从宗教的神恩衍生出来的个人主义 , 一方面又是将生物科学的演化论 , 武断地转变为解释人类关系的科学主义 , 而且俨然定论 。数百年来 , 如此种种 , 在美国的一般观念中 , 却是影响到人们的行为 , 以至于清教徒所秉持的“在神的面前一切都平等 , 在神的庇护下 , 所有人都应当有自由” , 竟然转变成为“我可以为所欲为 , 因为我是胜者” 。 这个现象 , 到今天并没有得到修正 。 这一理念或者说社会性的意旨 , 乃是这一新大陆的新舞台上 , 剧中人演唱的主旋律 。这一新局 , 毕竟还是有从基督教承受的理想层面 , 亦即博爱与公义 。 凭借这一温柔的曲调 , 在社会主义浪潮进入美国时 , 作为弱者的劳工可以凭借集体的力量 , 向雇主争取平等的人权 , 要求合理的待遇;他们也要求妇女、儿童不应当担任过分劳累的工作 。 这一番新的社会正义 , 其实还并不能真正平衡上述强烈个人主义所造成的独断和自私 。 迄于现代 , 美国才出现进步主义思潮 , 将社会公义和公平视为应当落实的要事 。在工业发展的阶段 , 工商业的园地就等于是向西开拓时候的内陆;龙腾虎跃的战场 , 成功与失败的标志都是以金钱衡量 。 那些镀金时代的大亨 , 努力工作聚集庞大财富 , 创建企业帝国 , 他们的动机 , 也就是上述特纳所指的开拓精神 。 好处在于他们能勇往直前地努力工作 , 实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 就以匹兹堡出身的卡耐基而论 , 据说他每日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 睡眠时间只有四个小时左右;他饮食清淡、生活简单 , 卧室是一张相当于行军床的单人床 。这些人物努力工作 , 要求的回报不是物质上的享受 , 也不是贪得无厌的欲望 , 而是实践神拣选了“我”后 , “我”对神的回应 。 他事业成功以后 , 将所有的产业都捐为公益之用:办了一所大学 , 捐建了全部苏格兰、爱尔兰和宾夕法尼亚州地区的公共图书馆 , 捐建了自然博物馆 , 也捐助建设了纽约的卡耐基音乐厅 , 还设立了一个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卡耐基基金会 。 他自己没有子女 , 身后没有留下家产给家人 。
推荐阅读
- 安徽明光|安徽明光:小蘑菇圆了脱贫致富梦
- 牡丹|模范先锋丨高金来:让致富路越走越宽
- 养殖|能靠养殖致富的人,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 劳动致富行不通,诈骗发财正流行
- 英媒:想靠“出租致富”的中国房东 日子不好过了
- 你笑起来真好看|你笑起来真好看云南玉溪江川这个“小家”脱贫了又带“大家”致富
- 张骅|驻村第一书记在一线:脱贫之后要致富 再送一程才放心
- 中年|浙江一女子收留3名乞丐,乞丐致富后携百万巨款来报恩,后来怎样
- 云南|云南丘北:“致富花”万寿菊花海美景
- 荷塘经济|满塘素红碧,风起玉珠落——小镇“荷塘经济”带动贫困户增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