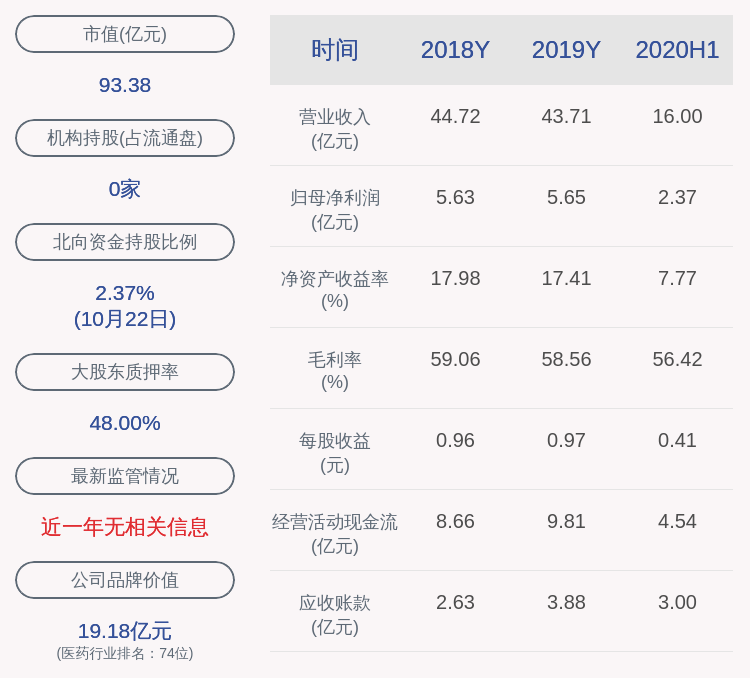费孝通|你听过多少鬼故事?( 二 )
进而 , 他把童年的恐惧、祖母的影子、房屋的角落 , 上升到了更高、更悠远广阔的哲学思考——“我们的生命并不只是在时间里穿行 , 过一刻、丢一刻;过一站、失一站 。 生命在创造中改变了时间的绝对性:它把过去变成现在 , 不 , 是在融合过去 , 现在 , 未来 , 成为一串不灭的 , 层层推出的情景——三度一体 , 这就是鬼 , 就是我不但不怕 , 而且开始渴求的对象 。 ”
他意识到了“鬼”在中国人心理和日常生活中的独特存在 , 也点出了美国文化中“鬼的消失” 。 他认为美国人高度流动的都市生活、独立居住的小家庭、联系不密切的血缘关系、千篇一律的住宅形态 , 让人与人、人与物的联系变淡了 , 对故人的幽思、对亡物的怀念 , 也都变淡了 。 因而 , 鬼也随之而灭 。
当然 , 费孝通没有看到当代中国已经发生的大流动 , 那个深宅浓荫、后花园充满传说、一草一木皆有神话、邻里巷陌不缺故事的古老中国 , 也一样逐渐去魅、消失了 。 然而 , “鬼”真的消失了吗?还是改变了文化形态 , 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
现代社会的高速流动、个体隐私、人际壁垒 , 让传统形态的鬼减少乃至消失了 , 但是现代化的精致的鬼却越来越多 。 那是香港都市爱情电影中的鬼 , 是日本电影里的怨鬼 , 它们多数是独居在公寓里、有各类心理疾病的男女老少 , 因为家庭、事业、爱情这三座大山而压得喘不过气来 , 于是由人变鬼 , 演绎起当代都市的幽冥志怪 。 可以说 , 从古至今 , 鬼从未缺席 。
幽冥故事不仅仅是对人间生活的反映和投射 , 它对人们的寻常生活、老百姓的世界观和生活观 , 常常有“润物细无声”的深刻影响 。 在口耳相传中 , 在好奇和恐惧的情绪之间 , 它仿佛跨越了代际和地域 , 告诉一代代人 ,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 你应该做什么 , 不应该做什么 。 它在人类文化里发挥着深层却又少人留意的巨大影响 , 需要引起更深的注意 。
“见鬼”以后如何
娜拉的出走 , 让鲁迅追问:“娜拉走后怎样?”而鬼却从未消失 , 只不过改头换面、如影随形 , 游荡在人间 。 前者是一个女性解放的难题 , 后者却是人们从传统走进现代的难题——“鬼”只是引子 , 引发人对自身、对传统和现代的思考 。 启蒙 , 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 也不是终极目标 , 启蒙从来就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反思过程 。
自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以来 , 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 , “科学”和“民主”成了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中心思想 , 举凡学术研究、政治、经济 , 皆奉“赛先生”和“德先生”为圭臬 。 而对于不合于二者的其他社会文化元素 , 或以“反动”批判 , 或以“迷信”拒斥 , 或以“不可知论”漠视 , 或以“神秘莫测”讳言 。 总之 , 百年来的学人学者和社会各界 , 对“鬼文化”的研究和书写 , 恐怕是远远不足的 。
相较而言 , 日本学界对“鬼文化”的研究 , 已有相当客观而且可观的积累 , 他们对自身传统文化里的鬼魅元素 , 也有相当早的整理和重新创造 。 从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到鸟山石燕的浮世绘 , 从井上圆了到柳田国男 , 无不展现出他们对日本“鬼文化”的探索 。 近世日本学人在习得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后 , 创造性地运用于整理、研究有关鬼魅的文献材料和民俗现象 , 终成一门特殊的学问——妖怪学 。
当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老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翻译了日本妖怪学之父、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后 , 竟然从中得到启发 , 抛开了科学与迷信、唯物与唯心、理智与情感的二元对立 , 开始觉得“心境之圆妙活泼 , 触发自然 , 不复作人世役役之想” 。 从前他认为“无稽之谈”的妖怪 , 在宗教学和人类学的显微镜下 , 竟然迸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 这是一次重新展开的启蒙过程 , 也可以说 , 这是一次“见鬼”的经历——“见鬼”是一次震慑 , 一次提醒 , 一次让人超脱寻常观念的体验 。 那么 , 如果用一双“鬼眼”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亚洲文化乃至西方文化 , 可能看到的将比以往的更多、更不同 。
推荐阅读
- 女性健康,更年期|女人多少岁进入更年期算正常?到了更年期,身体会有哪些提示?
- 车辆知多少|为防“热化”,阿尔卑斯山脉最古老冰川被盖上白毯
- 癌症肿瘤|生活中能防治肿瘤的蔬菜,有这9种,你知道多少?
- 吃货|还有多少人不知道“糊塌子”
- 装修|120平米三层农村自建房多少钱 农村自建房怎样省钱
- 男性养生|我国男女的平均身高是多少?
- 三国两晋南北朝|如果不是关羽出战华雄,而是赵云或者张飞出战华雄,有多少胜算?
- 癌症肿瘤|小测试:夏日水果中的抗癌秘笈知多少
- 健身|到了四五十岁,你还能做多少个俯卧撑?若超不过10个说明有问题
- 软装知多少|这样的纯正的美式轻奢风格你喜欢吗?反正我很喜欢,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