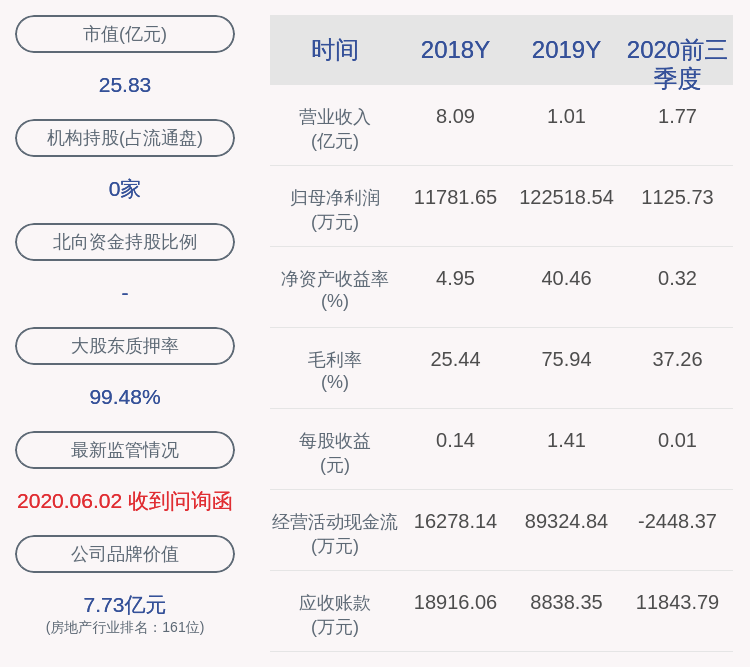иҝҗеҹҺ|гҖҠжҲ‘зҡ„й«ҳиҖғгҖӢжӣҫзңӢе“ӯдәҶж— ж•°дәәеұұиҘҝиҝҗеҹҺеёӮж”ҝеҚҸеҺҹдё»еёӯе®үж°ёе…ЁйҖқдё–( еӣӣ )
жҲ‘дёҖеҲҮйғҪж— д»ҺйЎҫеҸҠдәҶ пјҢ йҷӨдәҶдёҚж•ўеҒңжӯўжӢүиҪҰ пјҢ жҖ•еӨ§еӯҰдёҚдёҠеҸҲдёўдәҶйҘӯзў— пјҢ еӯҰд№ е·Іиҝ‘дәҺз–ҜзӢӮ гҖӮ йҷӨдәҶиҜ•йўҳ пјҢ йҷӨдәҶзӯ”жЎҲ пјҢ еҘҪеғҸдёҖеҲҮйғҪдёҚеӯҳеңЁдәҶ гҖӮ жҲ‘иҝӣиЎҢдәҶвҖңеӨҙжӮ¬жўҒгҖҒй”ҘеҲәиӮЎвҖқзҡ„е®һи·ө гҖӮ жҲ‘дёҚзҹҘйҒ“жҲҳеӣҪзҡ„иӢҸз§Ұе’ҢиҘҝжұүзҡ„еӯҷ敬еҪ“е№ҙжҳҜеҰӮдҪ•з”Ёиҝҷз§ҚеҠһжі•жҲҳиғңз–ІеҠізҡ„ пјҢ дҪҶеҪ“жҲ‘еӯҰд№ еҸӨдәәжҠҠеӨҙеҸ‘жүҺзҙ§з”Ёз»іеӯҗеҗҠеңЁеұӢйЎ¶дёҠ пјҢ дёҚдёҖдјҡд»Қ然еҸҲжІүжІүе…ҘзқЎ пјҢ йӮЈз§ҚиҪ»еәҰзҡ„з–јз—ӣж №жң¬ж— жі•жҲҳиғңйӮЈжҳҸиҝ·дјјзҡ„з–ІеҖҰ гҖӮ й”ҘеҲәиӮЎеҗ§ гҖӮ иҪ»дәҶ пјҢ еҲәдёҚеҮәиЎҖе°ұдёҚз–јзӯүдәҺдёҚеҲә пјҢ еҲәеҫ—еҺүе®ідәҶеҖ’жҳҜжңүж•Ҳ пјҢ дёүеӣӣдёӘе°Ҹж—¶еҶ…еҶҚд№ҹдёҚдјҡзқЎзқҖ пјҢ дёҖиҫ№жҚӮзқҖеҮәиЎҖзҡ„ең°ж–№дёҖиҫ№еӯҰд№ гҖӮ дҪҶеҲәдёҚдёҠеҮ ж¬Ў пјҢ дјӨеҸЈдҫҝеҸ‘з”ҹдәҶж„ҹжҹ“гҖҒжәғзғӮ гҖӮ жҲ‘жғіеҲ°дәҶдёҖдёӘеҠһжі• гҖӮ жҲ‘жғіиө·дәҶжҲ‘еҰҲ гҖӮ жҲ‘еҰҲжҳҜдёӘдјҹеӨ§иҖҢдёҘеҺүзҡ„дәә пјҢ и®°еҫ—е°Ҹж—¶еҖҷйҖғеӯҰиў«еҸ‘зҺ° пјҢ зҲ¶дәІжҠҠжҲ‘еҗҠеҲ°ж ‘дёҠ пјҢ жӢҝдёҖж №жңЁжЈҚ пјҢ и®ӯж–ҘеЈ°е’ҢеҠЁдҪңиҷҪеҫҲеӨ§ пјҢ дҪҶжЈҚеӯҗиҗҪеңЁиә«дёҠ并дёҚз–ј пјҢ дәҺжҳҜжҲ‘д»Қ继з»ӯйҖғеӯҰ гҖӮ 第дәҢж¬Ў пјҢ зҲ¶дәІеҸҲжү“жҲ‘ пјҢ жҲ‘еҰҲеңЁдёҖиҫ№зңӢзқҖ并дёҚиҜҙиҜқ пјҢ жӢҝдёҖжҠҠй’іеӯҗеңЁи…ҝдёҠзӢ зӢ дёҖжӢ§ пјҢ иҪ¬иә«е°ұиө° пјҢ жҲ‘еӨ§еҸ«дёҖеЈ° пјҢ и…ҝдёҠиҷҪ然没жңүжөҒиЎҖ пјҢ еҚҙеҶҚд№ҹдёҚж•ўйҖғеӯҰ гҖӮ жҲ‘жңҖзҲұжҲ‘еҰҲ пјҢ д№ҹжңҖжҖ•жҲ‘еҰҲ пјҢ дёҖи§ҒжҲ‘еҰҲжүӢйҮҢжӢҝиө·й’іеӯҗи…ҝе°ұеҸ‘жҠ– гҖӮ жҲ‘йңҖиҰҒжҲ‘еҰҲзҡ„й’іеӯҗ пјҢ е°ұжҠҠиҝҷжғіжі•е‘ҠиҜүжҲ‘еҰҲ гҖӮ жҲ‘еҰҲй—®жҲ‘ пјҢ е’ұдёҚиҖғе°ұдёҚиЎҢеҗ—пјҹжҲ‘иҜҙ пјҢ дёҚиҖғдёҚиЎҢ пјҢ и®©жҲ‘еҶҚиҜ•дёҖеӣһ гҖӮ жҲ‘еҰҲзӮ№дәҶзӮ№еӨҙ гҖӮ йӮЈдёҖеӨң пјҢ жҲ‘еҸҲзһҢзқЎдәҶ пјҢ еҪ“жҲ‘зҢӣ然被еӨ§и…ҝзҡ„еү§з—ӣе”ӨйҶ’ж—¶ пјҢ зңӢи§ҒжҲ‘еҰҲжүӢйҮҢжӢҝзқҖй’іеӯҗ пјҢ еҚҙж»Ўи„ёжіӘж°ҙ пјҢ е°ұеҶҚд№ҹзқЎдёҚзқҖдәҶвҖҰвҖҰ еңЁд»ҘеҗҺзҡ„еҚҒеҮ еӨ©йҮҢ пјҢ жҲ‘еҰҲе°ұе®ҲзқҖжҲ‘еӯҰд№ пјҢ иҷҪ然еҘ№еҶҚжІЎжңүз”ЁиҝҮжүӢйҮҢзҡ„й’іеӯҗ пјҢ дҪҶжҲ‘еҶҚд№ҹжІЎжңүзһҢзқЎиҝҮ пјҢ еқҡжҢҒжҜҸеӨ©еӯҰеҲ°еҮҢжҷЁдёүзӮ№ гҖӮ йӮЈдёҖж®ө пјҢ жҳҜжҲ‘з”ҹе‘ҪеҠӣзҡ„жһҒйҷҗ гҖӮ йӮЈдёҖж®ө пјҢ жҳҜжҲ‘еҰҲеҜ№жҲ‘зҡ„еҶҚз”ҹ гҖӮ й«ҳиҖғз»ҲдәҺжқҘеҲ°дәҶ пјҢ иҖғиҜ•з»ҲдәҺз»“жқҹдәҶ гҖӮ
жҲ‘еңЁеҝҗеҝ‘дёҚе®үзҡ„зӯүеҫ…дёӯеәҰж—ҘеҰӮе№ҙ пјҢ жёҗжёҗең° пјҢ еҗ¬иҜҙеҪ•еҸ–йҖҡзҹҘд№ҰйғҪдёӢжқҘдәҶ пјҢ еҸҲеҗ¬иҜҙеҺҝдёӯж–Ү科зҸӯдёүеҚҒдёғдёӘдәәеҸӘжңүдёҖдёӘдәәиҖғдёҠвҖңеұұиҘҝеӨ§еӯҰвҖқ пјҢ е°ұи§үеҫ—иҝҷдёҖж¬ЎеҸҲе®ҢдәҶ гҖӮ дёҖд№қе…ӯеӣӣе№ҙе…«жңҲдәҢеҚҒдә”еҸ· пјҢ иҝҷжҳҜжҲ‘жҜ•з”ҹйҡҫеҝҳзҡ„дёҖеӨ© гҖӮ дёӯеҚҲ пјҢ жҲ‘жӯЈеғҸеҫҖеёёдёҖж ·еңЁе®¶й—ЁеҸЈиЈ…иҙ§ пјҢ еҝҪи§ҒйӮ®йҖ’е‘ҳжӢҝзқҖдёҖе°ҒдҝЎжү“еҗ¬жҲ‘зҡ„еҗҚеӯ— пјҢ зӘҒеҸ‘зҡ„йў„ж„ҹдҪҝжҲ‘еҝғи·ійӘӨ然еҠ йҖҹ гҖӮ жҺҘиҝҮдҝЎ пјҢ жҲ‘зҡ„жүӢйўӨжҠ–дәҶеҘҪй•ҝж—¶й—ҙеҚҙдёҚж•ўеҺ»жӢҶ пјҢ жҲ‘з®ҖзӣҙжІЎжңүеӢҮж°”еҺ»иҒҶеҗ¬е‘ҪиҝҗеҜ№жҲ‘зҡ„е®ЈеҲӨ гҖӮ еҪ“жҲ‘з»ҲдәҺе’¬зқҖзүҷжү“ејҖе®ғж—¶ пјҢ дёҖеј й«ҳзӯүйҷўж ЎеҪ•еҸ–йҖҡзҹҘд№ҰеҮәзҺ°еңЁзңјеүҚпјҡе®үж°ёе…ЁеҗҢеӯҰ пјҢ дҪ иў«еҪ•еҸ–дёәеұұиҘҝеёҲиҢғеӯҰйҷўдёӯж–Үзі»еӯҰз”ҹ пјҢ иҜ·дәҺд№қжңҲеҚҒж—ҘеүҚжқҘжҠҘеҲ° гҖӮ жҲ‘й«ҳе…ҙеҫ—з®ҖзӣҙиҰҒз–ҜзӢӮ пјҢ з«ҹеғҸиҢғиҝӣдёӯдёҫдёҖж ·еңЁеӨ§иЎ—дёҠй«ҳе–ҠпјҡжҲ‘иҖғдёҠдәҶпјҒжҲ‘иҖғдёҠдәҶпјҒжҲ‘иҖғдёҠдәҶпјҒжҲ‘з»ҲдәҺз«ҷеңЁдёҖдёӘж–°зҡ„ең°е№ізәҝдёҠ гҖӮ иҷҪ然жҲ‘дёҚзҹҘйҒ“д»ҘеҗҺе°ҶиҰҒиө°еҗ‘д»Җд№Ҳең°ж–№ гҖӮ
еӣӣеҚҒе№ҙеүҚзҡ„й«ҳиҖғз»ҸеҺҶ пјҢ еј•еҸ‘дәҶжҲ‘еҜ№й«ҳиҖғзҡ„жҖқиҖғ гҖӮ жҳҜе•Ҡ пјҢ е°‘е№ҙиҠұеӯЈ пјҢ еҚҙжІЎжңүдәҶж¶Ҳй—І пјҢ жІЎжңүдәҶж¬ўе”ұ пјҢ зңӢеҲ°зҡ„е°ұжҳҜйӮЈдәӣеҶ°еҶ·зҡ„е…¬ејҸгҖҒеҚ•иҜҚгҖҒиҜ•йўҳ пјҢ е®ғе……еЎһзқҖдҪ гҖҒжҠҳзЈЁзқҖдҪ пјҢ иҖҢдё”дёҚжҳҜдёҖеӨ©гҖҒдёҖжңҲгҖҒдёҖе№ҙдёӨе№ҙ пјҢ дҪ еҸҜд»ҘиҜ…е’’е®ғжҳҜж®Ӣй…·зҡ„ пјҢ дҪҶе®ғзЎ®е®һдёәдҪ жҸҗдҫӣдәҶдёҖж¬Ўж”№еҸҳе‘Ҫиҝҗзҡ„жңәйҒҮ гҖӮ й«ҳиҖғе…¶е®һе°ұжҳҜеңЁиҖғдҪ зҡ„еҶіеҝғе’Ңж„Ҹеҝ— гҖӮ 既然йҖүжӢ©дәҶй«ҳиҖғ пјҢ дҪ е°ұеә”иҜҘйқўеҜ№зҺ°е®һ пјҢ жҲҳиғңиҮӘе·ұ пјҢ еӣһжҠҘдәІдәә пјҢ еӣһжҠҘзӨҫдјҡ гҖӮ
йғЁеҲҶжӮјж–Үиҫ‘еҪ•
е‘Ёе®—еҘҮпјҡжӮје®үж°ёе…ЁеҸӨиҜ—жңүдә‘пјҡвҖңи°Ғи°“жӯ»ж— зҹҘ пјҢ жҜҸеҮәиҫ„жқҘжўҰ гҖӮ вҖқжҳЁеӨңеҫ—ејӮжўҰ пјҢ дёҠеҚҲеҚіжңүеҚҸе№іе…„жҠҘжқҘеҷ©иҖ—пјҡж°ёе…Ёе…„йҒҪ然зҰ»дё–пјҒ
6жңҲйҮҢе°ұжңүзӮ№еҘҮжҖӘ пјҢ д»–д»ҺиҝҗеҹҺжҺҘиҝһзөҰжҲ‘жү“жқҘз”өиҜқ пјҢ й—®жҲ‘еңЁдёҚеңЁеӨӘеҺҹ пјҢ иҜҙжғіи§ҒжҲ‘ пјҢ еҘҪеҘҪиҒҠиҒҠ гҖӮ дёәд»Җд№ҲиҜҙеҘҮжҖӘе‘ўпјҹд»ҘеүҚд»–еҫҲе°‘зөҰжҲ‘жү“з”өиҜқ пјҢ йўҶеҜје№ІйғЁеҒҡд№…дәҶ пјҢ д№ жғҜеҗ¬еҲ«дәәжү“жқҘз”өиҜқ гҖӮ
7жңҲдёӯж—¬ пјҢ д»–еҸҲеҮ ж¬Ўжү“жқҘз”өиҜқ пјҢ иҗҪе®һжҲ‘зҡ„иЎҢиёӘ пјҢ иҜҙд»–еҫҲеҝ«жқҘеӨӘеҺҹ гҖӮ
7жңҲ24ж—Ҙ пјҢ жү“з”өиҜқиҜҙд»–е·ІеҲ°еӨӘеҺҹ пјҢ жҳҺеӨ©иғҪдёҚиғҪи§ҒйқўпјҹжҲ‘иҜҙжҲ‘еңЁжІҒж°ҙ пјҢ еҗҺеӨ©еӣһеҺ» пјҢ еӣһеҺ»е°ұзңӢдҪ еҺ» гҖӮ
7жңҲ30ж—Ҙ пјҢ жҲ‘们з»ҲдәҺеңЁд»–дёӢжҰ»зҡ„е®ҫйҰҶи§ҒдәҶйқў гҖӮ д»–жӣҙзҳҰдәҶ пјҢ дҪҶзІҫзҘһеӨҙдёҚй”ҷ пјҢ дёҖж°”дё»и®Іиҝ‘4дёӘе°Ҹж—¶ пјҢ и®Ід»–зҡ„з»ҸеҺҶ пјҢ и®Ід»–зҡ„е®ҳеҺҶ пјҢ и®ІжҲ‘们йңҚеҺҝйӮЈжү№ж–ҮеҸӢзҡ„ж—ўеҫҖи¶ЈдәӢ гҖӮ жҲ‘дёҖйқўи®ӨзңҹеҖҫеҗ¬ пјҢ дёҖйқўеҝғйҮҢиҜҙ пјҢ иҖҒжңӢеҸӢ пјҢ иҝҷдәӣжҲ‘йғҪеҗ¬дҪ и®ІиҝҮеҘҪеҮ йҒҚдәҶ гҖӮ д»–зҡ„иҝҷдёӘзҠ¶жҖҒ пјҢ еҸҲи®©жҲ‘з”ҹеҮәеҮ еҲҶеҘҮжҖӘ пјҢ жҲ‘иҝҷе…„ејҹжҖҺд№ҲдәҶпјҹдҪҶеҗғиө·йҘӯжқҘдёҖеҲҮз…§ж—§ пјҢ д»–жҳҜеҸӘе–қй…’еҸӘиҜҙиҜқ пјҢ е°‘еҗғиҸңдёҚеҗғйҘӯ гҖӮ дёҖдәәдёҖдёӘе°ҸеқӣжұҫдәҶз»“ пјҢ д»–иҝҳжғіиҰҒ пјҢ иў«жҲ‘жӢҰдҪҸ гҖӮ жҲ‘дјҡиҙҰ пјҢ д»–дёҚй«ҳе…ҙ гҖӮ жҲ‘иҜҙжҲ‘еҗғиҝҮдҪ еӨҡе°‘дәҶ пјҢ иҝҷж¬ЎжҲ‘еҝ…йЎ» гҖӮ д»–д№ҹе°ұдёҚеҗӯеЈ°дәҶ гҖӮ еӣһеҲ°е®ҫйҰҶй—ЁеҸЈ пјҢ жҲ‘иҜҙжҲ‘зӯүиҪҰ пјҢ дҪ еҝ«еӣһжҲҝй—ҙеҗ§ гҖӮ д»–е‘Ҷе‘ҶдёҚеҠЁ пјҢ дёҖдёӘеҠІй—® пјҢ жҳҺеӨ©жқҘеҗ—жҳҺеӨ©жқҘеҗ—пјҹжҲ‘иҜҙиҝҷдёӨеӨ©жңүдёӘе®үжҺ’ пјҢ еӣһеӨҙеҶҚжқҘ гҖӮ жҲ‘йғҪжү“дёҠиҪҰдәҶ пјҢ д»–иҝҳеңЁеӨ§еӨӘйҳідёӢз—ҙз—ҙең°зңӢжҲ‘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иҝҗеҹҺеёӮ|ејәеҲ¶зҢҘдәөеӯҰз”ҹ еұұиҘҝиҝҗеҹҺдёҖж•ҷеёҲдёҖе®ЎиҺ·еҲ‘8е№ҙ
- еұұиҘҝиҝҗеҹҺдёҖж•ҷеёҲејәеҲ¶зҢҘдәөеӯҰз”ҹдёҖе®ЎиҺ·еҲ‘8е№ҙ
- жҖҘеҜ»пјҒ28еІҒеҘіеӯҗеӨұиёӘ21еӨ©пјҢеҗҢдәӢжӣҫзңӢеҲ°еҘ№иў«еүҚз”·еҸӢеёҰиө°вҖҰвҖҰ
- иҪҰд№Ӣе…»жҠӨ|еҗүеҲ©9жңҲй”ҖйҮҸз ҙ12дёҮпјҢжҲҗеҠҹжү“и„ёжӣҫзңӢдёҚиө·иҮӘе·ұзҡ„еҗҲиө„е“ҒзүҢ
- зҪ‘дј еұұиҘҝиҝҗеҹҺдёҖдёӯеӯҰж•°еҚҒеӯҰз”ҹйЈҹзү©дёӯжҜ’ ж Ўж–№пјҡзЎ®жңүеӯҰз”ҹйҖҒеҫҖеҢ»йҷўпјҢз—…еӣ жҡӮдёҚжё…жҘҡ
- жҲ‘зҡ„й«ҳиҖғжҲҗз»©иғҪеҺ»з”өеӯҗ科еӨ§еӯҰйҖҡдҝЎе·ҘзЁӢorеҺ»еҗүеӨ§еӯҰйҮ‘иһҚпјҸдјҡи®ЎпјҢиҜҘжҖҺж ·йҖүжӢ©
- еұұиҘҝиҝҗеҹҺзІ®жІ№еә—йғҪе…ій—Ёиҙҙе°ҒжқЎпјҹе®ҳж–№еӣһеә”пјҡд»…8家пјҢдёәз§ҹиөҒеҲ°жңҹ
- и¶ЈеӨҙжқЎ|дҪ дёҺжҳҹжІізҡҶеҸҜ收и—Ҹ
- еұұиҘҝиҝҗеҹҺе»әзӯ‘е®үе…ЁжЈҖжҹҘпјҡжҢүеҚұйҷ©жҖ§еҲ’еҲҶ4зә§пјҢCгҖҒDзә§е®үжҺ’ж’ӨзҰ»
- еұұиҘҝзңҒ|гҖҗиҝҗеҹҺдёӯеӯҰ2020е№ҙй«ҳиҖғеҪ•еҸ–еҗҚеҚ•г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