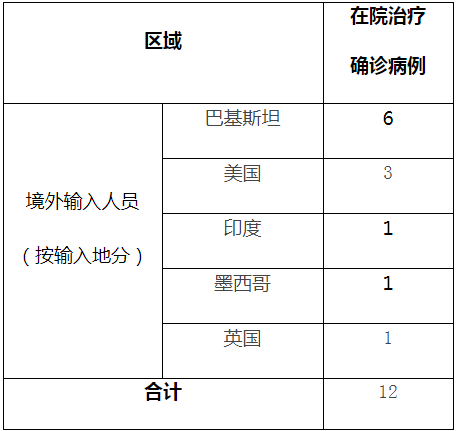иҖҗе…Ӣ|иҖҗе…ӢжӢҘжҠұи¶ҠеҚ—е·ҘеҺӮ еҚҙеӨұеҺ»дёӯеӣҪеёӮеңә
иҖҗе…ӢжӯЈеңЁ“иӮүзңјеҸҜи§Ғ”ең°еӨұеҺ»дёӯеӣҪеёӮеңә гҖӮ
еңЁ9жңҲеә•е…¬еёғзҡ„ж–°еӯЈеәҰиҙўжҠҘдёӯпјҢеӨ§дёӯеҚҺеҢәеёӮеңәжҲҗдёәдәҶиҖҗе…Ӣе…Ёзҗғй”Җе”®йўқеўһе№…жңҖе°Ҹзҡ„ең°ж–№пјҢеңЁ6жңҲеҲ°8жңҲй—ҙпјҢиҖҗе…ӢеңЁдёӯеӣҪеҢәзҡ„й”Җе”®йўқд»…еўһй•ҝ1%пјҲжүЈйҷӨжұҮзҺҮзӯүеӣ зҙ еҪұе“ҚеҗҺж•°еҖјпјү гҖӮ
иҖҢд»…д»…дёҖе№ҙеүҚпјҢиҝҷйҮҢиҝҳжҳҜиҖҗе…ӢеўһйҖҹжңҖеҝ«зҡ„еёӮеңәпјҢ2020е№ҙиҖҗе…ӢеңЁеӨ§дёӯеҚҺеҢәзҡ„й”Җе”®йўқеўһй•ҝиҝ‘51% гҖӮ
и®©иҖҗе…ӢйӣӘдёҠеҠ йңңзҡ„жҳҜпјҢ2008е№ҙејҖе§Ӣзҡ„е·ҘеҺӮжҗ¬зҰ»дёӯеӣҪ“и®ЎеҲ’”пјҢжӯЈеңЁи®©иҖҗе…Ӣйҷ·е…Ҙ“еҒңдә§жіҘжІј” гҖӮ
10жңҲ4ж—Ҙжҷҡй—ҙпјҢи¶ҠеҚ—зҙҜи®ЎзЎ®иҜҠз—…дҫӢи¶…иҝҮ81дёҮдәәпјҢиҖҢиғЎеҝ—жҳҺеёӮд»Ҙи¶…40дёҮзЎ®иҜҠз—…дҫӢжҲҗдёәи¶ҠеҚ—第дёҖеӨ§“ж–°еҶ з–«еҢә” гҖӮиҖҢиғЎеҝ—жҳҺеёӮпјҢжӯЈжҳҜиҖҗе…ӢеңЁдёңеҚ—дәҡжңҖеӨ§е·ҘеҺӮжүҖеңЁең° гҖӮ
еҸ—з–«жғ…еҪұе“ҚпјҢд»Ҡе№ҙд»ҘжқҘи¶ҠеҚ—еҪ“ең°еҒңдёҡжҲ–и§Јж•Јзҡ„дјҒдёҡе·Із»Ҹи¶…иҝҮ8дёҮ家 гҖӮ6жңҲејҖе§ӢпјҢи¶ҠеҚ—иҝӣе…Ҙж–°дёҖиҪ®з–«жғ…з®ЎжҺ§жңҹпјҢиҖҗе…ӢеңЁ7жңҲе®Јеёғи¶ҠеҚ—жүҖжңүе·ҘеҺӮиҝӣе…Ҙ“жҡӮеҒңиҝҗиҗҘ”зҠ¶жҖҒпјҢиҖҢжҡӮеҒңзҠ¶жҖҒжҢҒз»ӯдәҶиҝ‘дёүдёӘжңҲ гҖӮ
“иҖҗе…Ӣзҡ„дё»иҰҒжө·еӨ–з”ҹдә§ең°и¶ҠеҚ—е…ЁеӣҪиҢғеӣҙеҶ…е®һиЎҢе°Ғй”ҒпјҢеҜјиҮҙе…¬еҸёе·Із»ҸеңЁи¶ҠеҚ—жҚҹеӨұдәҶ10е‘Ёзҡ„з”ҹдә§ж—¶й—ҙпјҢеҠ дёҠжө·иҝҗж—¶й—ҙ延й•ҝпјҢжңӘжқҘеҮ дёӘеӯЈеәҰе…¬еҸёзҡ„еә“еӯҳе°Ҷйқўдёҙзҹӯзјә гҖӮ”еңЁиҝ‘жңҹзҡ„з”өиҜқдјҡи®®дёҠпјҢиҖҗе…ӢйҰ–еёӯиҙўеҠЎе®ҳ马дҝ®·еј—е…°еҫ·жҳҺзЎ®иЎЁзӨәпјҢи¶ҠеҚ—дә§иғҪзҡ„жҚҹеӨұпјҢе°ҶеҜ№иҖҗе…ӢжҺҘдёӢжқҘеңЁеҮ дёӘе…ій”®зҡ„“иҙӯзү©е‘Ёжңҹ”зҡ„дёҡз»©йҖ жҲҗеҪұе“Қ гҖӮ
еҖјеҫ—жіЁж„Ҹзҡ„жҳҜпјҢе’ҢиҖҗе…ӢдёҖиө·еңЁи¶ҠеҚ—йҒӯйҒҮдә§иғҪеӣ°еұҖзҡ„иҝҳжңүйҳҝиҝӘиҫҫж–ҜгҖҒе®үеҫ·зҺӣзӯүе“ҒзүҢ гҖӮиҮӘ2008е№ҙејҖе§ӢпјҢиҝҷдәӣе“ҒзүҢејҖе§ӢдәҶдёҖиҪ®“е·ҘеҺӮиҝҒеҫҷ”пјҢз”ұдәҺиҙӘж…•и¶ҠеҚ—жӣҙдёәдҪҺе»үзҡ„дәәе·Ҙд»·ж јпјҢ他们жҠҠеҺҹжң¬дҪҚдәҺдёӯеӣҪзҡ„е·ҘеҺӮиҝҒеҫҷеҲ°дәҶи¶ҠеҚ—гҖҒ马жқҘиҘҝдәҡгҖҒжі°еӣҪ гҖӮиҖҢеңЁжӯӨ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и¶ҠеҚ—е…¬ејҖжҸҗеҮәдәҶжҲҗдёәж–°“дё–з•Ңе·ҘеҺӮ”зҡ„зӣ®ж ҮпјҢ并еҗ‘иҝҷдәӣе“ҒзүҢж•һејҖжҖҖжҠұ гҖӮ
иҖҢиҝҷйҖҗжёҗжһ„жҲҗдәҶиҝҮеҺ»12е№ҙиҝҗеҠЁйһӢжңҚеёӮеңәзҡ„ж–°ж јеұҖпјҡиҖҗе…ӢгҖҒйҳҝиҝӘиҫҫж–ҜзӯүеӣҪйҷ…е“ҒзүҢпјҢйҖҡиҝҮи¶ҠеҚ—зҡ„е»үд»·е·ҘеҺӮе®ҢжҲҗз”ҹдә§пјҢ然еҗҺе°Ҷдә§е“Ғиҙ©еҚ–еҲ°дёӯеӣҪгҖҒзҫҺеӣҪзӯүе…ій”®еёӮеңә гҖӮ
дҪҶз–«жғ…жӯЈеңЁи®©дёҖеҲҮйҮҚеҗҜ гҖӮ
е·Із»ҸжңүеӣҪйҷ…е“ҒзүҢејҖе§Ӣж’ӨзҰ»и¶ҠеҚ— гҖӮиҜһз”ҹдәҺ1883е№ҙзҡ„зҫҺеӣҪйһӢзұ»йӣҶеӣўWOLVERINEпјҲж——дёӢе“ҒзүҢжңүCATгҖҒHUSH PUPPIESпјүе·Із»ҸејҖе§Ӣе°Ҷдә§иғҪиҪ¬еӣһдёӯеӣҪ гҖӮеңЁд»Ҡе№ҙ9жңҲзҡ„дёҖж¬ЎйҮҮи®ҝдёӯпјҢWOLVERINEй«ҳз®ЎжӣҫзӣҙиЁҖеҹәдәҺи¶ҠеҚ—е·ҘеҺӮзҡ„дҫӣеә”й“ҫжЁЎејҸ“жһҒз«ҜдёҚзЁіе®ҡ” гҖӮ
ж‘ҶеңЁиҖҗе…Ӣ们йқўеүҚзҡ„жҢ‘жҲҳе…¶е®һиҝҳжңүдёӯеӣҪжң¬еңҹеӣҪиҙ§зҡ„ејәеҠҝеҙӣиө· гҖӮжқҘиҮӘжқҺе®Ғе’Ңе®үиёҸзҡ„иҙўжҠҘжҳҫзӨәпјҢ2021е№ҙдёҠеҚҠе№ҙдёӨеӨ§жң¬еңҹе“ҒзүҢиҗҘ收еҗҢжҜ”еўһйҖҹеҲҶеҲ«иҫҫеҲ°55.5%гҖҒ65%пјҢиҖҢеңЁ2020е№ҙе®үиёҸеҮҖеҲ©ж¶Ұе·Із»Ҹи¶…и¶ҠйҳҝиҝӘиҫҫж–ҜдёӯеӣҪпјҢиҖҢеңЁд»Ҡе№ҙ6жңҲе®үиёҸеёӮеҖје·Із»Ҹи¶…иҝҮйҳҝиҝӘиҫҫж–Ҝ гҖӮ
иҖҗе…Ӣзҡ„и¶ҠеҚ—“иӢҰж—…”
“иҖҗе…Ӣе·ҘеҺӮжңүжңӣеңЁ10жңҲд»ҪеӨҚе·ҘпјҢдҪҶжҒўеӨҚдә§иғҪеҸҜиғҪйңҖиҰҒй•ҝиҫҫж•°жңҲзҡ„ж—¶й—ҙ гҖӮ”еңЁ9жңҲ24ж—ҘеҲҶжһҗеёҲз”өиҜқдјҡи®®дёҠпјҢиҖҗе…Ӣй«ҳз®ЎеҜ№иҖҗе…Ӣи¶ҠеҚ—дә§иғҪзҡ„еӨҚе·ҘиҝӣеәҰ“并дёҚд№җи§Ӯ” гҖӮ
д»Һ2012е№ҙдёӢеҚҠе№ҙиҮід»ҠпјҢи¶ҠеҚ—е·Із»ҸйҖҗжёҗжҲҗдёәиҖҗе…Ӣ第дёҖеӨ§з”ҹдә§еҹәең° гҖӮжқҘиҮӘиҖҗе…ӢиҙўжҠҘзҡ„ж•°жҚ®жҳҫзӨәпјҢ2019~2020е№ҙпјҢиҖҗе…Ӣзҡ„йһӢзұ»дә§е“Ғжңүиҝ‘50%дә§иҮӘи¶ҠеҚ—е·ҘеҺӮпјҢиҖҢжңҚиЈ…зұ»дә§е“Ғдёӯзҡ„дёүеҲҶд№ӢдёҖд№ҹдә§иҮӘиҝҷйҮҢ гҖӮ
еңЁд»Ҡе№ҙж—©дәӣж—¶еҖҷпјҢзҹҘеҗҚйҮ‘иһҚеҸҠдҝЎжҒҜжңҚеҠЎжңәжһ„S&P Globaе·Із»ҸеҜ№иҖҗе…Ӣзҡ„“ж–ӯиҙ§”иҝӣиЎҢдәҶйЈҺйҷ©йў„иӯҰ гҖӮеңЁеҪ“ж—¶зҡ„еҮ еҲҶеҲҶжһҗжҠҘе‘ҠдёӯпјҢ“иҖҗе…Ӣдә§иғҪй«ҳеәҰйӣҶдёӯдәҺи¶ҠеҚ—дёҖең°”иў«и§Ҷдёәе…ій”®йЈҺйҷ©йЎ№ гҖӮ
дә§иғҪйӣҶдёӯеәҰдёҖзӣҙжҳҜиҖҗе…Ӣеј•д»ҘдёәеӮІзҡ„зҺҜиҠӮд№ӢдёҖ гҖӮеңЁи¶ҠеҚ—пјҢиҖҗе…Ӣдә§е“Ғзҡ„з”ҹдә§пјҢдё»иҰҒйҖҡиҝҮ“д»Је·Ҙ”жЁЎејҸи§ЈеҶі гҖӮиҖҗе…ӢеңЁи¶ҠеҚ—дёӨдёӘжңҖйҮҚиҰҒзҡ„дҫӣеә”е•ҶеҲҶеҲ«жҳҜжқҘиҮӘйҹ©еӣҪзҡ„Changshin VietnamпјҢд»ҘеҸҠжқҘиҮӘдёӯеӣҪеҸ°ж№ҫзҡ„е®қжҲҗ гҖӮиҝҷдәӣд»Је·Ҙж–№зҡ„е·ҘеҺӮеӣҙз»•иғЎеҝ—жҳҺеёӮзӯүеҮ дёӘе…ій”®еҢәеқ—еҲҶеёғпјҢиҖҢе…¶жңҖеӨ§зҡ„е·ҘеҺӮеңЁж»Ўе·Ҙжңҹй—ҙпјҢиғҪе®№зәіиҝ‘7дёҮеҗҚе·Ҙдәә гҖӮ
йӣҶдёӯеәҰ并йқһжңқеӨ•д№ӢеҠҹ гҖӮи¶ҠеҚ—зҡ„ж”ҝзӯ–зәўеҲ©е’Ңе»үд»·е·ҘдәәжҲҗдёәдәҶеҗёеј•еӨ–иө„зҡ„дёӨеӨ§еј•ж“Һ гҖӮ
д»ҘиғЎеҝ—жҳҺеёӮдёәдҫӢпјҢдёәдәҶеҗёеј•иҖҗе…Ӣзҡ„д»Је·ҘеҺӮеңЁжӯӨеёғеұҖпјҢиғЎеҝ—жҳҺеёӮжҲҗз«ӢдәҶиӢҘе№Ізәәз»ҮжңҚиЈ…зұ»дә§дёҡеӣӯпјҢиҖҗе…Ӣзҡ„д»Је·ҘеҺӮе’ҢдёҠдёӢжёёдҫӣиҙ§ж–№йғҪеҸҜд»Ҙе…Ҙй©»дәҺжӯӨпјҢиҖҢиҝҷдәӣдә§дёҡеӣӯдјҡжҸҗдҫӣ“зЁҺиҙ№”ж–№йқўзҡ„дјҳжғ гҖӮ
и¶ҠеҚ—еҪ“ең°дёҖзі»еҲ—“еҗёеј•еӨ–иө„”зҡ„еҒҡжі•пјҢд»Һ2008е№ҙејҖе§ӢеҪўжҲҗдәҶдёҖиӮЎ“еј•иө„жҪ®” гҖӮйҹ©иө„дјҒдёҡе…¶е®һжҳҜжңҖж—©иҜ•ж°ҙи¶ҠеҚ—еёӮеңәзҡ„зҫӨдҪ“д№ӢдёҖпјҢ2008е№ҙд№ӢеҗҺпјҢеңЁи¶ҠеҚ—е»әз«Ӣе·ҘеҺӮжҲ–и®ҫзҪ®еҠһе…¬еӨ„зҡ„йҹ©иө„дјҒдёҡи¶…иҝҮдәҶ4000家 гҖӮ
еңЁиҝҷ4000еӨҡ家йҹ©иө„дјҒдёҡдёӯпјҢдёҚд№ҸжңҚиЈ…йһӢзұ»дјҒдёҡ гҖӮжҜ”еҰӮHansaeпјҢиҝҷ家公еҸёжӣҫеңЁи¶ҠеҚ—дёҖеҸЈж°”е»әз«Ӣдёү家е·ҘеҺӮпјҢиҖҢе®ғ们е®һйҷ…дёҠеҸӘжҳҜд»Је·Ҙж–№——Hansaeе…ҲжӢҝеҲ°GAPгҖҒиҖҗе…Ӣзӯү欧зҫҺе“ҒзүҢзҡ„и®ўеҚ•пјҢ然еҗҺйҖҡиҝҮи¶ҠеҚ—е·ҘеҺӮз”ҹдә§пјҢеҶҚз”ұдҪҚдәҺйҹ©еӣҪзҡ„Hansaeиҙёжҳ“е…¬еҸёе®ҢжҲҗй”Җе”® гҖӮ
еңЁиҝӣеҶӣи¶ҠеҚ—еүҚпјҢHansaeеңЁеҚ°еәҰе°јиҘҝдәҡгҖҒе°јеҠ жӢүз“ңзӯүең°йғҪжӣҫи®ҫз«ӢдәҶе·ҘеҺӮпјҢдҪҶд»Һ2008е№ҙеҲ°2012е№ҙпјҢHansaeиҝ…йҖҹжҠҠдә§иғҪеҗ‘и¶ҠеҚ—иҒҡйӣҶ——жҲӘиҮі2012е№ҙиҝҷйҮҢе·Із»ҸжҲҗдёәHansaeйҹ©еӣҪд№ӢеӨ–жңҖеӨ§дә§иғҪеҹәең°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AMD|жңҖй«ҳеҸҜйҖүй”җйҫҷ9пјҒMoreFineиҝ·дҪ PCдёҠж–°пјҡе…ЁйқўжӢҘжҠұAMD
- AMD|еёқзӣҹеҪ’жқҘпјҒж—¶йҡ”5е№ҙеҶҚж¬ЎжӢҘжҠұAMDжҳҫеҚЎ д»·ж јж®Ӣжҡҙ
- EVGA|дёҖеӨ§жү№RTX 30жҳҫеҚЎеңЁзҫҺеӣҪиў«зӣ—пјҡдёӨдёӘжңҲеҗҺзҺ°иә«и¶ҠеҚ— и¶…дҪҺд»·з”©еҚ–
- иҖҗе…Ӣ|иҖҗе…ӢжӯЈеӨұеҺ»дёӯеӣҪе№ҙиҪ»дәә
- зҘЁжҲҝ|2022е№ҙе…ғж—ҰжЎЈжҖ»зҘЁжҲҝз ҙ12дәҝпјҒгҖҠз©ҝиҝҮеҜ’еҶ¬жӢҘжҠұдҪ гҖӢжңҖзҒ« зҢ«зңј9.5еҲҶ
- з”ҹ科еҢ»еӯҰ|е®ҒжіўеҢ—д»‘дёҖе…¬еҸё2еӨ©жҠҘе‘Ҡ10дҫӢзЎ®иҜҠпјҡз—…жҜ’жқҘиҮӘи¶ҠеҚ—пјҹ
- зҘЁжҲҝ|е…ғж—ҰйҷўзәҝжҖ»зҘЁжҲҝзӘҒз ҙ10дәҝеӨ§е…іпјҡгҖҠз©ҝиҝҮеҜ’еҶ¬жӢҘжҠұдҪ гҖӢ4дәҝзҘЁжҲҝзўҫеҺӢејҸеӨәеҶ
- з”ҹ科еҢ»еӯҰ|50з®ұи¶ҠеҚ—иҝӣеҸЈж¶үз–«зҒ«йҫҷжһңжөҒе…ҘеұұиҘҝеӨӘеҺҹпјҡе·Із»Ҹе”®е®Ң
- з”өеҪұ|2022е№ҙе…ғж—ҰжЎЈж–°зүҮзҘЁжҲҝз ҙдәҝпјҒиҙҫзҺІгҖҒй»„жёӨдё»жј”гҖҠз©ҝиҝҮеҜ’еҶ¬жӢҘжҠұдҪ гҖӢйўҶи·‘
- е·ҘзЁӢе»әзӯ‘|и¶ҠеҚ—йҖ д»·1500дёҮзҡ„еӨ§жЎҘиҪ°з„¶еҖ’еЎҢ ж–ӯжҲҗеҮ жҲӘжә…иө·е·ЁеӨ§ж°ҙиҠұпјҡзҪ‘еҸӢзӣҙе‘јиҙЁйҮҸеӨӘ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