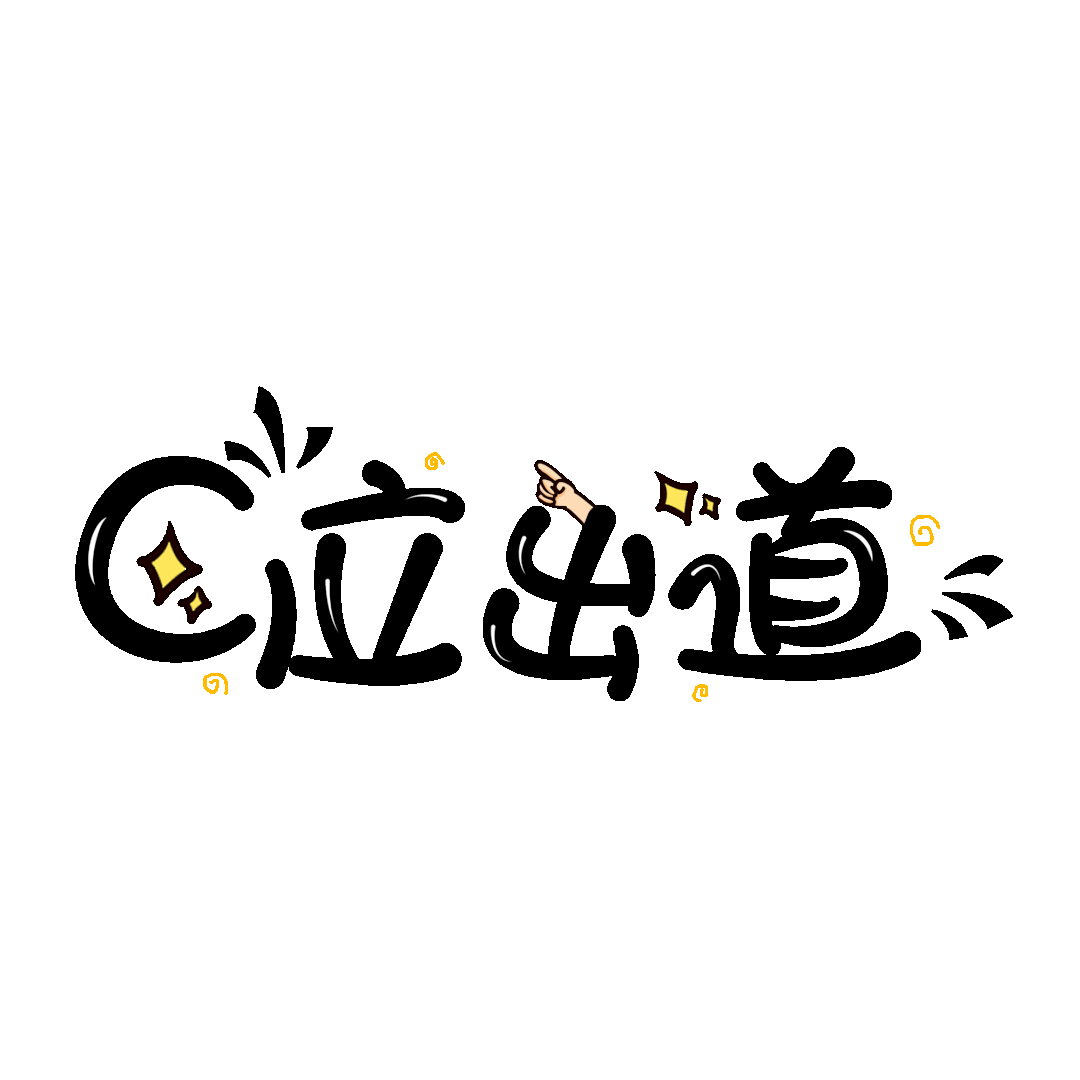йҳҺиҝһ科пјҡ?дёҖдёӘдҪң家еқҡжҢҒеҶҷдҪңпјҢжҳҜеӣ дёәд»–е§Ӣз»ҲеқҡдҝЎиҮӘе·ұеҸҜд»ҘеҶҷеҮәдјҳз§Җзҡ„дҪңе“Ғ( дәҢ )
иҜҡе®һеқҰиЁҖпјҢзӣҙеҲ°д»ҠеӨ©пјҢжҲ‘йғҪж— жі•и¶…и¶ҠеҜ№жӯ»дәЎзҡ„жҒҗж…ҢпјҢжҜҸжҜҸжғіеҲ°вҖңжӯ»дәЎвҖқдәҢеӯ—пјҢеҝғйҮҢе°ұжңүз§ҚзҒ°жҡ—зҡ„з–јз—ӣгҖӮдјҡжңүз§ҚеӨ§и„‘дҫӣиЎҖдёҚи¶ізҡ„еҝғж…ҢгҖӮе°ұжҳҜдёӨдёүе№ҙеүҚпјҢеҢ—дә¬дҪңеҚҸзҡ„иҖҒдҪң家жһ—ж–Өжҫңе…Ҳз”ҹеӣ з—…и°ўдё–пјҢжҲ‘жүҫдёҚеҲ°зҗҶз”ұдёҚеҺ»е…«е®қеұұдёәд»–йҖҒиЎҢпјҢеӣһжқҘеҗҺиҝҳиҝһз»ӯ3дёӘжҷҡдёҠеӨұзң зғҰжҒјпјҢеҗҺжӮ”дёҚиҜҘеҺ»йӮЈдёӘеҲ°еӨ„йғҪжҳҜвҖңзҘӯвҖқеӯ—гҖҒвҖңеҘ вҖқеӯ—е’Ңй»‘иҠұгҖҒзҷҪиҠұзҡ„ең°ж–№гҖӮ
зҺ°еңЁпјҢеј„дёҚжҳҺзҷҪжҲ‘дёәд»Җд№ҲиҰҒ继з»ӯеҶҷдҪңпјҢжҲ‘е°ұеҜ№дәәиҜҙпјҡвҖңеҶҷдҪңжҳҜдёәдәҶиҜҒжҳҺжҲ‘иҝҳеҒҘеә·ең°жҙ»зқҖгҖӮвҖқжҲ‘дёҚзҹҘйҒ“иҝҷеҸҘиҜқйҮҢжңүеӨҡе°‘е№Ҫй»ҳпјҢжңүеӨҡе°‘еҮҶзЎ®пјҢеҸӘжҳҜи§үеҫ—еҫҲж„ҝж„Ҹиҝҷж ·еҺ»иҜҙгҖӮеӣ дёәжҲ‘дёҚиғҪиҜҙпјҡвҖңжҲ‘еҶҷдҪңжҳҜдёәдәҶйҖғйҒҝе’ҢжҠөжҠ—жӯ»дәЎгҖӮвҖқйӮЈж ·дјҡи§үеҫ—еӨӘиҝҮжӯЈз»ҸпјҢжңӘе…ҚеӨҡжңүз§Җжј”гҖӮеҸҜжҠҠжӯ»дәЎе’ҢеҶҷдҪңпјҢжҠҠдёҖдёӘдәәзҡ„иҮӘ然з”ҹе‘Ҫе’Ңж–ҮеӯҰиҒ”зі»еңЁдёҖиө·ж—¶пјҢжҲ‘е®һеңЁжүҫдёҚеҲ°д»ӨжҲ‘е’Ңд»–дәәйғҪж„ҹжӣҙдёәиҙҙеҲҮгҖҒжӣҙдёәеҮҶзЎ®пјҢеҸҲеҸҜдҝЎе®һзҡ„жҹҗз§ҚиҜҙиҫһгҖӮ
жҲ‘еёёеёёеңЁжҹҗз§Қзҹӣзӣҫе’ҢжӮ–и®әдёӯеҶҷдҪңгҖӮеӣ дёәе®іжҖ•е’ҢйҖғйҒҝжӯ»дәЎжүҚиҰҒеҶҷдҪңпјҢиҖҢеҸҲеңЁеҶҷдҪңдёӯеҸҚеӨҚең°гҖҒйҮҚеӨҚең°еҺ»д№ҰеҶҷжӯ»дәЎгҖӮжҲ‘иҜҙгҖҠж—Ҙе…үжөҒе№ҙгҖӢжҳҜдёәеҜ№жҠ—жӯ»дәЎиҖҢдҪңпјҢе…¶е®һд№ҹеҸҜд»ҘиҜҙжҳҜеӣ жҒҗжғ§жӯ»дәЎиҖҢжӮ й•ҝзҡ„еҸ№жҒҜгҖӮгҖҠжҲ‘дёҺзҲ¶иҫҲгҖӢдёӯжңүеӨ§ж®өеҜ№жӯ»дәЎжө…зҷҪз®ҖеҚ•зҡ„и®®и®әпјҢйӮЈд№ҹе…¶е®һжҳҜиҮӘе·ұеҜ№жӯ»дәЎжҒҗжғ§иҖҢиЈ…и…”дҪңеҠҝзҡ„е‘җе–ҠгҖӮ
жҲ‘дёҚзҹҘйҒ“жҲ‘д»Җд№Ҳж—¶й—ҙгҖҒд»Җд№Ҳе№ҙеІҒеҸҜд»Ҙи¶…и¶ҠеҜ№жӯ»дәЎзҡ„жҒҗж…ҢпјҢдҪҶжҲ‘зҶҹжӮүзҡ„и°·е·қдҝҠеӨӘйғҺе…Ҳз”ҹпјҢеңЁе№ҙиҝ‘80еІҒж—¶иҜҙдәҶ вҖңз”ҹе‘ҪдәҺжҲ‘пјҢеү©дёӢзҡ„ж—¶й—ҙе°ұжҳҜ笑зқҖзӯүеҫ…жӯ»дәЎзҡ„еҲ°жқҘвҖқйӮЈж ·зҡ„иҜқпјҢи®©жҲ‘ж„ҹеҲ°жё©жҡ–зҡ„йңҮж’јгҖӮ
иҝҷеҸҘеҜ№иҮӘ然з”ҹе‘ҪдёҺжңӘжқҘжӯ»дәЎзҡ„ж„ҹж…Ёд№ӢиЁҖпјҢжҲ‘еёҢжңӣе®ғдјҡеғҸдёҖзІ’иҗӨзҒ«жҲ–дёҖзәҝзғӣе…үпјҢеңЁд»ҠеҗҺзҡ„ж—ҘеӯҗйҮҢпјҢз…§дә®жҲ‘д№Ӣз”ҹе‘ҪдёҺжӯ»дәЎйӮЈжңҖзҒ°жҡ—зҡ„ең°ж®өе’Ңи§’иҗҪпјҢи®©жҲ‘ж•ўдәҺжӯЈи§Ҷжӯ»дәЎпјҢеҰӮжӯЈи§ҶжҲ‘家зӘ—еүҚдёҖжЈөж ‘жңЁзҡ„еІҒжңҲжһҜиҚЈгҖӮ
еҰӮжһңжҠҠдәәзҡ„иҮӘ然з”ҹе‘Ҫи§ҶдёәдёҖжқЎжҹҗдёҖеӨ©ејҖе§ӢжөҒж·ҢгҖҒжҹҗдёҖеӨ©еҝ…然ж¶ҲеӨұзҡ„жІіжөҒпјҢдәҺдҪң家гҖҒиҜ—дәәгҖҒ画家гҖҒиүәжңҜ家зӯүзӯүзӣёзұ»дјјзҡ„дәәиҖҢиЁҖпјҢд»ҺиҝҷжқЎжІіжөҒдјҡжҙҫз”ҹеҮәеҸҰеӨ–зҡ„дёҖжқЎжІіжөҒжқҘгҖӮйӮЈе°ұжҳҜдҪ жҙ»зқҖж—¶еҲӣдҪңеҮәзҡ„дҪңе“Ғзҡ„з”ҹе‘Ҫж—¶й—ҙгҖӮ
жӣ№йӣӘиҠ№жҙ»дәҶеӨ§зәҰ40еҮ еІҒпјҢиҖҢгҖҠзәўжҘјжўҰгҖӢеҶҷе°ұзәҰиҝ‘250е№ҙпјҢдјјд№Һд»ҠеӨ©еҲҷеҲҡе…Ҙз”ҹе‘ҪзӣӣжңҹгҖӮжІЎжңүдәәиғҪи®©жӣ№йӣӘиҠ№йҮҚж–°жҙ»жқҘпјҢи…җйӘЁйҮҚз”ҹпјҢеҸҜд№ҹжІЎжңүдәәжңүиғҪеҠӣи®©гҖҠзәўжҘјжўҰгҖӢж¶ҲеӨұжӯ»еҺ»пјҢжҲҗдёәеәҹзәёзҒ°зғ¬гҖӮеҚЎеӨ«еҚЎ41еІҒж—¶з”ҹе‘Ҫж¶ҲеӨұпјҢиҖҢгҖҠеҹҺе ЎгҖӢгҖҒгҖҠеҸҳеҪўи®°гҖӢеҚҙз”ҹе‘Ҫ蔓延дёҚиЎ°пјҢеІҒжңҲд№…й•ҝд№…й•ҝгҖӮ
他们еңЁжҙ»зқҖ时并дёҚзҹҘиҮӘе·ұзҡ„дҪңе“Ғдјҡз”ҹе‘Ҫд№…иҝңпјҢе®ӣиӢҘжүҳе°”ж–Ҝжі°жҙ»зқҖж—¶пјҢдёҚеҜ№иҮӘе·ұзҡ„еҶҷдҪңе’ҢдҪңе“Ғе……ж»ЎдҝЎеҝғгҖӮдёҖдёӘ画家дёҚзӣёдҝЎиҮӘе·ұзҡ„дҪңе“ҒеҸҜд»Ҙй•ҝе‘ҪзҷҫеІҒпјҢ并дёҚзӯүдәҺд»–дёҚзҗҶжғізқҖиҮӘе·ұзҡ„дҪңе“Ғз”ҹе‘ҪдёҚжҒҜгҖӮ
дёҖдёӘдҪң家д№ӢжүҖд»ҘиҰҒ继з»ӯеҶҷдҪңпјҢжәҗжәҗдёҚж–ӯпјҢйҷӨдәҶз”ҹеӯҳзҡ„йңҖжұӮпјҢд»Һж №жң¬еҺ»иҜҙпјҢд»–иҝҳжҳҜзӣёдҝЎпјҢжҲ–иҖ…дҫҘе№ёиҮӘе·ұеҸҜд»ҘеҶҷеҮәеҘҪзҡ„д№ғиҮідјҹеӨ§зҡ„дҪңе“ҒжқҘгҖӮеҰӮжһңдёҚжҖ•жӢӣдәәи°©йӘӮпјҢжҲ‘е°ұеқҰ然жҲ‘жҖ»жҳҜеӯҳжңүиҝҷж ·дҫҘе№ёзҡ„иҺҪж’һйҮҺж„ҝгҖӮ
дҪҶжҲ‘д№ҹзҹҘйҒ“пјҢдәӢжғ…еёёеёёжҳҜдәӢдёҺж„ҝиҝқпјҢеҖҚеҠӣж— еҠҹпјҢеҰӮдёҖдёӘдёҖз”ҹй•ҝи·‘зҡ„иҝҗеҠЁе‘ҳпјҢеҲ°жӯ»дҪ зҡ„и„ҡжӯҘйғҪеңЁдј—дәәд№ӢеҗҺгҖӮдҪ зҡ„еҶІеҲәеҸӘжҳҜиҜҒжҳҺдҪ зҡ„еҸҢи„ҡиҝҳжңүеҠӣйҮҸзҡ„еӯҳеңЁпјҢиҜҒжҳҺдҪ еңЁй•ҝи·‘дёӯжҺүйҳҹдҪҶжІЎжңүйҖүжӢ©ж”ҫејғе’ҢйҖҖеҮәгҖӮеҰӮжӯӨиҖҢе·ІпјҢиҮіеӨҡд№ҹе°ұжҳҜйІҒиҝ…жӯҢйўӮзҡ„вҖңжңҖеҗҺдёҖдёӘи·‘иҖ…вҖқзҪўдәҶгҖӮ
еңЁдёӯеӣҪдҪң家дёӯпјҢжҲ‘дёҚжҳҜеҶҷеҫ—жңҖеӨҡзҡ„пјҢд№ҹдёҚжҳҜжңҖе°‘зҡ„пјӣдёҚжҳҜеҶҷеҫ—жңҖеҘҪзҡ„пјҢд№ҹдёҚжҳҜжңҖе·®зҡ„гҖӮжҲ‘жҳҜжҢӨеңЁи·‘йҒ“дёҠжІЎжңүеҒңи„ҡиҖ…зҡ„дёҖдёӘгҖӮи·‘еҲ°жңҖеүҚзҡ„пјҢд»–еңЁе№ҙиҖҒд№ӢеҗҺпјҢеҸҜд»ҘеқҰ然ең°з«ҷеңЁй«ҳеӨ„пјҢйқўеҜ№еӨ•йҳіпјҢе№ійқҷиҖҢзј“ж…ўең°иҮӘиҜӯпјҡвҖңз”ҹе‘ҪдәҺжҲ‘пјҢеү©дёӢзҡ„ж—¶й—ҙе°ұжҳҜ笑зқҖзӯүеҫ…жӯ»дәЎзҡ„еҲ°жқҘгҖӮвҖқеӣ дёә他们еңЁж—¶й—ҙдёӯиҜҒе®һ并еҸҜд»ҘзңӢеҲ°иҮӘе·ұдҪңе“Ғ蔓延ж—әиҢӮзҡ„з”ҹе‘ҪпјҢиҖҢжҲ‘дәҺиҝҷдәӣиҜҒе®һе’ҢзңӢеҲ°зҡ„пјҢеҚҙжҳҜдёҚеҸҜиғҪзҡ„дёҖдёӘжңӘжқҘгҖӮдҪ•еҶөзҺ°еңЁе·Із»Ҹ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йҳ…иҜ»зҡ„ж—¶д»ЈгҖӮдҪ•еҶөе·Із»Ҹжңүдәәж–ӯиЁҖе®ЈеёғпјҡвҖңе°ҸиҜҙе·Із»Ҹжӯ»дәЎпјҒвҖқ
еңЁжҲ‘жқҘиҜҙпјҢжҲ‘дёҚеҘўжңӣиҮӘе·ұзҡ„дҪңе“ҒжңүеӨҡй•ҝзҡ„з”ҹе‘ҪеҠӣпјҢеҸӘеёҢжңӣдёҠдёҖйғЁиғҪз»ҷдёӢдёҖйғЁеёҰжқҘеҶҷдҪңзҡ„еҠӣйҮҸпјҢи®©жҲ‘жҙ»зқҖж—¶пјҢж„ҹеҲ°еҶҷдҪңеҜ№иҮӘ然з”ҹе‘ҪеҸҜд»Ҙз”ҹеўһеӯҳеңЁзҡ„ж„Ҹд№үгҖӮ
д»ҠеӨ©пјҢдёҚжҳҜж–ҮеӯҰдёҺиҜ»д№Ұзҡ„ж—¶д»ЈпјҢжӣҙдёҚжҳҜиҜ—жӯҢзҡ„ж—¶д»ЈпјҢеҸҜи°·е·қдҝҠеӨӘйғҺзҡ„иҜ—еңЁж—Ҙжң¬еҚҙеҸҜд»ҘжҜҸйғЁеҚ°иҮі3дёҮдҪҷеҶҢпјҢдёҖйғЁиҜ—йҖүйӣҶеҚ°еҲ·50дҪҷзүҲпјҢ80еӨҡдёҮеҶҢпјҢдё”д»Һд»–20еІҒеҲ°79еІҒпјҢ60е№ҙжқҘпјҢеІҒеІҒз•…еҚ–еёёеҚ–гҖӮиҝҷж ·жҲ‘们еҜ№иҜ—дәәе·Із»ҸдёҚеҸҜеӨҡиҜҙд»Җд№ҲпјҢе°ұжҳҜиҒӮйІҒиҫҫе’Ңиүҫйқ’иҝҳжҙ»зқҖпјҢеҜ№д»ҠеӨ©ж—Ҙжң¬дәәз—ҙжғ…дәҺжҹҗдҪҚиҜ—дәәзҡ„йҳ…иҜ»пјҢд№ҹеҸӘиғҪжҳҜй»ҳй»ҳ敬仰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马жңӘйғҪпјҡд№ҫйҡҶе№ҙй—ҙзҡ„вҖңжңҲйҘјзӣ’вҖқпјҢеұһдәҺе®«дёӯзҸҚе“ҒпјҢдёҖдёӘд»·еҖјдёҖеҘ—жҲҝ
- еӯҷжӮҹз©әдёҖдёӘзӯӢж–—еҚҒдёҮе…«еҚғйҮҢпјҢдёәдҪ•дёҚиғҢзқҖе”җеғ§пјҢеҺҹеӣ жҳҜиғҢдёҚеҠЁ
- жўҒеұұжңҖдёҚеҗҲзҫӨзҡ„еҘҪжұүпјҢеңЁжўҒеұұжІЎдёҖдёӘжңӢеҸӢпјҢз”ҹз—…еҗҺжІЎдәәз…§йЎҫз—…йҖқ
- иҸ©жҸҗиҖҒзҘ–дёҺе…ғе§ӢеӨ©е°ҠжҳҜеҗҢдёҖдёӘдәәеҗ—пјҢдёӨиҖ…д»Җд№Ҳе…ізі»пјҢи°ҒжӣҙеҺүе®і
- вҖңеҸҢеҺЁзӢӮе–ңвҖқпјҢйҡӢе”җеӨ§иҝҗжІіеҚҡзү©йҰҶ&жҙӣе…«еҠһпјҢдҪ pickе“ӘдёҖдёӘ
- еӨ©и“¬е…ғеё…жҺҢз®Ў8дёҮж°ҙе…өпјҢдёәд»Җд№Ҳй…ҚдёҚдёҠдёҖдёӘе«ҰеЁҘпјҹ
- иҖҒдәәзӢ¬иҮӘз”ҹжҙ»еңЁеұұйҮҢпјҢд»–з”Ё40е№ҙзҡ„ж—¶й—ҙпјҢжҠҠжӮ¬еҙ–еҸҳжҲҗдёҖдёӘе·ЁеӨ§иүәжңҜе“Ғ
- дёҠиҚҜжңҚиҚҜеҗҢж—¶иҝӣиЎҢжІ»и„ҡж°”,и®°зүўиҝҷ3жӢӣ!иӯҰйҶ’вҖңдёҖдёӘж„ҹжҹ“2вҖқ
- иҜ—йІё2068гҖҠжҜҸдёҖдёӘжҲ‘们йғҪжӣҫжңүиҝҮиҝҷж ·зҡ„з»ҸеҺҶгҖӢ
- еҜ№дёӯеӣҪз–ҶеҹҹиҙЎзҢ®жңҖеӨ§зҡ„дёҖдёӘжңқд»ЈпјҢеҚҙдёҚиў«еҗҺдё–жүҖе–ңж¬ўпјҢжғ№жҳ“дёӯеӨ©еӨ§йӘ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