е…ЁеўһеҳҸпјҡе“ІеӯҰз ”з©¶иҰҒиҙҜйҖҡеҸӨд»ҠдёӯеӨ–|зӨјиөһеӨ§еёҲ | зӨјиөһ( еӣ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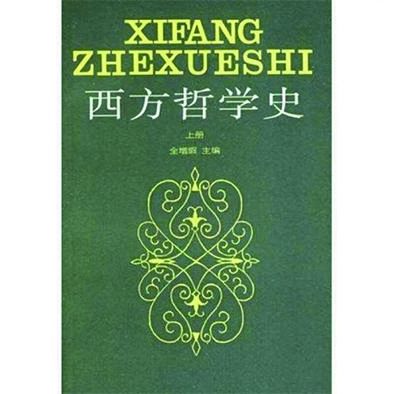
ж–Үз« жҸ’еӣҫ
гҖҠиҘҝж–№е“ІеӯҰеҸІгҖӢ
еҹ№е…»еӯҰз”ҹжҳҜвҖңжүӢе·ҘдҪңеқҠвҖқејҸзҡ„зІҫе·Ҙз»ҶдҪң
еҜ№дәҺиҮӘе·ұзҡ„еӯҰз”ҹпјҢе…ЁеўһеҳҸеҖҫжіЁдәҶе…ЁйғЁзҡ„еҝғиЎҖгҖӮ1962е№ҙпјҢж•ҷиӮІйғЁжӯЈејҸе®һж–Ҫз ”з©¶з”ҹжҠҘиҖғеҪ•еҸ–еҲ¶еәҰпјҢй»„йўӮжқ°е’Ңе§ҡд»ӢеҺҡдёӨдәәжҲҗдёә他第дёҖж¬ЎжӯЈејҸжӢӣ收зҡ„иҘҝж–№е“ІеӯҰз ”з©¶з”ҹгҖӮд»ҺйӮЈж—¶иө·пјҢе…ЁеўһеҳҸ家зҡ„иө·еұ…е®Өе°ұжҳҜеӯҰз”ҹзҡ„иҜҫе ӮпјҢд»–зҡ„еӨ«дәәиғЎж–Үж·‘е…Ҳз”ҹеҜ№жӯӨжҜ«ж— жҖЁиЁҖпјҢеҸҚиҖҢжҜҸж¬ЎйғҪзғӯжғ…жӢӣеҫ…гҖӮжңүж¬ЎеҘ№ејҖзҺ©з¬‘иҜҙпјҡвҖңдҪ 们иҝҷеҖ’еғҸжҳҜжүӢе·ҘдҪңеқҠпјҢеёҲеӮ…еёҰеҫ’ејҹпјҢзІҫе·Ҙз»ҶдҪңе•ҠпјҒвҖқе…ЁеўһеҳҸеӣһеә”иҜҙпјҡвҖңе°ұеә”иҜҘиҝҷж ·еӯҰжүҚеӯҰеҫ—еҘҪеҳӣпјҒвҖқпјҲй»„йўӮжқ°пјҢгҖҠзҷҫе№ҙеӨҚж—Ұе“ІеӯҰеӣӯең°зҡ„еӣӯдёҒгҖӢпјү
еңЁиҘҝж–№е“ІеӯҰзҡ„дё“дёҡеӯҰд№ дёҠпјҢе…ЁеўһеҳҸж•ҷеҜјеӯҰз”ҹйҰ–е…ҲиҰҒиҜ»жҮӮиҜ»йҖҸе“ІеӯҰ家зҡ„еҺҹи‘—пјҢејәи°ғйҳ…иҜ»дёӯиҰҒејҖеҠЁи„‘зӯӢпјҢжңүиҮӘе·ұзҡ„еҝғеҫ—гҖҒи§ҒиҜҶпјҢдёҚиғҪи®©д№Ұдёӯзҡ„вҖңйҮ‘жҲҲй“Ғ马вҖқеңЁи„‘жө·дёӯеҘ”驶дёҖз•ӘпјҢд»Җд№ҲйғҪдёҚз•ҷдёӢпјӣд»–иҰҒжұӮеӯҰз”ҹжҜҸдёӘжңҲйғҪиҰҒдәӨдёҖзҜҮиҜ»д№Ұеҝғеҫ—жҲ–ж–Үз« пјҢ并且з»ҶиҮҙең°иҜ„зӮ№дёҺжү№ж”№пјӣд»–еёёиҜҙеҶҷж–Үз« еҲҮеҝҢз©әжіӣеҸ‘и®®и®әпјҢеҠЎеҝ…иЁҖд№Ӣжңүзү©гҖҒиЁҖд№ӢжңүжҚ®пјҢд»–иҜҙеҒҡз§‘з ”иҰҒеғҸжө·з»өе–„дәҺеҗёж°ҙеҸҲиғҪж”ҫж°ҙгҖӮеӯҰжҹҸжӢүеӣҫе’ҢдәҡйҮҢеЈ«еӨҡеҫ·дё“йўҳж—¶пјҢд»–зү№ж„Ҹе®үжҺ’еӯҰз”ҹеҺ»еҚҺдёңеёҲеӨ§еҫҗжҖҖеҗҜе…Ҳз”ҹпјҲеЁҙзҶҹеёҢи…Ҡж–ҮгҖҒжӢүдёҒж–Үпјү家зҷ»й—ЁжұӮж•ҷгҖӮд»–иҝҳеӨҡж¬ЎеёҰеӯҰз”ҹеҺ»еҚ—жҳҢи·ҜдёҠжө·з§‘еӯҰдјҡе ӮпјҢеҸӮеҠ дёҠжө·е“ІеӯҰеӯҰдјҡжңүе…іиҘҝж–№е“ІеӯҰзҡ„жҙ»еҠЁгҖӮз”ұдәҺе…ЁеўһеҳҸжӣҫжӢ…д»»иҝҮеӨҚж—ҰеӨ§еӯҰеӣҫд№ҰйҰҶйҰҶй•ҝпјҢеҜ№еӣҫд№Ұиө„ж–ҷеҫҲзҶҹпјҢд»–еёёеёёдёәеӯҰз”ҹеҮҶеӨҮеҘҪеӯҰд№ зҡ„еӣҫд№ҰпјҢжңүзҡ„жҳҜд»–д»Һеӣҫд№ҰйҰҶеҖҹзҡ„пјҢжңүзҡ„жҳҜд»–иҮӘе·ұ收и—Ҹзҡ„пјҢиҝҷд»ӨеӯҰз”ҹ们ж·ұеҸ—ж„ҹеҠЁгҖӮпјҲе§ҡд»ӢеҺҡпјҢгҖҠд»ҺеӯҰжІ»еӯҰжІҗеёҲжҒ©гҖӢпјү
еңЁе…ЁеўһеҳҸзңӢжқҘпјҢдё“дёҡиӢұиҜӯиғҪеҠӣд№ҹжҳҜеӯҰеҘҪиҘҝж–№е“ІеӯҰзҡ„еҝ…еӨҮжҠҖиғҪгҖӮе§ҡд»ӢеҺҡеӣһеҝҶиҜҙпјҡвҖңи®°еҫ—第дёҖж¬ЎеҺ»е…Ҳз”ҹ家йҮҢжұӮж•ҷпјҢд»–жӢҝеҮәдёҖжң¬иӢұж–Үд№ҰжҢҮе®ҡе…¶дёӯжңүе…іеҸӨеёҢи…Ҡе“ІеӯҰзҡ„ж®өиҗҪиҰҒжҲ‘们з«ӢеҚіз¬”иҜ‘еҮәжқҘпјҢд»–еҪ“еңәе®Ўж”№иҜ‘ж–ҮгҖӮд»–е…іжіЁжҲ‘们дёҠз ”з©¶з”ҹе…¬е…ұиӢұиҜӯиҜҫпјҢжңҹжң«еҸЈиҜ•ж—¶иҝҷдҪҚеҺҹеӨ–ж–Үзі»дё»д»»з«ҹд№ҹзӘҒ然дёҙеңәеҗ¬иҖғпјҢеӨ–ж–Үзі»зҡ„дё»иҖғиҖҒеёҲе’ҢжҲ‘们дёӨеҗҚеӯҰз”ҹйғҪз”ҡдёәж„ҹеҠЁеҸҲжңүзӮ№зҙ§еј пјҢе№ёеҘҪеҫ—й«ҳеҲҶжІЎиҖғз ёгҖӮд»–дәІиҮӘеҹ№и®ӯжҲ‘们зҡ„дё“дёҡиӢұиҜӯпјҢж–№ејҸе°ұжҳҜжҢҮе®ҡиӢұж–ҮеҺҹи‘—дёӯжҹҗйғЁеҲҶи®©жҲ‘们еҪ“еңәеҸЈиҜ‘пјҢд»–з»ҷдәҲж ЎжӯЈпјҢдёҖ并и®ӯз»ғдәҶйҳ…иҜ»зҗҶи§ЈдёҺеҸЈиҜ‘иғҪеҠӣгҖӮжҲ‘еҪ“жң¬з§‘з”ҹж—¶еӯҰдҝ„иҜӯпјҢд»…йқ зңӢиӢұиҜӯиҜ»зү©з»ҙзі»дёӯеӯҰиӢұиҜӯиҖҒеә•еӯҗпјҢдё“дёҡиӢұиҜӯиғҪеҠӣжҳҜеңЁе…Ёе…Ҳз”ҹжҢҮеҜјдёӢеҹ№е…»зҡ„пјҢиҝҷеҜ№жҲ‘еҗҺжқҘжІ»еӯҰе’ҢеҸӮдёҺеҗ„з§ҚеӣҪйҷ…еӯҰжңҜдәӨеҫҖйғҪз”ҡжңүзӣҠеӨ„гҖӮвҖқ
еңЁжІ»еӯҰжҖҒеәҰдёҠпјҢе…ЁеўһеҳҸиҰҒжұӮеӯҰз”ҹеҝ…йЎ»дёҘи°ЁгҖҒиёҸе®һпјҢеҲҮеҝҢжҖҘеҠҹиҝ‘еҲ©гҖҒжҖҘдәҺжұӮжҲҗпјҢиҖҢд»–жң¬дәәдҫҝжҳҜжңҖеҘҪзҡ„жҰңж ·гҖӮжҚ®еӯҰз”ҹ们еӣһеҝҶпјҢвҖңд»–и®ІиҜҫжҖ»жңүеҮҶеӨҮе……еҲҶзҡ„и®ІзЁҝпјҢеҗ¬д»–зҡ„иҜҫе°ұжҳҜи®°дёҖзҜҮе®Ңж•ҙзҡ„ж–Үз« гҖӮд»–еҶҷи®әж–ҮжӣҙжҳҜзІҫзӣҠжұӮзІҫпјҢеұӮеұӮеү–жһҗгҖҒйҖ»иҫ‘жҖ§ејәгҖӮд»–е’ҢеӨ«дәәеҗҲиҜ‘зӢ„жӣҙж–Ҝзҡ„е°ҸиҜҙгҖҠиү°йҡҫж—¶дё–гҖӢпјҢеҫҖеҫҖдёәиҺ·дёҖжңҖдҪідёӯиҜ‘иҜҚиҖҢдәүи®әдёҚдј‘гҖӮвҖқе“ӘжҖ•зҝ»иҜ‘зҡ„д№ҰеҮәзүҲеҗҺпјҢд»–иҝҳиҰҒеҸҚеӨҚд»”з»Ҷж ЎзңӢ并дҝ®ж”№гҖӮвҖңж–Үйқ©вҖқеҗҺжңҹпјҢд»–иў«е®үжҺ’еҲ° вҖңиҮӘ然科еӯҰе“ІеӯҰзҝ»иҜ‘з»„вҖқпјҢе’Ңзү©зҗҶзі»зҺӢзҰҸеұұж•ҷжҺҲзҝ»иҜ‘дәҶеҘҪеҮ жң¬й«ҳйҡҫеәҰзҡ„еҗҚи‘—пјҢеҰӮеә·еҫ·зҡ„гҖҠиҮӘ然йҖҡеҸІе’ҢеӨ©дҪ“зҗҶи®әгҖӢгҖҒжў…жЈ®зҡ„гҖҠ科еӯҰеҸІгҖӢзӯүгҖӮ70е№ҙд»Јжң«пјҢдёҖж¬Ўе’ҢеӯҰз”ҹи°Ҳиө·гҖҠ科еӯҰеҸІгҖӢпјҢд»–иҜҙеҚідҫҝе·Із»ҸеүҚеүҚеҗҺеҗҺзңӢдәҶ20еӨҡйҒҚпјҢд№ҰеҮәзүҲеҗҺд№ҹиҝҳжҳҜдёҚеӨӘж»Ўж„ҸгҖӮжӯЈеҰӮй»„йўӮжқ°жүҖиҜҙпјҢвҖңе…Ёе…Ҳз”ҹж»ЎиӮҡеӯҗзҡ„еӯҰй—®пјҢеҸҜжҳҜд»–дёҚеҠЁеЈ°иүІпјҢдёҚж„ҝж„ҸжөҒйңІгҖӮд»–и®ЁеҺҢеҚ–еј„еӯҰй—®пјҢзӮ«иҖҖиҮӘеӨёпјҢд№ҹеҸҚеҜ№иҜ»д№ҰжұӮеҝ«иҖҢдёҚжұӮз”ҡи§ЈпјҢжӣҙеҸҚеҜ№дёҚжҮӮиЈ…жҮӮгҖӮиҝҷжҳҜ他们йӮЈдёҖиҫҲи®ёеӨҡеӯҰиҖ…е…ұеҗҢзҡ„зү№зӮ№пјҢдёҚиҝҮеңЁе…Ёе…Ҳз”ҹиә«дёҠиЎЁзҺ°еҫ—жӣҙеҠ зӘҒеҮәе’Ңе…ёеһӢгҖӮвҖқ пјҲй»„йўӮжқ°пјҢгҖҠзҷҫе№ҙеӨҚж—Ұе“ІеӯҰеӣӯең°зҡ„еӣӯдёҒгҖӢпјү
вҖңж–Үйқ©вҖқдёӯпјҢеӯҰз”ҹ们еҺҹе®ҡзҡ„жҜ•дёҡи®әж–ҮйҖүйўҳдёҚеҫ—е·ІвҖңиҪ¬еҗ‘вҖқпјҢе…ЁеўһеҳҸзҡ„з ”з©¶з”ҹж•ҷиӮІиў«еҪ“жҲҗвҖңдҝ®жӯЈдё»д№үвҖқж•ҷиӮІи·Ҝзәҝзҡ„е…ёеһӢгҖӮвҖңж–Үйқ©вҖқз»“жқҹеҗҺпјҢе…ЁеўһеҳҸзҡ„иә«дҪ“жҜҸеҶөж„ҲдёӢпјҢеҠ д№ӢеӨ«дәәеңЁвҖңж–Үйқ©вҖқдёӯзҰ»дё–зҡ„еҝғзҗҶжү“еҮ»пјҢиҝҳжңӘе°Ҷд»–ж·ұеҺҡзҡ„еӯҰиҜҶеҸ‘жҢҘеҮәжқҘпјҢиҝҳжңӘжқҘеҫ—еҸҠжҢҮеҜјж–°иҝӣзҡ„еҚҡеЈ«з ”з©¶з”ҹпјҢе…ЁеўһеҳҸдҫҝдәҺ1984е№ҙдёҺдё–й•ҝиҫһгҖӮ
然иҖҢпјҢйӮЈж®өиҝҪйҡҸиҖҒеёҲеӯҰд№ зҡ„дёҚй•ҝзҡ„е…үйҳҙпјҢиҝҳжҳҜеңЁй»„йўӮжқ°е’Ңе§ҡд»ӢеҺҡиә«дёҠз•ҷдёӢдәҶз»Ҳз”ҹзҡ„зғҷеҚ°гҖӮжӯЈжҳҜиө·жӯҘдәҺиҖҒеёҲзҡ„еҗҜиҝӘпјҢе§ҡд»ӢеҺҡеҗҺжқҘеӣһеҪ’еҸӨеёҢи…Ҡе“ІеӯҰпјҢе°Ҷе…¶дҪңдёәиҮӘе·ұжҜ•з”ҹзҡ„йҮҚзӮ№з ”究方еҗ‘гҖӮеңЁ2005е№ҙеҮәзүҲзҡ„гҖҠиҘҝж–№е“ІеӯҰеҸІпјҡеҸӨд»ЈеёҢи…ҠдёҺзҪ—马哲еӯҰгҖӢзҡ„еҗҺи®°дёӯпјҢд»–еҠЁжғ…ең°еҶҷйҒ“пјҡвҖңе№ҙиҝҲиҠұз”ІпјҢз»ҲдәҺе®ҢжҲҗжӯӨд№ҰеҶҷдҪңж—¶пјҢеҝғдёӯдёҚзҰҒж¶Ңиө·зј…жҖҖеҜјеёҲе…ЁеўһеҳҸж•ҷжҺҲзҡ„ж„ҹжҒ©д№Ӣжғ…вҖҰвҖҰе…ҲеёҲд»ҷйҖқе·ІйҖҫ20е№ҙпјҢжӯӨд№ҰиҷҪйқһзЎ•жһңпјҢд№ҹжҳҜзҢ®з»ҷд»–зҡ„дёҖз“ЈеҝғйҰҷгҖӮвҖқиҖҢеҜ№дәҺеӨҚж—ҰиҘҝж–№е“ІеӯҰеӯҰ科иҝҷеқ—еӣӯең°пјҢе…ЁеўһеҳҸеҪ“е№ҙж’ӯдёӢ并иҫӣеӢӨжөҮзҒҢзҡ„з§ҚеӯҗпјҢд№ҹж—©е·Ій•ҝжҲҗдёҖжЈөеҸӮеӨ©еӨ§ж ‘пјҢеҰӮд»ҠпјҢиҝҷйҮҢе·Із„¶ж №ж·ұеҸ¶иҢӮгҖҒзЎ•жһңзҙҜзҙҜ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ҺҶеҸІж–ҮеҢ–专家жҪңеҝғ40е№ҙзј–ж’°еҚғе№ҙеҸӨзҒөжё з ”з©¶жүӢзЁҝеҸ‘еёғ
- еҝ«иөҸйҪҗзҷҪзҹід№Ұжі•
- еұұдёңйҮҚзү№еӨ§з§‘жҠҖж”»е…іиҜҫйўҳз ”з©¶
- д»Һеә·еҫ·еҲ°й»‘ж је°”:зҪ—дјҜзү№В·еёғе…°йЎҝзҡ„иҜӯз”ЁеӯҰиҜӯиЁҖе“ІеӯҰ
- иҝ‘д»ЈиҜёеӯҗеӯҰз ”з©¶зҡ„д№үзҗҶиҪ¬еҗ‘
- гҖҗж–ҮеҢ–и®Іе ӮгҖ‘ејҖи®Іе•ҰпјҒдј з»ҹдҝ®иә«е“ІеӯҰзҡ„еҪ“д»Јд»·еҖј
- дёәйҳІжі„еҜҶжҲ‘еҶӣйҖҡи®ҜиҜҙж–№иЁҖпјҢеӣҪеӨ–专家зӘғеҗ¬з ”究30еӨ©пјҡи®Ізҡ„е°ұдёҚжҳҜдёӯж–Ү
- жҺўеҜ»дҝ—ж–ҮеӯҰз ”з©¶зҡ„ж—¶д»Јд»·еҖј
- жӣҫеӣҪи—©дёҖз”ҹдҝЎеҘүзҡ„е…«еӨ§еӨ„дё–е“ІеӯҰ
- еӣҪеҶ…йўҶе…ҲпјҒжҙӣйҳіе»әжҲҗеҸӨд»ЈеЈҒз”»дҝқжҠӨз ”з©¶еҹәе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