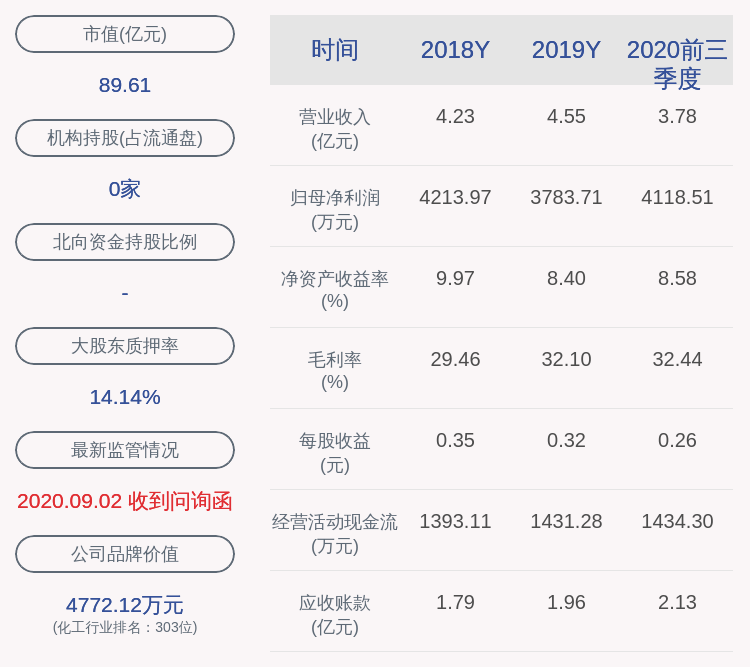一本杂志,三位先生( 四 )
李陀先生首先是个小说家 , 写过《愿你听到这首歌》《自由落体》等 , 前者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 后者是“文革”后最早带有实验性的短篇作品之一 。 后来他又涉足电影领域 , 然后专事文学批评 。 他是80年代重要的文学批评家 , 很多当时的文学事件和作家成名都与他有直接的关联 。 比如关于“现代派”的讨论 , 关于“伪现代派”的论争 , 关于“寻根文学”的缘起等等 。 他思维敏锐、敢于直言 , 不留情面 。 记得在一次文学讨论会上 , 一个很有名的评论家发言 , 他刚刚说了几句 , 就被李陀一句“你说得不对”给弄得下不来台 。 而对他喜欢的作家 , 他则绝不吝惜赞美之词 。 比如余华、马原、格非、刘索拉等等 。
1987年以后 , 文坛突然涌现出了一批“新”作家 , 余华、苏童、叶兆言、李锐、刘恒、格非、孙甘露、北村等 , 他们崭新的面目 , 陌生的叙事形式 , 让评论界手足无措 , 尤其是曾经在1985年以后十分活跃的一批青年批评家处于无语状态 。 李陀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 撰写了《昔日顽童今何在》的文章 , 发出了“批评落后于创作”的质问 , 并希望这些曾经的“顽童”——青年批评家们坐下来 , 认真地读这些新人的作品 。 当然 , 他对这些“新”作家的创作也并非一味称颂 , 而是褒贬分明 , 且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好恶 , 尤其是对两个风格相似的作家 , 评价竟然是天上地下 。 比如他喜欢刘索拉 , 不喜欢徐星 , 他喜欢马原 , 对洪峰却嗤之以鼻 。 他认为一个批评家必须有独立的批评精神 , 不应被金钱和人情左右 。 记得90年代 , 他刚从美国回国 , 我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很有钱的女作家的作品研讨会 , 他刚刚入座 , 就有会议方给在坐的评论家们分发红包 , 就是现在所说的专家费 。 当发到李陀时 , 他竟然将厚厚的信封甩到一边 , 起身离去 。
1986年至1989年初 , 他经常叫我去他在东大桥的寓所 , 给我介绍认识从各地来访的年轻作家 , 格非、孙甘露 , 还有后来的沈宏非都是那个时候结识的 。 记得他的客厅很小 , 书架、沙发、地上摞满了各种书籍 。 他讲话中会时不时抽出一本书推荐给我 。
90年代以后 , 李陀先生多数时间在美国生活 , 每年有一两个月时间回国讲学或游历 。 他每次回国 , 我们差不多都会见上一面 , 虽然他出国后关注的重点不在当代文学上 , 而专心于中国当代思想和文化研究 , 但依然关心国内当下文学的动态与发展 , 多次让我推荐年轻作家的作品 , 发现好的作者依然会兴奋 , 并且极力推荐给周围的人 。 每次我们见面他都会询问我的近况 , 尤其对我近几年的水墨创作给予了非常大的鼓励 。
2018年7月 , 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白马照夜明 , 青山无古今:兴安水墨艺术展” , 他和夫人、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化学者刘禾 , 还有艺术评论家鲍昆专程前来观展 。 他对我开始的水墨实践非常吃惊 , 给予了热情的赞誉 , 同时也从专业的角度给我提出了建议 , 他尤其对我写的旧体诗和题画诗给予了表扬 。 我知道 , 他对中国古典诗词有特殊的偏好 , 记得那会在《北京文学》的时候 , 他发言到关键的时候 , 经常会随口背出一句古诗词来 , 而且引用得恰到妙处 , 让在座的人很是惊讶 。 他们原以为一个热衷搞“现代派”的人 , 对传统或古典的东西一定是或者蔑视或者无知 。 我清楚地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带球过人 。 这是他借用足球比赛里的一句话 , 就是通过运球 , 甚至假动作 , 出其不意地突破对方的防线 。 李陀先生就是这样 , 他常常会给人意外之举 , 在你还没回过神来 , 就已经被他甩在身后 。
70岁以后的李陀先生比起80年代时的性情舒缓了许多 , 笑容里也是有了谦和 , 但他批评家的独立的品格和对事物的敏感一点也没有减弱 。 有一年 , 他回国 , 我试图组织一次当年与李陀先生常在一起的作家老友聚会 , 却被他谢绝了 。 他告诉我 , 三十年没见了 , 每个人的思想、经历都发生了变化 , 尤其是思想 , 甚至包括立场都产生分化和分歧 , 所以没有必要见面 , 有些人我也不想见 , 即使见了面 ,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 况且我很忙 , 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事情上 。 我理解他的想法 , 便放弃了这种聚会 。
推荐阅读
- 嘟嘟聊游戏|网友:能退多好,萌新玩家远离,王者:玩一局就丢仓库的三位英雄
- 乒乓杂志|水谷隼不敌宇田幸矢 丹羽孝希婚后首胜,明治大学乒乓球部梦幻赛
- 大学|这5所大学申请“改名”,将升级为一本院校,明年分数线会上涨
- 嘟嘟聊游戏|王者:玩一局就丢仓库的三位英雄,网友:能退多好,萌新玩家远离
- 公司|注意!英搏尔:三位股东拟减持合计不超过约216万股
- 姜桂|注意!英搏尔:三位股东拟减持合计不超过约216万股
- THEONE壹号杂志|壹号THEONE | 刘芸:驻颜精灵的秘密武器
- 公司|注意!创业慧康:三位股东拟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约2385万股
- 羽毛球杂志|握拍转换和步法都要做到位,羽毛球技术专家把脉:接发球时
- 千王里|中国历史上没有败绩的武将你知道几个?其中这三位实在是太可惜了






![[延迟退休年龄]延迟退休出新动态,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现在知](/renwen/images/defaultpic.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