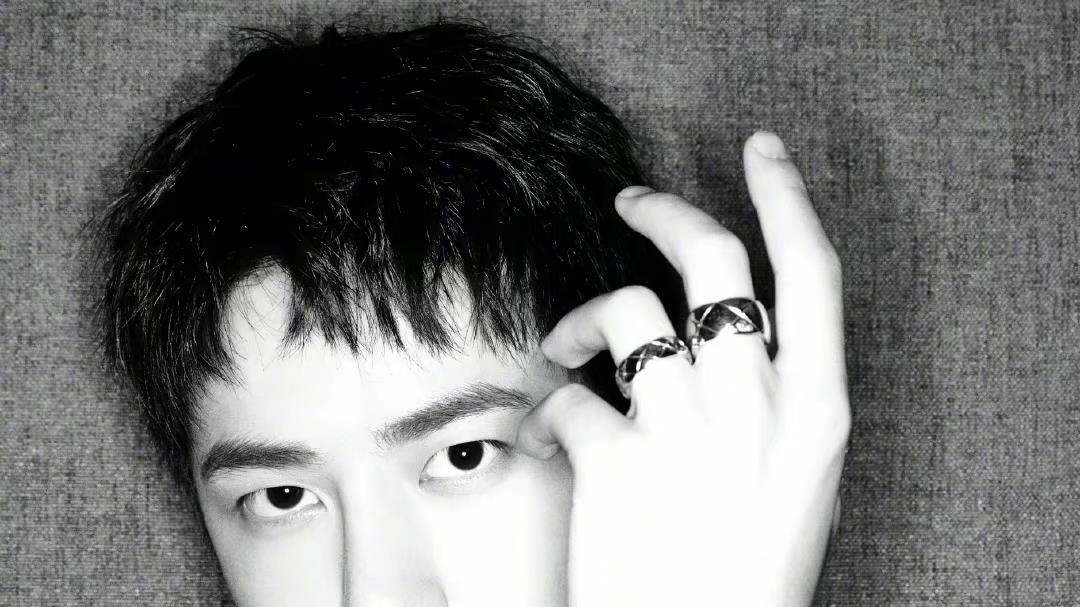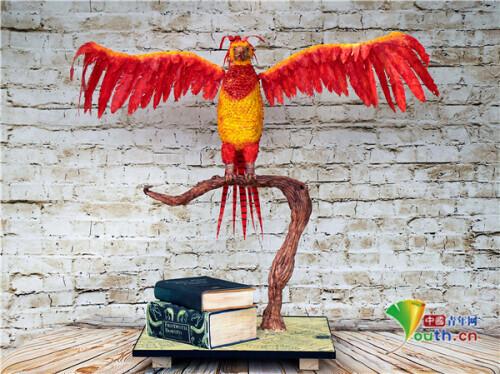ж–°гҖҠиҠұжңЁе…°гҖӢзҡ„еҸҢйҮҚе°ҙе°¬
ж–°гҖҠиҠұжңЁе…°гҖӢзҡ„еҸҢйҮҚе°ҙе°¬пјҡеӯқйҒ“дёҺеҘіжқғ пјҢ дј з»ҹдёҺзҺ°д»Јзҡ„еӨұиҙҘе’Ңи§ЈзҺӢдәҰиҜҡ В· жқҘжәҗпјҡжө·иһәзӨҫеҢәжңЁе…°ж•…дәӢжңҖдё»иҰҒзҡ„еҶ…еңЁеј еҠӣйғҪеңЁдәҺ пјҢ иҜ•еӣҫи®©вҖңеӯқвҖқиҝҷдёӘе®—жі•дјҰзҗҶи§ӮеҝөдёҺдёҖдёӘйқһдј з»ҹеҘіжҖ§зҡ„иҮӘжҲ‘е®һзҺ°зӣёдә’е’Ңи§Ј гҖӮеңЁдёӯеӣҪ家喻жҲ·жҷ“зҡ„иҠұжңЁе…°жӣҝзҲ¶д»ҺеҶӣзҡ„ж•…дәӢ пјҢ еҲҡеҲҡиҝҺжқҘдәҶеҘ№з»§1998е№ҙзҡ„гҖҠиҠұжңЁе…°гҖӢеҠЁз”»зүҮд№ӢеҗҺ пјҢ еңЁжөҒиЎҢж–ҮеҢ–дёӯзҡ„еҸҲдёҖжҳҘ гҖӮ з”ұеҲҳдәҰиҸІдё»жј”зҡ„иҝӘеЈ«е°јзңҹдәәзүҲеӨ§з”өеҪұгҖҠиҠұжңЁе…°гҖӢдәҺиҝ‘жңҹдёҠжҳ пјҢ ж— и®әжҳҜжӯӨеүҚжҢҒз»ӯзҡ„е®Јдј ж”»еҠҝ пјҢ иҝҳжҳҜеӣ ж–°еҶ з–«жғ…иҖҢ被延иҜҜж•°жңҲзҡ„еҸ‘еёғж—¶й—ҙ пјҢ йғҪеҗҠи¶ідәҶи§Ӯдј—зҡ„иғғеҸЈ гҖӮиҝӘеЈ«е°ји§Ҷи§’дёӢзҡ„вҖңеӯқйҒ“вҖқ пјҢ еӨҡе…ғж–ҮеҢ–дё»д№үзҡ„еӣ°еўғжІЎжңүд»Җд№ҲеңәжҷҜжҜ”зҰҸе»әеңҹжҘјжӣҙйҖӮеҗҲдёҖдёӘд»ҘйҒ“еҫ·гҖҒе°Өе…¶жҳҜ家еәӯйҒ“еҫ·дҪңдёәдё»йўҳзҡ„з”өеҪұдәҶ гҖӮ жҲ–и®ёжӯЈеӣ жӯӨ пјҢ иҝӘеЈ«е°јеҲ¶зүҮж–№дёҚжғңзүәзүІжҺүжң¬е·ІзЁҖи–„зҡ„еҺҶеҸІж„ҹ пјҢ е°ҶеҸ‘з”ҹеңЁеҢ—йӯҸж—¶жңҹзҡ„ж•…дәӢжҗ¬еҲ°зҰҸе»әжӢҚж‘„ гҖӮ еҺҶеҸІдёҠ пјҢ еқҡеӣәзҡ„зҺҜеҪўеңҹжҘјиў«жөҒеҫҷеҚ—иҝҒзҡ„客家дәәз”ЁдҪңжҠөеҫЎеӨ–йғЁж•Ңж„Ҹзҡ„е Ўеһ’ пјҢ зӣёдә’иҝһз»“зҡ„ж°Ҹж—ҸжүҺж №е…¶дёӯ пјҢ еҠ ејәеӣўз»“ гҖӮ еӣ жӯӨ пјҢ еңҹжҘјзҡ„зҺҜеўғжҳҫеҫ—дёҺдё–йҡ”з»қ пјҢ з”Ёд№ӢеүҚеҗҢж ·еңЁзҰҸе»әеңҹжҘјеҸ–жҷҜзҡ„гҖҠеӨ§йұјжө·жЈ гҖӢеҜјжј”зҡ„иҜқиҜҙжўҒз’Үзҡ„иҜқиҜҙпјҡеңҹжҘјжңүдёҖз§Қзү№ж®Ҡзҡ„зҘһз§ҳж„ҹ пјҢ еғҸжҳҜдёҖдёӘдё–еӨ–жЎғжәҗ гҖӮ 然иҖҢдёҺдё–йҡ”з»қзҡ„дё–еӨ–жЎғжәҗеңЁеёҰжқҘзҫҺзҡ„еҗҢж—¶д№ҹеёҰжқҘдёҖз§Қе°Ғй—ӯж„ҹ гҖӮ еңҶеҪўеәӯйҷўжһ„жҲҗдәҶдёҖдёӘвҖңеңҲеӯҗвҖқ пјҢ иҝҷж—ўжҳҜеӯ—йқўж„Ҹд№үдёҠзҡ„д№ҹжҳҜиұЎеҫҒж„Ҹд№үдёҠзҡ„ гҖӮ иҝҷдёӘеңҲеӯҗе…ұеҗҢе®ҲеҚ«зқҖеҗҢдёҖеҘ—д»·еҖјдҪ“зі» пјҢ иҖҢиҝҷдёӘд»·еҖјдҪ“зі»йҮҢжңҖйҮҚиҰҒзҡ„ пјҢ жҳҜд»Ҙ家ж—Ҹдёәдёӯеҝғзҡ„е®—жі•е’Ңзӯүзә§з§©еәҸ гҖӮ дёҺжӯӨеҗҢж—¶ пјҢ еңҹжҘјзҡ„еңҶеҪўеәӯйҷўе®һйҷ…дёҠжҳҜдёҖдёӘжІЎжңүдёӯеҝғзӣ‘жҺ§еЎ”зҡ„вҖңе…ЁжҷҜж•һи§ҶвҖқ з»“жһ„ гҖӮ иҝҷдёӘз»“жһ„е°ҶйҷўдёӯжүҖжңүдәәзҡ„дёҖдёҫдёҖеҠЁеңҲе®ҡеңЁдёҖдёӘеӣәе®ҡзҡ„иҢғеӣҙеҶ… пјҢ 并且жҡҙйңІз»ҷжҘјдёҠзҡ„жүҖжңүдәәйҡҸж—¶е®Ўи§Ҷ гҖӮ еңЁиҝҷз§ҚзҺҜеўғдёӯ пјҢ йҡҗеҪўзҡ„зӣ‘жҺ§ж— еӨ„дёҚеңЁ пјҢ йҷўеҶ…зҡ„дәәж—¶еҲ»еҸ—еҲ°йҒ“еҫ·зҡ„иҜ„еҲӨ гҖӮ2020зүҲгҖҠиҠұжңЁе…°гҖӢжңҖзӘҒеҮәзҡ„дё»йўҳжӯЈжҳҜеӯқзҡ„йҒ“еҫ· гҖӮ еҜјжј”йҖүжӢ©еӯқиҝҷдёӘеӯ— пјҢ еӨ§жҰӮжҳҜеҮәдәҺжҹҗз§ҚеҜ№дёңж–№ж–ҮеҢ–зҡ„е°ҠйҮҚ пјҢ жҜ•з«ҹд»Һиҙ№еӯқйҖҡд»ҘжқҘзҡ„дәәзұ»еӯҰ家 пјҢ жңҖз»ҸеёёжҢӮеңЁеҳҙиҫ№зҡ„дёҖдёӘз»“и®әе°ұжҳҜпјҡвҖңеӯқвҖқзҡ„дҝЎжқЎиҙҜз©ҝгҖҒз”ҡиҮіжҳҜж”Ҝж’‘дәҶдёӯеӣҪ儒家ж–ҮеҢ– гҖӮ еңЁиҝҷдёӘз»“и®әд№ӢдёӢ пјҢ зӘҒеҮәвҖңеӯқвҖқ пјҢ жҲ–и®ёе·Із»ҸжҲҗдёәдәҶдёҖз§ҚеҜ№дәҺиў«жҸҸз»ҳзҡ„дёңж–№ж–ҮеҢ–зҡ„вҖңж”ҝжІ»жӯЈзЎ®вҖқ гҖӮ иҝҷеҜјиҮҙдәҶдёҖдёӘиҜЎејӮзҡ„еұҖйқўпјҡиҝӘеЈ«е°јзҡ„ж–ҮеҢ–з”ҹдә§иҖ…еңЁйј“еҗ№дёӯеӣҪвҖңдј з»ҹвҖқйҒ“еҫ·и§Ӯеҝөж—¶ пјҢ з”ҡиҮіжҜ”еӨ§еӨҡж•°дёӯеӣҪзҡ„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йғҪиҰҒзӢӮзғӯ пјҢ иҝҷдҪҝеҫ—他们既иҰҒз«ҷеңЁйҒ“еҫ·и§Ҷи§’дёҠзҫҺеҢ–вҖңжӯЈз»ҹвҖқзҺӢжңқ пјҢ е°ҶеҢ—йӯҸжҸҸз»ҳдёәиў«йҮҺиӣ®дәәйӘҡжү°зҡ„зәҜжҙҒж— иҫңзҡ„еҸ—е®іиҖ…(дёҚд»…е°ҶеҢ—йӯҸдёҺжҹ”然й—ҙдә’жңүж”»е®Ҳзҡ„жҲҳдәүжҸҸз»ҳдёәе®Ңе…ЁйҒ“еҫ·еҢ–зҡ„йҳІеҫЎжҲҳдәү пјҢ д№ҹи®©еҢ—йӯҸжӢҘжңүдәҶ他们еҺҶеҸІдёҠ并дёҚжӣҫжӢҘжңүзҡ„иҘҝеҹҹең°еҢәз»ҹжІ»жқғ) пјҢ д№ҹе®Ңе…Ёж— и§ҶдәҶж—©жңҹеҢ—йӯҸзҺӢжңқзҡ„йІңеҚ‘иө·жәҗдёҺ儒家ж–ҮеҢ–д№Ӣй—ҙзҡ„еј еҠӣ(дёҖдәӣиҖғиҜҒи®Өдёәж•…дәӢдёӯзҡ„жңЁе…°еҫҲеҸҜиғҪжҳҜйІңеҚ‘дәә пјҢ е…¶жңҖзӣҙжҺҘзҡ„дҪ“зҺ°жҲ–и®ёеңЁдәҺгҖҠжңЁе…°иҜ—гҖӢзҡ„ж—©жңҹзүҲжң¬дёӯвҖңж„ҝеҖҹжҳҺй©јеҚғйҮҢи¶і пјҢ йҖҒе„ҝиҝҳж•…д№ЎвҖқзҡ„иҜ—еҸҘ) пјҢ жӣҙеҝҪи§ҶдәҶвҖңеӯқвҖқжҰӮеҝөжң¬иә«зҡ„й—®йўҳе’Ңзҹӣзӣҫ гҖӮиҜҡ然 пјҢ еӨҡе…ғж–ҮеҢ–дё»д№үжҲҗдёәдё»жөҒжҖқжҪ® пјҢ жҷ®дё–д»·еҖји§Ӯе·ІдёҚеҶҚжҳҜдёҖдёӘеҖјеҫ—иҝҪжұӮзҡ„зӣ®ж Ү гҖӮ 然иҖҢиў«еёӮеңәжҪ®жөҒеҝ«йҖҹзғ№йҘӘзҡ„жөҒиЎҢж–ҮеҢ–ж—ўжІЎжңүеҝғжҖқгҖҒд№ҹжІЎжңүж—¶й—ҙеҜ№еӨҡе…ғжҖ§иҝӣиЎҢж·ұеҲ»жҖқиҫЁ пјҢ дҪҝеҫ—жҜҸдёҖз§ҚвҖңдј з»ҹж–ҮеҢ–вҖқеҮ д№ҺйғҪе…·жңүдәҶд»ҝдҪӣеӨ©з„¶зҡ„жӯЈзЎ®жҖ§ гҖӮ 然иҖҢдәӢе®һжҳҜ пјҢ еңЁд»ҠеӨ© пјҢ еҗ„з§ҚвҖңдј з»ҹвҖқйғҪж—©е·Із»ҸиҝҮдәҶзҺ°д»Је·ҘдёҡзӨҫдјҡзҡ„еӨҡж¬ЎйҮҚж–°е»әжһ„е’ҢйҮҚж–°и§ЈиҜ» пјҢ иҰҒвҖңеӨҚеҺҹвҖқдёҖдёӘвҖңдј з»ҹж–ҮеҢ–вҖқ пјҢ е…¶е®һеҸӘиғҪдҫқйқ зҺ°д»Јж–ҮеҢ–зҡ„жғіиұЎ гҖӮ иҖҢиҝҷз§ҚжғіиұЎ пјҢ йҡҫе…ҚеёҰжңүд»ҺвҖңзҺ°д»ЈвҖқеҮқи§ҶвҖңеүҚзҺ°д»ЈвҖқзҡ„дёңж–№дё»д№үиүІеҪ© гҖӮ жӯЈжҳҜеӣ дёәиҝҷж ·зҡ„еӣ°еўғ пјҢ еңЁгҖҠй»‘иұ№гҖӢдёӯ пјҢ еҚідҪҝй»‘иұ№жІ»дёӢзҡ„з“ҰеқҺиҫҫзҺӢеӣҪ科жҠҖиҝңй«ҳдәҺзҫҺеӣҪ пјҢ д»Қ然被еҲ»з”»дёәдё“еҲ¶йғЁиҗҪзӨҫдјҡгҖҒйҖүзҺӢд»Қ然дҫқйқ жҜ”жӯҰ гҖӮ жҲ–и®ёеңЁжҹҗз§ҚеӨҡе…ғж–ҮеҢ–дё»д№үзҡ„зҗҶи§Јд№ӢдёӢ пјҢ иҝҷд№ҹжҳҜдёҖз§Қж–ҮеҢ–еӨҡе…ғ пјҢ еӣ дёәеҰӮжһңиөӢдәҲйқһжҙІзӨҫдјҡдёҖдёӘж°‘дё»иҖҢе№ізӯүзҡ„зӨҫдјҡз»“жһ„ пјҢ е°ұдё§еӨұдәҶйқһжҙІж–ҮеҢ–зҡ„еӨҡе…ғжҖ§ пјҢ иҖҢйқһжҙІвҖңжң¬жқҘвҖқзҡ„ж ·иІҢеҲҷзҗҶжүҖеҪ“然е°ұжҳҜдё“еҲ¶е’ҢеҺҹе§Ӣзҡ„ гҖӮ иҖҢеңЁгҖҠиҠұжңЁе…°гҖӢдёӯ пјҢ вҖңеӯқйҒ“вҖқеҲҷжҲҗдёәдәҶд»ЈиЎЁдёӯеӣҪвҖңжң¬жқҘвҖқж ·иІҢзҡ„ж–ҮеҢ–ж Үжң¬ гҖӮ еҰӮжһңиҜҙгҖҠй»‘иұ№гҖӢзҡ„жғ…иҠӮиҝҳ并жңӘжҡҙйңІеҮәдё“еҲ¶йғЁиҗҪзӨҫдјҡзҡ„еҶ…йғЁй—®йўҳ пјҢ з“ҰеқҺиҫҫжҲ–и®ёиҝҳеҸҜд»ҘдҪңдёәдёҖз§ҚиҘҝж–№зҺ°д»ЈжҖ§зҡ„жӣҝд»Је“Ғзҡ„иҜқ пјҢ йӮЈд№ҲеңЁжңЁе…°зҡ„ж•…дәӢйҮҢ пјҢ еҜ№вҖңеӯқвҖқиҝҷдёҖйҒ“еҫ·еҮҶеҲҷзҡ„ејәи°ғеҚҙеҮёжҳҫеҮәдәҶиҝҷдёӘж•…дәӢйҮҢж— жі•и°ғе’Ңзҡ„зҹӣзӣҫ гҖӮж— и®әеҜ№дәҺжңҖеҲқзҡ„еҢ—жңқж°‘жӯҢ пјҢ иҝҳжҳҜеҜ№дәҺ98зүҲеҠЁз”»зүҮ пјҢ жҲ–иҖ…жҳҜеҜ№дәҺиҝҷдёҖзүҲз”өеҪұиҖҢиЁҖ пјҢ жңЁе…°ж•…дәӢжңҖдё»иҰҒзҡ„еҶ…еңЁеј еҠӣйғҪеңЁдәҺ пјҢ иҜ•еӣҫи®©вҖңеӯқвҖқиҝҷдёӘе®—жі•дјҰзҗҶи§ӮеҝөдёҺдёҖдёӘйқһдј з»ҹеҘіжҖ§зҡ„иҮӘжҲ‘е®һзҺ°зӣёдә’е’Ңи§Ј гҖӮ иҖҢиҝҷдёҖзүҲз”өеҪұ пјҢ ж—ўеҮәдәҺеёҰжңүдёңж–№дё»д№үзҡ„ж–ҮеҢ–еӨҡе…ғиҝҪжұӮиҖҢиҰҒејәи°ғвҖңеӯқвҖқ пјҢ еҸҲеҮәдәҺиҝӘеЈ«е°јдёҖзӣҙд»ҘжқҘж ҮжҰңзҡ„еҘіжқғдё»д№үиҖҢиҰҒејәи°ғеҘіжҖ§зҡ„иҮӘжҲ‘е®һзҺ° пјҢ еӣ жӯӨи®©иҝҷдёӘзҹӣзӣҫиЎЁзҺ°еҫ—е°Өдёәжҳҫзңј гҖӮ еӣ дёәиҝҷдёӘзҹӣзӣҫзҡ„ж— жі•и°ғе’Ң пјҢ з”өеҪұжңҖз»ҲжҠҠжң¬еә”жӣҙдёәжҷ®дё–зҡ„еҘіжқғиҪ¬еҸҳдёәдәҶдёӘдәәеҘӢж–—еҸІ пјҢ дёҖдёӘеӣ иҮӘе·ұеӨ©иөӢејӮзҰҖиҖҢеҮәдәәеӨҙең°зҡ„еҠұеҝ—ж ·жң¬ гҖӮ дҪҶжңҖеҗҺ пјҢ иҝҷдёӘвҖңеӯқвҖқеӯ—еҪ“еӨҙзҡ„еҘіжҖ§еҘӢж–—еҸІеҚҙжіЁе®ҡеҸӘиғҪ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е°ҙе°¬зҡ„зҰ»зҫӨеҖј гҖӮдҪңдёәи§’иүІжү®жј”дҪ“зі»зҡ„вҖңеӯқвҖқд»Җд№ҲжҳҜвҖңеӯқвҖқ?еҪұзүҮдёҖејҖе§Ӣ пјҢ зҲ¶дәІи®Іиҝ°зҡ„еҜ№иұЎжҳҜвҖңзҘ–е…ҲвҖқ们 гҖӮ жҜ«ж— з–‘й—® пјҢ жң¬зүҮеҜјжј”д№ҹж„ҸиҜҶеҲ° пјҢ вҖңеӯқвҖқзҡ„жҰӮеҝөдёҚд»…д»…жҳҜзҲ¶еҘідәҢдәәд№Ӣй—ҙзҡ„е…ізі» пјҢ иҖҢжҳҜе…ізі»еҲ°ж•ҙдёӘ家ж—Ҹ гҖӮ вҖңеӯқвҖқж„Ҹе‘ізқҖеҜ№е®¶ж—ҸиҙҹиҙЈ пјҢ ж„Ҹе‘ізқҖеҜ№иҝҷдёӘзӨҫдјҡеңҲеӯҗжүҖе…ұеҗҢе®ҲеҚ«зҡ„家ж—Ҹ秩еәҸиҙҹиҙЈ гҖӮ д»ҺвҖңзҘ–е…ҲвҖқзҡ„и§’еәҰжқҘиҜҙ пјҢ вҖңеӯқвҖқж„Ҹе‘ізқҖе…үе®—иҖҖзҘ– гҖӮ иҖҢдёҚиғҪйҖҡиҝҮзҫҺеҘҪзҡ„е©ҡ姻жқҘе…үиҖҖй—ЁжҘЈ пјҢ д№ҹжҳҜеңҹжҘјйҮҢзҡ„е…¶д»–дәә家и®ӨдёәжңЁе…°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еҘҪеҘіе„ҝзҡ„еҺҹеӣ гҖӮ дҪҶеҚідҪҝжҳҜеңЁзӣҙ系家еұһеҶ…йғЁ пјҢ вҖңеӯқвҖқзҡ„жҰӮеҝөд№ҹз»қдёҚз®ҖеҚ•зҫҺеҘҪ гҖӮ е°Ҫз®Ўз”өеҪұеҠӘеҠӣеЎ‘йҖ дёҖдёӘеҘҪзҲ¶дәІзҡ„еҪўиұЎ пјҢ дҪҶж— и®әеҰӮдҪ•е°ҶвҖңеӯқвҖқзҡ„жҰӮеҝөдёӘдәәдё»д№үеҢ– пјҢ еҜјжј”д№ҹж— жі•и®©вҖңеӯқвҖқе®Ңе…ЁиҙҙеҗҲеҪ“д»Јж ёеҝғ家еәӯдёӯзҡ„вҖңзҲ¶зҲұвҖқжҰӮеҝө гҖӮвҖңеӯқвҖқз”ҡиҮід№ҹдёҚиғҪз®ҖеҚ•зӯүеҗҢдәҺзҲ¶жқғ гҖӮ иҙ№еӯқйҖҡе’ҢGary HamiltonзӯүеӨҡдҪҚдәәзұ»еӯҰ家们еңЁжҢҮеҮәвҖңеӯқвҖқзҡ„жҰӮеҝөж”Ҝж’‘дәҶе®—жі•дјҰзҗҶзҡ„еҗҢж—¶ пјҢ д№ҹжҢҮеҮәдәҶеҸҰеӨ–дёҖзӮ№пјҡвҖңеӯқвҖқзҡ„жң¬иҙЁе№¶дёҚжҳҜиҘҝж–№ж„Ҹд№үдёҠзҡ„зҲ¶жқғ пјҢ дёҚжҳҜзҲ¶дәІеҜ№е®¶ж—Ҹе…¶д»–жҲҗе‘ҳзҡ„жқғеҠӣ пјҢ иҖҢжҳҜдёҖз§Қзі»з»ҹзҡ„жқғеҠӣ пјҢ жӣҙзЎ®еҲҮең°иҜҙ пјҢ жҳҜдёҖз§Қи§’иүІжү®жј”зҡ„жқғеҠӣ гҖӮ еӯҗеҘіеҜ№зҲ¶дәІе°ҪеӯҗеҘівҖңеә”е°ҪвҖқзҡ„д№үеҠЎ пјҢ иҖҢзҲ¶дәІеҜ№еӯҗеҘіиЎҢдҪҝвҖңеә”иЎҢвҖқзҡ„жқғеҠӣ гҖӮ гҖҠеӯқз»ҸгҖӢзҡ„第дёҖз« иҜҙ пјҢ вҖңеӨ«еӯқ пјҢ е§ӢдәҺдәӢдәІ пјҢ дёӯдәҺдәӢеҗӣ пјҢ з»ҲдәҺз«Ӣиә«вҖқ гҖӮ дәҺжҳҜ пјҢ вҖңеӯқвҖқе°ұдёҚд»…д»…жҢҮеӯҗеҘідёҺзҲ¶жҜҚзҡ„е…ізі» пјҢ иҖҢжҳҜж„Ҹе‘ізқҖжӣҙе№ҝд№үгҖҒж¶өзӣ–ж•ҙдёӘзӨҫдјҡзҡ„жІ»зҗҶдҪ“зі» гҖӮ гҖҠеӯқз»ҸгҖӢдёӯйҳҗйҮҠзҡ„зҗҶжғізӨҫдјҡ пјҢ жӯЈжҳҜеӨ©еӯҗгҖҒиҜёдҫҜгҖҒеЈ«дәәгҖҒеә¶ж°‘еҗ„е°Ҫе…¶иҒҢзҡ„зӨҫдјҡ пјҢ иҖҢиҝҷдәӣи§’иүІеҲҶе·Ҙ пјҢ йғҪд»ҘвҖңеӯқвҖқзҡ„еҗҚд№үиҝӣиЎҢ гҖӮ жӯЈжҳҜеӣ дёәиҝҷз§Қи§’иүІжү®жј”ејҸзҡ„е…ізі» пјҢ вҖңеӯқвҖқжүҚиғҪжҲҗдёә宗法秩еәҸзҡ„ж”Ҝжҹұ пјҢ жүҚиғҪжҲҗдёәдёҚд»…жҳҜ家еәӯгҖҒ并且жҳҜеӣҪ家秩еәҸзҡ„зІҳеҗҲеүӮ пјҢ жүҚиғҪе°ҶзҲ¶дәІдёҺеҗӣзҺӢдёҖеҗҢзәіе…ҘвҖңеӯқвҖқзҡ„дҪ“зі»д№Ӣдёӯ пјҢ д№ҹжүҚдјҡжңүвҖңеҗӣеҗӣгҖҒиҮЈиҮЈгҖҒзҲ¶зҲ¶гҖҒеӯҗеӯҗвҖқзҡ„规и®ӯ гҖӮжҚўиЁҖд№Ӣ пјҢ вҖңеӯқвҖқзҡ„жң¬иҙЁ пјҢ жҳҜдҪ“зі»дёӯзҡ„жҜҸдёӘдәәеҗ„е°ұе…¶дҪҚ гҖӮ жӯЈеҰӮз”өеҪұдёӯжңЁе…°зҡ„зҲ¶дәІеҜ№еҘ№иҜҙзҡ„пјҡдҪ иҰҒи®Өжё…дҪ зҡ„дҪҚзҪ® гҖӮ 既然вҖңеӯқвҖқжҳҜе®—жі•дјҰзҗҶзҡ„ж ёеҝғ пјҢ йӮЈд№ҲдёҚйҡҫзҗҶи§Ј пјҢ еңЁе®—жі•дјҰзҗҶдёӯ пјҢ вҖңеҰҮйҒ“вҖқе…¶е®һжҳҜвҖңеӯқйҒ“вҖқзҡ„дёҖдёӘз»„жҲҗйғЁеҲҶ гҖӮ жңЁе…°зҡ„вҖңдёҚе®ҲеҰҮйҒ“вҖқ пјҢ е…¶е®һеңЁдёҖе®ҡзЁӢеәҰдёҠ пјҢ е·Із»ҸжҳҜдёҚе®ҲеӯқйҒ“дәҶ гҖӮ еҪұзүҮдёӯ既然еҸҚеӨҚеҮәзҺ°жңЁе…°вҖңдёә家ж—ҸеёҰжқҘдәҶиҖ»иҫұвҖқзҡ„иҜҙжі• пјҢ еҘ№зҗҶжүҖеҪ“然ең°д№ҹдёәжү®жј”зқҖж—Ҹй•ҝи§’иүІзҡ„зҲ¶дәІеёҰжқҘдәҶзҺ°иЎҢзҡ„иҖ»иҫұ гҖӮи§’иүІеҲҶжҳҺзҡ„вҖңеӯқвҖқ秩еәҸдёӯ пјҢ еҰӮдҪ•иғҪвҖңеӢҮж•ўеҒҡиҮӘе·ұвҖқпјҹиҝӘеЈ«е°јзҡ„з”өеҪұеҲҷиҜ•еӣҫи°ғе’ҢвҖңеӯқвҖқжҰӮеҝөдёӯзҡ„и§’иүІжү®жј”жҲҗеҲҶдёҺжңЁе…°иә«дёҠиў«еҜ„жүҳзҡ„дёӘдәәдё»д№үе’ҢеҘіжқғдё»д№үд№Ӣй—ҙзҡ„еј еҠӣ гҖӮ еӣ дёәиҰҒејәи°ғвҖңеӯқвҖқзҡ„йҒ“еҫ· пјҢ жүҖд»Ҙз”өеҪұеҪ“然дёҚиғҪзӘҒз ҙвҖңеӯқвҖқзҡ„жЎҶжһ¶ гҖӮ дәҺжҳҜ пјҢ жң¬зүҮйҮҮеҸ–зҡ„жҠҳдёӯд№Ӣжі• пјҢ е°ұжҳҜеңЁиҝҷдёӘдёҘж јзҡ„дҪ“зі»дёӯиөӢдәҲжңЁе…°дёҖдёӘдёҚеҗҢеҜ»еёёеҚҙвҖңе‘ҪдёӯжіЁе®ҡвҖқзҡ„и§’иүІ гҖӮ иЎЁйқўдёҠзңӢ пјҢ жңЁе…°е®һзҺ°дәҶиҮӘжҲ‘ пјҢ дҪҶе®һйҷ…дёҠ пјҢ з”өеҪұеҸӘжҳҜи®©еҘ№еңЁи§’иүІжү®жј”зҡ„дҪ“зі»д№Ӣдёӯиҝӣе…ҘдәҶеҸҰдёҖдёӘи§’иүІиҖҢе·І гҖӮз”өеҪұдёҖејҖеӨҙе°ұиЎЁзҺ°еҮәдәҶдёҖдёӘдёҺеҢ—жңқж°‘жӯҢе’Ң98зүҲеҠЁз”»зүҮзҡ„жҳҫи‘—дёҚеҗҢпјҡжңЁе…°е№¶дёҚ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жҷ®йҖҡзҡ„еҘіеӯ©еӯҗ пјҢ еҘ№д»Һе°Ҹе°ұиЎЁзҺ°еҮәдәҶдёҚеҮЎзҡ„вҖңж°”вҖқ(иҷҪ然з”өеҪұд»ҺжңӘи§ЈйҮҠжё…жҘҡиҝҷдёӘзҘһз§ҳиҖҢе…·жңүдёңж–№дё»д№үиүІеҪ©зҡ„вҖңж°”вҖқеҲ°еә•жҳҜд»Җд№Ҳ) пјҢ 并且еҜ№иҲһжһӘеј„жЈ’иЎЁзҺ°еҮәе…ҙи¶Ј гҖӮ еҰӮжһңиҜҙжӯӨеүҚжҲ‘们зҶҹжӮүзҡ„жңЁе…°жҳҜиў«дёҘеі»зҡ„зҺ°е®һйҖјдёҠжҲҳеңә пјҢ иҝҷдёҖзүҲйҮҢзҡ„жңЁе…°дёҚеҰӮиҜҙжҳҜж—©е°ұжңҹзӣјзқҖдёҖдёӘйҮҠж”ҫиҮӘжҲ‘д»·еҖјзҡ„жңәдјҡ гҖӮ еҘ№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жҷ®йҖҡзҡ„еҘіжҖ§ пјҢ иҖҢжҳҜдёҖдёӘе…·жңүдёҚеҗҢеҮЎе“Қзҡ„вҖңж°”вҖқзҡ„еҘіжҖ§ гҖӮ иҖҢеңЁж•ҙдёӘж•…дәӢдёӯ пјҢ еҶіе®ҡеҘ№е‘Ҫиҝҗзҡ„ пјҢ жӣҙз»қдёҚжҳҜеҘ№зҡ„еҘіжҖ§иә«д»Ҫ пјҢ иҖҢжҳҜеҘ№еӨ©иөӢејӮзҰҖзҡ„вҖңж°”вҖқ гҖӮжңЁе…°еңЁж•…дәӢдёӯ пјҢ дёҺе…¶иҜҙеҘ№жҳҜдёҖдёӘжҲҳж–—зҡ„еҘіжҖ§ пјҢ дёҚеҰӮиҜҙеҘ№е…·жңүеҸҢйҮҚиә«д»Ҫпјҡж—ўжҳҜдёҖдёӘвҖңж°”вҖқеәҰи¶…еҮЎзҡ„жҲҳеЈ« пјҢ еҸҲжҳҜдёҖдёӘеҘіжҖ§ гҖӮ еңЁж“Қз»ғеңәдёҠ пјҢ еҘ№иЎЁзҺ°еҮәзҡ„йғҪжҳҜжҲҳеЈ«зҡ„иә«д»Ҫ пјҢ иҖҢдёҚжҳҜеҘіжҖ§зҡ„иә«д»Ҫ;еҸӘжңүеңЁе·©дҝҗжү®жј”зҡ„жҹ”然еӣҪеёҲзҡ„жҢҮзӮ№дёӢ пјҢ еҘ№зҡ„еҘіжҖ§иә«д»Ҫдјјд№ҺеҝҪ然и§үйҶ’дәҶ гҖӮ дәҺжҳҜ пјҢ зӣёжҜ”98зүҲеҠЁз”»зүҮ(еҪ“然д№ҹеҢ…жӢ¬еҢ—жңқж°‘жӯҢ) пјҢ иҝҷйҮҢеҮәзҺ°дәҶеҸҲдёҖеӨ„жғ…иҠӮзҡ„ж”№еҠЁпјҡжңЁе…°е№¶дёҚжҳҜиў«еҸ‘зҺ°дәҶеҘіжҖ§иә«д»Ҫ пјҢ иҖҢжҳҜдё»еҠЁеңЁзҺҜеўғ并жңӘйҖјиҝ«еҘ№зҡ„жғ…еҶөдёӢжү”жҺүдәҶзҲ¶дәІзҡ„зӣ”з”І пјҢ жҒўеӨҚдәҶиҮӘе·ұзҡ„еҘіжҖ§иә«д»Ҫ гҖӮ еҘ№вҖңеҮәжҹңвҖқдәҶ гҖӮиҝҷйҮҢж¶үеҸҠеҲ°дёҖдёӘйҮҚиҰҒзҡ„й—®йўҳпјҡеҰӮжһңиҜҙжңЁе…°еҸӘжңүеңЁжүҝи®ӨиҮӘе·ұиә«д»Ҫзҡ„еүҚжҸҗдёӢжүҚиғҪеӨҹеҸ‘жҢҘиҮӘе·ұзҡ„вҖңж°”вҖқ(дёҚи®әиҝҷдёӘеүҚжҸҗжҳҜеҰӮдҪ•жҲҗз«Ӣзҡ„) пјҢ еҘ№дёҚиЎЁзҺ°еҮәиҮӘе·ұзҡ„еҘіжҖ§иә«д»ҪжҳҜеҗҰзңҹзҡ„е°ұж„Ҹе‘ізқҖеҘ№еҗҰи®ӨиҮӘе·ұзҡ„еҘіжҖ§иә«д»Ҫ?жҚўиЁҖд№Ӣ пјҢ е…ЁзҜҮдёҖзӣҙеңЁејәи°ғвҖңзңҹвҖқ пјҢ дҪҶиҝҷдёӘвҖңзңҹвҖқ пјҢ иҝҷдёӘвҖңbe true to yourselfвҖқ пјҢ еҲ°еә•жҳҜеҜ№иҮӘе·ұзҡ„еҶ…еҝғиҙҹиҙЈиҝҳжҳҜеҜ№зӨҫдјҡе®Јз§°иҮӘе·ұ?еңЁд»ҠеӨ©зҡ„иә«д»Ҫж”ҝжІ»дёӯ пјҢ иҝҷдәҢиҖ…дјјд№Һз»Ҹеёёж··дёәдёҖи°Ҳ гҖӮ 然иҖҢеҜ№LGBTQзҡ„еҝғзҗҶиҫ…еҜје·ҘдҪңзЁҚжңүзҶҹжӮүзҡ„дәәйғҪдјҡзҹҘйҒ“ пјҢ жІЎжңүд»»дҪ•дәәеә”еҪ“е°ҶвҖңеҮәжҹңвҖқи§ҶдҪңдёҖз§Қд№үеҠЎ пјҢ дёҚеҮәжҹңд№ҹз»қдёҚж„Ҹе‘ізқҖжӢ’з»қиҮӘе·ұзҡ„иә«д»Ҫ гҖӮ иҖҢдёҺд№ӢзӣёеҸҚ пјҢ жң¬зүҮеҚҙе°ҶеҜ№иҮӘе·ұжҖ§еҲ«иә«д»Ҫзҡ„и®ӨеҗҢе®Ңе…ЁзӯүеҗҢдәҺеңЁзӨҫдјҡйқўеүҚзҡ„жҖ§еҲ«иЎЁжј” пјҢ дёҚиў«еҗҢеғҡзңӢи§Ғзҡ„жҖ§еҲ«е°ұдёҚжҳҜжҖ§еҲ« гҖӮ然иҖҢжңҖйҮҚиҰҒзҡ„й—®йўҳиҝңйқһеҜ№иҮӘе·ұжҖ§еҲ«и®ӨеҗҢзҡ„ж–№ејҸ гҖӮ з”өеҪұзҡ„иҝӣеұ•дјјд№ҺеңЁе‘ҠиҜүи§Ӯдј— пјҢ д»»дҪ•ж—¶еҖҷ пјҢ еҸӘиҰҒвҖңеӢҮж•ўеҒҡиҮӘе·ұвҖқ пјҢ й—®йўҳйғҪдјҡиҮӘеҠЁиҝҺеҲғиҖҢи§Ј гҖӮ йҳҝеӨҡиҜәжӣҫжү№еҲӨвҖңBe yourselfвҖқиҝҷеҸҘеңЁзҺ°д»Јж–ҮеҢ–е·ҘдёҡдёӯжңҖеёёеҮәзҺ°зҡ„еҸЈеҸ·жҳҜдёҖз§Қе»үд»·зҡ„жӢңзү©ж•ҷйә»йҶүеүӮ пјҢ иҖҢиҝҷдёҖзӮ№еңЁиҝӘеЈ«е°јзҡ„дҪңе“ҒдёӯиЎЁзҺ°е…¶е®һжңҖдёәжҳҺзЎ® гҖӮ еңЁиҝӘеЈ«е°јзҡ„жүҖжңүз”өеҪұдёӯ пјҢ дё»и§’дјјд№ҺйғҪдёҚйңҖиҰҒеҒҡд»»дҪ•йҖүжӢ© пјҢ д№ҹдёҚйңҖиҰҒеҒҡеҮәд»»дҪ•зүәзүІ гҖӮ еҸӘиҰҒвҖңеҒҡиҮӘе·ұвҖқ пјҢ дҪ жүҖеӨұеҺ»зҡ„дёҖеҲҮе°ұжіЁе®ҡе°ҶиҰҒеӣһжқҘ гҖӮ вҖңеҒҡиҮӘе·ұвҖқдәҺжҳҜжҲҗдёәдәҶеҜ№жүҖжңүй—®йўҳзҡ„е”ҜдёҖж ҮеҮҶзӯ”жЎҲ пјҢ дјјд№ҺиҖҒеӨ©зҲ·е°ұжҳҜеҜ№еӢҮж•ўеҒҡиҮӘе·ұзҡ„еҘіеӯ©жғ…жңүзӢ¬й’ҹ гҖӮиҖҢжңЁе…°еңЁзЁҖйҮҢзіҠж¶Ӯең°еӢҮж•ўеҒҡдәҶиҮӘе·ұд№ӢеҗҺ(еҘ№иў«ејҖйҷӨеҮәйҳҹд№ӢеҗҺзҡ„иҢ«з„¶еҸҚеә”жҳҫ然表зӨәеҘ№жІЎжңүд»”з»ҶиҖғиҷ‘иҝҮеҮәжҹңзҡ„еҗҺжһң) пјҢ еҫҲеҝ«е°ұеҫ—еҲ°еҗҢеғҡзҡ„ж”ҜжҢҒиҖҢеӣһеҲ°йҳҹдјҚд№Ӣдёӯ;дёҖеҰӮгҖҠеҶ°йӣӘеҘҮзјҳгҖӢдёӯ пјҢ ElsaиҷҪ然йҖүжӢ©ж”ҫејғдәҶ家еәӯ пјҢ дҪҶеҘ№зҡ„家еәӯеҫҲеҝ«е°ұеҸҲе®Ңж»Ўең°еӣһеҲ°дәҶеҘ№иә«иҫ№ гҖӮ еңЁжңЁе…°иҝҷйҮҢ пјҢ еҘ№еӣ жҖ§еҲ«иә«д»ҪиҖҢйҒӯеҸ—ж”ҫйҖҗзҡ„ж—¶й—ҙз”ҡиҮіжҜ”ElsaиҝҳиҰҒзҹӯеҫҲеӨҡ пјҢ еҘ№зҡ„жҖ§еҲ«и®ӨеҗҢе…¶е®һжһҒе°‘жҲҗдёәеҘ№дәӢдёҡзҡ„йҳ»зўҚ гҖӮ иҝҷз§ҚеҲ»з”»з”ҡиҮіжҜ”еҪ“дёӢжөҒиЎҢзҡ„йғҪеёӮвҖңеӨ§еҘідё»вҖқз”өи§Ҷеү§иҝҳиҰҒжө…и–„ пјҢ еҗҺиҖ…йҖҡиҝҮи®©еҘідё»е№іиЎЎвҖңе·ҘдҪңдёҺ家еәӯвҖқд№Ӣй—ҙзҡ„дёӨйҡҫеҶІзӘҒ пјҢ еңЁж»Ўи¶іеҘіжҖ§и§Ӯдј—вҖңиөӢжқғвҖқйңҖжұӮзҡ„еҗҢж—¶ пјҢ д№ҹи®©иҝҷдёӘй—®йўҳзңӢдёҠеҺ»зҗҶжүҖеҪ“然 пјҢ е®һйҷ…дёҠеҚҙејәеҢ–дәҶеҲ»жқҝзҡ„жҖ§еҲ«еҲҶе·Ҙ(з”·дё»еӨ–гҖҒеҘідё»еҶ… пјҢ еҘіжҖ§иҝҪжұӮдәӢдёҡе°ұиҰҒйқўдёҙйҳ»зўҚ) пјҢ еҗҲзҗҶеҢ–дәҶеҘіжҖ§зҡ„вҖңдё“еұһвҖқйә»зғҰ гҖӮ иҖҢиҝӘеЈ«е°јз”ҡиҮіеңҶж»‘ең°ж·ЎеҢ–дәҶеӣ°жү°з»қеӨ§еӨҡж•°е·ҘдҪңеҘіжҖ§зҡ„жҖ§еҲ«еҲҶе·Ҙе’Ңе·ҘдҪңжӯ§и§Ҷй—®йўҳ пјҢ зҶ¬еҮәдәҶдёҖй”…е»үд»·зҡ„дёӘдәәдё»д№үз«ҘиҜқйёЎжұӨ гҖӮеҘіжҖ§зҡ„и§үйҶ’ пјҢ иҝҳжҳҜеҘіжҖ§зҡ„еҺӢжҠ‘пјҹ然иҖҢй—®йўҳзңҹзҡ„е°ұиҝҷж ·и§ЈеҶідәҶеҗ—?еңЁдј—е°ҶеЈ«еҶіе®ҡж”ҜжҢҒжңЁе…°еӣһеҲ°йҳҹдјҚзҡ„еңәжҷҜдёӯ пјҢ жҢҮжҢҘе®ҳдёәжңЁе…°дёӢзҡ„жңҖз»ҲеҲӨиҜҚжҳҜпјҡеҘ№иҷҪ然дёҚвҖңзңҹвҖқ(жҢҮеҘ№жІЎжңүеҜ№дј—дәәеұ•жј”иҮӘе·ұзҡ„жҖ§еҲ«) пјҢ дҪҶеҘ№зҡ„вҖңеҝ вҖқе’ҢвҖңеӢҮвҖқжңүзӣ®е…ұзқ№ гҖӮ иҝҷж„Ҹе‘ізқҖ пјҢ еҘ№дҪңдёәеҘіжҖ§зҡ„иә«д»ҪдёҚжҳҜиў«жҺҘеҸ—дәҶ пјҢ иҖҢжҳҜиў«жҗҒзҪ®дәҶ гҖӮ 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е·ЁеӨ§зҡ„и®ҪеҲәпјҡеңЁеҘ№еҶіе®ҡвҖңеӢҮж•ўеҒҡиҮӘе·ұвҖқд№ӢеҗҺ пјҢ еҘ№еҗ‘зӨҫдјҡеұ•зӨәдәҶиҮӘе·ұзҡ„жҖ§еҲ« пјҢ дҪҶеҘ№зҡ„жҖ§еҲ«иҮӘжҲ‘еҚҙе®һйҷ…дёҠйҡҸеҘ№зҡ„зӣ”з”ІдёҖиө·дёўжҺүдәҶ гҖӮ зҺ°еңЁзҡ„еҘ№еҸӘдҝқз•ҷдәҶдёҖдёӘиә«д»Ҫ пјҢ е°ұжҳҜеҘ№дҪңдёәжҲҳеЈ«зҡ„иә«д»Ҫ гҖӮ еҘ№еҸӘжҳҜ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дјҳз§Җзҡ„жҲҳеЈ«жүҚиў«жҺҘзәіеҸӮдёҺдәҶжҲҳж–— гҖӮ еңЁжҲҳж–—дёӯ пјҢ еҘ№е№¶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еҘіжҖ§ гҖӮиҝҷжҳҜдёҖдёӘжҖ§еҲ«и§’иүІй—®йўҳзҡ„е…ёеһӢзј©еҪұ гҖӮ з”өеҪұдёӯиҝҪжұӮвҖңжҖ§еҲ«е№ізӯүвҖқзҡ„йҖ»иҫ‘е…¶е®һдёҺдёӯеӣҪ50-70е№ҙд»Јжңҹй—ҙжҸҗеҖЎвҖңз”·еҘіе№ізӯүвҖқзҡ„йҖ»иҫ‘зұ»дјј гҖӮ жӯЈеҰӮжҲҙй”ҰеҚҺгҖҒжқЁзҫҺжғ (Mayfair Yang)зӯүдәәжҢҮеҮәзҡ„ пјҢ ж— и®әжҳҜвҖңеҘідәәиғҪйЎ¶еҚҠиҫ№еӨ©вҖқ пјҢ иҝҳжҳҜжӣҙйңІйӘЁзҡ„вҖңдёҚзҲұзәўиЈ…зҲұжӯҰиЈ…вҖқ пјҢ з”·еҘіе№ізӯүзҡ„иғҢеҗҺ пјҢ дёҚжҳҜжҖ§еҲ«зҡ„еҸ–ж¶Ҳ пјҢ иҖҢжҳҜеҘіжҖ§иў«з”·жҖ§зҡ„еҗҢеҢ– пјҢ еҘіжҖ§иў«иөӢдәҲдәҶз”·жҖ§вҖңж°”иҙЁвҖқ пјҢ дёҖе®ҡзЁӢеәҰдёҠд№ҹиў«иөӢдәҲдәҶз”·жҖ§иә«д»Ҫ гҖӮ еҘіжҖ§д№ӢжүҖд»ҘиҺ·еҫ—дәҶдёҖе®ҡзЁӢеәҰдёҠзҡ„е№ізӯү пјҢ жҳҜеӣ дёә他们еңЁзӨҫдјҡзҡ„жҖ§еҲ«зҡ„зӯүзә§з§©еәҸдёӯжҢӨиҝӣдәҶеҺҹжқҘе…ЁйғЁиў«з”·жҖ§еҚ жҚ®зҡ„й«ҳзӯүзә§ пјҢ иҖҢдёҚжҳҜеӣ дёәжҖ§еҲ«зӯүзә§зҡ„ж¶ҲиһҚ гҖӮдҪҶеңЁиҠұжңЁе…°зҡ„ж•…дәӢйҮҢ пјҢ иҝһи®©еҘіжҖ§иҝӣе…Ҙз”·жҖ§зҡ„жҖ§еҲ«зӯүзә§д№ҹеҒҡдёҚеҲ° гҖӮ еӣ дёәж•ҙдёӘзӨҫдјҡзҡ„宗法秩еәҸд»Қ然йңҖиҰҒдёҖдёӘжЈ®дёҘзҡ„зӯүзә§жқҘз»ҙжҢҒ пјҢ йңҖиҰҒжҜҸдёӘдәәжү®жј”他们еҗ„иҮӘзҡ„и§’иүІ гҖӮ иғҪеӨҹжҢӨиҝӣз”·жҖ§зӯүзә§дёӯзҡ„ пјҢ д»…д»…жҳҜеӨ©з”ҹе°ұеёҰжңүејәеӨ§зҡ„вҖңж°”вҖқзҡ„жңЁе…°дёҖдёӘдәә гҖӮ иҖҢе°ұиҝһиҝҷдёҖдёӘдәәзҡ„иҚЈе…ү пјҢ иҝӘеЈ«е°јд№ҹиҰҒд»ҘвҖңеӯқвҖқзҡ„еҗҚд№үеүҘеӨә гҖӮ жңЁе…°жңҖз»Ҳе®ҝе‘ҪдёҖиҲ¬ең°еӣһеҲ°еңҹжҘј пјҢ 继з»ӯйқўеҜ№е®—ж—Ҹ家法зҡ„еҮқи§Ҷ гҖӮ иҖҢеҘ№зҡ„еҰ№еҰ№д»Қ然жҳҜдёҖдёӘеҗ¬д»ҺзҲ¶жҜҚд№Ӣе‘ҪеӘ’еҰҒд№ӢиЁҖзҡ„е°Ҹ姑еЁҳ пјҢ йғ‘дҪ©дҪ©жү®жј”зҡ„еӘ’е©Ҷд№ҹд»Қ然жҳҜдёҖдёӘз”»зқҖиҠұи„ёзҡ„з”·жқғеё®еҮ¶ гҖӮ е®һйҷ…дёҠ пјҢ еңЁз”өеҪұдёӯ пјҢ йҷӨдәҶжңЁе…°д№ӢеӨ– пјҢ е…¶д»–зҡ„еҘіжҖ§и§’иүІйғҪеҲ»з”»еҫ—з®Җжҳ“иҖҢеҚ•и–„ пјҢ з”ҡиҮідё‘йҷӢ гҖӮжҲ‘们еңЁж•…дәӢзҡ„жңҖеҗҺзңӢеҲ°зҡ„ пјҢ 并дёҚжҳҜдёҖдёӘеҘіжҖ§иҺ·еҫ—и®ӨеҸҜзҡ„дё–з•Ң пјҢ еҸӘжҳҜдёҖдёӘвҖңжӯҰеҫ·е……жІӣвҖқзҡ„иӢұйӣ„иҺ·еҫ—и®ӨеҸҜзҡ„дё–з•Ң гҖӮ иҖҢиҝҷдёӘи®ӨеҸҜ пјҢ иЎЁйқўдёҠжҳҜдҫқйқ еқҰзҷҪиҮӘе·ұзҡ„еҘіжҖ§иә«д»Ҫ пјҢ е®һйҷ…дёҠеҚҙжҳҜдҫқйқ жҠӣејғиҮӘе·ұзҡ„еҘіжҖ§иә«д»ҪгҖҒиў«з”·жҖ§иә«д»ҪжүҖеҗҢеҢ–жқҘе®һзҺ°зҡ„ гҖӮз»“иҜӯпјҡиў«з”·жқғеҪўеЎ‘зҡ„еҘіжқғ пјҢ иў«зҺ°д»ЈжҢҹжҢҒзҡ„вҖңдј з»ҹвҖқзҡҮеёқиөҗз»ҷжңЁе…°зҡ„еү‘дёҠеҲ»зқҖдёҖдёӘвҖңеӯқвҖқеӯ— пјҢ иҝҷжҳҜдёҖз§ҚиҺ«еӨ§зҡ„и®ҪеҲә гҖӮ еӣ дёәеӯқдёҚд»…д»…жҳҜдёҖз§Қеҫ·жҖ§ пјҢ иҖҢжҳҜдёҖз§ҚдҪ“зі» гҖӮ жңЁе…°зҡ„ж•…дәӢж— жі•зҰ»ејҖиҝҷдёӘдҪ“зі»иҖҢеӯҳеңЁ гҖӮ з”өеҪұејҖеӨҙ пјҢ жңЁе…°иҝҪиө¶дёҖеҸӘйёЎ пјҢ и·ғдёҠеңҹжҘјзҡ„еұӢйЎ¶ пјҢ иұЎеҫҒзқҖеҘ№и¶…и¶ҠиҝҷдёӘе°Ғй—ӯ秩еәҸзҡ„жёҙжңӣ;дҪҶжңҖз»Ҳ пјҢ еҘ№иҝҳжҳҜиҰҒеӣһеҲ°еңҹжҘјйҮҢжқҘ пјҢ 并且让вҖңеӯқвҖқ继з»ӯдјҙйҡҸиҮӘе·ұзҡ„дҪҷз”ҹ пјҢ 继з»ӯиҝӣиЎҢзқҖ宗法秩еәҸдёӯзҡ„и§’иүІжү®жј” гҖӮж— и®әжңЁе…°еңЁжңҖеҗҺжҳҜеҗҰжҺҘеҸ—дәҶд»»е‘ҪжҲҗдёәеҶӣе®ҳ пјҢ ж•…дәӢдёӯзҡ„зҹӣзӣҫйғҪеҝ…然жҢҒз»ӯж·ұеҲ»ең°еӯҳеңЁ гҖӮ еҚідҪҝеҘ№жҺҘеҸ—дәҶзҡҮеёқзҡ„д»»е‘Ҫ пјҢ еҘ№д№ҹеҸӘжҳҜд»ҺвҖңзҲ¶зҲ¶еӯҗеӯҗвҖқзҡ„и§’иүІжү®жј”иҪ¬з§»еҲ°дәҶвҖңеҗӣеҗӣиҮЈиҮЈвҖқзҡ„и§’иүІжү®жј”иҖҢе·І пјҢ иҖҢвҖңеӯқвҖқзҡ„дҪ“зі»еҚҙжҳҜдёҚеҸҳзҡ„ гҖӮ еҸҜд»ҘжғіеғҸ пјҢ дҪңдёәдёҖдёӘиў«еҫЎиөҗвҖңеӯқвҖқеү‘зҡ„дәә пјҢ жңЁе…°жңӘжқҘзҡ„з”ҹжҙ»е·Із»ҸдёҚеҸҜиғҪзҰ»ејҖ宗法秩еәҸ пјҢ иҖҢеҘ№д№ҹе°Ҷ继з»ӯйқўдёҙзқҖи§’иүІжү®жј”дёӯзҡ„жҖ§еҲ«йә»зғҰ пјҢ жҲ–жҳҜйҖҗжёҗд№ жғҜе’ҢжҺҘеҸ—е…ЁжҷҜж•һи§Ҷзҡ„еҘіеҫ·е®ЎеҲӨ пјҢ жҲ–жҳҜжӣҙеҪ»еә•ең°дёўејғиҮӘе·ұзҡ„жҖ§еҲ«гҖҒиў«з”·жҖ§зӨҫдјҡеҗҢеҢ– пјҢ еҚідҪҝжңүд»Җд№ҲвҖңдёӨе…Ёд№Ӣзӯ–вҖқ пјҢ д№ҹж— йқһжҳҜжҠҠиҖҒзҲ¶иҖҒжҜҚжҺҘеҺ»дә¬еҹҺ пјҢ ж—©жҷЁе…Ҙжңқжү®жј”дёҖдёӘе®ҳеғҡи§’иүІ пјҢ жҷҡдёҠеӣһ家иҶқеүҚе°ҪеӯқгҖҒз»ҷзҲёзҲёеҰҲеҰҲжҙ—и„ҡзҪўдәҶ гҖӮ е®һйҷ…дёҠ пјҢ гҖҠиҠұжңЁе…°гҖӢиҝҷйғЁз”өеҪұеҸӘжҳҜе°ҶзҺ°д»ЈйғҪеёӮдёӯеҲ»жқҝзҡ„жҖ§еҲ«еҲҶе·Ҙй—®йўҳжҠ•е°„еҲ°дёҖдёӘеҸӨд»Јж•…дәӢдёҠ пјҢ иҖҢеҹәдәҺжҖ§еҲ«зҡ„зӨҫдјҡеҲҶе·Ҙ пјҢ 并жңӘеңЁиҝҷйғЁз”өеҪұдёӯиҺ·еҫ—и¶…и¶Ҡ гҖӮеҸҜд»ҘиҜҙ пјҢ иҝҷйғЁз”өеҪұе…¶е®һжҢҮи®ӨеҮәдәҶеҪ“д»Јж–ҮеҢ–дә§дёҡжүҖйқўдёҙзҡ„дёӨдёӘж №жң¬жҖ§й—®йўҳ гҖӮ йҰ–е…Ҳ пјҢ жӯЈеҰӮжҲҙй”ҰеҚҺжҢҮеҮәзҡ„ пјҢ и®©еҘіжҖ§иә«д»Ҫиў«з”·жҖ§жүҖеҗҢеҢ–зҡ„вҖңз”·еҘіе№ізӯүвҖқ пјҢ е®һйҷ…дёҠжҠ№еҺ»дәҶдёҖз§Қз§ҜжһҒзҡ„еҘіжҖ§жҖ§еҲ«и®ӨеҗҢзҡ„еҸҜиғҪ гҖӮ йӮЈд№ҲжҲ‘们зҡ„ж–ҮеҢ–еҸҷдәӢ пјҢ жҳҜеҗҰиҝҳиғҪеӨҹе»әжһ„еҮәдёҖз§Қж—ўдёҚд»Ҙз”·жҖ§иә«д»ҪдёәеҸӮиҖғзі»гҖҒеҸҲдёҚд»Ҙз”·жҖ§еҮқи§ҶдёәеәҰйҮҸиЎЎзҡ„еҘіжҖ§еҪўиұЎ?иҖҢдёҺд№ӢејӮжӣІеҗҢе·Ҙзҡ„еҸҰдёҖдёӘй—®йўҳжҳҜ пјҢ иҝҪжұӮеӨҡе…ғдё»д№үзҡ„иҘҝж–№ж–ҮеҢ–дә§дёҡеңЁи®Іиҝ°йқһиҘҝж–№зҡ„ж•…дәӢж—¶ пјҢ еҫҖеҫҖй’»иҝӣвҖңдј з»ҹвҖқзҡ„зүӣи§’е°– пјҢ иҜ•еӣҫд»ҺеҗҺиҖ…дёҺиҘҝж–№жҺҘи§Ұд№ӢеүҚзҡ„йҒҘиҝңиҝҮеҺ»дёӯеҜ»жүҫвҖңеӨҡе…ғвҖқзҡ„з—•иҝ№ гҖӮ иҝҷе°ұеҜјиҮҙдәҶдёҖз§Қд»ҺвҖңзҺ°д»ЈвҖқеҮәеҸ‘еҜ№вҖңеүҚзҺ°д»ЈвҖқзҡ„еҮқи§Ҷ пјҢ д»ҺиҖҢ пјҢ е®һйҷ…дёҠд№ҹжқңз»қдәҶд»»дҪ•йқһдёңж–№дё»д№үзҡ„еӨҡе…ғдё»д№үзҡ„еҸҜиғҪжҖ§ гҖӮ еңЁиҝҷз§Қжғ…еҶөдёӢ пјҢ иҘҝж–№ж–ҮеҢ–е·ҘдёҡеҜ№вҖңдј з»ҹвҖқдёҺвҖңзҺ°д»ЈвҖқзҡ„е«ҒжҺҘ пјҢ е°ұеҰӮеҗҢеңЁгҖҠиҠұжңЁе…°гҖӢз”өеҪұдёӯдј еңЈж—Ёзҡ„еӨӘзӣ‘еҜ№еҗ¬ж—Ёзҡ„зҷҫ姓称呼вҖңе…¬ж°‘вҖқ(citizens)дёҖж ·е°ҙе°¬ гҖӮ еңЁиҝҷж ·зҡ„е°ҙе°¬дёӯ пјҢ ж–ҮеҢ–дә§дёҡиҝҳиғҪеҗҰйҒҝе…ҚжңЁе…°дёҺвҖңеӯқвҖқиҝҷж ·зҡ„еҶ…еңЁзҹӣзӣҫ пјҢ и®©еӨҡе…ғж–ҮеҢ–дёҺиөӢжқғеҸҷдәӢдә’дёҚеҶІзӘҒ?
жҺЁиҚҗйҳ…иҜ»
- дёҙж·ұжҲҝд»·е·Із ҙ4дёҮпјҢвҖң3еӯ—еӨҙвҖқзҡ„ж·ұеңідёңйғЁйҡҫжҺ©е°ҙе°¬пјҹ
- и…ҫи®Ҝз ё2дәҝе…ғе…Қиҙ№еҸ‘еҚҺдёәжүӢжңә з»“жһңе°ҙе°¬дәҶ
- йқ’е№ҙ|еӨҸеӨ©еҘіз”ҹдёҠе®ҢеҺ•жүҖеҲ°еә•жңүеӨҡе°ҙе°¬пјҹпјҹпјҹжҲ‘е°ұ笑笑дёҚиҜҙиҜқпҪһ
- дҪ и®©еҲ«дәәж„ҹеҲ°жңҖе°ҙе°¬зҡ„з»ҸеҺҶжҳҜд»Җд№Ҳ
- йқ’е№ҙ|еҘ¶еҘ¶йӘ‘иҪҰеёҰеӯҷеҘіеӣһ家пјҢд»ҘдёәеӨ§иҙ§иҪҰдјҡи®©зқҖеҘ№пјҢдёӢдёҖз§’еҚҙе°ҙе°¬дәҶ
- зҫҺеӣҪдәәжӢҚе®ҢиҠұжңЁе…°пјҢеҸҲжқҘжӢҚе«ҰеЁҘдәҶ
- жө·зӣҗзҪ‘|жө·зӣҗе№ҙиҪ»дәәзҰ»иҒҢйғҪдјҡжӢүй»‘жүҖжңүеүҚеҗҢдәӢеҗ—пјҹдёҮдёҖзў°еҲ°еӨҡе°ҙе°¬пјҒ
- еұұеҜЁAirPodsпјҢи·Ҝеӯҗ究з«ҹжңүеӨҡйҮҺпјҹ
- е·ҫеёјдёҚи®©йЎ»зңү и°ҒиҜҙеҘіеӯҗдёҚеҰӮз”·
- зәўзӮ№|жҹҗдә”жҳҹзә§й…’еә—жғҠзҺ°еҒ·жӢҚвҖңжҺўеӨҙвҖқпјҹеҮҢжҷЁ5зӮ№еҘ№дёҖдёӘдёҫеҠЁе°ҙе°¬дәҶвҖҰвҖ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