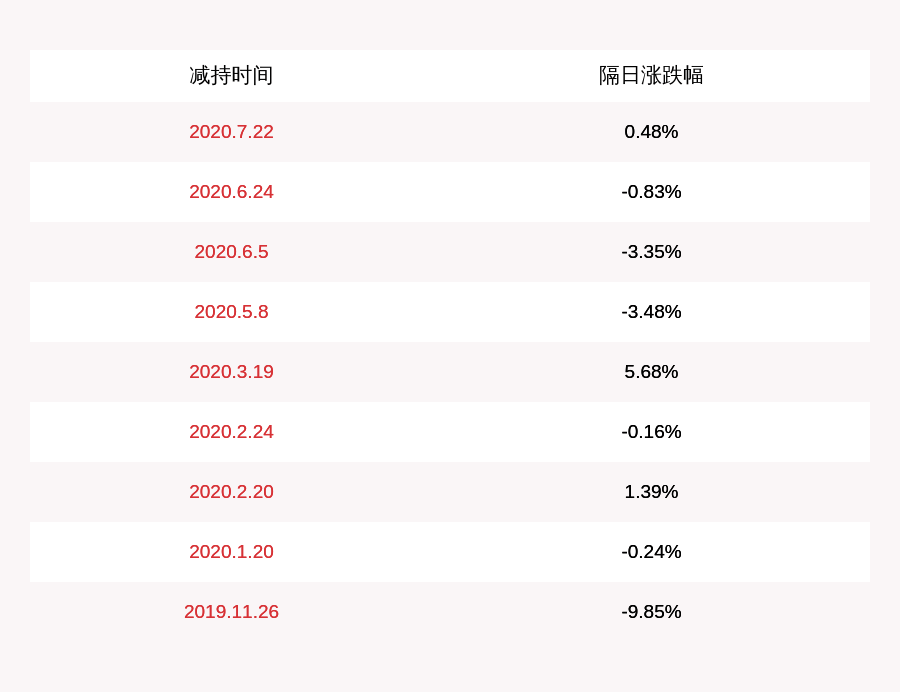иҝҷдәӣзҗҶе·Ҙз”ҹ笔дёӢзҡ„ж–Үеӯ— еӣҪ科еӨ§зҗҶе·Ҙз”ҹзҡ„ж–ҮеӯҰйҒҗжҖқ
дёӯеӣҪ科еӯҰйҷўеӨ§еӯҰзҡ„еӯҰеӯҗйҒҚеёғеӨ§жұҹеҚ—еҢ—гҖҒжһҒең°еҶ°е·қгҖҒзғӯеёҰйӣЁжһ— пјҢ и®ӯвҖңиӣҹйҫҷвҖқгҖҒзҪ®вҖңеҢ—ж–—вҖқгҖҒејҖвҖңеӨ©зңјвҖқгҖҒж–—вҖңж–°еҶ вҖқвҖҰвҖҰ科еӯҰжҲҳзәҝдёҠзҡ„他们еңЁеҘӢеҠӣж”»еқҡе…Ӣйҡҫ гҖӮ еҸҜжҳҜ пјҢ дҪ иғҪжғіиұЎеҫ—еҲ°еҗ— пјҢ иҝҷдәӣзҗҶе·Ҙз”ҹ笔дёӢзҡ„ж–Үеӯ— пјҢ еҸҲжҳҜжҖҺж ·дёҖз§ҚзҒөеҠЁгҖҒйІңжҙ»пјҹжҸЎдҪҸз”ҹжҙ»зҡ„з¬”еј е–Ҷ(24еІҒ)зү©зҗҶеҢ–еӯҰдё“дёҡеҚҡеЈ«з ”з©¶з”ҹеҹ№е…»еҚ•дҪҚпјҡдёӯеӣҪ科еӯҰйҷўеҢ–еӯҰз ”з©¶жүҖжҚ®жҲ‘иҖҒеҰҲиҜҙ пјҢ еҗғеҘ¶ж—¶еҖҷзҡ„жҲ‘е°ұе’ҢеҲ«зҡ„еӯ©еӯҗдёҚеҗҢ пјҢ еҲ«зҡ„еӯ©еӯҗжңүзҡ„зҲұе“ӯй—№ пјҢ жңүзҡ„еқҗдёҚдҪҸ пјҢ жңүзҡ„зҲұиәәеңЁе°ҸеәҠйҮҢзҝ»жқҘиҰҶеҺ» пјҢ жҲ‘е‘ўпјҹзҲ·зҲ·з»ҷжҲ‘еЎһдёҖдёӘ收йҹіжңә пјҢ жҲ‘е°ұиғҪе®үйқҷең°еҗ¬еҘҪд№… пјҢ иҝһзқЎи§үйғҪеҫҲе°‘зҝ»иә« гҖӮ жҲ‘дёҖзӣҙд»ҘдёәжҳҜиҖҒеҰҲеңЁеӨёжҲ‘вҖңеӨ©иөӢеӯҰд№ зҡ„ејӮзҰҖвҖқ пјҢ зӣҙеҲ°еҗҺжқҘ收жӢҫиЎЈжҹңж—¶зҝ»еҮәе°Ҹж—¶еҖҷзҡ„з…§зүҮпјҡвҖңеҰҲ пјҢ дҪ е‘ҠиҜүжҲ‘ пјҢ иғ–жҲҗиҝҷж ·зҡ„е©ҙе„ҝжҖҺд№ҲиҮӘе·ұзҝ»иә«пјҹпјҒвҖқй•ҝеӨ§дёҠеӯҰеҗҺ пјҢ вҖңеҗ¬д№ҰвҖқж…ўж…ўеҸҳжҲҗдәҶвҖңзңӢд№ҰвҖқ пјҢ д»ҺеӯҰд№ жҸЎз¬”гҖҒжӢјйҹігҖҒжҹҘеӯ—е…ёејҖе§Ӣ пјҢ д№Ұ пјҢ жҳҜдёҖжҚ§иө·е°ұж”ҫдёҚдёӢдәҶ гҖӮеӯҰдјҡзңӢд№Ұ пјҢ д»ҺдёҖжң¬зӣ—зүҲгҖҠз№ҒжҳҹВ·жҳҘж°ҙгҖӢејҖе§Ӣ гҖӮ еҲқдёӯжғід№°иҜҫеӨ–д№Ұж—¶д»ҺеҺҝеҹҺе°Ҹд№Ұеә—д№°еӣһдёҖжң¬гҖҠз№ҒжҳҹВ·жҳҘж°ҙгҖӢ пјҢ зӣ—зүҲд№Ұй”ҷиҜҜеӨҡ пјҢ дәҺжҳҜжңҖеӨ§зҡ„д№җи¶Је°ұжҳҜж”№д№Ұ гҖӮ ж”№й”ҷеҲ«еӯ—е’ҢжӢјйҹідёҚиҜҙ пјҢ иҝҳзҫҺж»Ӣж»Ӣең°з»ӯеҶҷйӮЈдәӣиў«й”ҷиҜҜжҺ’зүҲжҺҗеӨҙеҺ»е°ҫзҡ„вҖңж®Ӣз–ҫвҖқиҜ— пјҢ жҜҸжүҫеҲ°дёҖдёӘй”ҷиҜҜж—¶йғҪдјҡи§үеҫ—вҖңдҪ зңӢ пјҢ жҲ‘жҜ”дҪңиҖ…иҝҳиҒӘжҳҺ гҖӮ вҖқдјҙйҡҸзқҖе°Ҹе°Ҹзҡ„жІҫжІҫиҮӘе–ң пјҢ жҲ‘жңүдәҶдёҖжң¬зӢ¬дёҖж— дәҢзҡ„вҖңеҗҲи‘—вҖқ гҖӮеҗҺжқҘ пјҢ дёҖеј еҸҲдёҖеј иў«еЎ«ж»Ўзҡ„з©әзҷҪиҜ•еҚ·е’Ңз”іиҜ·иЎЁжӮ„жӮ„ж‘һжҲҗдәҶжҲ‘зҡ„й«ҳдёӯе’ҢеӨ§еӯҰ гҖӮ жңүйҷҗзҡ„з©әйҡҷж—¶й—ҙйҮҢ пјҢ иҜ»д№ҰеҚҙеҸҳжҲҗи·ҹйЈҺ пјҢ иҜҫжЎҢдёӢдј йҳ…зҡ„гҖҠиҜ»иҖ…гҖӢ пјҢ жҙ»и·ғеңЁжңӢеҸӢеңҲзҡ„йІҒиҝ… пјҢ иҝҳжңүеёёжҢӮзғӯжҗңзҡ„гҖҠйҫҷж—ҸгҖӢе’ҢгҖҠзӣ—墓笔记гҖӢ гҖӮ йҳ…иҜ»жң¬еә”жҳҜеҚҒеҲҶз§ҒеҜҶзҡ„дәӢ пјҢ жҲ‘еҚҙеғҸжЁЎд»ҝзҫӨдҪ“иЎҢдёәдёҖж ·еҸӘйЎҫзқҖиҝҪйҖҗи®Ёи®әиҜқйўҳе’ҢзҪ‘з»ңзғӯзӮ№зҡ„йЈҳ移 гҖӮ жӯӨж—¶ пјҢ еҸӘжңүеҪ“еҲқзҡ„жғіиҜ»гҖҒж•ўиҜ»иҝңиҝңдёҚеӨҹ пјҢ жІЎжңүиҮӘдё»жҢ‘йҖүе’Ңж„ҹеҸ—зҡ„йҳ…иҜ»еҸҳеҫ—еҢҶеҝҷж— жҜ”еҚҙжІЎжңүз»“жһң пјҢ е°ұеғҸеҪ“ж—¶иҝ·иҢ«зқҖеӣӣеӨ„еҶІж’һзҡ„йқ’жҳҘ гҖӮ еӣ дёәжҜҸдёҖж¬ЎйҖүжӢ©йғҪдёҚеҶҚжҢҮеҗ‘дёҖдёӘзЎ®е®ҡзҡ„зӯ”жЎҲ пјҢ еӯҰвҖңжҢ‘вҖқиҝҷ件дәӢ пјҢ жҲ‘е®һеңЁжҳҜиҠұиҙ№дәҶеӨӘй•ҝзҡ„ж—¶й—ҙ гҖӮ зӣҙеҲ°еҗҺжқҘжҢ‘еӯҰж ЎгҖҒжҢ‘дё“дёҡгҖҒжҢ‘иҜҫзЁӢгҖҒжҢ‘е·ҘдҪңвҖҰвҖҰеғҸеңЁжҢ‘дёҖж¬ЎжІЎжңүеҜјиҲӘзҡ„е…¬и·ҜеҶ’йҷ© пјҢ д№ҹеғҸжҢ‘дёҖжң¬жІЎжңүзӣ®еҪ•зҡ„з•ҷзҷҪе°Ҹдј гҖӮжҜ•дёҡеҗҺжҲ‘йҖүжӢ©з»ӯеҖҹеҗҚдёәеӯҰж Ўзҡ„д№Ұ пјҢ зҺ°еңЁзҡ„иҮӘе·ұдёҚеҶҚи·ҹйЈҺжү“еҚЎж— е…ізҪ‘иҜҫ пјҢ иҖҢжҳҜжүҫдәҶжҢҮеҜјиҖҒеёҲ пјҢ и®Өзңҹи®Ёи®әеҗҺжӢ·еӣһи®©UзӣҳеӯҳйҮҸжҳҫзӨәеҸҳзәўзҡ„ж•ҷжқҗе’Ңж–ҮзҢ® пјҢ жңҹеҫ…зҙҜз§Ҝзҡ„е®һйӘҢи®°еҪ•жңҖз»Ҳз”»еҮәйҮҚеҪ©дёҖ笔 гҖӮ еңЁе®һйӘҢе®ӨйҮҢд»°жңӣеңҹең° пјҢ и®©жҳҹз©әзҰ»еҫ—жӣҙиҝ‘ гҖӮ дёҖи·Ҝиө°жқҘ пјҢ жҲ‘们жҚўдәҶеӨӘеӨҡдёҚеҗҢзҡ„иҜҫжң¬ пјҢ зҺ°еңЁжҚ§иө·зҡ„иҝҷжң¬ пјҢ еҸ«з”ҹжҙ» гҖӮдёҠж¬ЎеҜ’еҒҮеӣһ家时еңЁзҲ·зҲ·йӮЈйҮҢзңӢеҲ°дёҖжң¬ж—§д№Ұ пјҢ зІ—зңӢеҮ йЎөе°ұеҸ‘зҺ°жҳҜзӣ—зүҲ пјҢ дәҺжҳҜжҲ‘иҜҙпјҡвҖңзҲ·зҲ· пјҢ иҝҷд№ҰйҮҢй”ҷеҲ«еӯ—дёҖж‘һ пјҢ жҲ‘з»ҷдҪ д№°жӯЈзүҲзҡ„еҗ§ гҖӮ вҖқзҲ·зҲ·еҚҙиҜҙпјҡвҖңдёҚз”Ё пјҢ иҝҷжҳҜжқ‘йҮҢ收еәҹе“Ғзҡ„дәәдёҚиҜҶеӯ— пјҢ еҸҲеҸҜжғңеҘҪеҘҪзҡ„д№ҰйҖҒеҺ»жү“зәёжөҶе°ұз»ҷжҲ‘дәҶ гҖӮ й”ҷеҲ«еӯ—жҲ‘йғҪз»ҷж”№иҝҮжқҘдәҶ пјҢ дёҚиҖҪиҜҜиҜ» гҖӮ вҖқжҲ‘еҶҚз»ҶзңӢ пјҢ жһң然еҘҪеӨҡең°ж–№йғҪз”»дёҠдәҶж Үи®° пјҢ з”Ёзҡ„йғҪжҳҜдҫ„еӯҗдҫ„еҘід»¬иҝҮеҺ»еҶҷдҪңдёҡж—¶иҗҪдёӢзҡ„笔 пјҢ еӯ—дёҚд»…иҠұиҠұз»ҝз»ҝзҡ„ пјҢ иҝҳеҫҲеӨ§ гҖӮиҝҷи®©еҪ“ж—¶е®һйӘҢдёҚйЎәжӯЈжө®иәҒзҡ„жҲ‘еҝҪ然жғіеҲ°еҪ“еҲқйӮЈжң¬гҖҠз№ҒжҳҹВ·жҳҘж°ҙгҖӢ пјҢ еҪ“ж—¶зҡ„иҮӘе·ұиғҪзЈЁд№Ұ пјҢ ж•ўж”№д№Ұ пјҢ зҹҘйҒ“д№ҰдјҡзҠҜй”ҷ пјҢ зҹҘйҒ“ж ҮеҮҶзӯ”жЎҲдёҚжҳҜе”ҜдёҖжӯЈи§Ј гҖӮ зҺ°еңЁзҡ„з”ҹжҙ»дёҚд№ҹжҳҜдёҖжң¬д»»з”ұиҮӘе·ұж¶ӮжҠ№еҶҷз”»зҡ„д№Ұеҗ—пјҹйӮЈдёәдҪ•дёҚеҶҚж¬Ўд»Һз”ҹжҙ»зҡ„гҖҠз№ҒжҳҹВ·жҳҘж°ҙгҖӢеҮәеҸ‘ пјҢ еӯҰзқҖиёҸе®һеқҗдёӢпјҹд№ҰдёҚеҒң пјҢ з”ҹжҙ»дёҚеҒң пјҢ йҳ…иҜ»дёҚеҒң пјҢ д№ҰеҶҷдёҚеҒң гҖӮ жҲ‘еқҗдёӢйҳ…иҜ» пјҢ жүҚиғҪи·‘еҫ—жӣҙеҝ« гҖӮ еҫҖеүҚзңӢж—¶ пјҢ д»ҝдҪӣеңЁзӯүзқҖеҗҚдёәж—¶й—ҙзҡ„дҪңиҖ…жҢүж—¶жӣҙж–° пјҢ еӣһеӨҙзңӢж—¶ пјҢ еҸҲеҸ‘зҺ°жҸЎзқҖ笔зҡ„еҲҶжҳҺеҸӘжңүиҮӘе·ұ пјҢ иҝҷеҗҚеҸ«з”ҹжҙ»зҡ„д№Ұе•Ҡ пјҢ жҲ‘们既жҳҜиҮӘе·ұзҡ„дҪңиҖ… пјҢ д№ҹжҳҜиҮӘе·ұзҡ„иҜ»иҖ… гҖӮжўҰиЎҢи®°жқҺеҶӣ(26еІҒ)зІҫеҜҶд»ӘеҷЁеҸҠжңәжў°дё“дёҡзЎ•еЈ«з ”з©¶з”ҹеҹ№е…»еҚ•дҪҚпјҡдёӯеӣҪ科еӯҰйҷўеҚ—дә¬еӨ©ж–Үе…үеӯҰжҠҖжңҜз ”з©¶жүҖеңЁиҗҪж—Ҙзҡ„дҪҷжҷ–йЈҳиҝңеӨ©йҷ…зҡ„ж—¶еҖҷ пјҢ жҲ‘еҸҢжүӢжҚ§зқҖдёҖжң¬иҜ—йӣҶ пјҢ еҶҚжіЎдёҠдёҖжқҜи…ҫзғӯзҡ„иҢүиҺүиҠұиҢ¶ пјҢ еңЁж—¶з©әзҡ„зјқйҡҷдёӯж•°зӮ№иҜ—жғ… гҖӮ зӣҙеҲ°вҖңеӨ•йҳіиҘҝдёӢ пјҢ ж–ӯиӮ дәәеңЁеӨ©ж¶ҜвҖқдёҺжҲ‘йҮҚйҖў пјҢ еҝғдёӯи—ҸеҢҝе·Ід№…зҡ„еҺҹе…ҪдҫҝдёҚеҶҚе®үеҲҶең°й…ЈзқЎ гҖӮ еҸҜиғҪжҳҜж„ҹеҸ—еҲ°дәҶдҪңдёәеӨ©ж¶Ҝжёёеӯҗзҡ„иӢҰй—· пјҢ е°ұд»ҝдҪӣжҲ‘дәҰеҰӮжёёеӯҗиҲ¬жҒӢ家иҖҢйғҒйғҒдёҚж¬ў гҖӮ дёҚиҜҘжғізҡ„иҮӘ然дёҚдјҡеҺ»жғі пјҢ иҜҘжғізҡ„д№ҹдјҡйҡҸзқҖзҳҰ马иёҸ蹄зҡ„и„ҡжӯҘеЈ°еҶІж•ЈеңЁжҪәжҪәзҡ„жөҒж°ҙдёӯ гҖӮ йҡҸеҗҺ пјҢ еҶҚд»Һд№Ұж©ұдёӯжҠҪеҮәдёҖжң¬гҖҠжўҰжёёд№ҰгҖӢ пјҢ зңӢзқҖдёҖдҪҚжқҘиҮӘеҸ°ж№ҫдёӯе№ҙеҘіжҖ§зҡ„жўҰ笔зҗҗдәӢ пјҢ еҚҙж»ЎиҪҪзқҖеҜ№з”ҹжҙ»зҡ„еҜ„жҖқ пјҢ дҪҝжҲ‘дёҚеҫ—дёҚжғҠеҸ№пјҡвҖңеҘ№иӮҜе®ҡжҳҜз»ҸеҺҶиҝҮеӨ§еҜӮеҜһзҡ„дәә гҖӮ вҖқдәҺжҳҜ пјҢ жҲ‘жӢҝиө·йқҷйқҷиәәеңЁд№ҰжЎҲдёҠзҡ„зӯҫеӯ—笔 пјҢ еңЁз¬”и®°жң¬дёҠеҶҷдёӢиҝҷж ·дёҖж®өиҜқпјҡвҖңжҹҗдёҖеӨ© пјҢ жҲ‘е®ҡдјҡдәІиҮӘеҺ»ж„ҹеҸ—дәәй—ҙ пјҢ ж„ҹеҸ—еӨ©ж¶Ҝ пјҢ ж„ҹеҸ—дёҖзј•жў…иҠұйҰҷжҳҜеҗҰиғҪдј йҖ’зқҖдёҚжңҪзҡ„иҜ—жғ… гҖӮ вҖқ然еҗҺ пјҢ дёҖеӨҙй’»иҝӣжё©жҡ–зҡ„иў«зӘқ пјҢ з”ЁдёҖеҸҢзҷҪйҮҢеёҰй»‘зҡ„зңјзқӣ пјҢ йҖҸиҝҮзӘ—дёҠзҡ„й»‘й“Ғж …ж Ҹ пјҢ еҮқи§ҶзқҖжё…жҷ°иҖҢжҳҺдә®зҡ„жҳҹз©әдёӢ пјҢ и®ёеӨҡдёӘдёҚдёәдәәзҹҘзҡ„з§ҳеҜҶ гҖӮжқҸиҠұзғҹйӣЁжұҹеҚ—йӣЁеӨңйқҷжӮ„жӮ„зҡ„ пјҢ еҰӮеҺҹе§ӢжЈ®жһ—дёӯж·ұйӮғзҡ„жҡ—йҒ“жүҖж•ЈеҸ‘зҡ„з§ҳеўғ гҖӮ дёҖдҪҚеӨ№еёҰзқҖжқҸиҠұйӣЁзҡ„дёҒйҰҷ姑еЁҳе°ұиҝҷж ·зӢ¬иҮӘж’‘зқҖдёҖжҠҠжІ№зәёдјһйЈҳиҝҮ гҖӮ ж»ҙзӯ”ж»ҙзӯ”зҡ„йӣЁеЈ°еңЁз ҙж—§зҡ„з“Ұз ҫе®үжҺ’дёӢдјҙйҡҸзқҖиҪ»иҖҢзј“зҡ„и„ҡжӯҘеЈ° пјҢ дёҚзҹҘдёҚи§үең°еј№еҘҸеҮәдәҶдёҖйҰ–и–„йӣҫжңҰиғ§зҡ„еұұжһ—е°ҸжӣІ гҖӮ иҖҒиЎ—ж—Ғзҡ„е®ўж Ҳж——йЈҺ пјҢ еңЁеҸӘжңүйӣЁжІЎжңүйЈҺзҡ„еӨңжҷҡ пјҢ иў«еІҒжңҲжӢүеҫ—з«–зӣҙ пјҢ зЎ¬з”ҹз”ҹең°жӢҰдҪҸдәҶеҘ№зҡ„еҺ»и·Ҝ гҖӮ дәҺжҳҜ пјҢ еңЁйӮЈд»Қж—§еңЁй»‘еӨңдёӢжіӣзқҖж·Ўж·ЎзҒ«зәўиүІзҡ„й—ЁжқҝдёҠ пјҢ еҘ№з”ЁеҸҢй’ұз»“еҸ©е“ҚдәҶж•ҙдёӘжұҹеҚ— гҖӮвҖң姑еЁҳ пјҢ жҳҜиҰҒдҪҸеә—еҗ—пјҹвҖқвҖңдёҚвҖҰвҖҰжҲ‘ж„ҝж„Ҹ继з»ӯз»•йҒ“иө°дёӢеҺ» гҖӮ вҖқе®ўж Ҳй—Ёж—Ғ пјҢ еә—家йӮЈж»Ўи„ёзҡұзә№зҡ„ж ·еӯҗиў«йўқеӨҙзҡ„з–‘жғ‘з»ҷеҲҶеүІжҲҗдәҶдёӨеҚҠ пјҢ еңЁз…ӨжІ№зҒҜеҫ®й—Әзҡ„жө…й»„иүІзҒҜе…үдёӢжҳҫеҫ—ж јеӨ–еҲҶжҳҺ гҖӮ 然иҖҢ пјҢ еңЁжӯӨеҲ» пјҢ еҘ№еҸӘжҳҜиҪ»иҪ»жҠ–дәҶжҠ–йқ’иүІйӣЁиЎ«дёҠзҡ„ж°ҙзҸ пјҢ еңЁеҫ®еҫ®жҢӨеј„зҡ„зІүзәўиүІеҳҙе”ҮдёӯжјҸеҮәдёҖдёқж°”жҒҜ пјҢ зҶ„зҒӯдәҶеҒңз•ҷеңЁеә—家иғёеүҚзҡ„з…ӨжІ№зҒҜ гҖӮвҖңиҖҒдәә家 пјҢ иҜ·дҝқжҢҒиҝҷжұҹеҚ—йӣЁеӨңеә”жңүзҡ„й»‘жҡ— гҖӮ вҖқеҘ№дёҚеӣһеӨҙең°иҫ№иө°иҫ№иҜҙ пјҢ д»»з”ұеү©дёӢдёҖеҜ№еңЁзәўиүІй—ЁжқҝдёҠзҡ„еҸҢй’ұз»“ пјҢ ж•Іжү“еҮәеҜӮйқҷзҡ„еҚҺеЈ° гҖӮеҸӨйҒ“иҘҝйЈҺзҳҰ马黢黑зҡ„д№ҢйёҰзә зј зқҖжҢӮеңЁж ‘жўўдёҠзҒ«зәўиүІзҡ„еӨ•йҳі пјҢ и®©е®ғиҝҹиҝҹдёҚиғҪиҗҪдёӢпјӣжһҜе№Ізҡ„иҗҪеҸ¶еҚҙзҰҒдёҚиө·иҘҝйЈҺзҡ„иҜұжғ‘ пјҢ ж—©ж—©ең°еҢ–дёәдәҶжқҘе№ҙзҡ„жҳҘжіҘ гҖӮ е°ұиҝҷж · пјҢ и®©дәҶдёҖдҪҚйӘ‘зқҖзҳҰ马зҡ„жёёеӯҗжӮ„жӮ„ең°и—ҸеҢҝдәҺе…¶дёӯ гҖӮйқ’иүІзҡ„й•ҝиЎ«еҠ дёҠеҲ«еңЁй©¬иғҢдёҠзҡ„ејҜи§’еЈ¶ пјҢ еҖ’д№ҹдёҚиҮідәҺи®©д»–дёҖж— жүҖжңү гҖӮ 然еҗҺ пјҢ д»–иҪ»иҪ»ең°жқҫејҖдәҶжүӢдёӯзҙ§жҸЎзҡ„зј°з»і пјҢ иҝҳдәҶзҳҰ马зҡ„ж— йҷҗиҮӘз”ұ гҖӮ иҖҢд»–иҮӘе·ұ пјҢ д№ҹйўӨйўӨең°жҠ–дәҶжҠ–й•ҝиЎ« пјҢ еҚёдёӢдәҶеёёе№ҙзҙ§зҡұзҡ„йўқеӨҙ пјҢ еҗ¬зқҖжұ иҫ№з§Ӣж°ҙзҡ„е‘јеҗёеЈ° гҖӮ жӯӨж—¶ пјҢ жҪәжҪәзҡ„жөҒж°ҙдёҠиҝҳжјӮжө®зқҖеҲҡд»Һжў§жЎҗж ‘жўўиҗҪдёӢзҡ„еҸ¶зүҮ пјҢ еҪ“然 пјҢ иҝҳжңүй»ўй»‘д№ҢйёҰзҡ„зҫҪжҜӣеңЁж°ҙдёӯж—ӢиҪ¬ пјҢ иҖҢиҝҷдәӣ пјҢ д»–йғҪзңӢеңЁдәҶзңјйҮҢ гҖӮжІҝзқҖжөҒж°ҙзҡ„дёҚиҝңеӨ„ пјҢ д»–з»ҲдәҺж¬Је–ңең°еҸ‘зҺ°дәҶдёҖжҲ·зүөеј•зқҖзӮҠзғҹзҡ„дәә家 гҖӮвҖңиҜ·й—®жңүдәәеҗ—пјҹвҖқд»–жҺўзқҖй•ҝд№…иҖ·жӢүзқҖзҡ„и„‘иўӢеҗ‘йӮЈй—ҙйҮ‘й»„иүІзҡ„иҢ…иҚүеұӢе–ҠйҒ“ пјҢ дјҙйҡҸзқҖиҚүеұӢеҗҺйқўж ‘жһ—дёӯзҡ„еҮ еҸӘйә»йӣҖзҡ„з°Ңз°ҢйЈһиө· гҖӮвҖңиҜ·й—®жңүдәәеҗ—пјҹвҖқд»–еңЁзӯүеҫ…дәҶи®ёд№…д№ӢеҗҺдёҚиҖҗзғҰең°еҶҚж¬Ўе–ҠйҒ“ гҖӮдҪҶ пјҢ д»Қж—§жІЎдәәеӣһзӯ” гҖӮ иҖҢдёҺ第дёҖж¬ЎдёҚеҗҢзҡ„жҳҜ пјҢ иҚүеұӢеҗҺйқўзҡ„йә»йӣҖдёҚеҶҚйЈһиө· пјҢ зүөеј•еңЁзғҹеӣұдёҺеӨ•йҳід№Ӣй—ҙзҡ„зӮҠзғҹд№ҹжёҗжёҗең°ж¶ҲеӨұдәҶ гҖӮ д»–й»ҳй»ҳең°еҶҚж¬ЎиҖ·жӢүзқҖи„‘иўӢ пјҢ 并жҸҗзҙ§дәҶжҸЎеңЁжүӢдёӯзҡ„зј°з»і гҖӮвҖңзңӢжқҘжҳҜ他们вҖҰвҖҰдёҚж„ҝвҖҰвҖҰдёҚж„ҝжҺҘеҫ…дёҖдёӘйҷҢи·Ҝзҡ„ж—…дәә гҖӮ вҖқд»–дёҖдёӘдәәз»Ҷз»Ҷең°еҳҖе’•йҒ“ пјҢ жіӣзәўзҡ„зңјзқӣйҮҢд№ҹеңЁй…қй…ҝзқҖеҮ ж»ҙеҶ°еҮүзҡ„жіӘж°ҙ гҖӮдәҺжҳҜ пјҢ д»–з”ЁеҠӣең°и°ғиҪ¬дәҶ马еӨҙ гҖӮ еңЁзҳҰ马дёҖеЈ°й•ҝй•ҝеҳ¶йёЈиҝҮеҗҺ пјҢ жғҠйҶ’дәҶзә зј еңЁж ‘жўўдёҠзҡ„й»‘д№ҢйёҰ пјҢ йҡҸзқҖд»–еҗ„иҮӘжңқзқҖеӨ©ж¶Ҝзҡ„ж–№еҗ‘йЈһеҺ» гҖӮеӨңеҚҠй’ҹеЈ°е®ўиҲ№йҒҘиҝңеҜ’еұұеҜәзҡ„й“ңй’ҹдҫқж—§дј«з«ӢеңЁеӨңиүІжңҰиғ§зҡ„жҷҡйңңдёӯ пјҢ жұҹдёҠжё”иҲ№зҡ„зҒҜзҒ«е°ұеҰӮж»ЎеӨ©з№Ғжҳҹзҡ„й—ӘзғҒдёҺж®ӢжңҲдәүиҫү гҖӮ жӯӨж—¶ пјҢ зқЎзқҖзҡ„дәәиҮӘ然жҳҜе…ҘжўҰдәҶ пјҢ иҖҢд»Қ然йҶ’зқҖзҡ„дәәеҚҙж— жі•еҖҹд№ҢйёҰзҡ„е•јеҸ«еЈ°жҺ’и§Јеҝғдёӯзҡ„ж„Ғй—· гҖӮжҲҙзқҖж–—з¬ зҡ„жё”еӨ«еңЁдёҚеҒңең°жҢҘж’’зқҖжүӢдёӯзҡ„жё”зҪ‘еҗ‘жұҹеҝғж’’еҺ» пјҢ ж®ӢеҝҚең°е°Ҷж®ӢжңҲзҡ„еҖ’еҪұеҶҚж¬Ўз ҙзўҺжҲҗеҮ з“Ј гҖӮ иҖҢд»–еҸӘжҳҜзӣ®и§ҶзқҖиҝҷдёҖеҲҮ пјҢ 并дёҚеёҰеҚҠзӮ№жҖңжғң гҖӮ еҪ“дёүжӣҙеӨ©зҡ„жұҹйЈҺжӮ„жӮ„ең°еҲ®иҝҮд»–зҡ„и„ёйўҠ пјҢ жү¬иө·дәҶд»–иҖіж—Ғй•ҝеҸ‘зҡ„ж—¶еҖҷ пјҢ еҜ’еұұеҜәзҡ„й’ҹеЈ°д№ҹйҷ„е’ҢзқҖеүҚжқҘ гҖӮвҖңиҲ№е®¶ пјҢ иҝҷд№ҲжҷҡдәҶжҖҺд№Ҳиҝҳдјҡжңүй’ҹеЈ°е‘ўпјҹвҖқжё”еӨ«ж„ЈдәҶж„Ј пјҢ йҡҸеҗҺз”ЁжүӢжҢҮзқҖ姑иӢҸеҹҺеӨ–зҡ„еҜ’еұұеҜәиҜҙпјҡвҖңзңӢи§ҒдәҶеҗ—пјҹй’ҹеЈ°е°ұжҳҜд»ҺйӮЈйҮҢдј жқҘзҡ„ гҖӮ йӮЈеә§еҜәеәҷд»ҺжҲ‘зҲ·зҲ·зҡ„йӮЈдёҖиҫҲе°ұжңүдәҶ пјҢ иҖҢиҝҷжҜҸеӨ©еҚҠеӨңзҡ„й’ҹеЈ°д№ҹжҳҜиҮӘжү“жҲ‘и®°дәӢиө·е°ұжІЎжңүеҒңжӯўиҝҮ гҖӮ вҖқвҖңйӮЈе®ғдёҚдјҡжғҠеҲ°вҖҰвҖҰжҲ‘зҡ„ж„ҸжҖқжҳҜдёҚдјҡжү“жү°еҲ°зҷҫ姓зҡ„з”ҹжҒҜеҗ—пјҹвҖқвҖңжү“жү°пјҹвҖқжё”еӨ«з¬‘дәҶ笑 пјҢ вҖңжҲ‘们иҝҷйҮҢзҡ„дәәйғҪе·Із»Ҹд№ жғҜдәҶиҝҷй’ҹеЈ° пјҢ еҸҚеҖ’жҳҜ пјҢ иӢҘе“ӘдёҖеӨ©иҝҷй’ҹеЈ°еҒңжӯўдәҶ пјҢ жҲ‘们еҖ’зқЎеҫ—дёҚе®үзЁідәҶпјҒвҖқвҖңжҖҺд№Ҳдјҡиҝҷж ·вҖҰвҖҰвҖқд»–иӢҘжңүжүҖеӨұең°жңӣзқҖиҝңеӨ„ гҖӮвҖңжҖҺд№ҲдәҶ пјҢ е®ўе®ҳпјҹжҳҜдёҚжҳҜеҗ¬зқҖиҝҷй’ҹеЈ°ж„ҹи§үжңүдәӣи®ёз–ІеҖҰдәҶе‘ўпјҹвҖқжё”еӨ«зҡұзқҖзңүеӨҙй—®йҒ“ гҖӮд»–зј“зј“ең°д»ҺиғҖеҫ—еҫ®еӨ§зҡ„иғёи…”дёӯжөҒеҮәдёҖеҸЈж°” пјҢ ж°”жҒҜеңЁеҜ’еҶ·зҡ„з©әж°”йҮҢзһ¬й—ҙеҢ–дёәдәҶдёҖеӣўзҷҪйӣҫйЈҳеҗ‘жұҹеҝғ гҖӮ йҡҸеҗҺ пјҢ д»–з”ЁйўӨжҠ–иҖҢдҪҺжІүзҡ„еЈ°йҹіиҜҙйҒ“пјҡвҖңзңӢжқҘжӮЁиҜҙзҡ„еҜ№ пјҢ еңЁеҜ’еұұеҜәиҝҷеӮ¬дәәе…ҘжўҰзҡ„й’ҹеЈ°йҮҢ пјҢ жҲ‘жҳҜиҜҘдј‘жҒҜдәҶвҖҰвҖҰвҖқжё”еӨ«дҪҺдёӢеӨҙ继з»ӯ收зқҖжүӢдёӯзҡ„жё”зҪ‘ пјҢ иҖҢжӣҫз»ҸеңЁжұҹдёӯзҡ„еҮ жқЎжҙ»и№Ұд№ұи·ізҡ„йІӨйұјд№ҹйҡҸд№Ӣе®үйқҷең°иәәеңЁдәҶжё”еӨ«зҡ„з«№зҜ“йҮҢ пјҢ еҸӘжҳҜеҒ¶е°”зңЁзңЁзңјгҖҒеҗҗеҗҗжіЎ пјҢ еҗ‘зқҖеҜ’еұұеҜәйӮЈйҒҘиҝңзҡ„й’ҹеЈ°й»ҳеҝөзқҖиҮӘе·ұзҡ„еҝғз»Ҹ гҖӮжҲ‘жҳҜдёҚжҳҜиҜҘйҶ’дәҶе‘ўпјҹеңЁиҝҷжҳҸжҡ—зҡ„еҸ°зҒҜдёӢ пјҢ еңЁиҝҷжіӣй»„зҡ„иҜ—йӣҶдёӯвҖҰвҖҰжһҒеҫ®жң«вҖ”вҖ”гҖҠдјӨйҖқгҖӢдёҺжҲ‘и‘Ји•ҙ(21еІҒ)дёӯеӣҪ科еӯҰйҷўеӨ§еӯҰз”ҹзү©з§‘еӯҰдё“дёҡжң¬з§‘з”ҹжңҖж—© пјҢ жҳҜжҜҚдәІиҚҗжҲ‘иҜ»зҡ„гҖҠдјӨйҖқгҖӢ пјҢ еҶҚиҜ»дёҖжҷғе·ІжҳҜзҺ°ж—¶дәҶ гҖӮ жӣҫз»ҸжҲ‘е°ҶиҺҺеЈ«жҜ”дәҡзҡ„дҪңе“Ғи§ҶдёәзҲұжғ…зҡ„еҗҜи’ҷвҖ”вҖ”жөӘжј«жҳҜй»‘еӨңзӘ—еҸ°дёӢдҪ зҡ„зңјзқӣиғңиҝҮ20жҠҠеҲ©еҲғеҲәз©ҝжҲ‘еҝғи„Ҹ пјҢ ж°ёжҒ’жҳҜжҲ‘дёәдҪ д»ҺеҶ°еҶ·зҡ„еқҹиҢ”дёӯйҶ’жқҘеҶҚдёҖеҗҢй•ҝзң вҖ”вҖ”дҪҶзӣҙеҲ°гҖҠдјӨйҖқгҖӢ пјҢ жҲ‘жүҚжңүдәҶжһҒзҺ°е®һзҡ„е…ідәҺзҲұжғ…зҡ„жҖқиҖғпјӣд№ҹжҳҜиҮӘжӯӨеҫҖеҗҺ пјҢ жҲ‘жүҚд»ҺеҚЎдҪӣгҖҒд»ҺиҸІиҢЁжқ°жӢүеҫ·гҖҒд»ҺеЎһжһ—ж јзҡ„ж–Үеӯ—д№Ӣй—ҙ пјҢ иҜ»еҮәйӮЈж ·вҖңзҲұжҳҜжғіи§Ұзў°еҚҙеҸҲзј©еӣһжүӢвҖқзҡ„е°Ҹеҝғзҝјзҝје’ҢдёҖйў—зңҹеҝғ гҖӮ жҲ‘们и°Ҳи®әзҡ„зҲұжғ…е•Ҡ пјҢ еҚ•жҳҜжҢӮзқҖвҖңжғ…вҖқеӯ— пјҢ е°ұи¶ід»Ҙе‘ҠзҹҘдәә们其дёӯеҝ…е®ҡе…ҚдёҚдәҶжҺәжқӮзқҖдәәжҖ§жң¬иә«зҡ„зјәйҷ·еёҰжқҘзҡ„дёҚеңҶж»Ўз”ҡиҮіжҳҜдё‘жҒ¶ пјҢ дҪҶд№ҹжӯЈеӣ еҰӮжӯӨ пјҢ е…¶дёӯйӮЈдәӣзңҹжӯЈдјҹеӨ§иҖҢиҜҡжҢҡзҡ„жғ…ж„ҹ пјҢ жүҚдјҡж„ҲеҸ‘иҖҖзӣ® гҖӮжҲ‘жғіжҲ‘жҲ–и®ёжҳҜиғҪеӨҹдҪ“дјҡжҜҚдәІзҡ„з”Ёж„ҸдәҶ гҖӮеҘ№жүҖеёҢжңӣзҡ„ пјҢ жҳҜжҲ‘еңЁд»“зҡҮеҺ»зҲұд№ӢеүҚ пјҢ е…Ҳе®ҢжҲҗдёҖдёӘиҮӘз”ұгҖҒжңүиҮӘжҲ‘ж„ҸиҜҶзҡ„дёӘдҪ“еӯҳеңЁзҡ„и®ӨзҹҘ пјҢ еңЁзҲұе’Ңиў«зҲұзҡ„иҝҮзЁӢд№Ӣдёӯе§Ӣз»ҲдҝқжҢҒи°ҰеҚ‘гҖҒе№ізӯү пјҢ дёҚж–ӯжҲҗй•ҝгҖҒиҮ»дәҺе®Ңе–„ пјҢ иҖҢдёҚжҳҜеҒҡдёҖдёӘиў«зӨҫдјҡзҺҜеўғе’Ңи§ӮеҝөжүҖеӣәеҢ–дәҶзҡ„зҺ©еҒ¶ејҸзҡ„еҘіжҖ§ гҖӮ жҲ‘д№ҹжӣҫжҡ—жғіеҪ“е№ҙж–Үйқ’ејҸзҡ„жҜҚдәІ пјҢ жҖҺе°ұе«Ғз»ҷдәҶд№ҸдәҺз”ңиЁҖиңңиҜӯзҡ„зҲ¶дәІвҖ”вҖ”дҪҶзҺ°еңЁжҲ‘жҳҺзҷҪ пјҢ жӣҙжңүиҝңи§Ғзҡ„зҡ„зЎ®жҳҜжҜҚдәІ пјҢ еҘ№жІЎи®©жһҒеҫ®жң«зҡ„з”ҹжҙ»жҠ№е№ідәҶеҘ№зҡ„ж„Ҹж°” пјҢ еңЁй•ҝиҫҫ20е№ҙзҡ„е©ҡ姻йҮҢ пјҢ еҘ№еЎ‘йҖ дәҶдёҖдёӘжё©ж–ҮиҖҢдёҠиҝӣзҡ„дјҙдҫЈ гҖӮ жҲ‘жғіжңҖзҗҶжғізҡ„е©ҡ姻зҠ¶жҖҒеӨ§жҰӮд№ҹиҺ«иҝҮдәҺжӯӨ пјҢ д»ҝдҪӣжқҫйңІе·§е…ӢеҠӣ пјҢ зҗҗзўҺзҡ„ж—ҘеёёжҳҜиЎЁйқўзҡ„еҸҜеҸҜзІү пјҢ дҪҶжҒ°еҲ°еҘҪеӨ„зҡ„жӯЈжҳҜиҝҷз”ңиңңдёҺиӢҰ涩зӣёиҫ…зӣёжҲҗгҖҒж°ҙд№ідәӨиһҚзҡ„йЈҺе‘і гҖӮ еҗ¬зқҖз”өиҜқйҮҢиҝңеңЁе®¶д№Ўе°Ҹй•Үзҡ„зҲ¶жҜҚеҸҷиҜҙзқҖ他们жҖҺж ·дёҖеҗҢеҺ»зңӢдәҶдёҚжҳҜеӨӘеҘҪзҡ„з”өеҪұ пјҢ жҖҺж ·дёҖиө·еҺ»ж№–иҫ№ж•ЈжӯҘи°ҲеӨ©ж¶ҲзЈЁжҺүдёҖдёӘдёӢеҚҲ пјҢ з”ҡиҮіжҳҜжҖҺж ·дёҖиө·еҒҡдәҶдёҖйҒ“еӨұиҙҘзҡ„иҸңе“Ғ пјҢ жҲ‘йғҪдјҡжғіиө·йІҒиҝ…е…Ҳз”ҹеҖҹ涓з”ҹд№ӢеҸЈжүҖиҜҙзҡ„иҜқвҖ”вҖ”вҖңдәәз”ҹзҡ„иҰҒд№ү пјҢ 第дёҖ пјҢ дҫҝжҳҜз”ҹжҙ» гҖӮ дәәеҝ…з”ҹжҙ»зқҖ пјҢ зҲұжүҚжңүжүҖйҷ„дёҪ гҖӮ вҖқе“ӘжҖ•жҳҜжһҒеҫ®жң«зҡ„з”ҹжҙ» пјҢ е“ӘжҖ•жҳҜжһҒеҫ®е°Ҹзҡ„иҮӘжҲ‘ пјҢ д№ҹжҳҜдёҖеҲҮзҲұзҡ„ж №еҹәе•Ҡ гҖӮиҺІжғ…дҪ•д№ҰзҗӘ(20еІҒ)дёӯеӣҪ科еӯҰйҷўеӨ§еӯҰеҢ–еӯҰзі»жң¬з§‘з”ҹеӯЈеӨҸзҡ„жё©еәҰж—©е·ІжІЎдәҶеӯҹеӨҸзҡ„еҲқзғӯдёҺд»ІеӨҸзҡ„зӮҪзӮҺ пјҢ д»…дҪҷжңүж·Ўж·Ўзҡ„еҫ®жё© пјҢ иҖҢиҝҷзӮ№ж°”еҖҷжҒ°еҘҪд»ӨжҲ‘еҶ…еҝғиҲ’йҖӮ гҖӮ жңӣзқҖиҝңж–№зҡ„йҳі пјҢ еҘ№д№ҹз–ІеҖҰдәҶзҷҪж—Ҙзҡ„е·ҘдҪң пјҢ еҫҗеҫҗеҗ‘иҘҝеҪ’еҺ» гҖӮ жҲ‘иҝҲзқҖе°ҸжӯҘеӯҗ пјҢ еңЁзҹіи·Ҝе°Ҹеҫ„иёұиЎҢ пјҢ иә«ж—ҒжңүжқҘеҺ»еҢҶеҢҶзҡ„жёёдәә пјҢ еҸҜиғҪеӣ дёәеӨӘеҝ«гҖҒеӨӘеҝ« пјҢ 他们зҡ„йқўеӯ”з«ҹ然иҪ¬зһ¬еҚійҖқ пјҢ дёҚз•ҷдёҖзӮ№иүІеҪ© гҖӮи¶ҒзқҖжҷҡйңһзҡ„дҪҷе…ү пјҢ жҲ‘з¬ғжӯҘеҗ‘зқҖйӮЈдёӘең°ж–№ гҖӮйӮЈең°ж–№ пјҢ йёҘй№ӯзҝ”йӣҶ пјҢ йӣҖиң“йЈһиҲһпјӣиқүиӣҷе’ҢйёЈ пјҢ йЈҺжҹіж‘Үжӣіпјӣж№–жұ зІјзІј пјҢ иҚ·иҺІз”°з”° пјҢ жӣҫдҪҝжҲ‘еҝғи·Ңе®• пјҢ д№…иҝ·дәҺжӯӨ гҖӮеӯҹеӨҸжҹҗж—Ҙ пјҢ еӣ иҜёдәӢжү°еҝғ пјҢ еҒ·еҫ—еҚҠж—Ҙжё…й—І пјҢ еӣӣеӨ„еҜ»жұӮеҝғе®үд№ӢеӨ„ пјҢ зӯүжқҘзҡ„еҸӘжңүж— жһңдәҢеӯ— гҖӮ и§…д№ӢеҚғзҷҫеәҰ пјҢ иҺ«иӢҘдёҖеӣһйҰ– гҖӮ еҶіж„ҸжҠҳиҝ”зҡ„ејҘз•ҷд№Ӣйҷ… пјҢ жҲ‘дёҚз»ҸдёҖзһҘ пјҢ еҚҙиў«дёҚиҝңзҡ„зҒөеҠЁйҮ‘е…үеҗёеј• гҖӮ жҸүжҸүз–Іжғ«зҡ„зңј пјҢ еҸ‘зҺ°йҮ‘е…үе‘ЁйҒӯжңүеӨ§зүҮзҡ„з»ҝе‘ў пјҢ 他们иҝҳеңЁж‘ҶеҠЁиә«е§ҝ гҖӮ ж¬ҫж¬ҫйқ иҝ‘еҗҺ пјҢ йқўйўҠж„ҹеҲ°еҫ®йЈҺзҡ„еҮүзҲҪ пјҢ дҪҶиә«дҪ“д»Қ然еғөзӣҙ гҖӮ дёҖжҠ№жө…жЎғйҡҗеңЁз»ҝдёӯ пјҢ дәӯдәӯеҮҖжӨҚдәҺйҮ‘е…үд№ӢдёҠ пјҢ еҘ№е°ҡжІЎеҸ—йӮЈйЈҺзҡ„еҪұе“Қ пјҢ дҫқж—§е®үиҜҰгҖҒиҷ”иҜҡең°дә«еҸ—йҮ‘е…үзҡ„жҒ©жіҪ гҖӮ еҘҪеҘҮй©ұеҠЁжҲ‘з”ЁжүӢи§ҰдәҶи§Ұеҗ«иӢһзҡ„жө…жЎғ пјҢ е“Ұ пјҢ иҝҷжҳҜиҺІж¬ё пјҢ еҘҪжғіеҶҚиҝ‘дәӣзңӢзңӢ гҖӮ дёҚ пјҢ иҺІ пјҢ еҸҜиҝңи§ӮиҖҢдёҚеҸҜдәөзҺ©з„ү гҖӮ еҶөдё” пјҢ иҺІдё»иҮӘ然 пјҢ иӢҹйқһеҗҫд№ӢжүҖжңү пјҢ иҷҪдёҖжҜ«иҖҢиҺ«еҸ– гҖӮ иҖҢ пјҢ иҺІ пјҢ дјјд№Һи§үеҜҹеҲ°жҲ‘ж„ҝдёҺзҹҘдәӨ пјҢ д№ҹж‘ҮжӣідәҶдёҖдёӢ гҖӮ жҲ‘жҖқзҙўиүҜд№…дҫҝзҰ»еҺ»дәҶ пјҢ ж—¶жңәжңӘиҮі пјҢ еҗӣеӯҗдёҚеӨәе…¶жүҖеҘҪ гҖӮзӯүеҫ…зҡ„ж—¶ж—ҘжҖ»жј«жј«й•ҝй•ҝ пјҢ зҶ¬иҝҮеӯҹеӨҸжҢҒз»ӯеҚҮжё© пјҢ иҝҺжқҘиҝҷзӮҺзӮҺзҡ„д»ІеӨҸ гҖӮ жҜҸжҜҸеҝөеҸҠйӮЈжҠ№жө…жЎғ пјҢ жҲ‘жұ№ж¶ҢжҫҺж№ғ пјҢ еёёжҖқеҘ№е®үеҘҪеҗҰ гҖӮ зңӢзқҖеӨ©иҝ‘еӨңиүІ пјҢ жҲ‘жӮ„然жәңеҺ»йӮЈең°ж–№ пјҢ еҺ»е№ҪдјҡжҲ‘зҡ„жўҰдёӯиҺІ гҖӮ йҮ‘е…үиҷҪдёҚеҶҚ пјҢ дҪҶйЎәзқҖдёҠж¬Ўзҡ„зҹіеҫ„ пјҢ ж‘ёзҙўзқҖд№ҹеҫҲеҝ«жқҘеҲ°иҺІзҡ„иә«ж—Ғ гҖӮиҺІзҡ„жө…жЎғе·Із»ҸжҚўжҲҗзҷҪиүІ пјҢ зәҜжҙҒиҖҢдјҳйӣ… пјҢ з“ЈдёҠзҡ„ж°ҙзҸ еҘҪдјјеңЁиҝ°иҜҙзқҖеҘ№еҲҡеҲҡжІҗжөҙе®Ң гҖӮ иҝҷеҮәж°ҙд»ҷеӯҗ пјҢ е®үйқҷдёӯйҖҸзқҖзҫһ涩 пјҢ и®©жҲ‘дёҚзҹҘжүҖжҺӘ пјҢ дәҺжҳҜе°ұиҝҷж · пјҢ жҢҒз»ӯеҜӮ然 гҖӮ жү“з ҙиҝҷзӘҳзҠ¶зҡ„жҳҜеҮәзҺ°дәҶдёҖеҜ№иҖҒеӨ«еҰҮ пјҢ иҖҒзҲ·зҲ·еңЁеүҚйқўйўӨйўӨе·Қе·Қең°жҢӘзқҖдёҚеҲ©зҙўзҡ„и„ҡ пјҢ дёҖеҸӘеҺҶз»ҸеІҒжңҲзҡ„жүӢзҙ§зҙ§ж”ҘзқҖиҖҒдјҙзҡ„жүӢ пјҢ иҖҢиҖҒдјҙеҚҙжҜ”д»–жӣҙйўӨйўӨе·Қе·ҚвҖҰвҖҰжҲ‘зҡ„зңји§’дёҚз”ұж№ҝж¶Ұ пјҢ и„‘жө·й—ӘиҝҮеҸ¶иҠқзҡ„иҜ—жӯҢгҖҠеҪ“дҪ иҖҒдәҶгҖӢ гҖӮ иҖҢеҸ¶иҠқзҡ„иў«жӢ’д№ҹж·ұж·ұең°зҠ№й’ҲжүҺеҝғ пјҢ еҶҚзңӢзңӢзҷҪиҺІдёӯеҝғ пјҢ иҚ·еҝғжҳҜйӮЈд№Ҳзҡ„зәўиүіе’§ пјҢ зҠ№еҰӮжҲ‘зҲұиҺІзҡ„дёҖзүҮиөӨеҝғ пјҢ жӣ·дёҚ委еҝғд»»еҺ»з•ҷе‘ўпјҹеҝғе°–жңүиӮЎеҠӣйҮҸеңЁзҝ»ж¶Ң пјҢ еҘҪеғҸеңЁжҡ—зӨәжҲ‘пјҡеҝ«е‘ҠиҜүеҘ№дҪ зҡ„еҝғеЈ°еҗ§пјҒеҝ«е‘ҠиҜүеҘ№дҪ зҡ„еҝғеЈ°еҗ§пјҒеҝ«е‘ҠиҜүеҘ№дҪ зҡ„еҝғеЈ°еҗ§пјҒжҲ‘е“Ҫе’ҪдәҶдёҖдёӢ пјҢ жҠ¬еӨҙ пјҢ з«ҹеҸ‘зҺ°д»ҠеӨңж— жңҲ пјҢ иҝңж–№зҡ„зҒҜзҒ«д№ҹеңЁйӣҫи’ҷй—ҙй»Ҝ然еӨұиүІ гҖӮ жҲ‘еҜ№иҮӘе·ұиҜҙдәҶиҜҙпјҡжғіжё…жҘҡе•Ҡ пјҢ иҝҷж ·еҸӘжңүдёӨз§ҚжһҒз«Ҝзҡ„з»“жһңпјҒдҪ е®іжҖ•еҘ№еҸ—дјӨ пјҢ дҪҶиҝҷд№ҹжҳҜдҪ еҝ…йЎ»еҫ—иҝҲиҝҮеҺ»зҡ„еқҺе„ҝе•ҠпјҒж·ұеҗёдёҖеҸЈж°”еҗҺ пјҢ жҲ‘з»Ҳ究иҜҙеҮәеҶ…еҝғзҡ„з–‘жғ‘пјҡиҺІ пјҢ дҪ жҳҜеҗҰж„ҝж„Ҹи®©жҲ‘зӯүеҫ…пјҹиҝҷж—¶ пјҢ зӘҒеҰӮе…¶жқҘзҡ„з»ҶйӣЁжү“еңЁжҲ‘зҡ„йқўйўҠдёҠ пјҢ д№ҹжү“еңЁеҘ№иә«дёҠ пјҢ иҺІеңЁз»ҶйӣЁдёӯж‘ҮдәҶж‘ҮиҢҺз§Ҷ пјҢ иҢҺз§Ҷиҫ№дә§з”ҹж°ҙжіўеҗ‘еӣӣе‘Ёжү©ж•Ј пјҢ дёҖеұӮиҚЎиө·дёҖеұӮ пјҢ еҘ№еӣһеӨҚзҪўпјҡеҗӣеӯҗд№ӢдәӨж·ЎиӢҘж°ҙ пјҢ зҹҘдәӨд»Қ然 гҖӮ з»ҶйӣЁз»өз»ө пјҢ жҲ‘жңЁз„¶дј«з«Ӣ пјҢ зӣҙиҮіжңқйҳізҡ„第дёҖзј•е…үйҖҸиҝҮдә‘еұӮжҙ’еҗ‘йқўйўҠ пјҢ еҝғдёӯжңүдәҶжӢЁдә‘и§Ғж—Ҙзҡ„йҮҠ然 пјҢ иҪ»иҪ»ең°дёҺд№Ӣе‘ҠеҲ« пјҢ иҪ»еҝ«ең°зҰ»еҺ»вҖҰвҖҰеӯЈеӨҸзҡ„иҗҪйңһеҸҲй©ұдҪҝжҲ‘жқҘзҹҘдәӨйӮЈе„ҝ гҖӮ зҹіи·Ҝдҫқж—§ пјҢ дҪҶзҷҪиүІзҡ„иҺІе·ІиӨӘеҺ»з“ЈиЈі пјҢ д»…жңүиҺІеӯҗеҚ§еңЁиҚ·еҝғ пјҢ зұій»„иүІзҡ„еӨ–иЎЈеҢ…иЈ№зқҖиҺІйқ’жҳҘзҡ„еӣһеҝҶ пјҢ иҖҢйқ’жҳҘд»ҚжҳҜжё…жҫҲеҰӮжӯӨ гҖӮ еҸӘеү©иҺІеӯҗзҡ„еҘ№ пјҢ иҷҪ然早已没дәҶйқ’жҳҘзҡ„зҫҺдёҪ пјҢ дҪҶеҝғе®үиӢҘзҙ гҖӮ жғіиө·йӮЈж—Ҙж— иҚ·еЎҳжңҲиүІ пјҢ еҚҙжңүеҮ еҲҶжңұиҮӘжё…е…Ҳз”ҹжҸҗеҸҠиҝҮзҡ„гҖҠиҘҝжҙІжӣІгҖӢ гҖӮдәҺжҲ‘ пјҢ еҸӘйЎәе…¶иҮӘ然 пјҢ дәҰеҝғдҫҝе®ү然вҖҰвҖҰ
жҺЁиҚҗйҳ…иҜ»
- з”ҹжҙ»йҮҢзҡ„еҲӣж„Ҹ|зҺӢж•ҷжҺҲиў«дёҫжҠҘеҗҺеҚҺеҚ—зҗҶе·ҘеӨ§еӯҰеҸҲжңүдәӢжғ…дәҶ: зңҹзӣёжңүеҫ…и°ғжҹҘ!
- жҫҺж№ғж–°й—»|иў«жҢҮејәеҘёеҘіз”ҹзҡ„еҚҺеҚ—зҗҶе·Ҙж•ҷжҺҲеӣһеә”з§°е°ҶеҒҡжҫ„жё…пјҢиӯҰж–№е’ҢеҰҮиҒ”д»Ӣе…Ҙ
- жңҚеҠЎдёҡ|дәәжүҚдҫӣз»ҷгҖҒжҖ»дҪ“зҙ иҙЁвҖҰвҖҰж–°иҒҢдёҡеҸ‘еұ•иҝҳйқўдёҙиҝҷдәӣй—®йўҳ
- еҺҰй—ЁзҺ©д№җ|иҝҷдәӣеӯҰж ЎжҳҜеҘҪеӯҰж Ў, е°ұжҳҜж ЎеҗҚеҸ–еҫ—жңүдәӣвҖңйЈҳвҖқдәҶ
- еҺҰй—ЁзҺ©д№җ|е…ӯе№ҙзә§ж•°еӯҰеҹ№дјҳпјҡеҲҶж•°еә”з”Ёйўҳз»јеҗҲиҝҗз”ЁпјҢжҲ–и®ёдҪ дёҺй«ҳеҲҶе°ұе·®иҝҷдәӣж–№жі•
- 家装зҷҫ科|еңҲйҮҚзӮ№пјҒз ”з©¶з”ҹиҖғиҜ•жӯЈејҸжҠҘеҗҚејҖе§ӢпјҢиҝҷдәӣжіЁж„ҸдәӢйЎ№иҜ·дёҖе®ҡиҰҒзңӢ
- еҒңе·Ҙд»Ө|ж–°дёҖиҪ®вҖңеҒңе·Ҙд»ӨвҖқжқҘдәҶпјҢжҢҒз»ӯеҲ°жҳҺе№ҙпјҹиҝҷдәӣиЎҢдёҡжҲ–е°ҶдёўжҺүйҘӯзў—
- иҝҷдәӣж¬Ўдё–д»Је“ҒзүҢпјҢдёәд»Җд№ҲеҸҜд»ҘжҺҸз©әдҪ зҡ„й’ұеҢ…
- йҖҡжҠҘжқҘдәҶпјҒиҝҷдәӣвҖңдё–з•Ңд№ӢжңҖвҖқеҝ…йЎ»ж•ҙж”№
- еҚҺеҚ—зҗҶе·ҘжҖ§дҫөжЎҲпјҡеҸӘи°ҲиҒҢдёҡж“Қе®ҲпјҢиӢҚзҷҪж— еҠ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