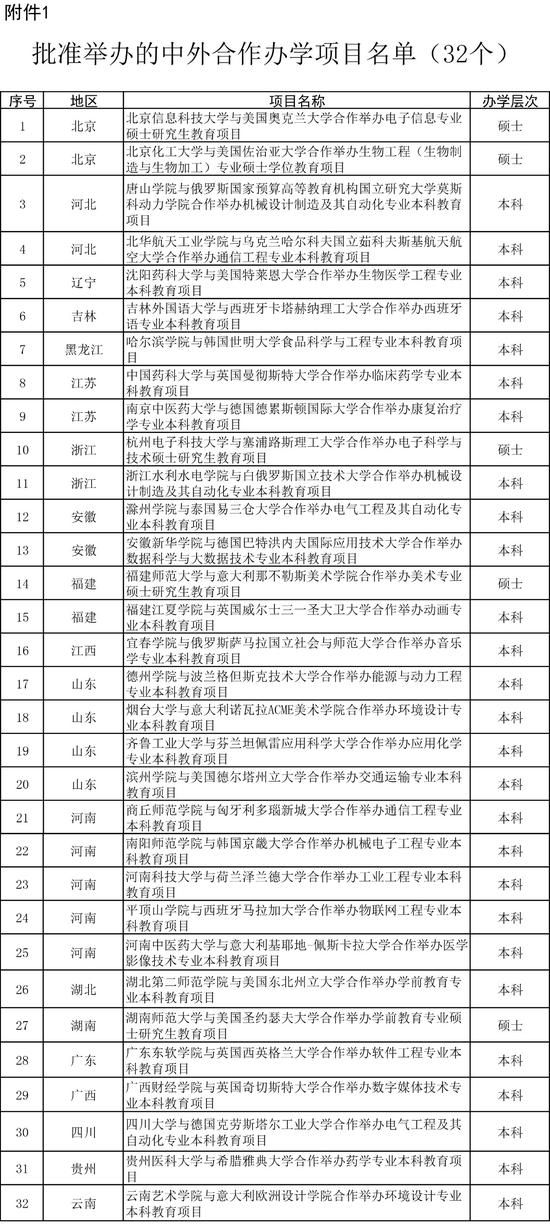йҮ‘йӣҒпјҡвҖңеңЁдёӨдёӘдё–з•Ңе…ұеҗҢдҪңжҲҳвҖқ
гҖҠж—·йҮҺйҮҢзҡ„иҖ¶зЁЈгҖӢ дјҠеҮЎВ·е…ӢжӢүе§Ҷж–ҜжҹҜдҫқдј—жүҖе‘ЁзҹҘ пјҢ иҘҝ欧зҡ„ж–ҮиүәеӨҚе…ҙжҳҜд»ҺзҘһжқғзҡ„жқҹзјҡдёӢж‘Ҷи„ұеҮәжқҘ пјҢ д»Ҙеј жү¬дәәжң¬дё»д№үзҡ„дёҖз§ҚжҖқжғіеҗҜи’ҷиҝҗеҠЁ гҖӮ дҪҶжҳҜеңЁдҝ„еӣҪ20дё–зәӘеҲқзҡ„ж”ҝжІ»иҲһеҸ°дёҠ пјҢ жҲ‘们еҚҙзңӢеҲ°дәҶдёҺжӯӨзӣёеҸҚзҡ„дёҖ幕вҖ”вҖ”е®—ж•ҷеӨҚе…ҙе’ҢжҖқжғіеҗҜи’ҷжҗәжүӢе…ұиҝӣ гҖӮ 1905е№ҙдҝ„еӣҪйўҒеёғвҖңе®—ж•ҷе®Ҫе®№жі•вҖқдёҺеҗҢе№ҙиҮӘжёёдё»д№үзҡ„з«Ӣе®Әж°‘з…®е…ҡжҲҗз«Ӣ пјҢ иЎЁйқўдёҠзңӢжҳҜдёӨдёӘеӯӨз«Ӣдә’дёҚзӣёе№Ізҡ„дәӢ件 пјҢ е…¶иғҢеҗҺеҚҙжңүдёҖжқЎзңӢдёҚи§Ғзҡ„зәўзәҝзӣёиҝһ гҖӮдҝ„еӣҪзҡ„иҮӘжёёдё»д№үе’Ңе®—ж•ҷзӣёдә’еҖҹеҠӣгҖҒе…ұеҗҢз”ҹй•ҝ пјҢ жј”з»ҺеҮәдёҺ欧жҙІж–ҮиүәеӨҚе…ҙвҖңиө°еҮәе®—ж•ҷвҖқзӣёеҸҚдҪҶз»“жһңзӣёеҗҢзҡ„иҝӣзЁӢ гҖӮ еңЁиҘҝ欧没жңүж–ҮиүәеӨҚе…ҙе°ұжІЎжңүдәәж–Үдё»д№ү пјҢ иҖҢеңЁдҝ„еӣҪ пјҢ е®—ж•ҷеӨҚе…ҙжҳҜе’Ңдәәж–Үдё»д№үжҳҜиҒ”зі»еңЁдёҖиө·зҡ„ гҖӮ жңүдәәдјҡй—® пјҢ е®—ж•ҷзҡ„дё–з•Ңи§ӮдёҺж”ҝжІ»еҸҚеҜ№жҙҫиҝҷдёӨдёӘйЈҺ马зүӣдёҚзӣёеҸҠзҡ„дёңиҘҝжҖҺд№ҲиғҪдә§з”ҹвҖңе…ұз”ҹгҖҒе…ұе®№вҖқе‘ўпјҹеңЁиҘҝ欧ж‘Ҷи„ұе®—ж•ҷй’іеҲ¶жҳҜиҝҺжқҘжҖқжғіи§Јж”ҫзҡ„еүҚжҸҗжқЎд»¶ пјҢ дёәд»Җд№ҲеңЁдҝ„еӣҪдјҡжңүвҖңйҖҶеҗ‘ж“ҚдҪңвҖқзҡ„еҺҶеҸІжј”з»Һе‘ўпјҹиҮӘз”ұдёҺе®—ж•ҷзҡ„зӢ„еҘҘе°јзҙўж–ҜеңЁиҘҝ欧з”ұдәҺж•ҷжқғеҠӣйҮҸејәеӨ§ пјҢ дәә们еӨ„еңЁж•ҷдјҡзҡ„жқҹзјҡдёӢ пјҢ жүҖд»Ҙиө°еҮәдёӯдё–зәӘдәә们е°ұиҰҒж‘Ҷи„ұж•ҷдјҡзҡ„жһ·й”Ғ пјҢ еңЁйӮЈйҮҢиҝ‘д»ЈеҢ–зҡ„иҝҮзЁӢеҗҢж—¶д№ҹжҳҜдё–дҝ—еҢ–зҡ„иҝҮзЁӢ гҖӮ 欧жҙІзҡ„е®—ж•ҷж”№йқ©еҲәжҝҖдәҶиө„жң¬дё»д№үзҡ„еҸ‘еұ•дёҺз§ҜзҙҜд»ҘеҸҠиө„дә§йҳ¶зә§зҡ„жҲҗй•ҝ пјҢ иҖҢдҝ„еӣҪзҡ„е®—ж•ҷж”№йқ©еҫ—еҲ©зҡ„жҳҜжІҷзҡҮж”ҝжқғ пјҢ е•Ҷдәәйҳ¶еұӮд№ҹжІЎжңүжҲҗй•ҝиө·жқҘ пјҢ д»Һзӯүзә§еҗӣдё»еҲ¶еҸ‘еұ•еҲ°з –еҲ¶еҗӣдё»еҲ¶ пјҢ ж•ҷдјҡзҡ„дҝҜйҰ–з§°иҮЈзӣҙжҺҘеҜјиҮҙдәҶе®—ж•ҷиӯҰеҜҹеҢ– пјҢ еӣ жӯӨдҝ„еӣҪиҝ‘д»ЈеҢ–зҡ„иҝҮзЁӢжҳҜиҰҒжү“з ҙеӣҪ家еһ„ж–ӯ пјҢ еңЁжҹҗз§Қж„Ҹд№үдёҠд№ҹжҳҜе®—ж•ҷзӢ¬з«Ӣж„ҸиҜҶи§үйҶ’зҡ„иҝҮзЁӢ гҖӮ жҚўеҸҘиҜқиҜҙ пјҢ е®—ж•ҷдёҺж”ҝжІ»д№Ӣй—ҙзҡ„дәҢе…ғз»“жһ„еҠӣйҮҸеҜ№жҜ”еҶіе®ҡдәҶе®ғ们зҡ„з»“зӣҹеҜ№иұЎе’Ңж–—дәүзӣ®ж Ү гҖӮдҝ„еӣҪж•ҷдјҡд»ҺеҪјеҫ—дёҖдё–ејҖе§ӢдёҖеҲҮдәӢзү©йғҪиҰҒе°ҠеҙҮвҖңжІҷзҡҮйҷӣдёӢзҡ„иҜҸд»ӨвҖқ гҖӮ жӯЈеҰӮж•ҷдјҡдәәеЈ«жүҖиҜҙзҡ„ пјҢ жҳҜвҖңеҪјеҫ—з –еҲ¶ж”ҝдҪ“д№Ӣй№° пјҢ е•„йЈҹдәҶдҝ„еӣҪдёңжӯЈж•ҷд№ӢеҝғвҖқ гҖӮ иҖҢжІҷзҡҮдёҖзӣҙжҠҠж•ҷдјҡзңӢдҪңжҳҜжңҖдё»иҰҒзҡ„жҪңеңЁеҸҚеҜ№иҖ… пјҢ д»ҺйӮЈж—¶иө·ж”ҝжқғе’Ңж•ҷдјҡд№Ӣй—ҙзҡ„зҙ§еј е…ізі»е§Ӣз»ҲеӯҳеңЁ пјҢ жүҖд»Ҙж•ҷдјҡеҶ…йғЁжңүеҫҲејәзҡ„жҠ—дәүеҠӣе’ҢзӢ¬з«ӢзІҫзҘһ гҖӮ 他们еҸҚеҜ№жҠҠзҘһзҡ„дёңиҘҝеҸҳжҲҗж”ҝжқғзҡ„дёңиҘҝ пјҢ еҸҚеҜ№жҠҠж•ҷдјҡеҸҳжҲҗж”ҝжқғзҡ„е·Ҙе…· гҖӮ
еҪјеҫ—дёҖдё–дәІиҮӘд»»е‘Ҫзҡ„еӨ§дё»ж•ҷ stephen yavorskyеңЁиҘҝ欧早已жҳҜвҖңиҝҮеҺ»ж—¶вҖқзҡ„вҖңе®—ж•ҷе’Ңдё–дҝ—дҪ“зі»жқғзӣҠзҡ„йҮҚж–°иҜ„дј°вҖқиҝҮзЁӢ пјҢ еңЁдҝ„еӣҪдёҖзӣҙеҲ°19дё–зәӘеҗҺеҚҠеҸ¶жүҚеҲҡеҲҡеұ•ејҖ гҖӮ жӯЈеҰӮе“ІеӯҰ家жҙӣж–ҜеҹәжүҖиҜҙ пјҢ дҝ„еӣҪвҖңжҖқжғіжҷҡжқҘзҡ„е’ҢиҝҹеҲ°зҡ„и§үйҶ’вҖқеҝ…е®ҡжҳҜе’Ңе®—ж•ҷзј з»•еңЁдёҖиө· гҖӮ з”ұдәҺеӣҪ家еһ„ж–ӯеҺӢеҲ¶дәҶдёҖеҲҮйўҶеҹҹ пјҢ еңЁзІҫзҘһеӯҰ科йҮҢе‘је”ӨвҖңдёӯдё–зәӘвҖқ并没жңүжҲҗдёәдәәж–Үдё»д№үжҲҗй•ҝзҡ„зҫҒз»Ҡ пјҢ еҸҚиҖҢеҸҜд»ҘеҖҹеҠ©е®—ж•ҷзҡ„еӨҚе…ҙдёәдәәж–Үдё»д№үжү«жё…йҡңзўҚ пјҢ еңЁж¬§жҙІеҸҚж•ҷжқғжҳҜеҜ№еҸӨе…ёе…ұе’Ңдё»д№үзҡ„еӨҚе…ҙ пјҢ иҖҢеңЁдҝ„еӣҪжҹҗз§ҚзЁӢеәҰдёҠеҚҙиЎЁзҺ°дёәеҸҚдё–дҝ—ж”ҝжқғеҗ‘зҘһеӯҰзҡ„еӨҚеҪ’ гҖӮеңЁиҘҝж–№е®—ж•ҷејӮеҢ–еҲ°йҳ»зўҚдәәжҖ§зҡ„ең°жӯҘ пјҢ еҜјиҮҙдәҶж–°ж•ҷдёҺиҮӘжёёдё»д№үзҡ„е…іиҒ” гҖӮ еңЁдҝ„еӣҪз”ұдәҺж”ҝжқғеҠӣйҮҸзҡ„жҺ§еҲ¶ж— жүҖдёҚеңЁе’ҢеҲҶиЈӮиҝҗеҠЁйҖ жҲҗзҡ„е®ҳж–№е®—ж•ҷзҡ„вҖңеҮқеӣәеҢ–вҖқ пјҢ еӣҪ家ејәиЎҢж”ҜжҢҒе®ҳеҠһе®—ж•ҷзҡ„з»“жһң пјҢ дёҖж–№йқўдҪҝеҫ—дёңжӯЈж•ҷж‘Ҷи„ұдёҚжҺүиҚүж №зҡ„еӨҡзҘһж•ҷ пјҢ дҪҝе®ғе°ҡеӨ„еңЁзӣҙи§үдё»д№үзҡ„ж„ҹжӮҹйҳ¶ж®ө гҖӮ еҸҰдёҖж–№йқў пјҢ з”ұдәҺжү§жӢ—зҡ„еқҡе®ҲжүҖи°“вҖңжӯЈз»ҹеҺҹеҲҷвҖқ пјҢ еҜјиҮҙе®ҳж–№е®—ж•ҷе“ІеӯҰдҪ“зі»зҡ„зӢӯйҡҳдҝқе®Ҳ пјҢ зӯүдәҺиҮӘжҲ‘ж–©ж–ӯдәҶе…·жңүдҝ®жӯЈеҠҹиғҪзҡ„вҖңзә й”ҷжңәеҲ¶вҖқ пјҢ еӣ жӯӨе®ҳж–№е®—ж•ҷеңЁж°‘й—ҙе’Ңиҙөж—ҸзҫӨдҪ“дёӯйғҪдёҚеҸ—вҖңеҫ…и§ҒвҖқ гҖӮ 19дё–зәӘжң«дҝ„еӣҪиҝӣе…ҘеҲ°вҖңеӨ–йғЁеҘҙеҪ№е’ҢеҶ…йғЁи§Јж”ҫвҖқжӢүй”Ҝж—¶жңҹ гҖӮе®үдёңе°јВ·иө«жӢүжіўз»ҙиҢЁйғҪдё»ж•ҷи®Өдёә пјҢ дҝ„зҪ—ж–Ҝж•ҷдјҡеҸ—еӣҪ家жҺ§еҲ¶ пјҢ ж•ҷдјҡиў«еҸ–ж¶ҲдәҶеҗҲжі•зҡ„йҰ–и„‘ пјҢ дәӨз”ұдё–дҝ—й•ҝе®ҳеҘҙеҪ№ пјҢ е®—ж•ҷз®ЎзҗҶеұҖжҳҜе®Ңе…ЁдёҚз¬ҰеҗҲж•ҷ规зҡ„жңәжһ„ пјҢ вҖңжҳҜзҘһеңЈдёңжӯЈж•ҷжүҖжІЎжңүзҡ„ пјҢ жҳҜеүҠејұе’Ңи…җиҡҖдёңжӯЈж•ҷзҡ„жқ°дҪңвҖқ пјҢ жҳҜжҠҠдёңжӯЈж•ҷдјҡдәӨз”ұиҝҷдёӘжңәжһ„еҘҙеҪ№ гҖӮ дёңжӯЈж•ҷдјҡзҡ„дәәйғҪзҹҘйҒ“ пјҢ еңЁдҝ„еӣҪдёҚжҳҜзү§йҰ–еңЁз®ЎзҗҶзқҖж•ҷдјҡ пјҢ иҖҢжҳҜжІҷзҡҮе’ҢеӣҪ家жңәе…іеңЁз®ЎзҗҶж•ҷдјҡ пјҢ жүҖд»ҘеңЁдҝ„еӣҪ пјҢ еғ§дҫЈе°Өе…¶жҳҜдёӢеұӮеғ§дҫЈж”ҝжІ»дёҠзҡ„иў«жҺ’ж–Ҙж„ҹгҖҒж–ҮеҢ–дёҠзҡ„иҫ№зјҳж„ҹе’Ңз»ҸжөҺдёҠзҡ„жҜҸеҶөж„ҲдёӢ пјҢ иҝ«дҪҝ他们е’Ңж”ҝжІ»еҸҚеҜ№жҙҫжҗәжүӢ пјҢ и¶ҠжқҘи¶ҠеӨҡзҡ„еҠ е…ҘзӨҫдјҡдёӢеұӮзҡ„еҸҚжҠ—иЎҢеҲ—дёӯ пјҢ з”ҡиҮіжңүж—¶дјҡжҲҗдёәзӨҫдјҡиҝҗеҠЁзҡ„еҗ‘еҜје’ҢзҗҶи®әеҲӣйҖ иҖ… гҖӮзҘһзҡ„зҺӢеӣҪиҰҒз»ҸиҝҮиҮӘз”ұзҡ„зҺӢеӣҪеҲ°19дё–зәӘжң«е’Ң20дё–зәӘеҲқ пјҢ дҝ„еӣҪзӨҫдјҡзҡ„иҗҢеҠЁе’ҢеӣҪ家жқғеҠӣжһ¶жһ„жқҫеҠЁе№¶еӯҳ пјҢ вҖңйҰ–ж¬Ўиҝӣе…Ҙ欧жҙІеңЁдёӯдё–зәӘж—©е·Із»ҸеҺҶиҝҮзҡ„зІҫзҘһеҸ‘еұ•йҳ¶ж®өвҖқ гҖӮ дәә们жҲ–и®ёдјҡдә§з”ҹз–‘й—® пјҢ еҚідҫҝдҝ„еӣҪзҡ„иҮӘз”ұе®—ж•ҷе’Ңдәәж–Үдё»д№үжңүе…іиҒ” пјҢ йӮЈд№ҹдёҚзӯүдәҺдёҺж”ҝжІ»еҸҚеҜ№жҙҫиғҪжүҜдёҠе…ізі» пјҢ иҝҷдёӨиҖ…д№Ӣй—ҙзҡ„зӣ®ж ҮжЁЎејҸзӣёе·®еҫҲеӨ§е•Ҡпјҹе…¶е®һиҝҷдё»иҰҒеҸ–еҶідәҺ他们зҡ„еЁҒиғҒжқҘиҮӘдәҺдҪ•ж–№ гҖӮ еңЁж•Ңи§Ҷдәәзҡ„зҺҜеўғйҮҢ пјҢ зӨҫдјҡиҮӘз”ұе’Ңе®—ж•ҷиҮӘз”ұдёӨиҖ…йғҪеҸ—еҲ°жү“еҺӢ пјҢ йғҪжҳҜйӣҶе…ЁдҪ“еҲ¶дёӢиў«з®ЎеҲ¶зҡ„еҜ№иұЎ пјҢ 他们д№Ӣй—ҙеҝ…然еӯҳеңЁзқҖзұ»дјјзҡ„вҖңеҸҚдҪңз”ЁеҠӣвҖқ пјҢ жүҖд»ҘеңЁдҝ„зҪ—ж–Ҝеғ§дҫЈйҳ¶еұӮеҸҠе…¶еӯҗејҹеҸӮеҠ еҸҚдҪ“еҲ¶зҡ„жҝҖиҝӣж”ҝжІ»жҙ»еҠЁдёҖзӮ№д№ҹдёҚзҪ•и§Ғ гҖӮиҝҷз§ҚзҠ¶жҖҒеңЁзҪ—马еёқеӣҪж—¶жңҹ пјҢ еңЁдёң欧еү§еҸҳзҡ„ж—¶еҖҷйғҪеӨҡж¬ЎеҮәзҺ°иҝҮ гҖӮ з”ұдәҺдёҠеёқзҡ„дҝЎеҝөиҰҒж—©дәҺе’Ңе№ҝдәҺиҮӘжёёдё»д№үжҲ–зӨҫдјҡдё»д№үзҡ„жҖқжғі пјҢ жүҖд»ҘиҮӘз”ұзҡ„е‘җе–Ҡиө·еҲқйғҪиәІи—ҸеңЁе®—ж•ҷиғҢеҗҺиЎЁиҫҫ гҖӮ ж°‘й—ҙж•ҷдјҡеёёиҜҙ пјҢ еңЁжҠҠдәәдёҚеҪ“дәәзҡ„ж—¶еҖҷ пјҢ еңЁдәә们иӢҰй—·е’ҢеӯӨзӢ¬зҡ„ж—¶еҖҷвҖңеҹәзқЈе°ұеҝ«еӣһжқҘдәҶвҖқ гҖӮ иҮӘжёёдё»д№үиҖ…еҲҷз§° пјҢ йҖҡеҗ‘зҘһзҡ„зҺӢеӣҪйҰ–е…ҲиҰҒйҖҡеҗ‘иҮӘз”ұзҡ„зҺӢеӣҪ гҖӮ з”ұдәҺдҝ„еӣҪзҡ„е®—ж•ҷеҠӣйҮҸе’ҢиҘҝ欧宗ж•ҷеҠӣйҮҸжү®жј”зҡ„ж”ҝжІ»и§’иүІдёҚеҗҢ пјҢ еӣ жӯӨе®ғ们еҪўжҲҗеҸҚе·®д№ҹе°ұдёҚйҡҫзҗҶи§ЈдәҶ гҖӮеҸҜд»ҘиҜҙ пјҢ дә§з”ҹиҮӘз”ұзҡ„йңҖиҰҒдёҺдә§з”ҹе®—ж•ҷзҡ„йңҖиҰҒеңЁиҝҷдёӘйҳ¶ж®ө并дёҚзҹӣзӣҫ пјҢ дёӨиҖ…й—ҙзҡ„вҖңж— еҪўиҒ”зӣҹвҖқж—ўжңүеҸҢж–№дҫқеӯҳзҡ„йңҖиҰҒ пјҢ д№ҹдҪ“зҺ°дәҶиҮӘжёёдё»д№үе°ҡеӨ„еңЁдёҚжҲҗзҶҹзҡ„йҳ¶ж®ө гҖӮ жҲ‘们еҸҜд»ҘзңӢеҲ° пјҢ еңЁ19дё–зәӘдёӢеҚҠеҸ¶ пјҢ дҝ„еӣҪеҗҜи’ҷиҝҗеҠЁзҡ„еҲқжңҹдёҚзјәд№Ҹе®—ж•ҷд№ҢжүҳйӮҰзҡ„иҝҪжұӮ пјҢ е®—ж•ҷеҸҚеҜ№жҙҫдёҺж”ҝжІ»еҸҚеҜ№жҙҫжңүж—¶еҫҲйҡҫеҢәеҲҶ пјҢ з”ҡиҮіеҮәзҺ°вҖңеҹәзқЈж•ҷж— зҘһи®әиҖ…вҖқгҖҒвҖңдёӘдәәдё»д№үеҹәзқЈж•ҷи®әиҖ…вҖқе’ҢвҖңдё–дҝ—зҘһеӯҰ家вҖқзӯүеҘҮжҖӘзҡ„并еҲ— гҖӮ ж— еҠ©зҡ„дәә们е–ңж¬ўз”ЁвҖңдёҠеёқвҖқиҝҷз§Қи¶…и¶Ҡзҡ„дҝЎеҝөеҺ»еҗҰе®ҡз –еҲ¶ж”ҝдҪ“ пјҢ дјјд№ҺдәәдёҺдёҠеёқеҗҲдҪңдҫҝе…·жңүи¶…иғҪеҠӣ пјҢ иҮіе°‘дәә们е°ҶеҶ…еҝғж·ұеӨ„зҡ„жёҙжңӣе’ҢеӨ–йғЁдё–з•ҢиҒ”зі»еңЁдёҖиө·зҡ„ж—¶еҖҷ пјҢ жңүвҖңзҘһеҠ©вҖқдҫҝжңүдёҖз§ҚзҘһеңЈзҡ„и¶…и¶ҠдҝЎеҝөеңЁеҝғдёӯ гҖӮиҖҢе®—ж•ҷжү®жј”иҖ…жҢ‘жҲҳж”ҝжІ»дҪ“зі»зҡ„ж–—дәүжӣҙжҳҜз”ұжқҘе·Ід№… пјҢ е®—ж•ҷжҸҗдҫӣдәҶж”ҝжқғжүҖдёҚиғҪз»ҷдёҺзҡ„еҸҰзұ»йҖүжӢ© пјҢ е®ғиҮіе°‘еҸҜд»ҘжҲҗдёәиЎЁиҫҫдёҚж»Ўзҡ„ең°ж–№ пјҢ вҖңиҰҒжұӮе®—ж•ҷиҮӘз”ұвҖ”вҖ”е°ұжҲҗдёәдәүеҸ–ж°‘з…®иҮӘз”ұзҡ„еҲ©еҷЁвҖқ пјҢ еҸҜд»ҘжҲҗдёәж‘Ҷи„ұеӣҪ家жҺ§еҲ¶зҡ„дёҖдёӘеҝ…з»ҸйҖ”еҫ„ гҖӮ еңЁеӣҪ家дёҺзӨҫдјҡд№Ӣй—ҙиҫғйҮҸзҡ„иҝҮзЁӢдёӯ пјҢ еҖҹеҠ©дәҺд»Җд№ҲеӨ–еңЁзҡ„еҪўејҸ并没жңүдёҖе®ҡд№Ӣ规 гҖӮе®—ж•ҷеӨҚе…ҙдёәзӨҫдјҡиҝҗеҠЁеҠ©еҠӣ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ҚҒж–№жёёжҲҸ|жҲ‘зҡ„дё–з•ҢпјҡжқҘжҲ‘зҡ„е®қз®ұеұӢжүҫе®қи—Ҹеҗ§пјҒеӨ§дҪ¬зҡ„еҲӣж„Ҹеұ…дҪҸжүҖпјҢдёҚеҗғзҒ°дёҚиЎҢ
- иҝҷдёӨдёӘеҘідәәеұ…然жҲҗеҘҪеҸӢдәҶпјҹ
- е…Ёж°‘еҢ»дҝқдјҡжқҘеҗ—пјҹ
- дёӯеӣҪзҡ„зЁҺ收全世з•ҢжңҖдҪҺпјҢеҗ¬иҝҮиҝҷз§ҚиҜҙжі•еҗ—пјҹ
- зү№жң—жҷ®дёҮдёҖиҝһд»»пјҢиҝҷдёӘдё–з•ҢдјҡжҖҺж ·пјҹ
- зҪ—зҙ пјҡиҝҷдёӘдё–з•Ңзҡ„й—®йўҳеңЁдәҺиҒӘжҳҺдәәе……ж»Ўз–‘жғ‘
- ж—Ҙжң¬GDPзҺ°еңЁеҚ дё–з•ҢеӨҡе°‘пјҹ
- жүҝи®ӨдәӢе®һ
- зҷҪйҫҷзңӢдё–з•Ң|иҙ§иҪҰйҖҒиҙ§йҖ”дёӯиў«жӢҰдёӢжЈҖжөӢе°ҫж°”пјҢз»“жһңж°ҙз®ұиў«жү“жҠҘеәҹпјҢиҪҰдё»пјҡжІЎдәәз®ЎжҲ‘
- еҚ°еәҰеҶ з—…з–«жғ…еҚҮеҠҝеҮҢеҺүпјҢдё–з•Ңз–«жғ…е–„еҗҺзңӢеҚ°еәҰ


![[зҷҪеҝ—еі°]зқЎи§үе§ҝеҠҝжңүеӨ§еӯҰй—®](/renwen/images/defaultpic.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