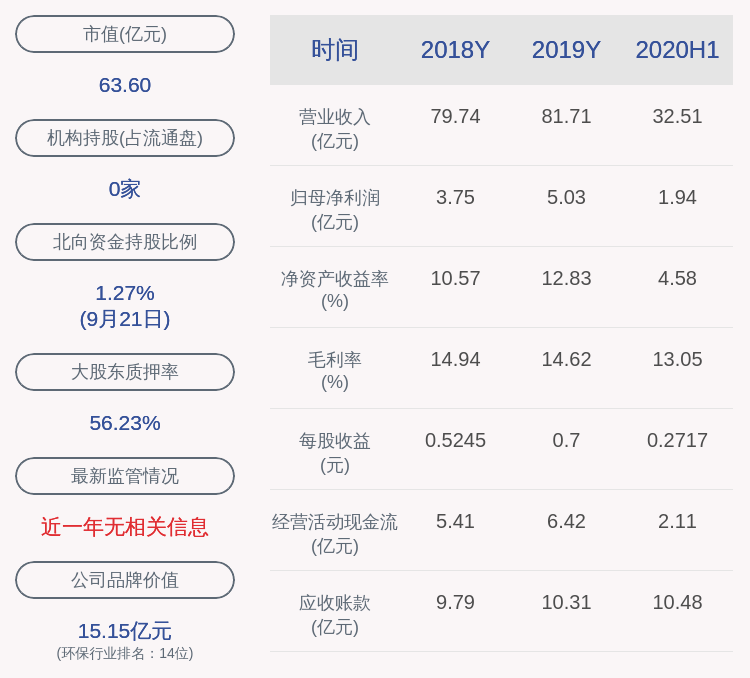з–«жғ…дёӢвҖңзҙ§ж—ҘеӯҗвҖқйӣӘдёҠеҠ йңңпјҢжү“е·ҘеӯҗејҹеӯҰж Ўеҝ«иҰҒе®ҲдёҚдҪҸзҡ„жңҖеҗҺдёҖз«ҷ( дәҢ )
ж–°еҶ з–«жғ…еҲҡејҖе§Ӣзҡ„ж—¶еҖҷ пјҢ й«ҳеұұд№ҹи§үеҫ—еҫҲеҝ«е°ұдјҡиҝҮеҺ» гҖӮ жҢүеҢ—дә¬еёӮж”ҝеәңзҡ„е®үжҺ’ пјҢ 6жңҲ1ж—Ҙе°ҸеӯҰе…ӯе№ҙзә§еӨҚиҜҫ пјҢ 6жңҲ8ж—Ҙе°ҸеӯҰеӣӣгҖҒдә”е№ҙзә§еӨҚиҜҫ пјҢ 6жңҲ15ж—Ҙе°ҸеӯҰдёҖиҮідёүе№ҙзә§еӨҚиҜҫ гҖӮ еңЁжӯӨд№ӢеүҚ пјҢ й«ҳеұұе·ІејҖе§ӢдёәеӨҚиҜҫеҒҡеҮҶеӨҮ гҖӮ
жҚ®й«ҳеұұд»Ӣз»Қ пјҢ ж•ҷ委дёәдәҶдҝқиҜҒеӯҰз”ҹеӨҚиҜҫеҗҺзҡ„е®үе…Ё пјҢ еҮәеҸ°дәҶвҖң49жқЎвҖқејҖеӯҰиҰҒжұӮ пјҢ жңүдё“й—Ёзҡ„иҒ”з»ңе‘ҳй©»ж ЎеҚҸеҠ©ж•ҙж”№ гҖӮ д»–еёҰзқҖдәҢеҚҒеӨҡеҗҚиҖҒеёҲвҖңеҘӢж–—дәҶеҚҒеҮ еӨ© пјҢ жүҚжҠҠдәӢжғ…еҠһжҲҗвҖқ гҖӮ
ж–Үз« еӣҫзүҮ
йҫҷжө·еӯҰж ЎеңЁз»ҷж•ҷе®Өж¶ҲжҜ’ гҖӮ йҮҮи®ҝеҜ№иұЎдҫӣеӣҫ
вҖңж•ҷ委зҡ„жЈҖжҹҘзү№еҲ«дёҘж ј гҖӮ вҖқиӢҸеҚ иӢұе’ҢиҖҒеёҲ们з»ҷжүҖжңүзҸӯзә§ж¶ҲжҜ’ пјҢ жҠҠжЎҢи…ҝжЎҢжӨ…йғҪж“Ұе№ІеҮҖ пјҢ вҖңеўҷи§’дёҠдёҖзӮ№жӯ»и§’йғҪжІЎжңүвҖқ гҖӮ еҘ№д»¬д№ҹеҒҡдәҶејҖеӯҰеҝғзҗҶиҫ…еҜјгҖҒиҝӣж ЎдҪ“жё©жөӢйҮҸгҖҒе°ҸзҸӯж•ҷеӯҰгҖҒй”ҷеі°дёҠдёӢеӯҰзӯүеҮҶеӨҮ гҖӮ
然иҖҢ пјҢ 6жңҲ10ж—Ҙ пјҢ вҖңиҘҝеҹҺеӨ§зҲ·вҖқеӣ еҸ‘зғ§е°ұиҜҠ пјҢ йҡҸеҗҺзЎ®иҜҠж–°еҶ гҖӮ жӯӨеҗҺдёӨеӨ©еҢ—дә¬иҝһз»ӯйҖҡжҠҘжӮЈиҖ… пјҢ жөҒи°ғз»“жһңеқҮжҢҮеҗ‘ж–°еҸ‘ең°еёӮеңә пјҢ з–«жғ…еӨҚзҮғ гҖӮ
6жңҲ12ж—Ҙ пјҢ еҢ—дә¬еҸ«еҒңдәҶе°ҸеӯҰдёҖиҮідёүе№ҙзә§зҡ„еӨҚиҜҫ гҖӮ 6жңҲ16ж—Ҙжҷҡ пјҢ еҲҡеҲҡдёӢи°ғ10еӨ©зҡ„еҢ—дә¬еә”жҖҘе“Қеә”зә§еҲ«йҮҚеӣһдәҢзә§ пјҢ еҗ„е№ҙзә§жҒўеӨҚдәҶзәҝдёҠж•ҷеӯҰ гҖӮ
дёҚж–ӯдёҠж¶Ёзҡ„зЎ®иҜҠжӮЈиҖ…ж•°еӯ—жҠҠй«ҳеұұе’Ң家й•ҝ们д№ҹйғҪжӢүеӣһдәҶзҺ°е®һ гҖӮ иҝҷдёӘж—¶еҖҷй«ҳеұұејҖе§ӢжӢ…еҝғз§ӢеӯЈеӯҰжңҹзҡ„ејҖеӯҰиҝӣеұ• гҖӮ вҖңеҰӮжһңеҶҚејҖдёҚдәҶеӯҰ пјҢ дёҚжӯўжҲ‘们иҝҷдәӣеӯҰж Ў пјҢ еҢ…жӢ¬й«ҳз«Ҝж°‘еҠһеӯҰж Ўж—Ҙеӯҗд№ҹдёҚеҘҪиҝҮ гҖӮ вҖқ
з–«жғ…дёӢ пјҢ жүӣзқҖиө„йҮ‘еҺӢеҠӣзҡ„иҝҷз§Қзӯүеҫ…и®©еҫҲеӨҡж Ўй•ҝеҝғзҗҶвҖңжІЎи°ұе„ҝвҖқ гҖӮ дёҖеҗҚеңЁиҝ‘жңҹж”ҫејғеҠһеӯҰзҡ„ж Ўй•ҝе‘ҠиҜүй•ҝжңҹе…іжіЁжү“е·ҘеӯҗејҹеӯҰж ЎеҸҠж•ҷеёҲз”ҹеӯҳзҠ¶еҶөзҡ„жӣ№иҖҒеёҲ пјҢ вҖңиҝҷдёӘдёңиҘҝеӨӘзҙҜдәәдәҶ пјҢ еӨӘиҙ№еҠІдәҶ гҖӮ вҖқ
иӢҸеҚ иӢұд№ҹиЎЁзӨә пјҢ еҰӮжһңеҪ“ж—¶иғҪеӨҚиҜҫ пјҢ иө·з ҒиғҪ收дёҖеҚҠеӯҰиҙ№ пјҢ еҺӢеҠӣдјҡе°ҸеҫҲеӨҡ гҖӮ вҖңиҝҷж ·дёҖжқҘ收е…ҘйғҪж–ӯдәҶ пјҢ з§ҹйҮ‘иҰҒдәӨ пјҢ иҖҒеёҲе·Ҙиө„дёҚиғҪдёҚеҸ‘ пјҢ иҝҷдёӨеӨ§ејҖж”Ҝе°ұжІЎжі•еә”д»ҳ гҖӮ вҖқй«ҳеұұеӨҡж¬Ўеҗ‘еҚ—йғҪйҮҮи®ҝдәәе‘ҳејәи°ғ гҖӮ
еңЁйӯҸдҪізҫҪзңӢжқҘ пјҢ дёҚе°‘еӯҰж Ўжң¬е°ұеҸҜиғҪеңЁжңӘжқҘеҮ е№ҙйҖҗжёҗе…іеҒң пјҢ з–«жғ…еҸӘжҳҜеҠ йҖҹдәҶиҝҷдёӘиҝҮзЁӢ гҖӮ вҖңз–«жғ…еҸҜиғҪи®©еӨ§е®¶йҮҚж–°е®Ўи§ҶиҮӘе·ұ пјҢ иҝҳиғҪеқҡжҢҒеӨҡд№…пјҹ вҖқ
жҚ®д»Ӣз»Қ пјҢ еҢ—дә¬е°ҡеӯҳзҡ„дёғе…«еҚҒжүҖжү“е·ҘеӯҗејҹеӯҰж ЎеӨ§еӨҡйғҪжҳҜиҝҮеҺ»дёҖиҪ®иҪ®ж·ҳжұ°дёӯзҡ„вҖңе№ёеӯҳиҖ…вҖқ гҖӮ
еҢ—дә¬жү“е·ҘеӯҗејҹеӯҰж Ўзҡ„е…ҙиЎ°дёҺеҹҺеёӮеҢ–иҝӣзЁӢй«ҳеәҰзӣёе…і гҖӮ 90е№ҙд»ЈеүҚеҗҺ пјҢ й«ҳйҖҹеҸ‘еұ•зҡ„еҢ—дә¬еҗёеј•дәҶе…ЁеӣҪеҗ„ең°зҡ„жү“е·ҘиҖ… гҖӮ йҡҸеҗҺеҚҒе№ҙдёӯдҝ®зӯ‘зҡ„еӣӣзҺҜе’Ңдә”зҺҜи·Ҝ пјҢ йҖҗжёҗжЎҶеҮәиҝҷеә§еҹҺеёӮзҡ„иҫ№з•Ң гҖӮ
жү“е·ҘиҖ…жқҘеҲ°еҢ—дә¬еҗҺ пјҢ еӯ©еӯҗдёҠеӯҰжҲҗдәҶдёҖеӨ§й—®йўҳ гҖӮ й«ҳеұұеӣһеҝҶ пјҢ еҪ“ж—¶еҢ—дә¬е°ҡжңӘеҮәеҸ°е…ҘеӯҰйҷҗеҲ¶ пјҢ еҜ№йқһдә¬зұҚе„ҝз«Ҙ пјҢ е…¬з«ӢеӯҰж Ўжҷ®йҒҚиҰҒ收еҸ–3дёҮе…ғе·ҰеҸізҡ„иөһеҠ©иҙ№ пјҢ еҫҲе°‘жңүдәәиғҪиҙҹжӢ…зҡ„иө· гҖӮ
дёҖдёӘеёёи§Ғзҡ„и§ЈеҶіж–№жЎҲжҳҜ пјҢ еҚҒеҮ еҲ°дәҢеҚҒеҮ еҗҚеҗҢд№ЎеҮ‘еңЁдёҖиө·з§ҹдёӘйҷўеӯҗ пјҢ еҮҶеӨҮеҘҪжЎҢжӨ…жқҝеҮіе’Ңй»‘жқҝ пјҢ иҜ·дёҖеҗҚиҖҒеёҲдё“иҒҢз»ҷеӯ©еӯҗ们дёҠиҜҫ гҖӮ вҖңе°ұеғҸз§ҒеЎҫйӮЈж · гҖӮ вҖқй«ҳеұұеҪўе®№ гҖӮ з”ҹж„ҸжҲҗеҠҹзҡ„еҢ…е·ҘеӨҙ们йҖҗжёҗејҖе§ӢдёҫеҠһгҖҒиөһеҠ©еӯҰж Ў пјҢ жү“е·ҘеӯҗејҹеӯҰж Ўиҝӣе…Ҙеҝ«йҖҹеҸ‘еұ•жңҹ гҖӮ
еӣҪеҠЎйҷўеҸ‘еұ•з ”究дёӯеҝғз ”з©¶е‘ҳиөөж ‘еҮҜ2000е№ҙеҸ‘иЎЁзҡ„дёҖйЎ№и°ғжҹҘжҳҫзӨә пјҢ еҪ“ж—¶еӯҰж Ўе№ҙеқҮеўһй•ҝзҺҮиҫҫеҲ°155% гҖӮ иҮійјҺзӣӣж—¶жңҹ пјҢ дёҚеҗҢз»ҹи®Ўиө„ж–ҷжҳҫзӨә пјҢ еҢ—дә¬зҡ„жү“е·ҘеӯҗејҹеӯҰж Ўж•°йҮҸиҫҫеҲ°350-500жүҖ гҖӮ
вҖңеёӮеңәйҖ»иҫ‘вҖқжҡӮж—¶ж»Ўи¶ідәҶеӯ©еӯҗ们зҡ„еҹәзЎҖж•ҷиӮІйңҖжұӮ пјҢ 2003-2005е№ҙ пјҢ иҝҷдәӣеӯҰж ЎдёҖеәҰиҝҺжқҘвҖңж”ҝзӯ–жҳҘеӨ©вҖқ гҖӮ еҪ“ж—¶ пјҢ еӨҡдёӘеҢәеҺҝзҡ„иҫғеӨ§и§„жЁЎжү“е·ҘеӯҗејҹеӯҰж ЎйғҪжӢҝеҲ°дәҶвҖңеҠһеӯҰи®ёеҸҜиҜҒвҖқ пјҢ е®ҢжҲҗдәҶеҗҲжі•иә«д»Ҫзҡ„иҪ¬еҸҳ гҖӮ жӯӨеҗҺ пјҢ ж”ҝзӯ–з©әй—ҙ收зҙ§ пјҢ иҝӣе…Ҙж•ҙйЎҝжңҹ гҖӮ
й«ҳеұұеӣһеҝҶе»әж Ўз»ҸеҺҶ пјҢ ж—©е№ҙй—ҙеӯҰж ЎжҜҸж¬Ўжҗ¬иҝҒйғҪжҳҜдёәдәҶжҚўжӣҙеӨ§ж ЎиҲҚгҖҒжҸҗй«ҳеҠһеӯҰжқЎд»¶ пјҢ еҗҺжқҘзҡ„жҗ¬иҝҒжӣҙеӨҡжҳҜдјҙйҡҸеҹҺеёӮеҸ‘еұ•йңҖиҰҒ гҖӮ йҡҸзқҖжқ‘еә„зҡ„жӢҶиҝҒ пјҢ еӯҰж Ўд№ҹдёҖи·Ҝеҗ‘еҢ— пјҢ зҰ»еёӮдёӯеҝғи¶ҠжқҘи¶Ҡиҝң гҖӮ 2011е№ҙ пјҢ еӯҰж Ўжҗ¬еҲ°зҺ°еқҖж—¶ пјҢ е‘Ёеӣҙе°ҡжңү10еӨҡжүҖеӯҰж Ў пјҢ зҺ°еңЁд»…еү©2жүҖ гҖӮ
еҗҢдёҖж—¶й—ҙ пјҢ еҢ—дә¬ејҖе§Ӣи°ғж•ҙдәәеҸЈж”ҝзӯ– пјҢ жү“е·ҘиҖ…зҡ„з”ҹжҙ»жҲҗжң¬д№ҹйҡҸз»ҸжөҺеҸ‘еұ•иҖҢеўһеҠ гҖӮ жңүдәәдёҫ家иҝ”д№Ў пјҢ д№ҹжңүдәәйҖҒеӯ©еӯҗеӣһ家вҖңз•ҷе®ҲвҖқ гҖӮ
йӯҸдҪізҫҪз»ҹи®Ў пјҢ д»Һ2014е№ҙејҖе§Ӣ пјҢ жү“е·ҘеӯҗејҹеӯҰж Ўе№іеқҮжҜҸеӯҰжңҹжөҒеӨұ5%~10%зҡ„еӯҰз”ҹ гҖӮ еҲ°2017е№ҙеҗҺ пјҢ еҢ—дә¬иҝӣдёҖжӯҘејәи°ғвҖңйҰ–йғҪеҠҹиғҪвҖқ пјҢ еҠ еӨ§дәәеҸЈз–Ҹи§ЈеҠӣеәҰ пјҢ жү“е·ҘеӯҗејҹеӯҰж Ўзҡ„еёӮеңәз©әй—ҙж—ҘжёҗзӢӯзӘ„пјҡй«ҳеұұеӯҰж Ўзҡ„еӯҰз”ҹж•°д»Һ900дәәеҮҸе°‘еҲ°600дәәеҶҚеҲ°400дәә гҖӮ йҫҷжө·еӯҰж Ўд»Һ2600дәәдёҖи·ҜеҮҸе°‘еҲ°1000еӨҡдәә пјҢ 规模дёҚи¶іеҺҹжқҘдёҖеҚҠ гҖӮ
иҖҢд»Ҡ пјҢ ж–°еҶ з–«жғ…жҲҗдёәеӣ°йҡҫж—¶жңҹзҡ„еҪ“еӨҙдёҖжЈ’ гҖӮ йӯҸдҪізҫҪйў„дј° пјҢ еҸ—ж–°еҶ з–«жғ…еҪұе“Қ пјҢ иҮіе°‘жңү20%-30%жөҒеҠЁе„ҝз«Ҙиҝ”д№Ў гҖӮ йҫҷжө·еӯҰж Ў7жңҲзҡ„еӯҰжңҹжң«иҝҪи®ҝжҳҫзӨә пјҢ иҜҘж ЎжҲ–е°ҶеҶҚжңү200еӨҡеҗҚеӯ©еӯҗиҝ”д№Ў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Ө§иҝһз–«жғ…жң¬еңҹзЎ®иҜҠз—…дҫӢеҸҠж— з—ҮзҠ¶ж„ҹжҹ“иҖ…жё…йӣ¶
- з–«жғ…еҜјиҮҙиӮҜе°јдәҡиҲӘз©әдёҠеҚҠе№ҙдәҸжҚҹй«ҳиҫҫ1.32дәҝзҫҺе…ғ
- з–«жғ…|дёҮдәҝзә§и¶…зә§зӢ¬и§’е…ҪиңӮзӢӮиҙӯ,иөӢиғҪзү№дә§иҝёеҸ‘з”ҹжңә
- жәғз–ЎжҖ§еӨ§иӮ зӮҺ|ж—ҘеӘ’пјҡе®үеҖҚеҚёд»»еүҚе°ҶиҮҙеҠӣз–«жғ…йҳІжҺ§ жӢҹдёҺеҗ„еӣҪйўҶеҜјдәәйҖҡиҜқ
- йәҰиҖғе°”жҠҘе‘Ҡж”ҝжІ»еҢ–ж–°еҶ з–«жғ…зҡ„и°ҺиЁҖдёҺдәӢе®һзңҹзӣё|йәҰиҖғе°”жҠҘе‘Ҡж”ҝжІ»еҢ–ж–°еҶ з–«жғ…зҡ„и°ҺиЁҖдёҺдәӢе®һзңҹзӣё
- йәҰиҖғе°”жҠҘе‘Ҡж”ҝжІ»еҢ–ж–°еҶ з–«жғ…зҡ„и°ҺиЁҖдёҺдәӢе®һзңҹзӣё
- зҺӢжҜ…|и®©вҖңж–°еҶ·жҲҳвҖқиҗҪз©ә вҖңеҗҺз–«жғ…ж—¶д»ЈвҖқдёӯ欧关系еҶҚеҮәеҸ‘
- дё»жү“|ж–°з–Ҷз–«жғ…дёӯй«ҳйЈҺйҷ©ең°еҢәд»ҠеӨ©жё…йӣ¶пјҢеҢ—з–ҶејҖиЎҢйҰ–и¶ҹеӨҚеӯҰдё“еҲ—
- зҫҺеӣҪз–«жғ…|зҫҺеӣҪж–°еҶ иӮәзӮҺжӯ»дәЎдәәж•°и¶…18дёҮпјҢдёӯиҘҝйғЁж•°е·һеҮәзҺ°з–«жғ…еўһй•ҝзӮ№
- д№ҢйІҒжңЁйҪҗеёӮеӨҡең°еҢәз–«жғ…йЈҺйҷ©зӯүзә§дёӢи°ғ з”ҹдә§з”ҹжҙ»з§©еәҸжӯЈжңүеәҸжҒўеӨ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