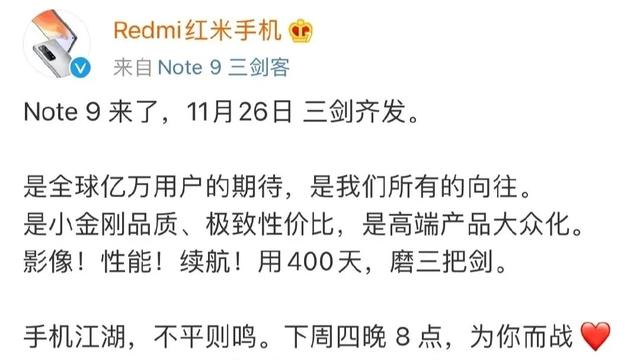иҜ‘иЁҖ|被马尔е…Ӣж–Ҝе’ҢиҺ«иЁҖи§ҶдёәеӨ§еёҲзҡ„д»–пјҢең°дҪҚд»…ж¬ЎдәҺиҺҺеЈ«жҜ”дәҡпјҢеұ…然й«ҳдёӯйғҪжІЎжңүжҜ•дёҡпјҹ( дәҢ )
зІҫеҪ©ж®өиҗҪ
жҲ‘们еҶҚдёҖж¬Ўи§ҒеҲ°зҲұзұідёҪе°Ҹе§җзҡ„ж—¶еҖҷ пјҢ еҘ№е·Із»ҸеҸ‘иғ–дәҶ пјҢ еӨҙеҸ‘д№ҹеҸҳеҫ—зҒ°зҷҪ гҖӮ еңЁжҺҘдёӢжқҘзҡ„еҮ е№ҙйҮҢ пјҢ еҘ№зҡ„еӨҙеҸ‘и¶ҠжқҘи¶ҠзҒ° пјҢ зӣҙеҲ°еҸҳжҲҗдәҶиғЎжӨ’зӣҗзҡ„йӮЈз§Қй“ҒзҒ°иүІ пјҢ йўңиүІе°ұдёҚеҶҚеҸҳдәҶ гҖӮ зӣҙеҲ°еҘ№еңЁдёғеҚҒеӣӣеІҒеҺ»дё–д№Ӣж—Ҙдёәжӯў пјҢ еҘ№зҡ„еӨҙеҸ‘дҫқ然жҳҜйЎҪејәзҡ„й“ҒзҒ°иүІ пјҢ еғҸдёҖдёӘд»Қ然жҙ»и·ғзҡ„з”·дәәзҡ„еӨҙеҸ‘ гҖӮ
д»ҺйӮЈж—¶еҖҷиө· пјҢ еҘ№зҡ„еүҚй—Ёе°ұеҶҚд№ҹжІЎжңүжү“ејҖиҝҮ пјҢ йҷӨдәҶеҘ№еӣӣеҚҒеІҒе·ҰеҸіжңүйӮЈд№Ҳе…ӯдёғе№ҙзҡ„е…үжҷҜ пјҢ еҘ№жү“ејҖй—Ёж•ҷжҺҲйҷ¶з“·еҪ©з»ҳ гҖӮ еңЁжҘјдёӢзҡ„дёҖдёӘжҲҝй—ҙйҮҢ пјҢ еҘ№еёғзҪ®дәҶдёҖдёӘз”»е®Ө пјҢ иҗЁжүҳйҮҢж–ҜдёҠж ЎеҗҢд»Јдәәзҡ„еҘіе„ҝгҖҒеӯҷеҘіе„ҝдјҡиў«йҖҒеҲ°еҘ№йӮЈйҮҢ пјҢ йЈҺйӣЁдёҚж”№ пјҢ д»ҝдҪӣе‘Ёж—ҘеёҰзқҖ25зҫҺеҲҶеҺ»ж•ҷе ӮеӢҹжҚҗйӮЈж ·иӮғз©Ҷ гҖӮ йӮЈж—¶ пјҢ еҘ№зҡ„зЁҺд»Қ然жҳҜиў«иұҒе…ҚдәҶзҡ„ гҖӮ
еҗҺжқҘ пјҢ ж–°зҡ„дёҖд»ЈжҲҗдёәдәҶе°Ҹй•Үзҡ„дё»еҝғйӘЁ пјҢ йӮЈдәӣеӯҰз”»зҡ„еӯҰз”ҹй•ҝеӨ§жҲҗдәәгҖҒйҖҗжёҗзҰ»ејҖ пјҢ 并没жңүи®©еҘ№д»¬зҡ„еӯ©еӯҗеёҰзқҖйўңж–ҷзӣ’гҖҒжһҜзҮҘзҡ„画笔е’Ңд»ҺеҘіжҖ§жқӮеҝ—дёҠеүӘдёӢзҡ„еӣҫзүҮеҲ°зҲұзұідёҪе°Ҹе§җйӮЈе„ҝеҺ»еӯҰз”»з”» гҖӮ еүҚй—ЁеҶҚдёҖж¬Ўең°е…ідёҠ пјҢ 并且永иҝңең°е…ідёҠ гҖӮ е°Ҹй•Үе®һиЎҢе…Қиҙ№зҡ„йӮ®йҖ’еҲ¶еәҰдәҶ пјҢ е”ҜзӢ¬зҲұзұідёҪе°Ҹе§җжӢ’з»қ让他们жҠҠйҮ‘еұһй—ЁзүҢеҸ·е’ҢйӮ®з®ұй’үеңЁиҮӘе·ұзҡ„жҲҝеұӢдёҠ гҖӮ еҘ№д№ҹжҮ’еҫ—еҗ¬д»–们解йҮҠ гҖӮ
ж—ҘеӨҚдёҖж—Ҙ пјҢ жңҲеӨҚдёҖжңҲ пјҢ е№ҙеӨҚдёҖе№ҙ пјҢ жҲ‘们зңјзңӢзқҖй»‘дәәзҡ„еӨҙеҸ‘еҸҳзҷҪдәҶ пјҢ иғҢд№ҹй©јдәҶ пјҢ иҝҳз…§ж ·жҸҗзқҖиҸңзҜ®еӯҗиҝӣиҝӣеҮәеҮә гҖӮ жҜҸйҖў12жңҲ пјҢ жҲ‘们з»ҷеҘ№еҜ„еҺ»дёҖеј зЁҺеҠЎйҖҡзҹҘеҚ• пјҢ дҪҶдёҖдёӘжҳҹжңҹеҗҺеҸҲиў«йӮ®еұҖйҖҖиҝҳ пјҢ ж— дәәи®ӨйўҶ гҖӮ жҲ‘们еҒ¶е°”иҝҳиғҪеңЁжҘјдёӢзҡ„дёҖдёӘзӘ—жҲ·ж—Ғиҫ№и§ҒеҲ°еҘ№зҡ„иә«еҪұвҖ”вҖ”еҫҲжҳҫ然еҘ№жҠҠжҘјдёҠе°ҒдәҶиө·жқҘ гҖӮ еҘ№еқҗеңЁйӮЈе„ҝ пјҢ д»ҝдҪӣзҘһйҫӣдёӯзҡ„дёҖеүҜйӣ•еЎ‘ пјҢ жҳҜдёҚжҳҜеңЁзңӢзқҖжҲ‘们 пјҢ жҲ‘们д№ҹиҜҙдёҚеҮҶ гҖӮ еҘ№е°ұиҝҷж ·з»ҸеҺҶдәҶдёҖд»ЈеҸҲдёҖд»ЈвҖ”вҖ”й«ҳиҙөжј з„¶гҖҒе®үе®Ғд№–еј пјҢ и®©дәәж— еӨ„й—ӘиәІ гҖӮ
еҘ№е°ұиҝҷж ·дёҺдё–й•ҝиҫһдәҶ гҖӮ еңЁиҝҷе°ҳеҹғж»ЎеёғгҖҒйҳҙеҪұйҒ®зӣ®зҡ„еӨ§еұӢйҮҢз—…еҖ’дәҶ пјҢ иә«иҫ№еҸӘжңүдёҖдёӘи№’и·ҡзҫёејұзҡ„й»‘дәәеңЁдјәеҖҷ гҖӮ жҲ‘们з”ҡиҮідёҚзҹҘйҒ“еҘ№з—…еҖ’дәҶ пјҢ еӣ дёәжҲ‘们еҫҲж—©д»ҘеүҚе°ұдёҚеҶҚд»Һй»‘дәәйӮЈйҮҢжү“еҗ¬еҘ№зҡ„ж¶ҲжҒҜ гҖӮ д»–д»ҺдёҚе’Ңд»»дҪ•дәәиҜҙиҜқ пјҢ жҒҗжҖ•еҜ№еҘ№д№ҹжҳҜеҰӮжӯӨ гҖӮ д»–зҡ„е—“еӯҗд№ҹеӣ дёәй•ҝжңҹдёҚеҗӯдёҖеЈ°иҖҢеҳ¶е“‘й”ҲиҡҖдәҶ гҖӮ
еҘ№жӯ»еңЁжҘјдёӢзҡ„дёҖдёӘжҲҝй—ҙйҮҢ пјҢ еңЁдёҖеј жҢӮзқҖеәҠеёҸзҡ„з¬ЁйҮҚзҡ„иғЎжЎғжңЁеәҠдёҠ пјҢ еҘ№ж»ЎжҳҜ银зҒ°иүІеӨҙеҸ‘зҡ„еӨҙжһ•зқҖдёҖдёӘйңүеҫ—еҸ‘й»„зҡ„жһ•еӨҙ пјҢ йӮЈж—¶еӣ дёәз»Ҹе№ҙзҙҜжңҲзҡ„з”ЁзқҖ пјҢ еҚҙеҸҲжҷ’дёҚзқҖдёҖдёқйҳіе…ү гҖӮ
й»‘дәәеңЁеүҚй—ЁжҺҘеҫ…дәҶжңҖе…ҲжқҘеҲ°зҡ„йӮЈжү№еҰҮеҘі пјҢ жҠҠеҘ№д»¬йўҶиҝӣдәҶеұӢ гҖӮ еҰҮеҘід»¬жӮ„еЈ°з»ҶиҜӯ пјҢ еҘҪеҘҮзҡ„зӣ®е…үеҝ«йҖҹжү“йҮҸзқҖеұӢеӯҗ гҖӮ й»‘дәәйҡҸеҚіж¶ҲеӨұдәҶ гҖӮ д»–з©ҝиҝҮеұӢеӯҗ пјҢ иө°еҮәеҗҺй—Ё пјҢ д»ҺжӯӨдёҚи§ҒдәҶиёӘеҪұ гҖӮ
дёӨдҪҚе Ӯе§җеҰ№д№ҹеҗҢж—¶иө¶жқҘдәҶ гҖӮ 葬зӨјеңЁз¬¬дәҢеӨ©дёҫиЎҢ пјҢ е…Ёй•Үзҡ„дәәйғҪиө¶жқҘзңӢзҲұзұідёҪе°Ҹе§җйӮЈиҰҶзӣ–еңЁйІңиҠұеә•дёӢзҡ„йҒ—дҪ“ гҖӮ жЈәжқҗдёҠж–№жҢӮзқҖзҲұзұідёҪе°Ҹе§җзҲ¶дәІзҡ„зӮӯ笔画еғҸ пјҢ д»–зңӢдёҠеҺ»дёҖи„ёж·ұжҖқпјӣеҰҮеҘід»¬еңЁеҸҪеҸҪе–іе–іең°и®Ёи®әзқҖжӯ»дәЎзҡ„жҒҗжҖ–пјӣйӮЈдәӣе№ҙй•ҝзҡ„з”·дәәе‘ўвҖ”вҖ”жңүдёҖдәӣз©ҝдёҠдәҶеҲ·еҫ—е№ІеҮҖ笔зӣҙзҡ„еҚ—ж–№еҗҢзӣҹеҶӣеҲ¶жңҚвҖ”вҖ”з«ҷеңЁй•ҝе»ҠжҲ–иҚүең°дёҠ пјҢ и°Ҳи®әзқҖзҲұзұідёҪе°Ҹе§җ пјҢ еҘҪеғҸеҘ№жҳҜ他们зҡ„еҗҢд»Јдәә пјҢ иҝҳи®Өе®ҡиҮӘе·ұжӣҫз»Ҹи·ҹеҘ№и·іиҝҮиҲһжҲ–иҖ…иҝҪжұӮиҝҮеҘ№пјӣе°ұеғҸжүҖжңүиҖҒдәә家дёҖж · пјҢ 他们已з»Ҹи®°дёҚжё…ж—¶й—ҙе…ҲеҗҺйЎәеәҸдәҶпјӣеҜ№дәҺ他们жқҘиҜҙ пјҢ иҝҮеҺ»е№¶йқһдёҖжқЎи¶Ҡиө°и¶ҠзӘ„зҡ„и·Ҝ пјҢ иҖҢжҳҜдёҖзүҮжІЎжңүеҶ¬еӯЈзҡ„иҚүең° пјҢ еҸӘжҳҜжңҖиҝ‘зҡ„еҚҒе№ҙеғҸзӘ„е°Ҹзҡ„瓶йўҲжҠҠ他们дёҺиҝҮеҺ»йҡ”з»қдәҶ гҖӮ
гҖҗиҜ‘иЁҖ|被马尔е…Ӣж–Ҝе’ҢиҺ«иЁҖи§ҶдёәеӨ§еёҲзҡ„д»–пјҢең°дҪҚд»…ж¬ЎдәҺиҺҺеЈ«жҜ”дәҡпјҢеұ…然й«ҳдёӯйғҪжІЎжңүжҜ•дёҡпјҹгҖ‘жҲ‘们еҫҲд№…д»ҘеүҚе°ұзҹҘйҒ“жҘјдёҠжңүдёҖдёӘжҲҝй—ҙ пјҢ еңЁиҝҷеӣӣеҚҒе№ҙйҮҢи°Ғд№ҹжІЎжңүи§ҒиҝҮ пјҢ иҰҒиҝӣеҺ»е°ұеҫ—ж’¬й—ЁдәҶ гҖӮ зӯүеҲ°зҲұзұідёҪе°Ҹе§җе…Ҙеңҹдёәе®үд»ҘеҗҺ пјҢ 他们жүҚеҺ»жҠҠй—Ёжү“ејҖ гҖӮ
зҢӣең°жү“ејҖй—Ё пјҢ ж•ҙдёӘжҲҝй—ҙиў«йңҮеҫ—зҒ°е°ҳејҘжј« гҖӮ иҝҷй—ҙеёғзҪ®еҫ—еғҸж–°жҲҝдёҖж ·зҡ„жҲҝй—ҙ пјҢ еҚҙеӨ„еӨ„з¬јзҪ©зқҖеқҹеў“иҲ¬ж·Ўж·Ўзҡ„еҮ„жғЁзҡ„йҳҙжЈ®пјҡиӨӘиүІзҡ„зҺ«з‘°иүІзӘ—еёҳ пјҢ зҺ«з‘°иүІзҒҜзҪ© пјҢ жўіеҰҶеҸ° пјҢ дёҖжҺ’зІҫиҮҙзҡ„ж°ҙжҷ¶е·Ҙиүәе“Ғе’Ң银зҷҪиүІиЎ¬еә•зҡ„з”·еЈ«зӣҘжҙ—з”Ёе…· пјҢ дҪҶйӮЈй“¶зҷҪиүІе·ІеӨұеҺ»е…үжіҪ пјҢ еҲ»еңЁдёҠйқўзҡ„еӯ—жҜҚд№ҹйҡҫд»ҘиҫЁи®Ө гҖӮ жқӮзү©д№Ӣй—ҙжңүдёҖжқЎзЎ¬йўҶе’ҢйўҶеёҰ пјҢ д»ҝдҪӣжүҚеҲҡд»Һиә«дёҠеҸ–дёӢжқҘ пјҢ жӢҝиө·жқҘд№ӢеҗҺ пјҢ еңЁй“әж»Ўе°ҳеҹғзҡ„еҸ°йқўдёҠз•ҷдёӢжө…жө…зҡ„жңҲзүҷеҚ°еӯҗ гҖӮ жӨ…еӯҗдёҠж”ҫзқҖдёҖеҘ—иҘҝиЈ… пјҢ еҸ еҫ—дёҖдёқдёҚиӢҹпјӣиЎЈжңҚдёӢйқўжҳҜдёӨеҸӘеҜӮеҜһж— еЈ°зҡ„йһӢеӯҗе’ҢдёҖеҸҢдёўејғдәҶзҡ„иўңеӯҗ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11-20дёҮ|13дёҮеӨҡе…ғзҰҸзү№зҰҸе…Ӣж–ҜпјҢжҳ”ж—Ҙй«ҳдәәж°”дёӨеҺўиҪҰпјҢвҖңеҚҮзә§вҖқеҗҺдёәе•ҘдёҚйҰҷдәҶ
- еӯҳзҹҘе·ұеҜ„еӯҳдёЁиЎҢжқҺеҜ„еӯҳе№іеҸ°|й•°д»“гҖҒ马尔代еӨ«гҖҒз‘һеЈ«вҖҰвҖҰд»Ҡе№ҙиҝҷдәӣең°ж–№дёҖдёӘд№ҹеҺ»дёҚдәҶпјҢдёӯеӣҪзүҲе№іжӣҝжқҘе•ҰпјҒ
- иҙәиҙә-иҙәе°Ҹе”Ҹ|е®һжӢҚе№ҝдёңжңҖзҫҺжө·ж»©д№ӢдёҖпјҢйЈҺжҷҜеҸҜеӘІзҫҺ马尔代еӨ«е’Ңе·ҙеҺҳеІӣпјҢж¶Ҳиҙ№и¶…дҪҺпјҒ
- зҲұж—…жёёзҡ„е“Ҷе•Ұ|еӨ§иҘҝеҢ—зӘҒ然жөҒеҮәдёҖжү№з…§зүҮпјҒж№–ж°ҙжё…жҫҲеҸ«жқҝ马尔代еӨ«пјҢжғҠиүідәҶж•ҙдёӘдёӯеӣҪ
- еӨ©дёӢйүҙеҸІ|дёӯеӣҪдҝ®е»әвҖң马尔代еӨ«вҖқпјҢжҠҪе№І58000дәҝеҗЁжө·ж°ҙпјҢеј•иҒ”еҗҲеӣҪиөһеҸ№010203з»“иҜӯ
- жҲ‘зҡ„ж—…иЎҢж—Ҙи®°|дёӯеӣҪзүҲзҡ„вҖң马尔代еӨ«вҖқпјҢж·ұеҸ—еӨ–ең°жёёе®ўзҡ„иҝҪжҚ§пјҢжң¬ең°дәәеҚҙиЎЁзӨәдёҚеҘҪзҺ©
- |дёӯеӣҪзҡ„马尔代еӨ«пјҢж°ҙиҙЁе№ІеҮҖжё…жҫҲпјҢз®ҖзӣҙжҳҜжҪңж°ҙеӨ©е Ӯ
- иҘҝжІҷзҫӨеІӣ|еӣҪеҶ…е”ҜдёҖд»…еҜ№еӣҪдәәејҖж”ҫзҡ„жө·еІӣпјҢжҷҜиүІдёҚиҫ“马尔代еӨ«пјҢеҺҹеӣ з«ҹдј—жүҖе‘ЁзҹҘ
- Autoе®һйӘҢе®Ө|зҰҸе…Ӣж–Ҝ8.4дёҮжӢҝдёӢпјҢ1.5TпјӢ8ATпјҢй«ҳйҖҹ200з ҒдёҚйЈҳ
- иҪҰе°ҡеҪұ|зҰҸе…Ӣж–ҜеҖјеҫ—е…ҘжүӢеҗ—пјҹе®ғжңүе“Әдәӣй—Әе…үзӮ№пјҹиҝҷзҜҮж–Үз« з»ҷдҪ и§Јзӯ”з–‘ж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