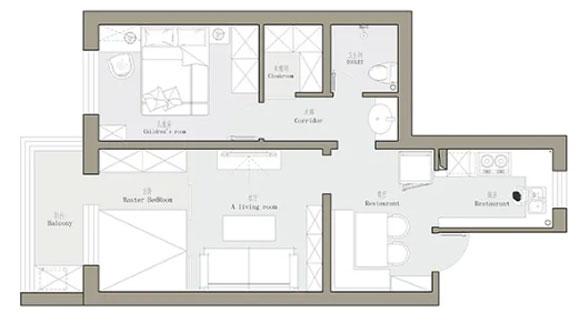纸质书数字化时代,我们如何解读纸质书的价值( 三 )
值得一提的是 , 文字的载体在书籍印刷史上同样存在选择——尽管它们并不如封面、插画那般常见 。 15世纪印刷术发明之时 , 纸张早已是手抄书最普遍的载体 , 自然也成为大规模印刷的首选 。 然而 , 早期出版商在生产纸质书的同时还会付印一批更高质量的牛皮版本 , 为买家提供一种更加奢侈的选择 。 到了16世纪 , 使用这样奢侈的材料印刷已不太常见 。 19世纪之后 , 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一本用牛皮装订而成的书籍 。
大卫·皮尔森在《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中谈到的这些文本以外的书籍元素 , 仿佛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 那么 , 回归到书籍的根本——“文字”本身 , 一本纸质书是否还拥有电子版本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相比数字时代“编辑”“保存”的干净利落 , 纸质媒介的勘误要复杂得多 。 一篇文稿从编辑到付印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 任何差错以及随之而来的修正 , 都可能带来同一版本书籍的个体多样性 。 譬如 , 在一批同时出版的书中 , 可能有几本没有插入勘误的页面;有几本中的错误没有修正;有几本的错误页没被取出;还有几本的勘误页和原页被装订到一起……从这些与文字勘误有关的错误中 , 我们或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改变 , 或可以窥见时局的风向转变 。
1775年 ,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西部岛屿之旅》第一次付印时 , 有一段批评利奇菲尔德大教堂的教长和全体教士的文字 , 指责他们试图出售大教堂屋顶上的铅块 。 出于某些原因 , 这段言论很快被修改 , 取而代之的是一段口气温和的文字 。 1932年 , 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斯坦布尔列车》在预发行时引起另一位英国作家普莱斯列的注意 , 格林借书中某个角色讽刺后者 , 普莱斯列威胁要提起诉讼 。 最终格林不得不做了修改 , 由出版社重新印刷发行 。 诸如此类的勘正 , 正是由于纸质书作为实体的特性 , 得以被今人所知 。
许多世纪以来 , 书籍都是独一无二的手工制品 。 直至19和20世纪 , 机械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同一版本的书与书之间几乎没有区别 。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这些走出印刷厂的书籍会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 。 不同的读者或收藏家会在书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 从那些标记、批注或藏书票中 , 我们可以分析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私密关系 , 也可以了解一本书可能产生的时代影响 。
《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与“拥有者的印记”相关的案例——
英国都铎王朝早期的伦敦史家罗伯特·法比安在他所藏的《纽伦堡编年史》中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和有关当时政府官员的记录 , 堪称他有关伦敦历史的个人百科全书;19世纪早期剑桥大学的学生沃尔特·特里维廉的一本笔记 , 向后人展示了当时的化学课是如何教授、如何学习的;17世纪早期的荷兰律师彼得·范·维恩将一本蒙田的《随笔集》送给儿子做礼物 , 并在书后写了整整一篇个人回忆录……
如果一本书曾经被某位名人收藏过 , 那么它极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窥探这些人心智及思维发展过程的窗口:我们之所以了解英国作家威廉·布莱克对画家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评价 , 是因为布莱克在雷诺兹文集的标题页上留下这样的题字:“这个人是被雇来压制艺术的 。 ”亨利八世的藏书有不少被大英图书馆收藏 , 它们的价值不仅在于曾被亨利八世拿在手上 , 更因为他在一些与政治或道德有关的段落上做过的标记和评论 , 让人们得以捕捉他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和态度 。
最后 , 也是最让人惊叹的 , 是历史上纸质书不可或缺的装帧过程给后人留下的意想不到的遗产 。
数百年来 , 书籍装帧作为一门手工工艺一直延续到19世纪 。 在这一过程中 , 可用于装帧的纸张、纸板和羊皮纸不仅数量有限 , 而且价格昂贵 。 于是回收再利用就成为装帧师的工作常态 , 用过的校样、印坏的书页、多余的纸张 , 都可以成为装订新一代书籍的材料 。 它们有的被用作新书的扉页或是外层包装 , 有的被用作书脊的衬里 , 有的被粘压在一起制成封面和封底……在这些“废纸”中 , 书目学侦探们收获了许多令人兴奋的发现——
推荐阅读
- 返校湖北省初高三学生返校 2000多所学校用钉钉数字化复学
- 桑榆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珠海路街道离退休干部唱响时代“战歌”
- 记东风有限“倍受信赖”企业文化2.0 的源与远
- 个人信息微信辟谣监听用户聊天记录,数字时代如何保护个人信息?
- 电池针刺试验告一段落,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分出胜负了吗?
- 中小企业多方合力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 多方合力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 阿里CMO董本洪:后疫情时代的营销新想象
- 施净岚:"生逢伟大时代,我与改革开放共奋进"
- 政法英模|施净岚:"生逢伟大时代,我与改革开放共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