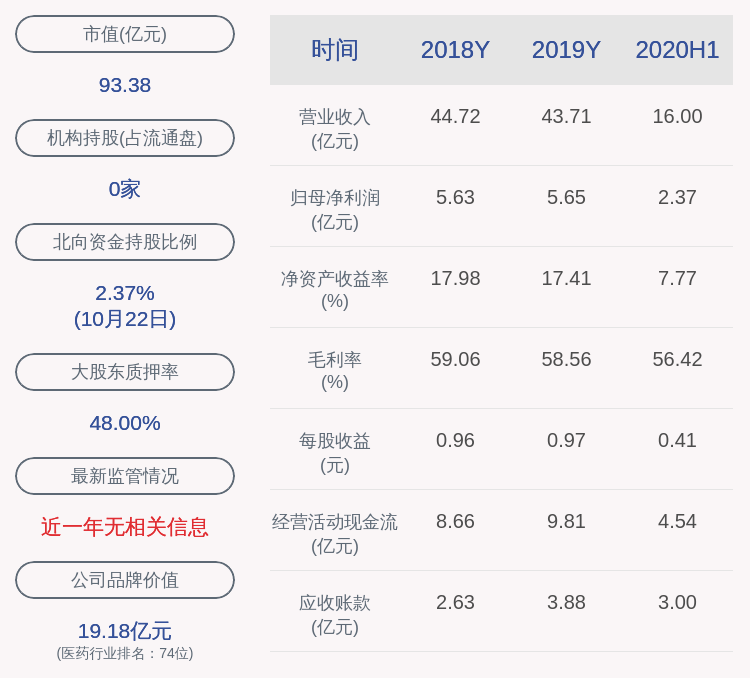「战犯」忏悔与重生:日军战犯笔供背后的故事( 三 )
“我之前一直担忧 , 如果坦白 , 就难免一死 , 于是一直消极抵抗着 。 但花九天时间看完全部控(诉)材料后 , 我怎(么)死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创立了日中友好军人协会的前侵华日军航空兵中将远藤三郎曾率团访问旅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 , 在旅顺 , 他面对昔日的战友藤田茂时 , 两人久坐不言 。 当听到对方斟酌着语句想安慰自己 , 藤田茂站了起来 , 低头忏悔起自己的罪行 。 而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 前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甚至痛哭着讲述自己参与的那些用细菌杀害无辜者的细节 , 以至情绪过于激动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
亲笔写下自己的罪行供述同时 , 战犯们还被安排去听受害者的控诉 。 在抚顺露天矿坑附近的平顶山 , 1932年南满抗日义勇军曾用游击战歼灭过日军一个分队 , 日军随后大举报复 , 将村镇里3000多无辜百姓驱赶到平顶山屠杀 。
唯一的幸存者是年仅7岁的女孩方素荣 , 当她再次面对这些惨案制造者时 , 她已经30岁了 , 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 “鬼子端着刺刀闯进我家 , 父亲跳出窗口 , 没跑几步就被打死了 。 走出家门 , 前前后后都是街坊 , 爷爷领着我和弟弟 , 妈妈抱着我还不会说话的小弟 。 鬼子和汉奸吆喝着说去照相 。 我问爷爷 , 照相是什么?爷爷把一个高粱秆风车塞到我手里 , 说别问了 , 别问了……”
随即开始的屠杀中 , 子弹像割麦子一样杀死她所有亲人 , 日军还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一息尚存者 , 自己的弟弟就在这时被刺刀戳穿了脑袋……
还没有讲完 , 全部战犯便跪倒在地 , 接待室里回荡着战犯们的痛哭声 。
从1950年到1955年 , 在抚顺和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 , 共计1062名战犯全部低头认罪 , 他们每人都亲笔写下了自己的罪行供述 ,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最终的审判 , 多数人认为自己的罪行“不能免死” , 但此时他们都不知道 , 当时的中国政府已作出决定 , 对于认罪的战犯 , 全部免除死刑 。
律师的难题:如何辩护?
沈阳的战犯审判在北陵电影院改建成的法庭中举行 , 这里如今已恢复1956年的原貌 , 建成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旧址陈列馆 。 现在已82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廉希圣想到那场审判仍满怀感慨 , 他当年身着西装在这个法庭上发言 , 作为律师为三名日本战犯辩护 。
“被安排成为战犯律师是1955年下半年 , 那年我23岁 , 刚刚参加工作 , 在大学里讲宪法 。 ”廉希圣回忆 , 当时包括自己在内一共20多人分别担任45名战犯的辩护律师 , 在当年司法部律师司的牵头下 , 在香山卧佛寺大殿东侧的一个小院里开始了集中培训 。
“那个时候 , 战犯笔供的最终定稿已经都到了我们手里了 , 也就是这次中央档案馆公布的这些笔供 。 ”廉希圣说 , 但在他们面前还摆着一个巨大的难题 , 就是如何为这些罪行深重的战犯辩护 。 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沾满数以千计的中国人民的鲜血 , 其中还包括杀害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的部队指挥官 。
当时的司法部律师司司长王汝琪传达了上级指示 , 这些侵华日军战犯本身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 。 从这个思路出发 , 律师们拟写了辩护词 , 廉希圣解释:“他们受的是军国主义教育 , 以武士道精神为天皇效忠;作为军国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 他们个人只是顺从国家意志 。 我们的辩护词其实是更多地把战争罪责归结为一种国家行为 , 而不完全是个人的主观恶意 。 ”
廉希圣代为辩护的三名日本战犯是籐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 , 他1932年出生于天津 , 虽经历过日本占领天津时期 , 但他本人却没有经受过战火 , 不过 , 看到这三名战犯的案卷时 , 廉希圣说自己感情上很纠结:“我为什么要为这些手上沾满鲜血的战犯辩护?”
推荐阅读
- 战犯@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从宽处理令顽石点头
- 『』国军头号战犯回大陆,为何六大开国元帅为其接风,还多次设宴邀请
- 「季奇」名列巴尔干“战犯”,逃亡七年被捕归案,成海牙法庭审判最后一人
- 「麦克阿瑟」如果把侵华天皇按战犯处死,日本会有什么变化
- 『日本』侵华日军大批细菌战战犯未被审批反成美国座上宾
- [意大利]二战后德日都受到审判,为何只有意大利的1200名战犯啥事都没有?
- 纳粹■德国投降后,斯大林要枪毙10万战犯,盟国为何不同意?
- 『特赦』特赦释放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的前前后后
- 『裕仁』NHK披露裕仁天皇悔恨未能阻止南京大屠杀 公开忏悔被首相阻止
- 石原■当不上战犯的石原莞尔:日本愤青眼中的日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