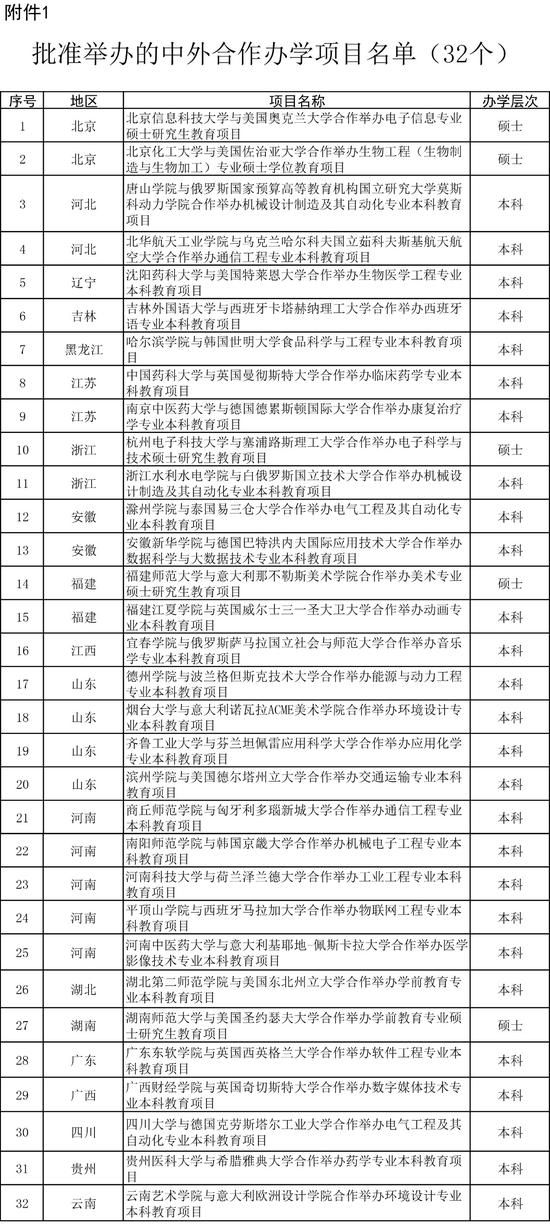那些年东尹村的村民们










那些年东尹村的村民们1975年4月至1978年2月 , 我在河北省栾城县楼底公社东尹村下乡插队当知青 。 在两年零十个月的农村劳动中 , 我和东尹村的村民朝夕相处 , 印象很深 。 四十多年过去了 , 当年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成了六十多岁的老人 。 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 田间劳作 , 挥洒汗水 , 青春年华 , 有喜有忧 。 每当看到网上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 , 就会联想到自己的知青经历 。 去年我写过一篇《难忘东尹村知青生活》的网文 , 表现了知青生活 , 这次写一下东尹村的村民们 , 表达一下对他们的敬意 。(一)大队干部及相关人员东尹村生产大队的大队干部只有五、六个人 , 书记、副书记兼治保主任、大队长、民兵连长、大队会计、大队妇联主任等 。 我下乡期间与大队干部接触不多 , 只能写一点个人感受 。东尹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换比较频繁 , 印象中两年内更换了三任书记 , 都是复员军人 。 大队长经常在广播喇叭里讲生产上的事 , 表扬某个生产队 , 不指名批评个别生产队 。大队有专职管理污水灌溉的管水员 。 石家庄市东郊有一条污水灌溉渠道东明渠 , 每年春季、秋季统一用污水灌溉农田 。 污水是来自市区的生活污水 , 浇地很肥田 。 轮到某个生产队灌溉污水 , 大队管水员会提前通知生产队长 , 生产队安排人连夜准备 。 毕竟污水灌溉省力、省钱、省工 。东尹村大队有一个大队农场 , 负责制种和搞农业试验 。 大队农场有一台12马力小四轮拖拉机 , 配了两个女机手 。 这是个轻松岗位 , 两个女机手闲着没事干时 , 就与一帮男社员扯闲天 。东尹村大队有一个卫生所 , 大队实行合作医疗 , 小病不用花钱 。 我有一次在卸磷肥时 , 被同队一个回乡知青不慎用铁锹铲到眼眶 , 一寸长的口子 , 伤口混进了磷肥 。 到大队卫生所 , 先用针管冲洗伤口 , 再涂碘酒 , 最后用两条胶布将伤口粘到一起 , 在胶布与伤口接触处 , 铰出三角形豁口 。 还好 , 伤口顺利愈合 , 没有留下疤痕 。东尹村大队有一所小学 , 位于村中央位置 。 学校的房屋有些老旧 , 操场旁边有一个较大的平台 , 平台边上有几棵槐树 。 晚上大队在村小学操场召开“评水浒反对投降派 , 促进农业生产大会” , 十二个生产队都要上台发言 。 结果一半以上的生产队上台发言的都是知青 。(二)生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包括书记(又称指导员)、队长、副队长、民兵排长、技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记工员等 。 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一样干活记工分 , 赶上到大队、公社开会办事 , 如果当时生产队有活 , 就照记工分 , 如果当时生产队没活 , 就不记工分 , 纯属尽义务 。 副队长、民兵排长、技术队长、妇女队长都是带领干活的 。 知青第一年有当记工员和出纳的 , 第二年有当民兵排长、妇女队长的 。我在九队 , 队长姓冯 , 四十多岁 , 个子不高 , 性格比较直 , 三年来一直是冯队长当政 。 书记换过 , 妇女队长换过 。 1975年至1976年 , 我在九队当过一年记工员 。冯队长嘱咐过我应当留意几个有混工分习惯的社员 , 对他们必须问细一些 , 时间长记不清了 , 要找一起干活的人证明才能记工分 。 知青没有农村宗族包袱 , 新人比较认真 , 让知青当记工员就是看中的这一点 。但有时遇到一些事记工员也很难处理 。 九队妇女队长带领一批年轻姑娘给棉花打农药 , 因天热和连续操作 , 几人收工后头晕呕吐 , 出现农药中毒迹象 。 于是这几人按工伤处理 , 休息期间全额记工分 。 一周后 , 多数人恢复健康下地干活 , 只有一人仍不出工 。 社员们纷纷议论 , 妇女队长更是有意见 。 我把情况汇报给了冯队长 , 冯队长问是谁议论的 , 谁意见最大 , 我当然不能告诉 。 又过了一周 , 情况照旧 , 大家意见更大 。 我私下找这家的家长和亲戚了解情况 , 一个说 , 现在还头晕 , 一个说 , 情况不清楚 。 这件事最后怎样收场的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 好像是在月底上墙的工分榜单上扣了这个社员的部分工分 , 大家比较满意 , 但这个社员不满意 , 队长、书记也不置可否 , 成了记工员出面得罪人 。 九队的会计和一个联系副业业务的人平时下地干活很少 , 月底却要记满勤 , 对此 , 社员们议论很大 。 作为记工员 , 我只能尽力维护公平 。 我私下对这两人说了大家的反映 , 他们也自知自己报的有水分 , 主动减了几天 , 并且今后自己建一本细账 , 能够说清自己每天干了什么工作 。 这种事情实际在农村相当普遍 , 部分有权的人及其亲属总想占集体一点便宜 , 只要不太过分 , 大家就装不知道 。 凡是提出来公开议论的 , 不是当事人做得太过分就是农村宗族矛盾的反映 , 想靠知青来改变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的 , 但是知青当记工员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这种状况 。九队技术队长的父亲是困难时期从城市回到家乡农村的 , 他会锡焊手艺 , 能自己制作酒壶和煤油灯 。 技术队长的父亲给九队场院做了几个煤油灯芯 , 技术队长找我要给父亲记几个工分 , 我感觉有些过分了 , 焊几个灯芯能用多少时间?我还听说技术队长将队上打农药剩下的铝瓶子都拿出去卖了 , 趁这个机会就说:“你父亲焊灯芯记多少工分我要请示一下队领导 。 听说你把队上打农药剩下的铝瓶子都拿出去卖了 , 是真的吗?”技术队长回答:“那你就问一下吧 , 以前也是给队上焊灯芯给记工分的 。 药瓶子是我们打农药剩下的 , 就应当归我们 , 参加打农药的人人有份 , 以前也是这样 。 ”我汇报给九队书记 , 书记让给技术队长的父亲记半天工 , 卖农药瓶子是惯例 , 队上不说什么 。 我对这件事一直不以为然 。 一次晚上我参加为技术队长家帮忙垫房基地劳动 , 结束后技术队长家按照村里的风俗习惯 , 在家摆了一桌酒席犒赏大家 。 技术队长的父亲亲自向大家敬酒 , 酒至半酣 , 他讲起当年他刚在村里落户的情形 。 孩子多 , 年岁小 , 家里劳力少 , 生活艰难 , 还受人欺负 。 这些年 , 随着孩子长大 , 加上自己的锡焊手艺 , 日子才有了起色 。 他送给当天参加酒席的全体人员每人一把他亲手制作的烫酒壶 。 从老人的讲述中 , 我体会到一家外来户要想在村里立足是多么的不容易 。 有些做法可能要的只是刷存在感 , 并不一定在意那几个工分 , 那一点卖废品的小钱 。九队妇女队长同时也是九队的团小组长 , 干活泼辣 , 嘴不饶人 。 我当时正在积极申请加入团组织 , 和她打交道多一些 。 1975年秋季 , 村里发展了一批团员 , 没有我 , 我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交给团小组长 。 我在汇报里检讨自己斗争精神不强 , “身上缺刺 , 头上缺角 , ”在记工员工作中坚持原则不够 , 表示要继续接受组织的考验 , 争取早日加入组织 。 过了几天 , 我问团小组长 , 是否已将我写的思想汇报交上去了?她说已经交到村团支部了 , 并说交之前她看了一遍 , 认为写得很好 , 让我不要灰心 , 继续努力 , 九队团小组支持我 。(三)与社员的交往下乡的第一年 , 我在一家社员准备结婚的新房住 。 青砖平顶 , 三间两头 , 标准的栾城农村小家院落 。 房主还没有对象 , 年龄到了 , 先盖好房 , 这是那个年代的普遍做法 。 一次房主要出去相亲 , 想借知青的衣服 , 这样显得体面一些 。 我把自己带的衣服让他挑选 , 他选了一件蓝色四个兜的上衣 , 一条军绿色裤子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 , 我搬到另一家姓冯的社员家住 。 他父母双亡 , 一个姐姐过去是村妇女主任 , 嫁到了外村 , 一个哥哥毕业于天津工学院(现在的河北工业大学) , 在外地工作 。 他家有不少哥哥留下的高中课本 , 我发现后如获至宝 , 经常阅读 。后邻是姓苗的一家三口 , 儿子和我年龄相仿 , 父亲身体不好 , 常年在家休养 , 母亲照看家里 , 有时也参加生产队劳动 。 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儿子挣的工分 。 冬天我经常和同队的知青一起到这家喝茶聊天 。 烧水用的是汆子 , 一个形状像杯子的铁皮容器 , 放入炉膛内 , 烧开水很方便 。 我看这家的暖瓶竹子外壳已经腐烂了 , 回市里时就买了一个 , 带回村里 , 换上正好 。 这家人一定要给钱 , 没办法 , 只好接受 。东尹村小学对面住着九队的冯家三兄弟 。 老大是九队的干活能手 , 浇地时 , 老大带领一拨人 , 里面有知青的话 , 总是让知青先回去吃饭 , 晚上十点钟左右 , 就让知青回去睡觉 , 天亮后来一下就行 。 为了防止发生因单相保险丝烧断后未及时发现造成烧电机事故 , 老大将闸刀开关的三相保险丝都用刀划出痕迹 , 用一根马尾一头绑在闸刀手柄上 , 并坠上小半块砖头 , 一头挂在三相保险丝的划痕处 。 一旦有单相保险丝烧断 , 马尾就会在砖头的作用下将闸刀手柄拉下 , 切断电源 。 这种方法是否可靠不得而知 , 但老大的钻研精神和对知青的友好态度都是应当肯定和赞扬的 。 老二是东尹村小学四年级的民办老师 , 教算术 。 学校放假期间 , 老二在九队参加劳动挣工分 。 老三两口子都很精明 , 我和老三一起骑自行车赶过元氏县城的集市 。 和冯家三兄弟在一个大院住的是一位姓苗的大哥 , 他个子很高 , 人很厚道 , 娶的媳妇似乎有点头脑不够使 , 很少下地 , 孩子还小 , 一家人就靠大哥一人挣工分 。九队的场院有一排牲口棚 , 当地称为“头圈” , “头”指牲口 , “圈”指养牲口的地方 。 每天在头圈的炕上都会聚集一批聊天的社员 。 到人少时 , 就会有人提议“燎它一锅子” 。 将喂牲口的黄豆或黑豆放在筛子里 , 下边点上几把麦草火 , 摇动筛子 , 很快就将豆子烤熟了 。 吃豆子时也有讲究 , 要用手将豆子一粒一粒扔向嘴里 , 嘴要同时配合好 , 一接一个准 。 这样做的目的是 , 如果突然有人进来 , 便于掩饰燎豆子的事实 。 如果直接用嘴吃 , 会吃得满嘴黑 , 想掩饰都掩饰不住 。 群众的创造力真是无穷的 , 想占集体一点便宜 , 又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 就只有用这种方法 。 其实队领导对这种做法早就知道 , 只是不去认真管就是了 。九队有几户成分高的社员 。 其中一户的家长是带帽四类分子 , 据说是历史反革命 。 这家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 , 只有老大一人成家 。 老二已经快三十岁了 , 仍然找不到对象 , 平时在队上属于“刺头”一类 , 经常和队干部以及其他社员发生争执 。 老三是女孩 , 据说已经找到婆家 。 老四和我年龄差不多 , 干活和为人处事很好 。 另一户属于地主子女 , 一家人为人低调 , 说话和气 , 家长在队上的菜园种菜 , 大儿子、二儿子已结婚成家 , 三儿子比我大几岁 , 四儿子和我同岁 。 大儿子有瓦匠手艺 , 常年在大队干活 , 二儿子是驾驭牲口的好手 , 队上有播种、驾车活计时 , 总有他的身影 。 第三户人家属于富农子弟 , 家长是干农活的好手 , 经常干驾车、驾耧的活计 。 这家的女孩二十四、五岁 , 尚未出嫁 , 从不多说话 , 干活是把好手 。 这家的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 , 头脑灵活 , 性格开朗 。 他曾在干活时与队上一个刚刚复员的转业军人发生口角 , 被对方揭短:“地富子弟有什么可狂的?”在一起干活的姐姐赶忙拉弟弟躲开 , 弟弟也只好示弱:“说不过了拿这个说事 , 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那些年家庭成分在农村是决定性的大事 , 地富家庭子女往往干活踏实 , 行事低调 , 群众关系良好 , 与队干部的关系也很好 。 这样的家庭在经济上都会过得很好 , 唯一困难的就是男孩很难娶上媳妇 , 不得不降低条件娶相貌不佳或者贫困地区的女子为妻 。九队保管员姓窦 , 快四十岁了还没有成家 , 自己陪着双目失明的老母亲过日子 。 窦保管生得膀阔腰圆 , 力气很大 , 倒库房扛麻袋他是主力 。 我到过他家 , 家里收拾得整齐利索 , 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可以自己摸索着进出房门 。九队有几个常年在大队干活的人 , 都是有技术的能人 。 1977年秋季 , 其中一人回到九队干活 , 队上安排他当秋季场院的场长 , 安排我当副场长 。 队上分菜 , 将六个知青的分在一起 。 我们将不值钱的大路菜上交知青食堂 , 值钱一些的分给知青个人 。 我在窝棚里放了一辆自行车 , 有时晚上骑车回家一趟送菜 , 第二天起大早赶回 , 还能赶上早上干活 。 晚上没事就下象棋 , 我的棋艺一般 , 不是场长的对手 。1978年2月我考上大学后 , 清理知青食堂账目 , 下乡两年零十个月我共欠知青食堂两百多斤玉米 。 我将这件事报告给九队队委会 , 请求队上帮助解决 。 九队领导班子十分重视 , 决定从库存粮食中出这两百多斤玉米 , 以示对知青的支持和关怀 。(四)尾声2018年10月 , 我和东尹村的另一名知青一起回村看了一下 , 找到九队的一位社员 , 他邀请我们到他刚扩建了三层楼的家里看一下 。 东尹村的土地已经被征用了不少 , 村子周边有不少企业 , 全村离彻底拆迁可能已经不远了 。 四十多年前的痕迹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 。 东尹村西北角村委会旁边有一个公交车总站 , 共有三趟从这里始发进市的公交车 。四十年沧桑巨变 , 不变的是对青春岁月的回忆和憧憬 , 对东尹村父老乡亲们的惦念和感恩 。(2019.8.3.至8.4.写于河北廊坊万庄雅园三区)
推荐阅读
- 「数据那些事」深圳市死亡丧葬费抚恤金标准
- 『能英律所蒋花』一不小心成为“老赖”,个人征信那些事你知道么?
- 「长沙周边那些事」湖北到贵州迎来黄金高铁,时速350,途经9站,有没有路过你家?
- 『法律裁判那些事』外甥/侄子,是否能作为侵权责任案件中作为原告提起诉讼?
- [赵一雄]赵一雄,你在机场前的那些举动都被拍下来了!
- 【平安密云】暖心故事!巡逻中蜀黍和店主发生的那些事儿……
- 「晨益阳」“米粉大擂台”引网友热议 那些藏在米粉里的故事都涌来了
- #马桶#那些年常见的装修遗憾,你中了几条?
- 编辑@太难了,那些自私的人无视隔离令,蜂拥到海滩上享受日光浴
- 博闻焦点:那些感动人的爱心救助背后隐藏的不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