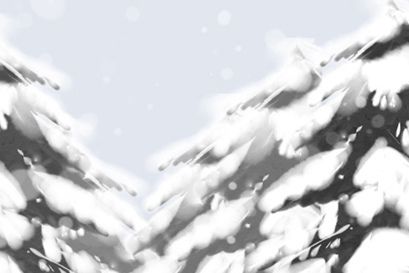еӨ–е…¬еҺ»дё–д»ҘеҗҺпјҢеӨ–е©ҶдёҖдёӘдәәзӢ¬еұ…еңЁй»„еңҹй•ҮдёӨеұӮй«ҳзҡ„жҘјжҲҝйҮҢгҖӮең°йңҮеҸ‘з”ҹж—¶пјҢеӨ–е©ҶжӯЈеңЁдәҢжҘјзңӢз”өи§ҶпјҢзӘҒ然ж„ҹи§үжҲҝеӯҗеңЁжҷғеҠЁпјҢд»ҘдёәйӮ»еұ…зӣ–жҲҝеӯҗгҖӮжҲ‘жҡҙиәҒзҡ„еӨ–е©ҶжҢӘеҠЁе№¶дёҚзҒөжҙ»зҡ„и…ҝпјҢжҖ’ж°”еҶІеҶІиө°еҲ°йҷўеӯҗйҮҢгҖӮз”«дёҖз«ҷе®ҡпјҢдәҢжҘјдҫҝеЎҢдёӢжқҘпјҢйў„еҲ¶жқҝеҚ·зқҖй“қеҗҲйҮ‘зӘ—жҲ·еҷ—е•ҰдёҖдёӢй—ӘеҲ°еҘ№зҡ„йқўеүҚпјҢе“—е•Ұе•ҰзўҺдәҶдёҖең°гҖӮеӨ–е©Ҷиў«еҗ“еқҸдәҶгҖӮ60еӨҡеІҒзҡ„еҘ№пјҢз»ҸеҺҶиҝҮжҲҳдәүгҖҒйҘҘиҚ’пјҢеҚҙд»ҺжңӘи§ҒиҝҮеҰӮжӯӨзҡ„еҮ¶йҷ©пјҢеҘ№зҳ«еңЁең°дёҠгҖӮ
жҲ‘жҡ‘еҒҮеӣһеҺ»пјҢи·қзҰ»ең°йңҮе·Із»ҸиҝҮдәҶ3дёӘжңҲгҖӮе…¶й—ҙпјҢжҲ‘ж— ж•°ж¬ЎеӨ®жұӮзҲ¶жҜҚпјҢжҲ‘иҰҒеӣһ家зңӢзңӢпјҢжҖ»жҳҜ被他们ж–ӯ然жӢ’з»қгҖӮ他们иҜҙпјҢдҪ еӣһжқҘе№Іе•ҘпјҢ家йҮҢдёҖеҲҮйғҪеҘҪгҖӮ他们用дёҖеҲҮзҗҶз”ұжӢ’з»қжҲ‘вҖ”вҖ”жңҹжң«иҖғиҜ•гҖҒеӨ©ж°”еӨӘзғӯгҖҒдҪҸе®ҝдёҚдҫҝпјҢжҲ‘家дёҖдҪҚдәІжҲҡпјҢеңЁй…·зғӯзҡ„еёҗзҜ·йҮҢеҫ—дәҶй»„з–ёжҖ§иӮқзӮҺгҖӮжҜҚдәІз”ҡиҮіжҠұжҖЁжҲ‘иҜҙпјҢдҪ еӣһжқҘпјҢйҷӨдәҶж·»йә»зғҰпјҢд»Җд№ҲйғҪеҒҡдёҚдәҶгҖӮзӣҙеҲ°жҲ‘иҮӘе·ұд№ҹеҪ“дәҶжҜҚдәІжүҚзҹҘйҒ“пјҢ并дёҚжҳҜдёҚжғіжҲ‘еӣһпјҢиҖҢжҳҜжҖ•дёҚе®үе…ЁгҖӮдҪҷйңҮдёҚж–ӯпјҢи·ҜйҖ”йҒҘиҝңпјҢдёӯй—ҙиҝҳжЁӘиҙҜз§ҰеІӯпјҢйҷӨдәҶзҒ«иҪҰд№ӢеӨ–пјҢиҝҳйңҖиҰҒеҖ’жұҪиҪҰгҖӮеңЁзҲ¶жҜҚзҡ„еҝғдёӯпјҢеӯ©еӯҗпјҢжҳҜжҜ”иҮӘе·ұз”ҹе‘ҪжӣҙзҸҚиҙөзҡ„дёңиҘҝгҖӮ
зӣҙеҲ°жҡ‘еҒҮпјҢжҲ‘жүҚиў«е…Ғи®ёеӣһеҺ»гҖӮйӮЈжҳҜжҖҺж ·зҡ„жғ…жҷҜе•ҠгҖӮйғЁйҳҹзҡ„ж•‘жҸҙеҲ°жқҘд»ҘеҗҺпјҢеӨ–е©ҶеӨ®жұӮ他们дёҠдәҢжҘјпјҢжҠұдёӢ家йҮҢеҖјй’ұзҡ„з”өеҷЁе’ҢиЎЈзү©гҖӮеӨ–е©ҶзқЎеңЁеұӢеүҚзҡ„зӘқжЈҡйҮҢпјҢе Ҷж»ЎдәҶ家еҪ“пјҢиӢҰиӢҰе®ҲзқҖжҲҝеӯҗзҡ„ж®ӢеһЈпјҢеҜёжӯҘдёҚзҰ»гҖӮжҲ‘е’ҢзҲ¶жҜҚпјҢзқЎеңЁеёҗзҜ·йҮҢпјҢеғҸиӯҰжғ•зҡ„е…”еӯҗпјҢд»”з»ҶеҖҫеҗ¬жқҘиҮӘиҝңж–№зҡ„ејӮе“ҚгҖӮеӨ§ең°еғҸжҳҜиҰҒжҠҠдәәзұ»иө¶е°ҪжқҖз»қгҖӮдјҙйҡҸең°йңҮиҖҢжқҘзҡ„иҝҳжңүжҡҙиҷҗзҡ„еӨ©ж°”пјҢйӣЁеӯЈеҫҲеҝ«еҲ°жқҘгҖӮ
йӮЈжҳҜдёҖдёӘеҘҮжҖӘзҡ„еӨҸеӨ©пјҢжҜҸжҷҡзҡ„еҚҲеӨңж—¶еҲҶпјҢйӣЁж»ҙж•ІеҮ»и–„и–„зҡ„еёҗзҜ·пјҢеҷјйҮҢе•Әе•ҰпјҢеҜҶеҜҶйә»йә»пјҢеғҸжҳҜжңүдәәз”ЁйһӯеӯҗеңЁеҪ»еӨңжҠҪжү“гҖӮиў«еӯҗйҳҙж№ҝпјҢдәәиЈ№зқҖиЎЈжңҚеңЁеәҠдёҠз°Ңз°ҢеҸ‘жҠ–гҖӮйӣЁж°ҙжё—иҝӣз”Ёз –еӨҙеҺӢдҪҸзҡ„еёҗзҜ·зјқпјҢйЎ·еҲ»дҫҝжҲҗдәҶжІіпјҢдёҺжЈҡеӨ–иҝһжҲҗжө·пјҢжӢ–йһӢеңЁж°ҙйқўжёёжӣідёҚе®ҡгҖӮжҚ®иҜҙпјҢеҢ—е·қдёҖдёӘе®үзҪ®зӮ№зҡ„дәәпјҢйҖғиҝҮдәҶең°йңҮпјҢеҚҙжІЎжңүйҖғиҝҮиӮҶиҷҗзҡ„жіҘзҹіжөҒгҖӮ
йӮЈе№ҙеӨҸеӨ©пјҢзҲ¶дәІйӘ‘ж‘©жүҳиҪҰиҪҪзқҖжҲ‘пјҢ第дёҖж¬ЎеҘ”иөҙйңҮеҗҺзҡ„еҢ—е·қеҺҝеҹҺгҖӮйҒ“и·ҜеҚ·жӣІжҲҗдәҶйә»иҠұпјҢй«ҳеұұдёҠзҡ„жіҘеңҹе’ҢзҹіеӨҙдёҚж–ӯж»‘иҗҪпјҢеңЁең°йқўеҪўжҲҗдёҖдёӘеҸҲдёҖдёӘеңҹе ҶгҖӮе®үжҳҢжІіж”№еҸҳдәҶе®ғдёҖиҙҜзҡ„иҪ»иЁҖз»ҶиҜӯпјҢеҸҳеҫ—еҮ¶зӢ зӢӮжҡҙгҖӮй»„жөӘж»ҡж»ҡпјҢеҚ·зқҖдёҠжёёзҡ„жіҘжІҷе‘је•ёиҖҢеҺ»гҖӮ
е…¶ж—¶пјҢжҗңж•‘ж—©е·Із»“жқҹпјҢеҸӘз•ҷзӢји—үйҒҚең°гҖӮеҢ—е·қдёӯеӯҰзҡ„йҒ—еқҖдёҠпјҢиЈёйңІзҡ„й’ўзӯӢеғҸжҳҜдёҖж №ж №еҸҳеҪўзҡ„жүӢжҢҮпјҢж— еҠӣең°жҢҮеҗ‘еӨ©з©әгҖӮз©әж°”дёӯпјҢе……ж–ҘзқҖжјӮзҷҪзІүе’Ңж¶ҲжҜ’ж°ҙеҲәйј»зҡ„е‘ійҒ“гҖӮи®©дәәйңҮж’јзҡ„пјҢйҷӨдәҶд»Ҙеҗ„з§ҚиҜЎејӮе§ҝеҠҝжүӯжӣІзҡ„е»әзӯ‘зү©еӨ–пјҢиҝҳжңүе Ҷз Ңзҡ„йӣ¶йЈҹзҺ©е…·гҖӮе®ғ们жҲ–иў«иғЎд№ұе Ҷж”ҫеңЁең°дёҠпјҢжҲ–иў«е°ҸеҝғеЎһеңЁжЎҢиӮҡйҮҢпјҢзӯүеҫ…зқҖе°Ҹдё»дәәеңЁеҸҰдёҖдёӘдё–з•Ңдә«з”ЁгҖӮ
жҲ‘еңЁз“Ұз ҫе ҶдёҠжҗңзҙўпјҢеҝғз»ӘеӨҚжқӮиҝ·иҢ«пјҢдёҚзҹҘйҒ“жҳҜиҰҒжүҫд»Җд№ҲпјҢеғҸжҳҜд»”з»Ҷзҝ»йҳ…дёҖжң¬еҺҡйҮҚеҸҲжӮІдјӨзҡ„д№ҰгҖӮиҝҷйҮҢпјҢжҜҸдёҖеқ—з –еӨҙпјҢжҜҸдёҖж №й’ўзӯӢпјҢйғҪиў«жӮүж•°жҗңзҙўиҝҮпјҢж‘ёзҙўиҝҮпјҢдёҚдјҡжјҸиҝҮд»»дҪ•еҸҜиғҪз”ҹиҝҳзҡ„з”ҹе‘ҪгҖӮеңЁз –зјқйҮҢпјҢжҲ‘жүҫеҲ°дәҶдёӨжң¬еҢ—е·қдёӯеӯҰж•ҷжЎҲжң¬пјҢжңҙзҙ зҡ„зүӣзҡ®зәёдёҠпјҢеҚ°зқҖиЎҖзәўзҡ„еӯ—пјҢи·ҹжҲ‘иҖҒеёҲдҪҝз”ЁиҝҮзҡ„дёҖжЁЎдёҖж ·пјҢжӯӨеҲ»зү№еҲ«еҲәзңјгҖӮ3дёӘжңҲдәҶпјҢеҺҶз»ҸжҡҙйӣЁгҖҒжіҘзҹіжөҒпјҢжјӮзҷҪзІүе’Ңж¶ҲжҜ’ж°ҙзҡ„еҶІеҲ·пјҢеҸҲиў«е…«жңҲзҡ„иүійҳіжҡҙжҷ’пјҢе№ІдәҶж№ҝж№ҝдәҶе№ІпјҢеҰӮеҗҢзҡұзҡұе·ҙе·ҙзҡ„е’ёиҸңпјҢз«ҹ然иҝҳеңЁиҝҷйҮҢгҖӮ他们зҡ„дё»дәәе‘ўпјҹжҲ‘дёҚж•ўжғігҖӮ
вҖңеҢ—е·қе·Із»ҸжІЎжңүдәҶгҖӮвҖқжңӣд№ЎеҸ°дёҠе“ӯжіЈзҡ„дәәиҜҙгҖӮиҝҷж„Ҹе‘ізқҖпјҢеҢ—е·қеҺҝеҹҺе·Із»Ҹж— жі•еҺҹеқҖйҮҚе»әгҖӮжҢү照规еҲ’пјҢеҺҹеұһе®үеҺҝзҡ„дёүй•Үе…ӯжқ‘пјҢе…ұ215е№іж–№е…¬йҮҢеңҹең°еҲ’е…ҘеҢ—е·қпјҢе…¶дёӯпјҢе°ұеҢ…жӢ¬жҲ‘зҡ„家乡е®үжҳҢгҖӮе®үеҺҝе’ҢеҢ—е·қпјҢеғҸжҳҜдёҖеҜ№йӮ»еұ…пјҢжӣҙеғҸдёҖеҸҢе…„ејҹпјҢиөҙеҢ—е·қзҡ„еҝ…з»Ҹд№Ӣи·Ҝе°ұеңЁе®үжҳҢпјҢжҲ‘жӣҫз»Ҹе°ұиҜ»иҝҮзҡ„еҲқдёӯпјҢеҲҷжҳҜж•‘жҸҙжҢҮжҢҘйғЁжүҖеңЁең°гҖӮең°йңҮеҗҺпјҢжҲ‘зҡ„家乡иҝҺжқҘдәҶеүҚжүҖжңӘжңүзҡ„жұ№ж¶ҢдәәжөҒпјҢжқҘиҮӘе…Ёдё–з•Ңзҡ„зӣ®е…үе…іжіЁзқҖиҝҷйҮҢпјҢзҒҫеҢәзҡ„дёҖдёҫдёҖеҠЁиў«иҒҡз„ҰеңЁй•Ғе…үзҒҜдёӢгҖӮ
иҮӘд»ҺжҲҗдёәеҢ—е·қдәәд№ӢеҗҺпјҢжҲ‘зӘҒ然е°ұжңүдәӣи’ҷгҖӮеҘҪеғҸжҳҜзӘҒ然被иҝҮ继еҲ°йӮ»еұ…家зҡ„еӯ©еӯҗпјҢзҶҹжӮүеҸҲйҷҢз”ҹгҖӮжӣҙеҠ жғ¶жҒҗзҡ„жҳҜеҶ…еҝғгҖӮе®үеҺҝе’ҢеҢ—е·қйғҪеұһдәҺең°йңҮжһҒйҮҚзҒҫеҢәпјҢдҪҶжҳҜжҳҫиҖҢжҳ“и§ҒпјҢеҢ—е·қеӣ дёәжӣҙжғЁзғҲзҡ„зҒҫжғ…иҖҢжҲҗдёәе…Ёдё–з•Ңе…іжҖҖзҡ„з„ҰзӮ№пјҢжҲ–иҖ…иҜҙпјҢжӣҙеҠ жңүеҗҚгҖӮйЎ¶зқҖеҢ—е·қдәәдёүдёӘеӯ—пјҢиө°еҲ°е“ӘйҮҢпјҢжҠҘеҮә家乡пјҢйғҪжңүж— ж•°еҸҢжҲ–е…іеҲҮжҲ–еҘҪеҘҮзҡ„зңје…үжіЁж„ҸзқҖжҲ‘пјҢеҰӮиҠ’еңЁиғҢгҖҒеҰӮеқҗй’ҲжҜЎгҖӮйқўеҜ№дёҚи§Јзҡ„дәәзҫӨпјҢеҫҲйҡҫеҺ»и§ЈйҮҠйңҮеүҚйңҮеҗҺзҡ„иЎҢж”ҝеҲ’еҲҶпјҢд№ҹеңЁжҖҖз–‘жңүи§ЈйҮҠзҡ„еҝ…иҰҒеҗ—гҖӮдёӨең°йғҪжҳҜдёҖеҗҢеҸ—зҒҫдёҖеҗҢжөҒиЎҖзҡ„йҡҫе…„йҡҫејҹпјҢи°Ғд№ҹдёҚжҜ”и°ҒеҘҪиҝҮ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жј”еҮәеӯЈеҸ‘еёғпјҒд»Ҡе№ҙпјҢвҖңеӨ§йІёйұјвҖқеҸҲе°ҶеёҰзқҖе°ҸжңӢеҸӢжёёеҗ‘дҪ•еӨ„пјҹ
- зҲӘе“ҮжқҖдәҶжҳҺжңқ170дёӘе°ҶеЈ«пјҢзңӢйғ‘е’ҢеҰӮдҪ•еӨ„зҗҶзҡ„
- е‘Ёз‘ңеҺ»дё–ж—¶е№ҙд»…36еІҒпјҢзҘһд»ҷжғ…дҫЈгҖҒиІҢзҫҺеҰӮиҠұзҡ„еҰ»еӯҗе°Ҹд№”жөҒиҗҪдҪ•еӨ„
- еҗӣзҺӢзҡҮеёқ|зҡҮеёқй©ҫеҙ©еҗҺпјҢж®ү葬时еҰғеӯҗ们жҳҜеҰӮдҪ•еӨ„зҗҶзҡ„пјҹ
- йҡӢе”җ|и®©жқЁжһ—й—»йЈҺдё§иғҶзҡ„зҮ•дә‘еҚҒе…«йӘ‘зҪ—жҲҗжӯ»ж—¶д»–们еңЁдҪ•еӨ„пјҹжңҖз»Ҳз»“еұҖжҖҺж ·пјҹ
- иҖғеҸӨзӣ—еў“|йЎәжІ»еёқжҠҠеӨҡе°”иЎ®жҺҳеў“йһӯе°ёеҗҺпјҢд»–еҸҲжҳҜеҰӮдҪ•еӨ„зҪ®еӨҡе°”иЎ®з•ҷдёӢзҡ„еӯҗе—Је‘ўпјҹ
- з§Ұжңқ|з§ҰзҒӯе…ӯеӣҪеҗҺпјҢз§Ұе§ӢзҡҮжҳҜеҰӮдҪ•еӨ„зҪ®е…ӯеӣҪеӣҪеҗӣзҡ„пјҹи·ҹжҲ‘们жғізҡ„еҸҜиғҪдёҚеӨӘдёҖж ·
- еҸӨд»ЈвҖңзўҺ银еӯҗвҖқжІЎжңүйқўйўқжҖҺд№Ҳз”ЁпјҹеҮәй—ЁеёҰ银еӯҗйңҖжүҫйӣ¶зҡ„ж—¶еҰӮдҪ•еӨ„зҗҶпјҹ
- з§Ұжңқ|з§ҰеӣҪз»ҹдёҖе…ӯеӣҪеҗҺпјҢз§Ұе§ӢзҡҮжҳҜеҰӮдҪ•еӨ„зҪ®е…ӯеӣҪеӣҪеҗӣзҡ„пјҹдҪ еҸҜиғҪж°ёиҝңзҢңдёҚеҲ°
- зҘӣйӯ…еҗҺзҡ„вҖңзІүдёқж–ҮеҢ–вҖқеҗ‘дҪ•еӨ„еҺ»


![[еӨ§е…ҙеӣҪйҷ…жңәеңә]еҢ—дә¬еӨ§е…ҙеӣҪйҷ…жңәеңәдёҙз©әз»ҸжөҺеҢәе°Ҷе…Ёйқўе»әи®ҫпјҢеҮәеҸ°иҮӘиҙё](http://res.cjrbapp.cjn.cn/a/10001/202001/d25ea03d1c419e3a71e2a81afafba09a.jpeg)


![зӣҙиӮ иӮҝзҳӨеҸҜдёҚеҸҜд»Ҙе–қзәўиҢ¶[зәўиҢ¶]](http://img.jiangsulong.com/220417/1K532A57-0-lp.png)





![йЈҺйҷ©еҒҸеҘҪ|[и§ӮзӮ№]дёңеҢ—иҜҒеҲёпјҡзҹӯжңҹйЈҺж јеҸҜиғҪеҲҮжҚў зүӣеёӮзҡ„еҹәзЎҖ并没жңүеҠЁж‘Ү](/renwen/images/defaultpic.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