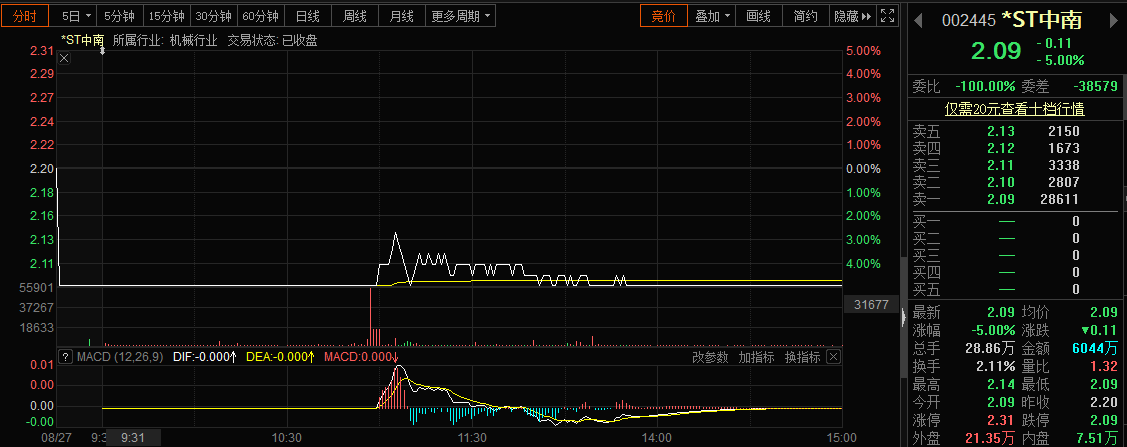еҫҲй•ҝдёҖж®өж—¶й—ҙпјҢжҲ‘йғҪдёҚзҹҘйҒ“家乡еңЁе“ӘйҮҢгҖӮ
еңЁж–°еҮәзүҲзҡ„ең°еӣҫдёҠеҜ»жүҫпјҢжҲ‘жҳҜеҢ—е·қдәәгҖӮд»Һжғ…ж„ҹдёҠи®ІпјҢжҲ‘еҸҲжҳҜе®үеҺҝдәәгҖӮжҲ‘究з«ҹеұһдәҺе“ӘйҮҢпјҹжҲ‘еҺ»жҺўз©¶пјҢеҚҙжӣҙеҠ и§үеҫ—еүІиЈӮпјҢз”Ёйҷ•иҘҝиҜқиҜҙпјҢжңЁд№ұгҖӮ
жҲ‘жҳҜеҢ—е·қдәәгҖӮ
еҢ—пјҢжҳҜеңЁеӣӣе·қеҢ—йғЁпјҢе·қпјҢжҳҜзјҳзқҖдёүжқЎжІіжөҒгҖӮжҲ‘еҜ№еҢ—е·қжҳҜйҷҢз”ҹзҡ„пјҢж„ҹжғ…д№ҹжҳҜеӨҚжқӮзҡ„гҖӮжҖҺж ·иҜҙиө·йӮЈдёӘең°ж–№е‘ўпјҹжҲ‘зҡ„家е°ұеңЁйӮЈйҮҢгҖӮйӮЈеҸӨиҖҒеҸҲеҙӯж–°гҖҒйҒҘиҝңеҸҲиҙҙиҝ‘зҡ„дәәзҫӨпјҢ他们и—ҸеңЁеӣӣе·қзӣҶең°иҫ№зјҳйҡҸж„ҸжӢұиө·зҡ„йҮҚйҮҚеұұеіҰй—ҙпјҢжІҗжөҙеңЁиҫЈжӨ’дёҺиҠұжӨ’зҡ„иҠійҰҷеӣӣжәўдёӯгҖӮзҫҢдәәгҖҒи—ҸдәәпјҢеӨ§зҰ№гҖҒзҫҠзҘһпјҢдҪңдёәе°‘ж•°ж°‘ж—Ҹең°еҢәзҡ„еӨҡж•°ж°‘ж—ҸпјҢжҲ‘并дёҚзҶҹжӮүиҝҷдёҖеҲҮгҖӮд№ӢжүҖд»ҘжҲҗдёәеҢ—е·қдәәпјҢжҳҜеңЁ2008е№ҙең°йңҮд№ӢеҗҺпјҢж–°зҡ„иЎҢж”ҝеҢәеҲ’еҮәжқҘпјҢжҲ‘е°ұеңЁдёҖеӨңд№Ӣй—ҙж”№дәҶ家乡гҖӮ
жҲ‘жҳҜе®үеҺҝдәәгҖӮ
е°Ҹж—¶еҖҷпјҢзҲ¶дәІеңЁе®үеҺҝжЎ‘жһЈй•ҮпјҢжҜҚдәІеңЁе®үеҺҝй»„еңҹй•ҮпјҢжҲ‘еңЁдёӨй•ҮйғҪжңүдёҚй•ҝдёҚзҹӯзҡ„еұ…дҪҸеҸІгҖӮе°ҸеӯҰд»ҘеҗҺпјҢзҲ¶жҜҚжҗәжҲ‘е®ҡеұ…е®үжҳҢй•ҮгҖӮиҝҷйҮҢжҳҜе®үеҺҝзҡ„еҺҝеҹҺжүҖеңЁең°пјҢиҝҒе…Ҙд№ӢеҗҺпјҢжҲ‘зҡ„жҲ·еҸЈжҲҗдәҶеҺҝеҹҺдәәгҖӮеңЁйӮЈдёӘе№ҙд»ЈпјҢиҝҷж ·дёҖдёӘжҲ·еҸЈжң¬пјҢжҳҜдёҖ家е®үиә«з«Ӣе‘Ҫзҡ„ж №жң¬пјҢжҳҜжҲ‘们еңЁиҝҷеә§е°Ҹй•Үзҡ„ж №гҖӮ
2002е№ҙпјҢеҺҝеҹҺиҝҒ移еҲ°дәҶең°еҠҝжӣҙдёәе№іеқҰзҡ„иҠұиҚ„й•ҮгҖӮе®үжҳҢпјҢиҝҷдёӘжңү50еӨҡе№ҙеҹҺе…іеҸІзҡ„еңәй•ҮпјҢж…ўж…ўиў«иҫ№зјҳеҢ–пјҢе№ҙиҪ»дәәйҷҶз»ӯзҰ»ејҖпјҢз•ҷдёӢзҡ„дәәйғҪжңүдәҶдәӣе№ҙзәӘгҖӮе’Ңиҝҷеә§еҹҺдёҖж ·пјҢдёҺдё–ж— дәүпјҢе–қиҢ¶йә»е°ҶпјҢеҰӮе®үжҳҢжІідёҖж ·ж— жүҖдәӢдәӢең°жөҒж·ҢгҖӮ2016е№ҙпјҢе®үеҺҝеҚҮзә§дёәз»өйҳіе®үе·һеҢәпјҢдёҖдёӘжӣҙеҠ йҷҢз”ҹзҡ„еҗҚиҜҚгҖӮ
еӨҡе№ҙеҗҺеӣһеҝҶеҪ“еҲқпјҢдёҚеҫ—дёҚжүҝи®ӨпјҢеҪ“ж—¶дё»еҜјеҺҝеҹҺжҗ¬иҝҒзҡ„зҲ¶жҜҚе®ҳпјҢиҝҳжҳҜиЎЁзҺ°еҮәдәҶдёҖе®ҡзҡ„й«ҳзһ»иҝңзһ©гҖӮеӨ§ең°йңҮдёӯпјҢе®үеҺҝе’ҢеҢ—е·қйғҪжҲҗдёәжһҒйҮҚзҒҫеҢәпјҢиҠұиҚ„еӣ дёәдёҖ马平е·қпјҢе№ёе…ҚдәҺйҡҫгҖӮиҖҢеҢ—е·қзҡ„еҺҝеҹҺпјҢеңЁзҫӨеұұеҢ…еӣҙд№Ӣдёӯиў«еҢ…дәҶйҘәеӯҗвҖ”вҖ”дёӨеә§еӨ§еұұеҪ»еә•еқҚеЎҢпјҢжҠҠеӨ§еҚҠзҡ„еҢ—е·қеҺҝеҹҺж°ёиҝңжҺ©еҹӢеңЁй»‘жҡ—еҪ“дёӯгҖӮ
еӨ§ең°йңҮеҲ°жқҘзҡ„ж—¶еҖҷпјҢжҲ‘еңЁиҘҝе®үиҜ»з ”пјҢйҡ”дәҶеҚғйҮҢзҡ„и·ҜзЁӢпјҢд»Қ然ж„ҹи§үең°еҠЁеұұж‘ҮгҖӮиө·еҲқпјҢжҲ‘并没жңүеңЁж„ҸгҖӮжҲ‘зҡ„й•Үе®ҡе’ҢеҢ—ж–№еҗҢеӯҰзҡ„жғҠж…ҢеӨұжҺӘеҜ№жҜ”йІңжҳҺгҖӮеңЁйҫҷй—Ёеұұж–ӯиЈӮеёҰпјҢең°йңҮеҸёз©әи§ҒжғҜгҖӮдёҠиҜҫйңҮпјҢдёӢиҜҫйңҮпјҢзңӢз”өи§ҶйңҮпјҢеҒҡдҪңдёҡйңҮгҖӮж–ӯиЈӮеёҰзҡ„дәәеҜ№еҫ…ең°йңҮзҡ„жҖҒеәҰпјҢжҳҜжңүеҮ еҲҶиҪ»ж…ўе’ҢжҲҸи°‘зҡ„гҖӮең°йңҮпјҢе°ұеғҸдёҖдёӘзҲұејҖзҺ©з¬‘зҡ„жңӢеҸӢпјҢжІЎдәәдјҡжҠҠе®ғзҡ„еҗ“唬еҪ“зңҹгҖӮ
гҖҗд№Ўе…ідҪ•еӨ„гҖ‘и°ҒдјҡжғіеҲ°пјҢеӨ§иҮӘ然зңҹжӯЈеҸ‘жҖ’зҡ„ж—¶еҖҷпјҢеЁҒеҠӣдјҡеҰӮжӯӨе·ЁеӨ§пјҹ
еҪ“ж—¶жҺҘйҖҡз”өиҜқзҡ„е№ёиҝҗе„ҝпјҢд»Һе…ЁеӣҪеҗ„ең°еҫ—еҲ°дәҶдҝЎжҒҜпјҢжҪ®ж°ҙдёҖиҲ¬ж¶Ңе…ҘжҲ‘зҡ„иҖіжңөпјҢйңҮдёӯеңЁеӣӣе·қпјҢйңҮдёӯеңЁжұ¶е·қвҖҰвҖҰең°йңҮ7.8зә§гҖӮ
жҲ‘ж…ҢдәҶпјҢжүӢжҢҮеӨҙе“Ҷе—ҰзқҖпјҢжү“ејҖжүӢжңәйҖҡи®ҜеҪ•пјҢеҮЎжҳҜз»өйҳізҡ„еҸ·з ҒпјҢдёҖдёӘдёҖдёӘжӢЁжү“гҖӮз«ҹ然没жңүдёҖдёӘжҺҘйҖҡгҖӮ
дәӢеҗҺжҲ‘жүҚзҹҘйҒ“пјҢең°йңҮеҸ‘з”ҹеҗҺпјҢеҹәз«ҷ被摧жҜҒпјҢз”өиҜқдҝЎеҸ·дёӯж–ӯпјҢеӨ–йқўзҡ„з”өиҜқжү“дёҚиҝӣеҺ»пјҢйҮҢйқўзҡ„з”өиҜқжү“дёҚеҮәжқҘгҖӮйңҮеҢәпјҢжҲҗдәҶдёҖеә§еӯӨеІӣгҖӮ
иҝһз»ӯдёҚж–ӯжӢЁдәҶдёҖдёӢеҚҲпјҢзӣҙеҲ°жүӢжҢҮеӨҙеҸ‘йә»пјҢеҚҙдёҖж— жүҖиҺ·гҖӮеҝғи¶ҠжқҘи¶ҠдёӢжІүпјҢжІүеҲ°е№Ҫж·ұзҡ„и°·еә•гҖӮи„‘еӯҗйҮҢпјҢж— ж•°з”»йқўйЈҳиҝҮгҖӮеңЁеҶңжқ‘жҗһе…»ж®–зҡ„зҲ¶жҜҚжҖҺд№ҲеҠһпјҹзӢ¬еұ…зҡ„еӨ–е©ҶжҖҺд№ҲеҠһпјҹжҲ‘жҒЁдёҚеҫ—马дёҠе°ұйЈһиө·пјҢеӣһеҲ°иҖҒ家зңӢзңӢгҖӮеҸҲжҖӘзҪӘиҮӘе·ұпјҢдёәд»Җд№ҲиҰҒжқҘиҝҷд№Ҳиҝңзҡ„ең°ж–№дёҠеӯҰпјҢдёҖж—ҰжңүдәӢпјҢз«ҹеӣһдёҚеҺ»гҖӮ
дёҚзҹҘйҒ“иҝҮдәҶеӨҡд№…пјҢз”өиҜқйӮЈеӨҙдј жқҘдёҖдёӘеҘіеЈ°вҖ”вҖ”е–ӮгҖӮиҝҷеӨҙзҡ„жҲ‘е’ҢйӮЈеӨҙзҡ„еҘ№еҗҢж ·иҜ§ејӮпјҢжҲ‘зҡ„иҲҢеӨҙеғҸжҳҜеғөзЎ¬дәҶпјҢеҲ°еҳҙиҫ№зҡ„иҜқдјјд№ҺеҮқеӣәгҖӮйӮЈеӨҙе–Ӯе–ӮдәҶеҘҪеҮ еЈ°пјҢжҲ‘жүҚеҸҚеә”иҝҮжқҘгҖӮжҲ‘йўӨжҠ–зқҖй—®пјҢдҪ жҳҜе“ӘйҮҢпјҹ
йӮЈеӨҙиҜҙпјҢжҲ‘жҳҜз»өйҳіеёӮж–ҮиҒ”гҖӮ
йӮЈж—¶еҖҷжҲ‘е·Із»ҸеңЁзҪ‘дёҠиҝһиҪҪе°ҸиҜҙпјҢеҮәзүҲдәҶиҮӘе·ұзҡ„еӨ„еҘідҪңпјҢе’Ңз»өйҳіеёӮж–ҮиҒ”зҡ„зҺӢиҖҒеёҲи§ҒиҝҮдёҖйқўпјҢз•ҷдәҶд»–зҡ„жүӢжңәе’Ңеӣәе®ҡз”өиҜқгҖӮеҲҡжүҚжІЎеӨҙи„‘ең°дёҖйҖҡжӢЁжү“пјҢз«ҹ然жҺҘйҖҡдәҶзҺӢиҖҒеёҲдёҖе№ҙеүҚз•ҷз»ҷжҲ‘зҡ„еә§жңәгҖӮ
зҺӢиҖҒеёҲеә”еЈ°иҖҢжқҘпјҢеЈ°йҹійҮҢжңүеҠ«еҗҺдҪҷз”ҹзҡ„еәҶе№ёе’ҢжҺҘеҲ°еӨ–з•Ңи®ҜжҒҜзҡ„жҝҖеҠЁгҖӮд»–иҜҙпјҢз»өйҳійңҮеҫ—еҮ¶пјҢ他们йғҪеҗ“жғЁдәҶгҖӮ
дәӢеҗҺпјҢжҲ‘жүҚзҹҘйҒ“пјҢең°йңҮеҗҺпјҢзҺӢиҖҒеёҲжҺҘеҲ°зҡ„第дёҖдёӘз”өиҜқе°ұжҳҜжҲ‘жү“жқҘзҡ„пјҢиҖҢжҲ‘жӢЁйҖҡзҡ„第дёҖдёӘз”өиҜқд№ҹжҳҜд»–зҡ„гҖӮжҲ‘иҮід»Ҡд№ҹжғідёҚжҳҺзҷҪпјҢйҖҡдҝЎдёӯж–ӯзҡ„жғ…еҶөдёӢпјҢиҝҷдёӘз”өиҜқжҳҜжҖҺж ·еҘҮиҝ№иҲ¬жҺҘйҖҡзҡ„гҖӮ
жҲ‘дёҚзҹҘйҒ“зҡ„жҳҜпјҢеҪ“жҲ‘з„ҰжҖҘдёҮеҲҶзҡ„ж—¶еҖҷпјҢжҲ‘зҡ„зҲ¶жҜҚпјҢд№ҹеңЁз–ҜзӢӮжӢЁжү“жҲ‘зҡ„жүӢжңәгҖӮең°йңҮеҲ°жқҘж—¶пјҢжҜҚдәІеңЁеҶңз”°йҮҢй”„иҚүпјҢзһ¬й—ҙең°еҠЁеұұж‘ҮпјҢеҘ№еҸҢжүӢжҠұж ‘жүҚиғҪз«ҷзЁіпјҢзңӢеҲ°иҮӘ家зҡ„йҷўеўҷеЎҢдәҶпјҢеҲҶдёҚжё…жҒҗжғ§иҝҳжҳҜеҸҜжғңпјҢзңјжіӘе”°ең°жөҒдёӢжқҘгҖӮзҲ¶дәІйӘ‘зқҖж‘©жүҳиҪҰпјҢеҺҹжң¬жү“з®—еҺ»и°ҲдёҖ笔з”ҹж„ҸпјҢзӘҒ然пјҢиҪҰеӯҗеҸҳжҲҗдёҖиүҳйЈҳеҝҪдёҚе®ҡзҡ„е°ҸиҲ№пјҢйҒ“и·ҜдёӨж—Ғзҡ„жҲҝеӯҗз§ҜжңЁдёҖиҲ¬еЎҢйҷ·гҖӮжғҠйӯӮжңӘе®ҡзҡ„зҲ¶дәІдёҖи„ҡжІ№й—ЁеҸҲејҖеӣһ家пјҢдёҺжҜҚдәІдјҡеҗҲд»ҘеҗҺпјҢе°ұзүөжҢӮжҲ‘вҖ”вҖ”他们зӢ¬з”ҹеҘізҡ„е®үеҚұ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ж–°жј”еҮәеӯЈеҸ‘еёғпјҒд»Ҡе№ҙпјҢвҖңеӨ§йІёйұјвҖқеҸҲе°ҶеёҰзқҖе°ҸжңӢеҸӢжёёеҗ‘дҪ•еӨ„пјҹ
- зҲӘе“ҮжқҖдәҶжҳҺжңқ170дёӘе°ҶеЈ«пјҢзңӢйғ‘е’ҢеҰӮдҪ•еӨ„зҗҶзҡ„
- е‘Ёз‘ңеҺ»дё–ж—¶е№ҙд»…36еІҒпјҢзҘһд»ҷжғ…дҫЈгҖҒиІҢзҫҺеҰӮиҠұзҡ„еҰ»еӯҗе°Ҹд№”жөҒиҗҪдҪ•еӨ„
- еҗӣзҺӢзҡҮеёқ|зҡҮеёқй©ҫеҙ©еҗҺпјҢж®ү葬时еҰғеӯҗ们жҳҜеҰӮдҪ•еӨ„зҗҶзҡ„пјҹ
- йҡӢе”җ|и®©жқЁжһ—й—»йЈҺдё§иғҶзҡ„зҮ•дә‘еҚҒе…«йӘ‘зҪ—жҲҗжӯ»ж—¶д»–们еңЁдҪ•еӨ„пјҹжңҖз»Ҳз»“еұҖжҖҺж ·пјҹ
- иҖғеҸӨзӣ—еў“|йЎәжІ»еёқжҠҠеӨҡе°”иЎ®жҺҳеў“йһӯе°ёеҗҺпјҢд»–еҸҲжҳҜеҰӮдҪ•еӨ„зҪ®еӨҡе°”иЎ®з•ҷдёӢзҡ„еӯҗе—Је‘ўпјҹ
- з§Ұжңқ|з§ҰзҒӯе…ӯеӣҪеҗҺпјҢз§Ұе§ӢзҡҮжҳҜеҰӮдҪ•еӨ„зҪ®е…ӯеӣҪеӣҪеҗӣзҡ„пјҹи·ҹжҲ‘们жғізҡ„еҸҜиғҪдёҚеӨӘдёҖж ·
- еҸӨд»ЈвҖңзўҺ银еӯҗвҖқжІЎжңүйқўйўқжҖҺд№Ҳз”ЁпјҹеҮәй—ЁеёҰ银еӯҗйңҖжүҫйӣ¶зҡ„ж—¶еҰӮдҪ•еӨ„зҗҶпјҹ
- з§Ұжңқ|з§ҰеӣҪз»ҹдёҖе…ӯеӣҪеҗҺпјҢз§Ұе§ӢзҡҮжҳҜеҰӮдҪ•еӨ„зҪ®е…ӯеӣҪеӣҪеҗӣзҡ„пјҹдҪ еҸҜиғҪж°ёиҝңзҢңдёҚеҲ°
- зҘӣйӯ…еҗҺзҡ„вҖңзІүдёқж–ҮеҢ–вҖқеҗ‘дҪ•еӨ„е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