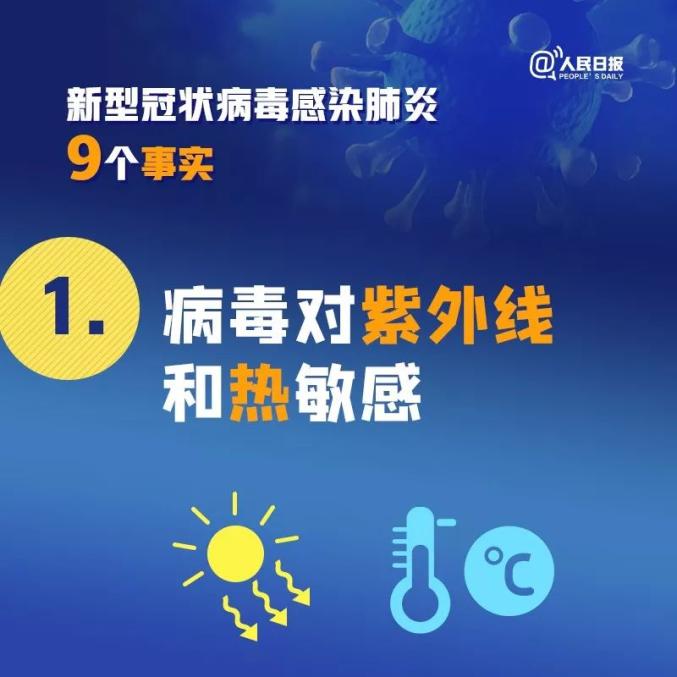应该说,导演对剧本的删改与表现形式的选择有着直接的关联,这里最关键的,是导演能否甘于成为、真正成为“作家的化身”,成为作品的“助产士”,“死而复生在演员的创造中”。
其次,焦菊隐对话剧表现形式的探索是一种立足于中国话剧现实处境并具备长远眼光的行为,并非只是导演个人在艺术上的求新求变。
我们知道,从导演《夜店》、《上海屋檐下》到《龙须沟》、《明朗的天》,焦菊隐探索的重心主要是寻找一套符合中国演员情况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他创造性地发展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排练方法,在斯氏“内心视象”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心象说”。焦菊隐“心象说”的提出,揭开了长期以来蒙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上的神秘面纱,使演员对如何“体验”有了明晰而切实的认识,也从技术层面解决了话剧表演的一大难题。从导、表演的角度说,《龙须沟》的成功,主要得力于焦菊隐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借鉴,得力于一种非常生活化的演出风格,而这恰好是与剧本本身所提供的现实生活内容相吻合的。此外,浓郁的地方色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文章插图
换句话说,剧本所描述的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而且正是发生在演员身边的事件,事件中的人物又都是剧组人员较为熟悉,是周围的现实生活中很容易找到的。因此,当焦菊隐以其“心象说”理论组织排演,要求演员从生活体验出发去把握角色,获得“心象”时,就较为容易达到预期的目的,演员的表演也较为容易产生真实感。可是,一旦剧本的题材、风格发生变化,一旦剧中人物与演员所熟悉的生活有较大的距离,这种以现实生活为蓝本,以酷似现实生活为追求的排练、表演方法是否还能奏效呢?
焦菊隐开始了新的探索。1954年8月执导曹禺的新剧作《明朗的天》时,便采用了由外到内的方法。根据从书本上掌握的知识,焦菊隐一反排演《龙须沟》时让演员先体验生活的做法,而是由导演直接向演员讲解和分析角色的性格特征。他要求演员先由掌握角色的外部动作入手,去体验、感受角色内心世界,然后再在内心体验的基础上发展、丰富外部动作。这个思路不能说没有理论依据,也确实符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关形体行动方法的表述,可是在实际的排演中却收效甚微,实际效果与焦菊隐所预想的相去甚远。
1956年7月,焦菊隐执导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这是他首次有意识地尝试在话剧中借鉴戏曲手法。焦菊隐称《虎符》是“吸取戏曲精神也兼带形式的一种试验”。就其本意而言,他希望话剧向戏曲学习应重在精神,但事实上,由于是第一次尝试,《虎符》在形式层面上的借鉴相对说来更多一些。而在随后执导的《茶馆》中,焦菊隐便把学习的重心放在了戏曲精神上,并化用戏曲表现手法,使之与话剧的艺术特性有机融合,于写实的基调中增添了写意的色彩。

文章插图
到了执导《蔡文姬》、《武则天》时,焦菊隐对戏曲精神的学习运用可以说已经深入其堂奥,达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根据表现剧本特定内容、风格的需要,创造性地结合话剧与戏曲的美学精神,既丰富了话剧艺术的表现手法,又赋予演出以浓郁的民族色彩。还应该提到《关汉卿》的导演。在这出戏中,焦菊隐的话剧民族化探索又有新的突破,由舞台形式延伸到剧本结构,延伸到“戏曲的独特的艺术方法”的核心,即支配、决定戏曲程式的“构成法”。他希望通过这一新的探索,“给话剧创造一个自己的程式,使话剧的演出,也能和戏曲一样具有连贯性,并使短短的过场戏在话剧里也能产生揭示人物心情的效果”。尽管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焦菊隐未能完全实现他预期的构想,但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探索历程却是再明显不过的。
推荐阅读
- 李商隐的忘忧诗,明月高悬,灵感喷发,读完让人感到安静和从容
- 李商隐的诗常常引用典故,只有这首《落花》,全诗纯用白描的手法
- 李商隐的《登乐游原》是千古名篇,其实杜牧也写过一首,同样经典
- 王维的名句,李商隐的名句,杜牧的名句,全是经典,收藏细品!
- 李商隐|李商隐的这首诗人人会背,但是却没人真正能懂
- 灵活|李商隐的这首《细雨》,写得灵活而新鲜,通篇写雨没有一个雨字!
- 斗争|李商隐的《蝉》,在政治斗争中始终保持士人风骨和高洁
- 诗词歌赋|李商隐的冬至:玉管葭灰细细吹,忆把枯条憾雪时
- 不信|辞官归隐的宰相,若与正七品县令对比谁职权更大说出你都不信
- 大唐|他是一代名臣,大唐宰相,还是杜牧与李商隐的亲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