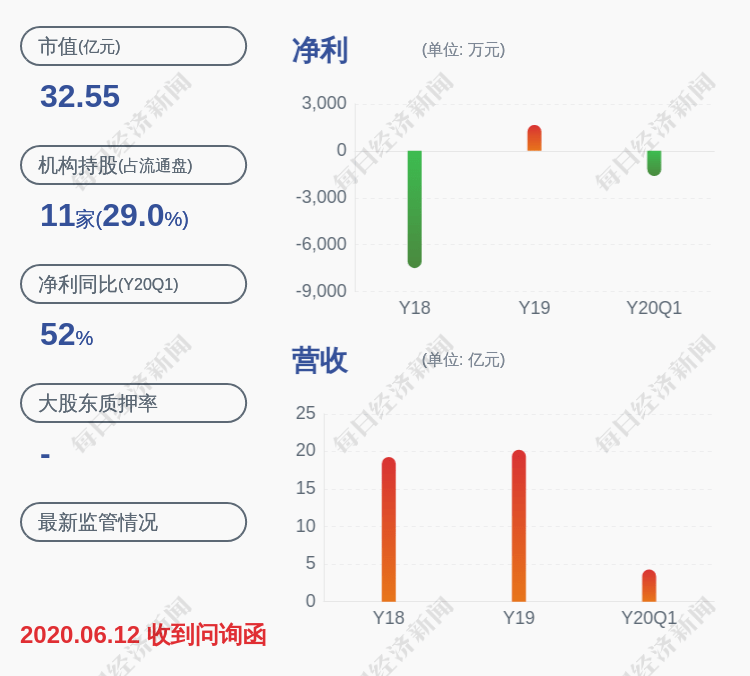文章插图
司马迁像,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
在此基础上,陈正宏老师提出文献之间是有层次性的。近现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往往过于重视出土的文献,而轻视了传世文献的价值。在史学的研究中,地方出土的文献资料当然有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重大价值,但是这些异说的发现并不必然影响像《史记》那样的一流名著的史学价值,因为相比于后世人们发掘的只言片语,显然身处历史现场,掌握着众多第一手资料的司马迁所记录下来的内容,文献等级更高。这一点也从历史上众多史学家对于《史记》史学价值的推重可以看出。刘向、扬雄二人,皆为西汉时人,也都是博览群书的大学问家,成书于东汉的《汉书》虽然对司马迁本人的价值观有诸多批评,但在《司马迁传》中,对于《史记》的史学价值,也十分肯定,记录了刘、扬二人对于司马迁的评价,认为他“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与司马迁撰述时间相近的人,都肯定了《史记》的史学价值。
由《汉书》开始,作为史书的《史记》进入了漫长的价值波动的过程,唐代的刘知幾,宋代的欧阳修、郑樵,历朝历代的史学家都对《史记》发表的不同的看法,或批评其体例,或认为其在史料上不加选择。延至明清,《史记》作为史书的价值,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已经被完全忽视了,不少文献学的大家都对《史记》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批评,甚至有“八书皆赝鼎”的说法,认为流传中的《史记》有部分篇章并非司马迁原本所有,而是后人根据《汉书》抄纂的结果。虽然这种说法很快受到了驳斥,但仍旧对《史记》的传播与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现代学术研究影响深远的梁启超先生就在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认为《史记》中有“全篇可疑者“,即”今本《史记》中多有与《汉书》略同,而玩其文意,乃似《史记》割裂《汉书》,非《汉书》删去《史记》者”,因此“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惟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
在陈正宏老师看来,正是这样的认识,使得后代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表面上对《史记》十分推崇,在实际研究中,却往往绕着走。这样的做法,在陈老师看来,显然有因噎废食之嫌。一方面,《史记》在成书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受重视,虽有篇章的缺失,但受到篡改机会并不多;另一方面,今天流传的《史记》中保留了大量反对王权的内容,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史记》在流传过程中,并未遭受严重的删改。基于《史记》所写西汉部分是汉代的第一手资料,西汉以前的部分虽是编纂之前的有关文献,但因时间久远,不少原始文献已经佚失,即使文献尚存也有版本差异,陈正宏老师认为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件事的叙述,《史记》所载价值不应低于其他文献资料。同时因为司马迁综合整理了当时的文献中的各种说法,而未对其大幅度修改,研读《史记》甚至就有了以一当百的效果。
从对《史记》史书价值的讨论展开去,陈老师将讲座的话题进一步延伸,指出当代人读古书的方法其实是有可商榷之处的。譬如很多人因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错以为《史记》中的内容都是创作。殊不知,这一家之言,并不是只一方面的见解,而是“诸子百家中的别一家”。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为同时代学者梁玉绳著《史记志疑》所撰序中说:“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这段话正点名了《史记》在古代学术版图上的综合性特征,按照传统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来说,就是《史记》是一部兼跨经、史、子三部的著作。从史部而言,他是开创性的,而后来班固等编《汉书》,只是在他的基础上,有所修改,因此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史家之宗”。
推荐阅读
- 玩收藏︱快乐很重要
- 宋代娱乐活动大揭秘!看完这篇你就知道了!
- 传承剪纸文化 构建特色课程 朱老庄镇观堂幼儿园开展剪纸培训活动
- 镜湖区文化馆积极开展馆际交流活动,促进群文工作繁荣和发展
- 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沐凡舍分馆 -----大型公益青年联谊活动
- 甘州区南街街道泰安社区妇联开展新年新气象巾帼展风采活动
- 艺术培训进社区 文化传播暖人心——建筑新村街道办事处开展文艺培训进社区活动
- 东莞一景区70万元征集下联活动截稿,收稿超16万句
- 周村区城北中学开展第九届校园合唱节暨优秀童谣传唱活动
- 芝罘文化路小学开展“学先锋做先锋”感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