д»ҺйІҒиҝ…еҲ°дёҒзҺІпјҡиҝ‘д»ЈдёӯеӣҪзҡ„з–ҫз—…йҡҗе–»дёҺж–ҮеӯҰз–—жІ»
жқҘжәҗпјҡеҮӨеҮ°зҪ‘ж–ҮеҢ–вҖңзҮ•еӣӯдёүеү‘е®ўвҖқд№ӢдёҖзҡ„й»„еӯҗе№іе…Ҳз”ҹеҜ№20дё–зәӘдёӯеӣҪж–ҮеӯҰжңүйқһеёёж·ұеҺҡзҡ„еӯҰжңҜз ”з©¶ пјҢ д»–йҖҡиҝҮеҜ№дәҺвҖңйқ©е‘ҪвҖқе°ҸиҜҙзҡ„з»ҶиҜ» пјҢ е»әз«Ӣиө·зӨҫдјҡеҺҶеҸІеҸ‘еұ•дёҺж–Үжң¬й—ҙзӣёдә’иҒ”зі»гҖҒзӣёдә’е»әжһ„зҡ„зј з»•е…ізі» пјҢ еҸ‘еұ•еҮәд»Ҙ йқ©е‘ҪВ·еҺҶеҸІВ·е°ҸиҜҙ дёәе…ій”®иҜҚзҡ„з ”з©¶и„үз»ң гҖӮжң¬ж–ҮиҠӮйҖүиҮӘй»„еӯҗе№іе…Ҳз”ҹ1990е№ҙзҡ„и®әи‘—гҖҠзҒ°йҳ‘дёӯзҡ„еҸҷиҝ°гҖӢ пјҢ д»ҺдёҒзҺІзҡ„зҹӯзҜҮе°ҸиҜҙгҖҠеңЁеҢ»йҷўдёӯгҖӢеҮәеҸ‘ пјҢ йҳҗйҮҠйӮЈдёӘе№ҙд»Јж–Үжң¬дёӯе…ідәҺз–ҫз—…зҡ„йҡҗе–» гҖӮ дёҒзҺІзҡ„еҶҷдҪңд»Ҙз»Ҷи…»зҡ„жғ…ж„ҹе’ҢеҝғзҗҶжҸҸеҶҷи‘—з§° пјҢ иҖҢеҘ№иҮӘиә«дј еҘҮзҡ„з»ҸеҺҶгҖҒеқҺеқ·зҡ„жғ…ж„ҹе’Ңж–ҮеӯҰиҪ¬еҗ‘д№ҹжҳҜеҗҺдәәи°Ҳи®әзҡ„з„ҰзӮ№ гҖӮгҖҠеңЁеҢ»йҷўдёӯгҖӢжҳҜдёҒзҺІеҲӣдҪңд№Ӣи·ҜдёҠд»ҺвҖңдә”еӣӣж–°еҘіжҖ§вҖқеҲ°вҖңзӨҫдјҡдё»д№үеҘіеҠіжЁЎвҖқзҡ„иҪ¬жҠҳзӮ№ пјҢ й»„еӯҗе№іе…Ҳз”ҹеү–жһҗеҪ“ж—¶зҡ„зӨҫдјҡеўғеҶө пјҢ д»ҘвҖңз–ҫз—…зҡ„йҡҗе–»вҖқдёәеҲҮе…ҘзӮ№ пјҢ иҙЁиҜўдҪң家еңЁж–ҮеӯҰз”ҹдә§дёӯвҖңиў«жІ»ж„ҲвҖқзҡ„еҸҜиғҪжҖ§ гҖӮ
й»„еӯҗе№іеүҚиЁҖд»Һж–ҮеӯҰеҸІжҲ–зӨҫдјҡжҖқжғіеҸІзҡ„и§’еәҰиҜ»дёҒзҺІзҡ„зҹӯзҜҮе°ҸиҜҙгҖҠеңЁеҢ»йҷўдёӯгҖӢ пјҢ е…¶еҖјеҫ—йҮҚи§Ҷзҡ„еҺҹеӣ дёҚеңЁиҝҷйғЁдҪңе“Ғжң¬иә« пјҢ иҖҢеңЁдҪңе“ҒдёҺеӨҡйҮҚеҺҶеҸІиҜӯеўғд№Ӣй—ҙзҡ„е…ізі» пјҢ еңЁдҪңе“ҒдёҺе…¶д»–иҜқиҜӯд№Ӣй—ҙзҡ„дә’ж–ҮжҖ§ пјҢ еңЁдҪңе“Ғиҝӣе…Ҙ20дё–зәӘзҡ„"иҜқиҜӯпјҚжқғеҠӣ"зҪ‘з»ңеҗҺзҡ„дёҖзі»еҲ—еҶҚз”ҹдә§иҝҮзЁӢ гҖӮе°ұдёҒзҺІжҜ•з”ҹзҡ„еҲӣдҪңиҖҢиЁҖ пјҢ д»ҺгҖҠиҺҺиҸІеҘіеЈ«зҡ„ж—Ҙи®°гҖӢпјҲ"дә”еӣӣж–°еҘіжҖ§"пјүеҲ°гҖҠжқңжҷҡйҰҷгҖӢпјҲ"зӨҫдјҡдё»д№үеҘіеҠіжЁЎ"пјү пјҢ гҖҠеңЁеҢ»йҷўдёӯгҖӢжҒ°еҘҪжҳҜдёҖдёӘжҲҸеү§жҖ§зҡ„иҪ¬жҚ©зӮ№ гҖӮиҢ…зӣҫжӣҫеңЁд»–зҡ„гҖҠеҘідҪң家дёҒзҺІгҖӢдёӯиҜҙ пјҢ "еҘ№зҡ„иҺҺиҸІеҘіеЈ«жҳҜеҝғзҒөдёҠиҙҹзқҖж—¶д»ЈиӢҰй—·зҡ„еҲӣдјӨзҡ„йқ’е№ҙеҘіжҖ§зҡ„еҸӣйҖҶзҡ„з»қеҸ«иҖ…" гҖӮ гҖҠеңЁеҢ»йҷўдёӯгҖӢйҮҢзҡ„йҷҶиҗҚ пјҢ жӯЈжҳҜдёҒзҺІеҶҷдҪңдёӯжңҖеҗҺдёҖдёӘиҝҷж ·зҡ„"з»қеҸ«иҖ…" гҖӮ иҮӘжӯӨд№ӢеҗҺ пјҢ "ж—¶д»ЈиӢҰй—·зҡ„еҲӣдјӨ"е°ұеңЁдёҒзҺІз¬”дёӢж¶ҲеӨұдәҶ пјҢ жҲ–иҖ…иҜҙ пјҢ "жІ»ж„Ҳ"дәҶ гҖӮжЁӘеҗ‘жқҘзңӢ пјҢ иҝҷзҜҮе°ҸиҜҙдёҺдёҒзҺІйӮЈдёҖж—¶жңҹзҡ„е…¶д»–дҪңе“ҒпјҲгҖҠжҲ‘еңЁйңһжқ‘зҡ„ж—¶еҖҷгҖӢпј»1940е№ҙпјҪгҖҒгҖҠеӨңгҖӢпј»1941е№ҙпјҪгҖҒгҖҠдёүе…«иҠӮжңүж„ҹгҖӢпј»1942е№ҙпјҪгҖҒгҖҠйЈҺйӣЁдёӯеҝҶиҗ§зәўгҖӢпј»1942е№ҙпјҪзӯүзӯүпјү пјҢ д»ҘеҸҠеҗҢдёҖж—¶жңҹиүҫйқ’гҖҒзҪ—зғҪгҖҒиҗ§еҶӣгҖҒзҺӢе®һе‘ізӯүдәәзҡ„дҪңе“Ғ пјҢ дёҖиө·жһ„жҲҗдәҶдёҖз§Қж·ұеҲ»дёҚе®үзҡ„еҺҶеҸІж°”ж°ӣ гҖӮ "дә”еӣӣ"жүҖз•Ңе®ҡзҡ„ж–ҮеӯҰзҡ„зӨҫдјҡеҠҹиғҪгҖҒж–ҮеӯҰ家зҡ„зӨҫдјҡи§’иүІгҖҒж–ҮеӯҰзҡ„еҶҷдҪңж–№ејҸзӯүзӯү пјҢ еҠҝеҝ…жҺҘеҸ—ж–°зҡ„еҺҶеҸІиҜӯеўғпјҲ"зҺ°д»ЈзүҲзҡ„еҶңж°‘йқ©е‘ҪжҲҳдәү"пјүзҡ„йҮҚж–°зј–з Ғ гҖӮ иҝҷдёҖзј–з ҒпјҲ"жІ»з–—"пјүиҝҮзЁӢ пјҢ ж”№еҸҳдәҶ20дё–зәӘеҗҺеҚҠеҸ¶дёӯеӣҪж–ҮеӯҰзҡ„еҶҷдҪңж–№ејҸе’ҢеҸ‘еұ•иҝӣзЁӢ пјҢ д№ҹйҮҚеЎ‘дәҶж–ҮеӯҰ家гҖҒ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гҖҒ"дәәзұ»зҒөйӯӮе·ҘзЁӢеёҲ"们зҡ„зҒөйӯӮ гҖ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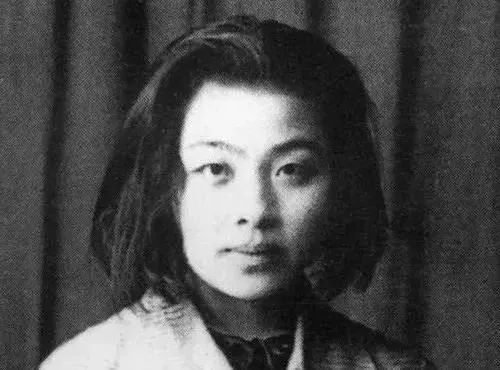
дёҒзҺІзәөеҗ‘жқҘзңӢ пјҢ 1958е№ҙгҖҠж–ҮиүәжҠҘгҖӢеҸ‘еҠЁеҜ№гҖҠеңЁеҢ»йҷўдёӯгҖӢзӯүдҪңе“Ғзҡ„"еҶҚжү№еҲӨ" пјҢ иҜҒжҳҺдәҶ"дә”еӣӣ"дёҺ"дә”В·дәҢдёү"пјҲдә”жңҲдәҢеҚҒдёүж—ҘдёәжҜӣжіҪдёңгҖҠеңЁе»¶е®үж–Үиүәеә§и°ҲдјҡдёҠзҡ„и®ІиҜқгҖӢеҸ‘иЎЁзҡ„зәӘеҝөж—Ҙпјү гҖӮ иҝҷдёӨз§ҚиҜӯз Ғд№Ӣй—ҙзҡ„жүӢжңҜеҲҖеҸЈејҘеҗҲеҫ—并дёҚе®ҢзҫҺ пјҢ ж•ҙдёӘ"зј–з ҒпјҚжІ»з–—"иҝҮзЁӢеҝ…йЎ»еҸҚеӨҚиҝӣиЎҢжүҚиғҪеҘҸж•Ҳ гҖӮ дёҖзӣҙ延伸еҲ°20дё–зәӘ80е№ҙд»Јзҡ„"жё…йҷӨзІҫзҘһжұЎжҹ“"зӯүиҝҗеҠЁ пјҢ д»ҚжҳҜиҝҷжӣҫз»ҸеЈ°еҠҝжө©еӨ§еҰӮд»ҠеҚҙжёҗи¶ӢејҸеҫ®зҡ„"зӨҫдјҡеҚ«з”ҹеӯҰ"пјҲsocialhygieneпјүй©ұйӮӘжІ»з–—д»ӘејҸзҡ„继з»ӯ гҖӮ01вҖңејғеҢ»д»Һж–ҮвҖқзҡ„ж•…дәӢеңЁеҪұе“Қ20дё–зәӘдёӯеӣҪжҖқжҪ®зҡ„и®ёеӨҡиҮӘ然科еӯҰзҗҶи®әдёӯ пјҢ иҝ‘д»Јз”ҹзү©еӯҰзҡ„"иҢғејҸ"дҪңз”ЁжңҖдёәж·ұиҝңжҷ®жіӣ гҖӮиҫҫе°”ж–Үзҡ„иҝӣеҢ–и®әеӣә然з»ҷеҮәдәҶдёҖжқЎд№җи§Ӯеҗ‘дёҠзҡ„ж—¶й—ҙзҹўзәҝ пјҢ жҝҖеҠұеӣҪдәәеңЁ"еӨ©жј”дәәжӢ©"зҡ„жүҖи°“"规еҫӢ"дёӯж•‘дәЎеӣҫеӯҳпјӣ е°ҶзӨҫдјҡгҖҒеӣҪ家гҖҒз§Қж—ҸзӯүзӯүзңӢдҪңдёҖдёӘеҒҘеә·жҲ–з—…жҖҒзҡ„жңүжңәдҪ“зҡ„и§ӮзӮ№ пјҢ дәҰдёҺдј з»ҹж–ҮеҢ–дёӯзҡ„жңүжңәиҮӘ然и§ӮдёҖжӢҚеҚіеҗҲ гҖӮ既然дёӯеӣҪе·Іиў«и§ҶдёәдёҖ"дёңдәҡз—…еӨ«" пјҢ еҜ№дјҹеӨ§"еҢ»еӣҪжүӢ"зҡ„еӣһжҳҘд№ӢжңҜзҡ„жңҹеҫ… пјҢ еҜ№з§Қз§Қ"жІ»з–—ж–№жЎҲ"зҡ„и®Ёи®әе’Ңдәүи®ә пјҢ е°ұеңЁе…¶еӨ§еүҚжҸҗд»ҺдёҚеј•иө·з–‘й—®зҡ„жғ…еҪўдёӢиҝӣиЎҢ гҖӮ еңЁиҝҷж ·дёҖз§ҚеҺҶеҸІиҜӯеўғдёӯ пјҢ "дә”еӣӣ"ж—¶д»ЈеҜ№ж–ҮеӯҰзҡ„зӨҫдјҡеҠҹиғҪгҖҒж–ҮеӯҰ家зҡ„зӨҫдјҡи§’иүІзӯүзӯүзҡ„з•Ңе®ҡ пјҢ иҮӘ然еҫҲж–№дҫҝең°д»ҺеҢ»еӯҰз•ҢиҺ·еҫ—з”ҹеҠЁеҪўиұЎзҡ„еҖҹе–» гҖӮйІҒиҝ…"ејғеҢ»д»Һж–Ү"зҡ„ж•…дәӢ пјҢ еёёиў«з”ЁжқҘжһҒеҮқз»ғеҸҲжһҒдё°еҜҢең°ж¶өжӢ¬иҝҷдёҖзұ»и§Ӯеҝө гҖӮ "е№»зҒҜзүҮдәӢ件"дјјд№ҺжҲҸеү§жҖ§ең°ж”№еҸҳдәҶдёҖдёӘзҹҘиҜҶеҲҶеӯҗзҡ„з”ҹжҙ»йҒ“и·Ҝ пјҢ еҚҙд»…д»…жҳҜйІҒиҝ…еӨҡе№ҙжқҘеҜ№"дёӯеӣҪеӣҪж°‘жҖ§зҡ„з—…ж №дҪ•еңЁ"зҡ„еҸҚеӨҚжҖқзҙўзҡ„еҝ…然结жһң гҖӮ еӨҡе№ҙеҗҺйІҒиҝ…еңЁгҖҠжҲ‘жҖҺд№ҲеҒҡиө·е°ҸиҜҙжқҘгҖӢдёҖж–Үдёӯ пјҢ дәҰйҮҚз”ідәҶд»–зҡ„з«Ӣеңәпјҡ"иҜҙеҲ°'дёәд»Җд№Ҳ'еҒҡе°ҸиҜҙеҗ§ пјҢ жҲ‘д»ҚжҠұзқҖеҚҒеӨҡе№ҙеүҚзҡ„'еҗҜи’ҷдё»д№ү' пјҢ д»Ҙдёәеҝ…йЎ»жҳҜ'дёәдәәз”ҹ' пјҢ иҖҢдё”иҰҒж”№иүҜиҝҷдәәз”ҹ гҖӮ вҖҰвҖҰжүҖд»ҘжҲ‘зҡ„еҸ–жқҗ пјҢ еӨҡйҮҮиҮӘз—…жҖҒзӨҫдјҡзҡ„дёҚе№ёзҡ„дәә们дёӯ гҖӮ ж„ҸжҖқжҳҜеңЁжҸӯеҮәз—…иӢҰ пјҢ еј•иө·з–—ж•‘зҡ„жіЁж„Ҹ гҖӮ "дҪҶйІҒиҝ…зҡ„ж·ұеҲ»д№ӢеӨ„е’ҢзӢ¬еҲ°д№ӢеӨ„еңЁдәҺ пјҢ д»–иҮӘе§ӢиҮіз»ҲеҜ№ж–ҮеӯҰзҡ„"жІ»з–—ж•Ҳжһң"зҡ„иҝ‘д№Һз»қжңӣзҡ„жҖҖз–‘ пјҢ д»ҘеҸҠдёҺжӯӨзӣёе…ізҡ„ пјҢ еҜ№ж–ҮеӯҰ家жүҖжүҝжӢ…зҡ„"жҖқжғіпјҚж–ҮеҢ–"еҢ»з–—е·ҘдҪңиҖ…зҡ„и§’иүІзҡ„ж·ұеҲ»жҖҖз–‘ гҖӮ иҝҷдёҖзӮ№жҲ‘们еңЁеҗҺйқўеҶҚеұ•ејҖи®Ёи®ә гҖӮ
з”өеҪұгҖҠй»„йҮ‘ж—¶д»ЈгҖӢдёӯзҡ„йІҒиҝ…зҺ°еңЁжқҘзңӢзңӢгҖҠеңЁеҢ»йҷўдёӯгҖӢзҡ„йҷҶиҗҚвҖ”вҖ”жһҒе…·и®ҪеҲәж„Ҹе‘ізҡ„жҳҜ пјҢ еҘ№иө°дәҶдёҖжқЎиў«иҝ«"ејғж–Үд»ҺеҢ»"зҡ„йҒ“и·ҜпјҒе…ҲжҳҜ"дҫқз…§еҘ№зҲ¶дәІзҡ„зҗҶжғі"е°ұиҜ»дәҺдёҠжө·зҡ„дёҖдёӘдә§з§‘еӯҰж Ў пјҢ "жүҚиҝӣеҺ»дәҶдёӨе№ҙ пјҢ еҘ№иҮӘе·ұе°ұж„ҹеҲ°еҘ№жҳҜдёҚйҖӮе®ңдәҺеҒҡдёҖдёӘдә§з§‘еҢ»з”ҹ гҖӮ еҘ№еҜ№дәҺж–ҮеӯҰд№ҰзұҚжӣҙж„ҹе…ҙи¶Ј пјҢ еҘ№жңүж—¶з”ҡиҮіи®ЁеҺҢдёҖеҲҮеҢ»з”ҹ пјҢ дҪҶд»Қж•ҙж•ҙдҪҸдәҶеӣӣе№ҙ" гҖӮ еҘҪдёҚе®№жҳ“иҫ—иҪ¬жөҒжөӘеҲ°дәҶ延е®үиҜ»"жҠ—еӨ§" пјҢ жҶ§жҶ¬жҲҗдёәдёҖдёӘ"жҙ»и·ғзҡ„ж”ҝжІ»е·ҘдҪңиҖ…" пјҢ еҸҜжҳҜе…ҡйңҖиҰҒеҘ№еҲ°иҝҷдёӘж–°е»әзҡ„еҢ»йҷўеҒҡ"дә§е©Ҷ" гҖӮеңЁиҝҷйҮҢ пјҢ "ж–ҮеӯҰ"е’Ң"еҢ»еӯҰ"зҡ„еҜ№з«ӢйҰ–е…ҲдёҚжҳҜз”ұдәҺ"ж”№еҸҳеӣҪж°‘зҡ„зІҫзҘһдёә第дёҖиҰҒзқҖ" пјҢ иҖҢжҳҜз”ұдәҺдәәзү©зҡ„жҖ§ж је’Ңж°”иҙЁ пјҢ д»ҘеҸҠиҝҷжҖ§ж је’Ңж°”иҙЁдёҺ"зҲ¶д№Ӣжі•"пјҲз”ҹиә«д№ӢзҲ¶е’Ңйқ©е‘Ҫд№Ӣ"зҲ¶"пјүзҡ„еҶІзӘҒ гҖӮ дҪҶеҪ“дёҒзҺІжҠҠ"ж–ҮеӯҰ"дёҺ"ж”ҝжІ»е·ҘдҪңиҖ…"зӣёжҸҗ并и®әж—¶ пјҢ иҝҷзғӯзҲұ"ж–ҮеӯҰ"зҡ„ж°”иҙЁеҲҶжҳҺж„Ҹе‘ізқҖжӣҙеӨҡзҡ„дёңиҘҝпјҡзғӯжғ…гҖҒзҗҶжғігҖҒеҜ№зҺ°зҠ¶зҡ„дёҚж»ЎгҖҒж”№йқ©з—…жҖҒзҺҜеўғзҡ„еҶіеҝғе’Ңе®һи·өзӯүзӯү гҖӮдёҒзҺІдјјд№Һжү§ж„ҸиҰҒжҠҠиҝҷз§Қ"ж–ҮеӯҰж°”иҙЁ"дҪңдёәжӯЈйқўзҡ„гҖҒжҳҺдә®зҡ„еӣ зҙ еҠ д»Ҙејәи°ғ пјҢ з”ҡиҮіеңЁеҶҷеҲ°еҢ»йҷўдёӯдёҚеӨҡзҡ„дёҺйҷҶиҗҚи°Ҳеҫ—жқҘзҡ„дёӨдёӘжңӢеҸӢж—¶ пјҢ д№ҹдёҚеҝҳи®°зӮ№еҮәйӮЈдёӘдёҘиӮғзҡ„еӨ–科еҢ»з”ҹйғ‘й№Ҹ пјҢ "еёёеёёеҶҷзӮ№зҹӯзҜҮе°ҸиҜҙжҲ–зҹӯеү§" пјҢ "иҖҢдё”жҳҜеҫҲй•ҝдәҺжҸҸз»ҳзҡ„" гҖӮ еңЁйҷҶиҗҚдёәж”№еҸҳеҢ»йҷўзҺҜеўғиҖҢжҸҗеҮәзҡ„з§Қз§ҚиҰҒжұӮдёӯ пјҢ йҷӨдәҶжӣҝз—…е‘ҳдәүеҸ–"жё…жҙҒзҡ„иў«иў„ пјҢ жҡ–е’Ңзҡ„дҪҸе®Ө пјҢ ж»ӢиЎҘзҡ„иҗҘе…» пјҢ жңүж¬ЎеәҸзҡ„з”ҹжҙ»"д№ӢеӨ– пјҢ иҝҳжңү"еӣҫз”»гҖҒд№ҰжҠҘ пјҢ дёҚжӢҳеҪўејҸзҡ„еә§и°Ҳдјҡ пјҢ е’Ңе°ҸеһӢзҡ„еЁұд№җжҷҡдјҡ" гҖӮж–ҮеӯҰ家иөӢдәҲиҮӘе·ұе–ңзҲұзҡ„дәәзү©дёҖзӮ№"ж–ҮеӯҰж°”иҙЁ" пјҢ дјјд№ҺжҳҜйЎәзҗҶжҲҗз« е№¶ж— еӨҡеӨ§ж·ұж„Ҹзҡ„дәӢжғ… гҖӮ дҪҶжҳҜеңЁдёҒзҺІеҶҷдҪңгҖҠеңЁеҢ»йҷўдёӯгҖӢзҡ„еҗҢдёҖж—¶й—ҙеҶҷдёӢзҡ„дёҖзҜҮж–Үз« йҮҢ пјҢ еҘ№жҳҺзЎ®ж— иҜҜең°жҸҙеј•дәҶйІҒиҝ…"ејғеҢ»д»Һж–Ү"зҡ„ж•…дәӢпјҡ"йІҒиҝ…е…Ҳз”ҹеӣ дёәиҰҒд»ҺеҢ»жІ»дәәзұ»зҡ„еҝғзҒөдёӢжүӢ пјҢ жүҖд»Ҙж”ҫејғдәҶеҢ»еӯҰиҖҢд»ҺдәӢж–ҮеӯҰ гҖӮ "еӣ жӯӨдёҒзҺІжңүж„Ҹж— ж„Ҹең°еҶҷеҮәдёҖдёӘиў«иҝ«"ејғж–Үд»ҺеҢ»"зҡ„ж•…дәӢж—¶ пјҢ "ж–ҮеӯҰпјҚеҢ»еӯҰ"зҡ„еҜ№з«ӢжҲ–еҖҹе–»е…ізі»еңЁжӯӨж—¶жӯӨең° пјҢ е°ұж·»еҠ еҮәдёҖеұӮж–°зҡ„ж„Ҹд№ү гҖӮ дёҺйІҒиҝ…дҪңдёәеҗҜи’ҷжҖқжғіе®¶дёӘдәәйқўеҜ№дёҖзӣҳж•ЈжІҷзҡ„еӣҪж°‘еӨ§дёҚзӣёеҗҢ пјҢ дёҒзҺІз¬”дёӢзҡ„е…·жңүж–ҮеӯҰж°”иҙЁзҡ„йқ’е№ҙдәә пјҢ жҳҜиў«"е…ҡ"жҙҫеҲ°дёҖдёӘ"еҢ»йҷў"дёӯеҺ»зҡ„ гҖӮ02 еҢ»йҷўдёӯж–°жқҘзҡ„йқ’е№ҙдәәгҖҠеңЁеҢ»йҷўдёӯгҖӢжҳҜдёҖзҜҮжғ…иҠӮзӣёеҪ“з®ҖеҚ•зҡ„е°ҸиҜҙ гҖӮдҫқз…§"еҺҹеһӢ"зҗҶи®әдҪ еҸҜд»ҘиҜҙе®ғжҳҜ"зҰ»е®¶пјҚжҺўйҷ©пјҚеӣһ家"з«ҘиҜқзҡ„жҹҗз§ҚеҸҳеҘҸпјҡ еңЁ"з…Өж°”дёӯжҜ’дәӢ件"зҡ„еүҚеӨң пјҢ дёҒзҺІзӘҒ然еңЁе…ЁзҜҮжҖҘдҝғйҖјд»„зҡ„иҜӯж°”дёӯ пјҢ иҚЎејҖдёҖ笔 пјҢ еҶҷеҲ°йҷҶиҗҚеҜ№"еҚ—ж–№зҡ„й•ҝзқҖз»ҝиҚүзҡ„еҺҹйҮҺгҖҒжәӘжөҒгҖҒжқ‘иҗҪгҖҒеҗ„з§ҚдёҚзҹҘеҗҚзҡ„еӨ§ж ‘гҖҒ家йҮҢзҡ„еәӯйҷўгҖҒжҜҚдәІе’ҢејҹејҹеҰ№еҰ№гҖҒеұӢйЎ¶дёҠзҡ„зӮҠзғҹ"зҡ„жғіеҝө пјҢ иҝҷз§ҚеҜ№"еӣһ家"зҡ„жёҙжңӣжӯЈжҳӯжҳҫдәҶеҘ№еңЁеҜ’еҶ·зҡ„йҷ•еҢ—й«ҳеҺҹзҡ„еҢ»йҷўдёӯзҡ„"еҺҶйҷ©жҖ§" гҖӮдҪ д№ҹеҸҜд»ҘиҜҙе®ғжҳҜдёҖзҜҮ"жҲҗй•ҝе°ҸиҜҙ"зҡ„зүҮж®өпјҡ дәәзү©еңЁж–°зҡ„зҺҜеўғе’Ңж–°зҡ„дәәзҫӨдёӯеӯҰд№ дәәз”ҹзҡ„иҜҫзЁӢ пјҢ йҖҗжёҗжҲҗй•ҝиө·жқҘдәҶ гҖӮе°ҸиҜҙзҜҮжң«зҡ„"иӯҰеҸҘ"жҚ®иҜҙиў«и®ёеӨҡеҪ“时延е®үзҡ„йқ’е№ҙдәәжҠ„дёӢжқҘиҙҙеңЁзӘ‘жҙһйҮҢеҒҡеә§еҸій“ӯпјҡ "ж–°зҡ„з”ҹжҙ»иҷҪиҰҒејҖе§Ӣ пјҢ 然иҖҢиҝҳжңүж–°зҡ„иҚҶжЈҳ гҖӮдәәжҳҜиҰҒз»ҸиҝҮеҚғй”ӨзҷҫзӮјиҖҢдёҚж¶Ҳжә¶жүҚиғҪзңҹзңҹжңүз”Ё гҖӮдәәжҳҜеңЁиү°иӢҰдёӯжҲҗй•ҝ гҖӮ"дҪҶиҒҡз„ҰдәҺжң¬ж–ҮжүҖи®Ёи®әзҡ„дё»йўҳ пјҢ жҲ‘们иҜ»еҲ°зҡ„ пјҢ еҚҙжҳҜдёҖдёӘиҮӘд»Ҙдёә"еҒҘеә·"зҡ„дәәзү© пјҢ еҠӣеӣҫжІ»ж„Ҳ"з—…жҖҒ"зҡ„зҺҜеўғ пјҢ еҚҙз»ҲдәҺиў«зҺҜеўғжүҖжІ»ж„Ҳзҡ„ж•…дәӢпјҲеңЁиҝҷз§ҚиҜ»и§Јдёӯ пјҢ дҪ дјҡжғіеҲ° пјҢ иҝҷжҳҜгҖҠзӢӮдәәж—Ҙи®°гҖӢж•…дәӢзҡ„"зҺ°е®һдё»д№ү"еҸҳеҘҸпјҡ "зӢӮдәә"е‘јеҗҒдәә们"ж”№жӮ”" пјҢ жңҖз»ҲеҚҙиў«жІ»ж„Ҳ пјҢ "иөҙжҹҗеҺҝеҖҷиЎҘ"еҺ»дәҶпјү гҖӮе°ҸиҜҙдёҖејҖеӨҙе°ұз”өеҪұејҸең°з»ҷеҮәдёҖдёӘ并дёҚд»Өдәәж„үжӮҰзҡ„з©әй—ҙжҷҜи§ӮпјҡеҚҒдәҢжңҲйҮҢзҡ„жң«е°ҫ пјҢ дёӢиҝҮдәҶ第дёҖеңәйӣӘ пјҢ еӨ§жІіе°ҸжІійғҪз»“дәҶеҶ° пјҢ йЈҺд»Һ收иҺ·дәҶзҡ„еұұеҶҲдёҠеҗ№жқҘ пјҢ еҲ®зқҖжӢҰзүІеҸЈзҡ„зҜ·йЎ¶дёҠзҡ„иӢҮз§Ҷ пјҢ е‘ңе‘ңзҡ„еҸ«зқҖ пјҢ еҸҲиҝҲжӯҘеҲ°жІҹеә•еҺ»дәҶ гҖӮ иҚүдёӣйҮҢи—ҸзқҖзҡ„йҮҺйӣү пјҢ дҫҝе”°е”°зҡ„ж•ҙзқҖзҝ…еӯҗ пјҢ жӣҙй’»иҝӣйӮЈдәӣзҹізјқжҲ–жҳҜеңҹзӘҹжҙһйҮҢеҺ» гҖӮ зҷҪеӨ©зҡ„йҳіе…ү пјҢ з…§е°„еңЁйӮЈдәӣеҶ°еҶ»дәҶзҡ„зүӣ马зІӘе ҶдёҠ пјҢ и’ёеҸ‘еҮәдёҖиӮЎйҡҫй—»зҡ„ж°”е‘і гҖӮ еҮ дёӘж— еҠӣзҡ„иӢҚиқҮеңЁйӮЈйҮҢжү“ж—Ӣ пјҢ еҸҜжҳҜй»„жҳҸеҫҲеҝ«зҡ„е°ұзҪ©дёӢжқҘдәҶ пјҢ иӢҚиҢ«ең° пјҢ еҮүе№Ҫе№Ҫзҡ„д»Һиҝңиҝңзҡ„еұұеҶҲдёҠ пјҢ д»ҺеҲҡеҲҡеҸҜд»ҘзңӢи§Ғзҡ„еӨ©йҷ…иҫ№ пјҢ ж— еЈ°зҡ„ пјҢ еӣӣйқўе…«ж–№зҡ„йқ иҝ‘жқҘ пјҢ д№ҢйёҰйғҪжү“зқҖеҜ’жҲҳ пјҢ зӢ—д№ҹеӨ№зҙ§дәҶе°ҫе·ҙ гҖӮ дәә们дҫҝйғҪеӣһеҲ°д»–们зҡ„家 пјҢ йӮЈе”ҜдёҖзҡ„и—Ҹиә«зҡ„зӘ‘жҙһйҮҢеҺ»дәҶ гҖӮ然еҗҺжүҚжҳҜдёҖдёӘиҝ‘жҷҜпјҡ"дёҖдёӘз©ҝзҒ°иүІжЈүеҶӣжңҚзҡ„е№ҙиҪ»еҘіеӯҗ пјҢ и·ҹеңЁдёҖдёӘжҠ«дёҖ件зҫҠзҡ®еӨ§иЎЈзҡ„жұүеӯҗеҗҺйқў пјҢ д»ҺжІҹеә•дёӢзҡ„и·ҜдёҠиө°жқҘ" пјҢ "еҘ№еңЁжңүж„Ҹзҡ„еҒҡеҮәдёҖеүҜй«ҳе…ҙзҡ„зҘһж°” пјҢ зқҒзқҖдёӨйў—еңҶзҡ„й»‘зҡ„е°Ҹзңј пјҢ ж¬Је–ңзҡ„жҺўз…§иҚ’еҮүзҡ„еӣӣе‘Ё" гҖӮ йҡҸеҗҺжҳҜдёҖиҝһдёІзӣёеҪ“йҳҙйғҒзҡ„зҺҜеўғжҸҸеҶҷ пјҢ е№Ҫжҡ—жҪ®ж№ҝиҖҢеҜ’еҶ·зҡ„дҪҸеӨ„ пјҢ и·іеҲ°иў«еӯҗдёҠзҡ„иҖҒйј пјҢ жӣҙйҮҚиҰҒзҡ„ пјҢ ж•ҙдёӘд»ӨдәәдёҚеҝ«зҡ„дәәйҷ…е…ізі»зӯүзӯү гҖӮзҺҜеўғжҸҸеҶҷзҡ„"дёҚзҺ°е®һ" пјҢ дёҖзӣҙжҳҜиҝҷзҜҮе°ҸиҜҙеј•еҸ‘жү№еҲӨиҖ…们зҡ„ж„ӨжҖ’е’Ңзғӯжғ…зҡ„дё»иҰҒеҺҹеӣ гҖӮ жңҖж—©зҡ„жү№еҲӨж–Үз« еҸ‘иЎЁдәҺ"延е®үж–Үиүәеә§и°Ҳдјҡ"ејҖиҝҮжІЎеҮ еӨ© пјҢ жү№иҜ„家еңЁиҜҰе°ҪеҲҶжһҗдёҒзҺІз”Ё"ж—§зҺ°е®һдё»д№ү"зҡ„еҲӣдҪңж–№жі•иҗҘйҖ дёҖдёӘж¶ҲжһҒгҖҒйқҷжӯўгҖҒиҗҪеҗҺзҡ„зҺҜеўғзҡ„еҗҢж—¶ пјҢ иҝҳжһҒз»ҶиҮҙең°жҢҮеҮәдёӨеӨ„жңүе…і"иӢҚиқҮ"зҡ„"жҷҜзү©жҸҸеҶҷдёҠзҡ„й”ҷиҜҜ" пјҢ дёҖеӨ„е°ұжҳҜеҲҡжүҚжүҖеј•еҲ°зҡ„ејҖеӨҙзҡ„"еҮ дёӘж— еҠӣзҡ„иӢҚиқҮеңЁйӮЈйҮҢжү“ж—Ӣ" пјҢ дёҖеӨ„еңЁз¬¬дёүиҠӮ第дёҖж®өпјҡ"йҷўеӯҗйҮҢеӣӣеӨ„йғҪзңӢеҫ—и§Ғжңүз”ЁиҝҮзҡ„жЈүиҠұе’Ңзәұеёғ пјҢ е…»иӮІзқҖеҮ дёӘдёҚжӯ»зҡ„иӢҚиқҮ" гҖӮ еҶ°еӨ©йӣӘең°зҡ„йҷ•еҢ—еҚҒдәҢжңҲеә• пјҢ жҖҺиғҪ"дё»и§Ӯең°"иӮҜе®ҡиӢҚиқҮ"дёҚжӯ»"е‘ўпјҹжү№иҜ„家зҡ„е—…и§үзЎ®е®һжҳҜеҫҲж•Ҹй”җзҡ„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ҸӨжңүдәҡеҺҶеұұеӨ§иҝңеҫҒжұүйҖҗеҢҲеҘҙдёәдҪ•иҝ‘д»ЈеҗҺеӢӨеҸҚи¶ҠжқҘи¶Ҡејұ
- иҚҶиҪІе…¶дәә
- йІҒиҝ…зҡ„з«Ӣеңә
- йІҒиҝ…жҳҜжҖҺд№ҲиҜ„д»·еә·д№ҫзӣӣдё–зҡ„пјҹ
- йІҒиҝ…еҜ№зӨҫдјҡзҡ„еҚұе®іжҳҜд»Җд№Ҳпјҹ
- йҳҝQзҡ„зІҫзҘһиғңеҲ©жі•еӯҳеңЁеҗ—пјҹ
- зҘҘжһ—е«Ӯдёәд»Җд№Ҳиў«дәәи®ЁеҺҢпјҢиў«дәәеҚ‘и§Ҷпјҹ
- йІҒиҝ…жңүеӨҡе°‘дёӘ马甲пјҹ
- йІҒиҝ…зҡ„е°ҸиҜҙжҳҜдёҚжҳҜдёҖз§Қй»‘иүІй«ҳеӨ§е…Ёе‘ўпјҹ
- иҖғиҜҒйІҒиҝ…зҡ„дә”еҚғе№ҙеҺҶеҸІе°ұжҳҜеҗғдә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