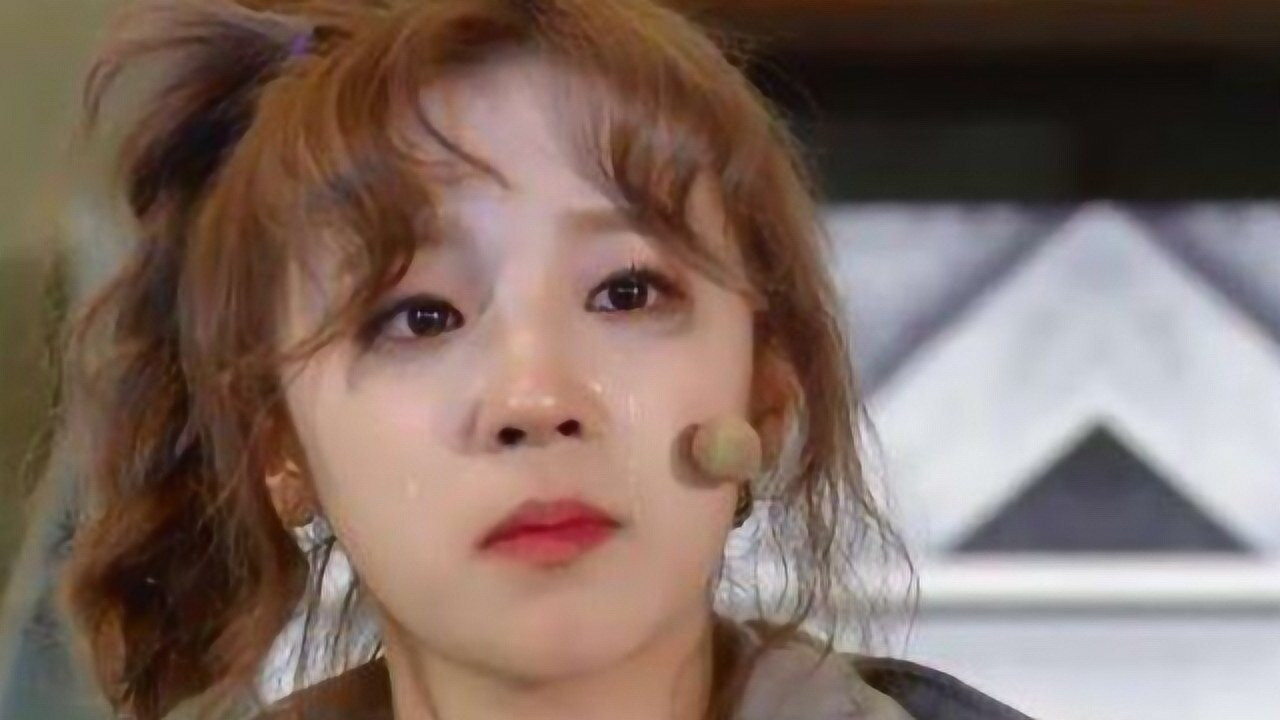推脱|到后来的艺术教室筹备论证阶段,有时被推脱出去
摘要:艺术教育对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总是奢侈的。但一群来自上海的志愿者,用三年时间,在六所乡村小学里改造了八间艺术教室,为留守儿童艺术教育。他们相信,美也是平等的,“在他们走出去之前,应该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画一朵云。
阴云是沉闷的烟灰,火烧云是绚烂的红霞,晴空的白云像棉花糖,它千变万化,有时像鲸鱼,有时像小马,有时被飞机惊扰成一串项链—城市的学校里,数十种水彩笔与蜡笔可以肆意涂抹,而在湖北省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涨水坪小学,云是统一的,是黑板上老师用笔勾出的几个大半圆,孩子们临摹,“白云们”依次上交,一堂小学美术课就完成了。
这里并不缺乏色彩,甚至像个天然的艺术素材库:满眼的绿。翠色一泻千里,层峦叠嶂山岚萦绕,溪涧混着褐色山石,碧空下的乡道很少热闹起来。而在教室里,他们见得最多的是书本与试卷上的黑白。
但一间有些梦幻的教室为这里带来了改变。去年9月,上海心得益彰公益基金会建造的艺术教室正式投入教学使用,明黄色给墙壁描边,明亮的蓝粉橘交替装饰,崭新的桌椅对着先进的投影屏幕,孩子们按音乐、美术、体育等分成小组,志愿者老师们每年定期去授课。
在这间教室里,云不再是云,是孩子们身上的白T恤和新教室的水墨地砖;山绵延到画纸上,还可以是水粉色;梦中的美少女和超级英雄也都被彩泥捏在手上。“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多次到一线担任志愿者的基金会吴佳雨说,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也知道流行的新名词,他们听过“椰子鞋”但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在地域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状下,乡村的孩子少有机会接触优质艺术教育,但美也应该是平等的,“在他们走出去之前,应该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
文章图片
孩子的画作 受访者供图
最差的那个学生
和许多贫困山区的学校一样,涨水坪小学评判孩子们的标准有些简单:学习好的是好孩子,学习不好的是坏孩子。吴佳雨见到林志时,他就是别人说的那种“坏孩子”瘦弱矮小,眼睛细长,耳朵尖尖,“像个小老鼠”
林志反应很快,但基础拼音很差,到了四五年级,很多课本上的字都不认识,平日里,孩子们一起上晚自习,只有最后一个同学完成了作业,大家才能一起出去活动,耽误大家活动的总是林志。他总在座位上不安分,志愿者老师到的第一天,他也大胆去扯扯老师们的辫子,想吸引他们的注意。
班里的孩子们不喜欢林志,但吴佳雨注意到了他,主动上前和林志说话,还拿出单反相机给孩子们拍照。
林志破天荒安静下来,小心翼翼跟在老师们身边,他不敢碰新老师的任何东西,怕弄坏了要挨骂和赔偿。
“我…可不可以碰碰?”跟拍了许久,林志终于开口。
吴佳雨把相机交在他手上,开关、取景器、对焦按钮、镜头等等,她仔细说明,并示范拍照给他看。拿到相机后,林志琢磨了一整个下午,不仅是相机的使用,甚至还加上三脚架辅助,他拍了很多老师的照片,回想起来,吴佳雨还觉得惊喜:“他的对焦拍摄完全没问题。”她忍不住夸林志聪明机灵,林志愣了愣:“老师,从来没有人夸过我,你是第一个。”
向其他学生了解情况后,她才知道,林志一直是学校里“最差的那个”
第二天,艺术教室开始给学生们上课,彩泥到了孩子们手上,很快被捏成一个个具体的梦,林志的梦送给了吴佳雨—一台绿色的单反相机,带着男孩有些害羞别扭的表达:“这是给你的!”吴佳雨把小相机捧在手里,发现上面细致到连旋钮刻度都没落下。“老师,谢谢你教我拍照。”林志说。
文章图片
云南旧乃山完小的学生在上艺术课 受访者供图
两千多公里外,穿过荒凉的戈壁与沙漠,甘肃省敦煌市瓜州县广至乡洮砚村小学的艺术教室里,志愿者黄老师把“选择”摆在孩子们面前,她在上海工作,擅长财商领域,认为孩子们应该在价值观形成时,就懂得最智慧的取舍。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坚定且急迫,因为到了当地,她听到一些女生说:“大不了不读书以后找个人嫁了。”
一个小男孩眼睛发光,全程都听得很认真,举手抢答:“他失去了获得教育的机会。”黄老师感慨:“可能有些孩子以后会面临这个选择,他一定会想起今天这堂课,慎重考虑一下。”
黄老师还记得洮砚村小学艺术教室刚建成时,孩子们早早等在教室门口,像欢快的小鹿。他们画自家猪圈的猪,也尝试画没见过的东方明珠;他们刚开始了解素描,就能把人物的眉眼拓在笔下;三三两两一组,将剪纸彩泥塑成摩登女郎。
他们的心从来没被大山困住过,最初到云南做老师时,志愿者彭佳曾问孩子们的梦想,一个低年级孩子十分笃定:“我想当总统。”彭佳感慨:“你会发现,只要给孩子们相对平等的机会,他们和城里的孩子对这个世界的野心是一样的。”
文章图片
涨水坪小学的学生与志愿者老师合影 受访者供图
“你要做个好人”
但无论是乡村教育资源分配,还是当地观念的改变,走起来都很漫长。
推荐阅读
- 明星八卦|佘诗曼张曼玉郭富城早期演技稚嫩被批,后来努力磨炼大翻身
- 艺术展|中国美术馆为因公殉职扶贫干部黄文秀塑像
- 姚玉忠|盗墓祖师爷姚玉忠,被判死刑时大喊:我能打开秦始皇陵!后来呢?
- 引起共鸣|这位艺术家把迪士尼公主变成了母亲,每一张照片都能引起共鸣
- 明星八卦|画家以画风奇妙的画作,嘲讽痴迷裸体油画是一种荒谬的艺术行为
- 清算|鲶鱼入场!首家外资银行卡清算机构连通揭牌后来者如何突围?
- 时尚|服装设计师、时尚摊主、艺术达人齐聚 快来青岛纺织谷时尚大集邂逅“牛飞凤舞”
- 重会|与艺术重会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第五大道主馆即将正式对公众开放
- 刘野|为了得到男友的爱,当年那个瘦至58斤的“骷髅女孩”,后来怎样?
- 本科|最后一次艺术本科机会!山东发布艺术本科批第三次志愿投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