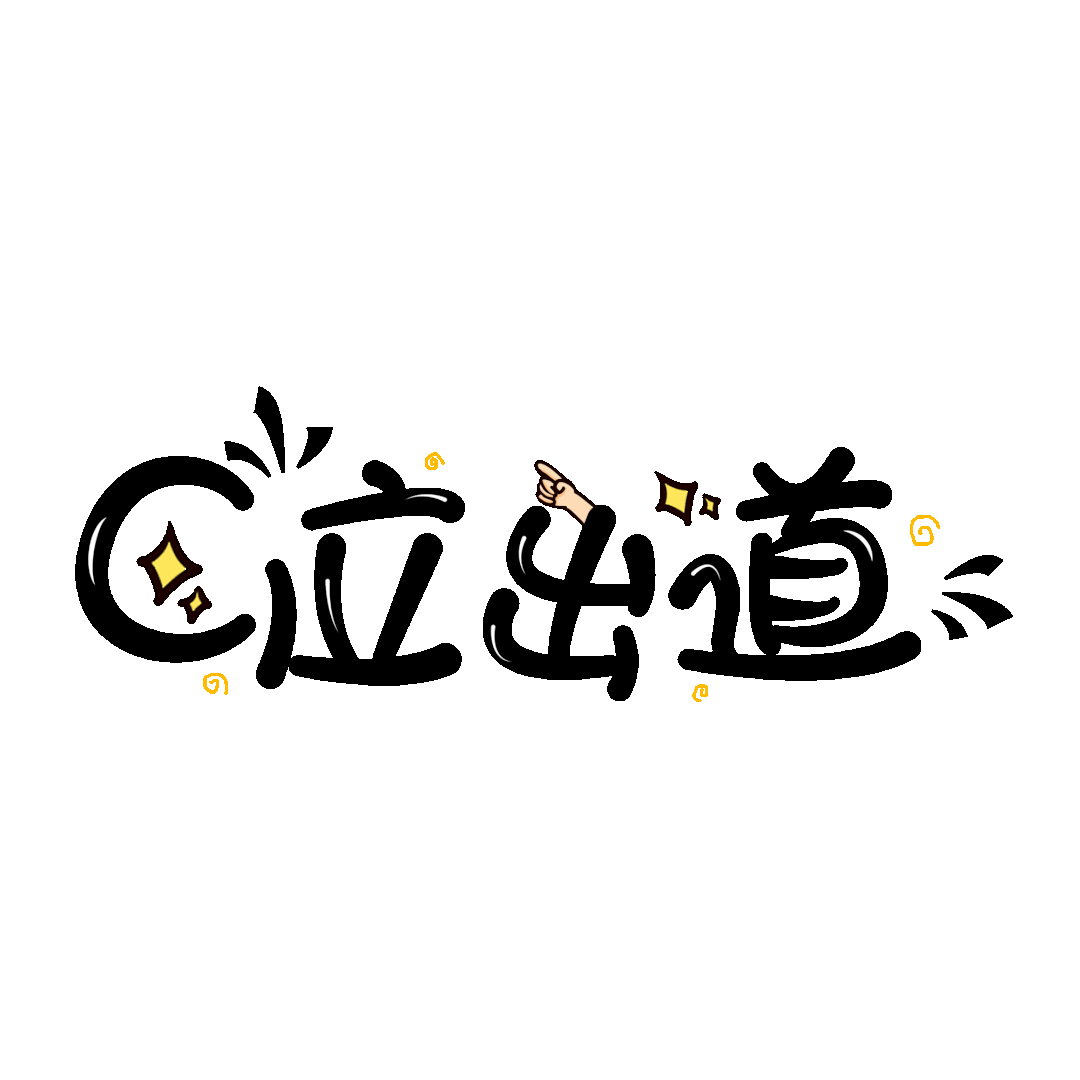“湖州法华寺招聘新媒体小编月入1万元,上海这边待遇怎么样?”采访人员问余儒文 。“差不多吧 。”余儒文微微一笑 。
去年初,“80后”摄影师余儒文收到一封录用通知,来自上海玉佛寺 。这是与静安寺、龙华寺一道并称为上海三大古刹的寺庙之一 。
朋友说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就在脑补余儒文穿着袈裟摄影的样子 。余儒文觉得好笑,在寺庙工作就是出家吗?
多元社会,“新兴”岗位层出不穷,不去了解,便会有偏见 。在北京智化寺工作的胡庆学介绍,寺庙里的许多工作如新媒体编辑、摄影、插花艺术、演奏,还有义工,都是普通人担任 。对寺庙来说,有些人是过客,有些人会久留 。

文章图片
入寺
特殊时期,游客稀少 。“没人的寺庙,最好拍 。”余儒文喜欢建筑里的光阴与细节 。在一处无人小院里,一位灰袍僧人独自坐在木头椅子上,专心阅读经书 。余儒文端起相机,悄声用镜头定格下这一画面 。
余儒文,上海人,34岁,美术专业出身 。在进入寺庙工作之前,他曾以“高空摄影师”的身份活跃于上海摄影界,并斩获多个国际奖项 。
2019年1月,关注玉佛寺微信公众号的余儒文偶然间看到寺庙发布的一篇招新推文,是招聘新媒体中心摄影摄像职位 。余儒文坦言,“当时的想法是,可以将一个城市的宗教文化与城市文化结合起来,拍一组作品” 。而且薪水,确实比原来职位高 。两轮面试之后,他成功入职 。
胡庆学的岗位则有些特殊性 。他在北京智化寺演奏国家级非遗项目——京音乐 。
胡庆学是河北人,1988年他初二辍学,跟着村里乐队学吹管子 。17岁那年,在北京的首届文物节上,胡庆学随家乡乐队参演 。乐种相似,队里年轻人又多,他们很快被智化寺文物保管所几位京音乐“末代艺僧”看在眼里 。十几天后,智化寺文物保管所两个领导和本兴、福广和慧明三位艺僧便开车来到村里 。
胡庆学当时在工地做活,村里人赶紧叫他回来,说北京来的师傅要找传承人 。那时他不知道什么是传承人,只记得稀里糊涂回家,几个小孩乌拉乌拉地吹了一段 。三位师傅看着面相挺慈祥 。晚上,所里两位领导找到几个小孩家挨家挨户问愿不愿意让小孩去北京学习音乐 。没过多久,6个孩子就坐着一辆破面包车去了智化寺,还签了智化寺京音乐首批见习考察班的学员合同 。胡庆学就是其中之一 。
相比上海,北京寺庙中领薪水的岗位少些 。“在寺里工作,只拿点死工资 。”胡庆学一笑,“我没多久就想办法创收去了 。”
佛系
与静安寺一样,玉佛寺位于上海繁华的闹市区 。现代都市与晨钟暮鼓在这里交融 。
在余儒文的镜下,有年轻人会拿着刚买的手机、iPad前来”开光”,也有人厌倦了快节奏的生活,来参与寺里的“七日禅”活动——过七天修身养性的日子,需上交手机、每日吃斋念佛,此外还有“二日禅”、“一日禅” 。
结果,“十日禅”活动很快变为了“四日禅”,“二日禅”,最后变为“一日禅”,因为能坚持过完规定天数的人少之又少 。
余儒文觉得有趣:许多人把佛系理解为随性,但真正的佛系其实是自律 。 他的工作内容是拍摄寺庙里举行的各种活动,每天上班需打四次卡 。寺庙举行法会,法会时间不一,最早从凌晨两三点开始,即使是疫情期间,法师们也会戴口罩如期进行,他也须跟拍 。
法师们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不可接近 。寺庙里有WIFI,僧人们也用手机;有僧人酷爱无人机,有人喜欢投喂寺庙里的猫,也有人会请教余儒文摄影问题 。但通常普通的工作人员和僧侣还是会保持距离,仿佛两个平行世界,互不打扰 。
有些规矩还是要遵守:比如肉不能在寺里吃,食堂的斋菜和游客吃的斋菜并不一样,吃两天就腻了;能量不够时,糖、巧克力来补,再不行,只好出门找肉吃 。
对胡庆学来说,寺庙更像是一座学校 。
在那里,胡庆学第一次了解了京音乐——它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跟宗教相关,却不是佛教音乐 。它最初是宫廷音乐,太监王振把它移入自家智化寺 。京津冀地区民间有好多同源同类的音乐,说白了就是明代的流行音乐 。
胡庆学记得,那时在寺里天天吹管 。智化寺京音乐断代了几十年,一开始练习时,街坊邻居不爱听,说他们扰民,实在受不了了还往院里扔砖头 。为了不扰民,他们每天出门到日坛公园练习 。练习讲究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夏天汗流浃背,冬天哈气成霜 。练习时非常严格,不能动,一动就挨打 。吹笙的时候,在笙嘴上面放两摞铜钱,绝对不能动,一动铜钱就哗啦哗啦往下掉 。
离开,还是久留
胡庆学1991年进寺,生活费是90元,1995年才涨到270元 。
智化寺1992年在原址建成北京文博交流馆,只有住宿没有伙食,在外边吃一顿要两三元,270元连一个月吃饭都不够,还得跟家里要钱 。21岁,在农村已是该成家立业的年纪 。然而胡庆学不说养家糊口,自己都养不活自己 。
那时北京“闹黄虫”(出租车),他想改变生活方式,就学了开车 。考到了驾照才知道,要开出租,必须要北京户口,还要英语过关 。离寺后,他开起货车跑运输 。6位一起入寺的年轻人相继离寺,胡庆学记得师傅并无太多遗憾 。“他们也是过来人 。他们只希望京音乐传承下去 。”
8年货车司机生涯,胡庆学偶尔回寺 。不过通常是因为违章车被扣在北京城里,得空就去找师傅喝上一杯,聊聊天 。“师傅说你干吗来了,我说嗨,车又被扣在东大桥了 。离这挺近,找你来喝一杯 。”
2003年11月,胡庆学接到了智化寺管理所领导的电话 。为保护保护智化寺京音乐,智化寺要出一版CD,文物局跟老师傅想请传人们原汁原味地录一版 。胡庆学问了另外5位传人,大家也都有兴趣 。CD录了10天,进录音棚吹了5首曲子 。
2004年3月份,他又接到电话,说智化寺申请了保护经费,希望请京音乐传人回来传承智化寺京音乐 。这一年胡庆学已经30岁了 。他想,17岁学艺时,没有趁着师傅们技艺最好的时候细心钻研,只是把大框架学了下来 。再回寺认真考虑传承时,师傅身体已经大不如前 。那时,他只觉得一种责任寄托于身 。
4月1日,他卖了货车正式回到智化寺上班,第一个月工资900元,一年工资只有2万元钱 。而跑货运时,他一个月至少有5000元,光景好时,能跑近2万元 。但他还是说服自己,传承京音乐比货车司机更适合作为自己的长期事业 。
为了补点收入,他把拍摄短视频做副业,快手平台上,他边吹管子,边售卖自制乐器,收入倒也不错;凭着吹奏乐器一手好本事,他干了8年吹鼓手,在外边接应酬、白事,也赚了不少钱 。
在上海,由于团队发展方向改变,余儒文选择离职 。今年4月的一天,他像来时一样打包好自己的东西,离开了玉佛寺 。
“我现在还加着他们(僧人)的微信,只是这样而已 。”对于年轻人是否可以选择去寺庙工作,他保持中立态度,“这只是个人的职业选择问题,如果对佛教文化感兴趣,当然没有问题 。”
一个改变是,拍惯了大场面的余儒文开始聚焦更微小的东西 。拍上海的小弄堂,他拍居民的窗,“一窗一世界,一户一人家”,他说 。

文章图片
【上海玉佛寺|月入差不多1万,在上海玉佛寺上班,是怎样的体验?】玉佛寺一景 。余儒文摄
推荐阅读
- | 万多福开心果开心补给站亮相上海外滩BFC创意集市
- 外卖小哥|消防车被堵,外卖小哥上海街头霸气指挥交通,被重奖了!
- 中国新闻网|上海市报告新增14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 科技日报|功能性玉米被端上餐桌 这个数据库帮了大忙
- 林黛玉|林黛玉的百万财产去了哪里?贾琏一语道破!
- 劝降|清军劝降死不投降的陈玉成, 为何却处死愿意投降的李秀成!
- 小美女|街拍:长相清秀的小美女,肌肤如玉,尊贵优雅显大气
- 8月|上海市报告新增14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 推荐|上海昨日新增1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详情公布,9例来自同一地
- 舅妈|聊聊阴阳师SP烬天玉藻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