д»ҺвҖңзҘһз«ҘвҖқеҲ°вҖңж’ӨеҘ–вҖқпјҡйҖ жўҰзҡ„еӨ§иөӣ еҸҳе‘ізҡ„з«һдәү( дёү )
д»–зғӯзҲұиҝҷдёӘжҜ”иөӣ,зңӢеҲ°жҜ”иөӣе’Ң科еҲӣиў«жұЎеҗҚеҢ–,й»„жқғжө©ж— еҘҲ,з”ҡиҮіж„ӨжҖ’:вҖңзңҹжӯЈзҲұ科еҲӣзҡ„дәә,йғҪеҜ№йҖ еҒҮе—Өд№Ӣд»Ҙйј» гҖӮвҖқ
е°ұжҹҗй—®зӯ”е№іеҸ°дёҠйқ’еҲӣеӨ§иөӣиҝҷдёҖиҜқйўҳ,й»„жқғжө©и·ҹж”»еҮ»жҜ”иөӣзҡ„иЁҖи®әдәүеҗөиҝҮеҫҲеӨҡж¬Ў гҖӮвҖң他们иҜҙеә”иҜҘеҸ–ж¶ҲиҝҷдёӘжҜ”иөӣ гҖӮжҖҺд№ҲиғҪеӣ дёәдёӘеҲ«йҖүжүӢзҡ„иЎҢдёә,е°ұе…ЁзӣҳеҗҰе®ҡиҝҷдёӘжҜ”иөӣ,еҗҰе®ҡдәҶжүҖжңүйҖүжүӢзҡ„иү°иҫӣеҠӘеҠӣд»ҘеҸҠжұ—ж°ҙ?!вҖқй»„жқғжө©иҜҙ,д»ҘеҸӮиөӣдёәзӣ®ж Ү,еңЁе…ЁеӣҪеҗ„дёӘең°еҢәеҗ„дёӘеӯҰж Ў,иҜһз”ҹдәҶеӨҡ少科жҠҖеҲӣж–°зӨҫеӣў;иҝҷдәӣзӨҫеӣўйҮҢ,еҸҲжңүеӨҡе°‘еҲӣж–°ж•…дәӢ;еӣҙз»•еҗ„дёӘеұӮзә§зҡ„жҜ”иөӣжүҖеұ•ејҖзҡ„дёҖзі»еҲ—е·ҘдҪңе’Ңе®Јдј ,еҸҲжҝҖеҸ‘дәҶеӨҡе°‘еӯ©еӯҗзҡ„е…ҙи¶Ј,еҶіе®ҡжҠ•иә«дәҺеӯҰжңҜйўҶеҹҹ гҖӮвҖңеҪ“е№ҙжҲ‘и®ӨиҜҶзҡ„е°Ҹдјҷдјҙ们,жңүеҫҲеӨҡзҺ°е·ІжҲҗдёәдјҳз§Җзҡ„з§‘з ”дәәе‘ҳ гҖӮвҖқ
еӯ©еӯҗзҡ„еҲӣж–°
дёҚеҝ…вҖңй«ҳеӨ§дёҠвҖқ
вҖңеҲ«иҜҙе°ҸеӯҰз”ҹ,иҝһз ”з©¶з”ҹйғҪеҫҲйҡҫд»ҺеӨҙеҲ°е°ҫзӢ¬з«ӢеҒҡе®Ңж•ҙйЎ№зӣ®,иҰҒзҗҶжҖ§зңӢеҫ…йқ’е°‘е№ҙ科жҠҖж•ҷиӮІзҡ„зӣ®зҡ„е’Ңдҫ§йҮҚзӮ№ гҖӮвҖқ
жҹҗй«ҳж ЎдёҖдҪҚй•ҝжңҹеҸӮдёҺйқ’е°‘е№ҙ科жҠҖеҲӣж–°ж•ҷиӮІзҡ„иҖҒеёҲжҢҮеҮә,е…¬дј—иҰҒзҗҶжҖ§зңӢеҫ…йқ’е°‘е№ҙ科жҠҖж•ҷиӮІзҡ„зӣ®зҡ„е’Ңдҫ§йҮҚзӮ№ гҖӮ
вҖңеҲ«иҜҙе°ҸеӯҰз”ҹгҖҒйқ’е°‘е№ҙ,з”ҡиҮіиҝһз ”з©¶з”ҹйғҪеҫҲйҡҫд»ҺеӨҙеҲ°е°ҫзӢ¬з«Ӣең°еҒҡдёҖдёӘе®Ңж•ҙйЎ№зӣ® гҖӮеңЁеӨ§еӨҡж•°е®һйӘҢе®ӨйҮҢ,йғҪжҳҜеҜјеёҲжҸҗеҮәжғіжі•,еӯҰз”ҹж“ҚдҪң гҖӮвҖқдёҠиҝ°иҖҒеёҲжҢҮеҮә,ж–°жҖқи·Ҝе’Ңж–°жғіжі•зҡ„жҸҗеҮәжңүиө–еӨ§йҮҸз§ҜзҙҜ,дёҚиғҪжҢҮжңӣеңЁйқ’е°‘е№ҙйҳ¶ж®ө,еӯҰз”ҹе°ұиғҪд»ҺжҰӮеҝөејҖе§ӢзӢ¬з«ӢжҸҗеҮәй—®йўҳгҖҒи§ЈеҶій—®йўҳ гҖӮ
жё…еҚҺеӨ§еӯҰе…¬е…ұз®ЎзҗҶеӯҰйҷўйҷўй•ҝеҠ©зҗҶгҖҒи·Ёз•ҢеҲӣж–°з ”з©¶дёӯеҝғдё»д»»еҲҳиҫүи®Өдёә,科еҲӣзұ»иөӣдәӢдҫ§йҮҚиҖғжҹҘзҡ„иҝҳжҳҜеӯ©еӯҗзҡ„еҲӣж–°ж„Ҹж„ҝ,еҸ‘зҺ°й—®йўҳи§ЈеҶій—®йўҳзҡ„иғҪеҠӣгҖҒеҠЁжүӢе®һи·өиғҪеҠӣд»ҘеҸҠеҲӣж–°ж„ҸиҜҶ гҖӮд»–иЎЁзӨә,иҝҷзұ»иөӣдәӢеә”е……еҲҶејәи°ғд»ҘеӯҰз”ҹдёәдёӯеҝғзҡ„еҺҹеҲҷ,并и®ҫзҪ®зӣёеә”жңәеҲ¶жқҘдҝқйҡңиҝҷдёҖеҺҹеҲҷ гҖӮ
йқ’еҲӣеӨ§иөӣзҡ„иҜ„е®Ўејәи°ғвҖңдёүиҮӘвҖқ,еҚіиҮӘе·ұйҖүйўҳ,иҮӘе·ұи®ҫи®Ўе’Ңз ”з©¶,иҮӘе·ұеҲ¶дҪңе’Ңж’°еҶҷ гҖӮз”іжҠҘжқҗж–ҷж—¶,еҝ…йЎ»дәӨдёҠз”іжҠҘд№ҰгҖҒжҹҘж–°жҠҘе‘ҠгҖҒйЎ№зӣ®з ”究жҠҘе‘ҠеҸҠйҷ„件 гҖӮ
е…Ҙеӣҙз»ҲиҜ„зҡ„йЎ№зӣ®,еҝ…йЎ»еңЁз»ҲиҜ„й—®иҫ©зҺ°еңәеҗ‘иҜ„委жҸҗдҫӣеҺҹе§Ӣе®һйӘҢи®°еҪ•гҖҒз ”з©¶ж—Ҙеҝ—зӯүзӣёе…іжқҗж–ҷ,并зҺ°еңәеұ•зӨәйЎ№зӣ®з ”究жҠҘе‘ҠдёӯжҸҗеҲ°зҡ„дё»иҰҒеҲӣж–°зӮ№ гҖӮ
вҖңеҸӮиөӣйЎ№зӣ®зӢ¬з«Ӣе®ҢжҲҗзҡ„ж ҮеҮҶжҳҜеӯҰз”ҹжңүиҮӘе·ұзҡ„жҖқи·Ҝ,иҮӘе·ұзҡ„и®ҫи®Ўж–№жЎҲ,иҮӘе·ұи®ҫи®Ўеӣҫзәёзӯү гҖӮеҠ е·Ҙе·ҘиүәдёҠеҸҜд»Ҙжүҫд»Је·Ҙ,иҜ•йӘҢзҡ„и®ҫи®ЎгҖҒжқҗж–ҷзҡ„йҖүжӢ©еӯҰз”ҹжҳҜдё»дҪ“,иҜ•йӘҢд»ӘеҷЁи®ҫеӨҮе’Ңжқҗж–ҷзҡ„жҸҗдҫӣеҸҜд»ҘеҜ»жұӮеё®еҠ© гҖӮвҖқеұұдёңзңҒжӣІйҳңеёӮжқҸеқӣдёӯеӯҰиҖҒеёҲгҖҒе…ЁеӣҪеҚҒдҪідјҳз§Җ科жҠҖиҫ…еҜје‘ҳйҷҲзҷ»ж°‘д»Ӣз»Қ гҖӮе…¶е®һ,еӨ§иөӣ并дёҚжҺ’ж–ҘдёӯеӯҰз”ҹеҸӮдёҺиҜҫйўҳз»„з§‘з ”,д№ҹдёҚеҸҚеҜ№д»–们еңЁдёҖдёӘеӨ§йЎ№зӣ®дёӯеҒҡиҮӘе·ұзҡ„е°ҸйЎ№зӣ® гҖӮдҪҶе…ій”®еңЁдәҺ,еӯҰз”ҹеҲ°еә•иҮӘе·ұеҒҡдәҶд»Җд№Ҳ гҖӮ
йӮЈдёәд»Җд№ҲжңүдәӣиҺ·еҘ–йЎ№зӣ®,зңӢиө·жқҘе·Із»Ҹе®Ңе…Ёи¶…и¶ҠдәҶдёӯе°ҸеӯҰз”ҹзҡ„ж°ҙе№і?
жңүдәӣ,еҸҜиғҪжҳҜж Үйўҳеј•иө·зҡ„иҜҜи§Ј гҖӮвҖңиҜҙзҷҪдәҶжҳҜвҖҳж—§зү©ж–°з”ЁвҖҷ гҖӮдј з»ҹдёҠз”ЁдәҺAйўҶеҹҹзҡ„жҠҖжңҜ,иў«еҲӣйҖ жҖ§ең°з”ЁеңЁдәҶBйўҶеҹҹдёҠ гҖӮдҪҶиҝҷдёӘжҠҖжңҜжң¬иә«,дёҚдёҖе®ҡйқһиҰҒжҳҜеӯҰз”ҹиҮӘе·ұеҸ‘жҳҺзҡ„ гҖӮвҖқй»„жқғжө©иҜҙ,иҝҷж¬ЎиҺ·еҘ–жҲҗжһңиў«зҪ‘еҸӢж”»еҮ»,еҸҜиғҪеӨ§е®¶д№ҹиҜҘеҸҚзңҒдёӢеӨҡе№ҙжқҘзҡ„дёҖдёӘеҸӮиөӣд№ жғҜвҖ”вҖ”з”Ёй«ҳеӨ§дёҘи°Ёзҡ„ж ҮйўҳжқҘжҸҸиҝ°иҮӘе·ұзҡ„иҜҫйўҳ гҖӮвҖңе®ғе®№жҳ“еј•иө·жіЁж„Ҹ,дҪҶдёҚе°Ҹеҝғд№ҹжҲҗдәҶвҖҳж Үйўҳе…ҡвҖҷ гҖӮвҖқ
иҝҳжңүдёҖдәӣ,еҸҜиғҪзңҹзҡ„ж¶үе«Ңиҝқ规иЎҢдёә гҖӮ
вҖңе…¬дј—зҡ„иҙЁз–‘зҡ„зЎ®з»ҷеӨ§иөӣдё»еҠһж–№жҸҗдәҶдёӘйҶ’ гҖӮвҖқзүӣзҒөжұҹеқҰйҷҲ,вҖңжҲ‘们еҝ…йЎ»еқҡжҢҒеҠһиҝҷдёӘеӨ§иөӣзҡ„еҲқеҝғ,йӮЈе°ұжҳҜеҹ№е…»е’ҢйҖүжӢ”жңүжҪңеҠӣзҡ„科жҠҖеҲӣж–°дәәжүҚ,е®ғдёҚеә”иҜҘжҲҗдёәе°‘йғЁеҲҶдәәеҫҮз§Ғзҡ„е·Ҙе…· гҖӮвҖқ
йҷҲзҷ»ж°‘жҢҮеҮә,жҜ”иөӣйңҖиҰҒйЈҺжё…ж°”жӯЈзҡ„зҺҜеўғ,д№ҹйңҖиҰҒеӨ§дј—еӘ’дҪ“еҸӮдёҺзӣ‘зқЈ гҖӮд»–е»әи®®,жҜ”иөӣеҜ№еҸӮиөӣйҖүжүӢзҡ„дҪңејҠдҪңеҒҮиҝҳиҰҒжңүжӣҙе®Ңе–„зҡ„йүҙеҲ«жңәеҲ¶,жҜ”еҰӮз»ҷйҖүжүӢжҸҗдҫӣеӨ§еӯҰжҲ–з ”з©¶жүҖзҡ„е®һйӘҢе®Ө,з”ЁдәҺйҖүжүӢзӢ¬з«ӢйҮҚеӨҚжҹҗдёӘиҜ•йӘҢзҺҜиҠӮжҲ–ж”№иҝӣе…¶йЎ№зӣ®зҡ„жҹҗзҺҜиҠӮ,д»ҘйүҙеҲ«йҖүжүӢйЎ№зӣ®з ”究зҡ„зңҹе®һжҖ§ гҖӮ
гҖҗд»ҺвҖңзҘһз«ҘвҖқеҲ°вҖңж’ӨеҘ–вҖқпјҡйҖ жўҰзҡ„еӨ§иөӣ еҸҳе‘ізҡ„з«һдәүгҖ‘вҖңжҲ‘们еёҢжңӣзӣёе…ійғЁй—ЁеҜ№еҸӮиөӣдҪңејҠйҖ еҒҮиЎҢдёәжңүжғ©зҪҡеҸҠй—®иҙЈжңәеҲ¶,дҝқйҡңеӨ§иөӣйҖүжӢ”еҮәзңҹжӯЈзҡ„еҲӣж–°дәәжүҚ,дҪҝеӨ§иөӣдёҚж–ӯеҸ‘еұ•е®Ңе–„ гҖӮвҖқйҷҲзҷ»ж°‘иҜҙ гҖӮ
еҺ»еҠҹеҲ©еҢ–
и®©жӣҙеӨҡиӢ—еӯҗвҖңеҶ’вҖқеҮәжқҘ
еңЁеҫҲеӨҡзңҒеёӮ,йқ’еҲӣеӨ§иөӣжҲҗз»©д»ҚжҳҜдёӯиҖғеҪ•еҸ–е’Ңе°ҸеҚҮеҲқзҡ„еҠ еҲҶйЎ№ гҖӮ
иҖҒеёҲвҖңд»ЈеҠівҖқгҖҒ家й•ҝвҖңиҝҮеәҰеҸӮдёҺвҖқгҖҒжңәжһ„еҢ…иЈ…вҖңй«ҳеӨ§дёҠвҖқзҡ„йЎ№зӣ®вҖҰвҖҰиҝҷдәӣйқ’е°‘е№ҙ科еҲӣжҜ”иөӣдёӯзҡ„жҖӘзҺ°иұЎ,йҖғдёҚејҖвҖңеҲ©зӣҠвҖқдәҢеӯ— гҖӮ
е…¶е®һ,иҝ‘е№ҙжқҘйқ’еҲӣеӨ§иөӣе·Із»ҸйҖҗжёҗе’ҢеҚҮеӯҰвҖңи„ұй’©вҖқ гҖӮеүҚеҮ е№ҙ,еңЁиҜҘжҜ”иөӣиҺ·еҫ—е…ЁеӣҪжҖ§дёҖзӯүеҘ–иғҪеӨҹеңЁй«ҳиҖғдёӯеҠ еҲҶ,еҘ–йЎ№д№ҹжҲҗдёәй«ҳж ЎиҮӘдё»жӢӣз”ҹе…Ҙеӣҙзҡ„ж•Ій—Ёз – гҖӮдҪҶзҺ°еңЁ,е®ғеңЁй«ҳжӢӣдёӯзҡ„дҪңз”Ёе·Із»ҸејұеҢ– гҖӮиҮӘдё»жӢӣз”ҹ,еңЁ2020е№ҙд№ҹжҲҗдәҶвҖңејәеҹәи®ЎеҲ’вҖқ гҖӮд»Һ36жүҖй«ҳж Ўзҡ„жӢӣз”ҹз®Җз« еҸҜд»ҘзңӢеҮә,е…ЁеӣҪйқ’еҲӣеӨ§иөӣеҘ–项并дёҚеңЁз ҙж је…ҘеӣҙжқЎд»¶д№ӢеҲ— гҖӮдҪҶеңЁеҫҲеӨҡзңҒеёӮ,йқ’еҲӣеӨ§иөӣжҲҗз»©д»ҚжҳҜдёӯиҖғеҪ•еҸ–е’Ңе°ҸеҚҮеҲқзҡ„еҠ еҲҶйЎ№ гҖӮ
жҺЁиҚҗйҳ…иҜ»
- еІ‘жҹҗиҜә|16еІҒзҘһз«Ҙж—ҘдҪңиҜ—2000йҰ–пјҹж¶үдәӢеҹ№и®ӯжңәжһ„еӨ§й—Ёзҙ§й—ӯ
- вҖң16еІҒеҘізҘһз«ҘвҖқиғҢеҗҺпјҢйҡҗи—ҸзқҖдёҖжқЎвҖңйқһеҗҢеҜ»еёёвҖқзҡ„е…ізі»й“ҫ
- пјӮзј”йҖ 16еІҒзҘһз«ҘпјӮеҹ№и®ӯжңәжһ„е…ій—Ё еҲӣе§ӢдәәйҖҖеҮәе…¬еҸёиӮЎд»Ҫ
- вҖңзј”йҖ 16еІҒзҘһз«ҘвҖқеҹ№и®ӯжңәжһ„е…ій—Ё еҲӣе§ӢдәәйҖҖеҮәе…¬еҸёиӮЎд»Ҫ
- еӨ§зҢ«иҙўз»Ҹ|дёӯеӣҪзҘһз«ҘйҖҖеҢ–еҸІпјҡеҮә家гҖҒеҗ№зүӣгҖҒйҖ еҒҮгҖҒжҗһдј й”Җ
- |еұӮеҮәдёҚз©·зҡ„дёӯеӣҪвҖңзҘһз«ҘвҖқ
- 16еІҒеҘіеӯ©вҖңж—ҘдҪңиҜ—дёӨеҚғйҰ–вҖқпјҒи°ҒеңЁеҲ¶йҖ вҖңзҘһз«ҘвҖқпјҹ
- е…ЁеӣҪйқ’е°‘е№ҙ科жҠҖеҲӣж–°еӨ§иөӣ|д»ҺвҖңзҘһз«ҘвҖқеҲ°вҖңж’ӨеҘ–вҖқпјҡйҖ жўҰзҡ„еӨ§иөӣ еҸҳе‘ізҡ„з«һдәү
- зҘһз«Ҙ|жІЎжңүвҖңзҘһз«ҘвҖқпјҢеҸӘжңүиҝқ规зҡ„вҖңзҘһж“ҚдҪңвҖқ
- и®із–ҫеҝҢеҢ»|вҖңзҘһз«ҘвҖқеҰӮжӯӨйҖ пјҢи°ҒиҜҘеҗғзӮ№вҖңиҚҜвҖқпј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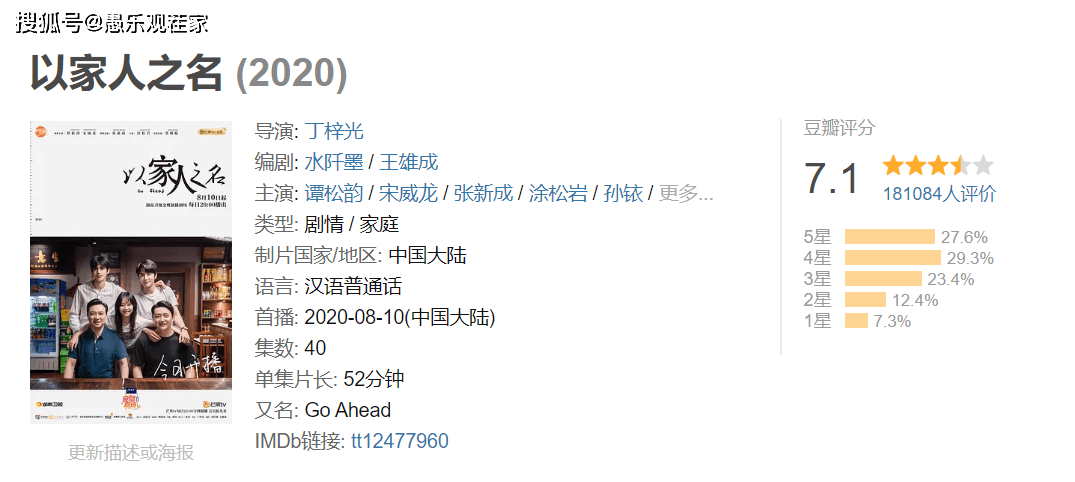









![[е•ҶеҠЎйғЁ]е•ҶеҠЎйғЁпјҡдёӯеӣҪжІЎжңүд№ҹдёҚдјҡеҮәзҺ°еӨ§и§„жЁЎеӨ–иө„ж’ӨзҰ»жғ…еҶө](http://aqimg.010lm.com/img.php?https://pic.bbanp.com/img/5080851962419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