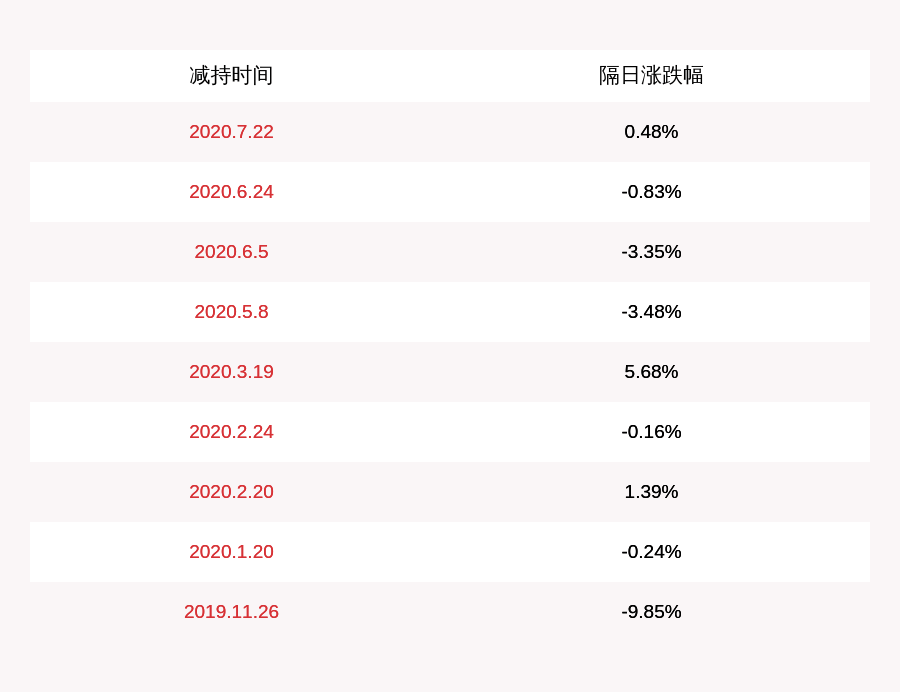先祖们走过白令陆桥多少次,才最终定居在美洲
原文作者:Anne C. Stone人类曾在末次冰期从西伯利亚东北部迁移至美洲 。 通过分析古代和现代个体的基因组 , 研究人员揭示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群的历史 。遥远的西伯利亚东北部曾是古人类进入美洲的入口 , 而今居住着文化背景各异、讲着不同语言的群体 。 在晚更新世时期(从12.6万年前到1.17万年前的冰河时期) , 西伯利亚的这块地区与北美相连 , 大陆桥和毗连区域形成了一块名为“白令陆桥”(Beringia)的区域 。 狩猎采集者似乎曾穿越[1–3]西伯利亚的广袤土地 , 进入了白令陆桥 , 期间以猛犸象等巨型动物和其它动物为生 。 Sikora团队[4]和Flegontov团队[5]在《自然》发表的两篇最新论文 , 考察了西伯利亚东北部和北美北部的古代人群的基因足迹 , 以期揭示他们与现代人群的关系 。 Sikora团队还考察了在过去的4万年中 , 这些人群如何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Sikora等人对古代西伯利亚东北部的34人的基因组进行了分析 。 其中两人被埋在俄罗斯的Yana RHS——一个已有3.16万年历史的考古遗址 , 拥有来自西伯利亚东北的最早人类遗骸;其它个体则来自9800年前至600年前 。 迄今为止 , Yana的个体信息可以说是末次盛冰期(LGM , 约2.65万-1.9万年前)前 , 从西伯利亚东北部采集到的唯一的基因组数据——不过有证据显示 , 人类早在4.5万年前就占据了西伯利亚中部[6] 。正是因为LGM前的欧亚人基因组数据非常有限 , 这也为认识当时的人群差异情况带来了挑战 。 Sikora等人的分析支持这样一种观点 , 即这些人群分布广泛 , 且很有规律(不同人群之间存在遗传学差异) 。 作者还指出 , Yana人属于一支研究小组称之为“古代北西伯利亚人”(Ancient North Siberians, ANS)的群体 , 这一群体在3.8万年前从西欧亚人中分离出来 , 此前不久西欧亚人也刚与东亚人分离 。欧亚和北美之间的大陆桥从3.4万年前一直存在至1.1万年前[3,7] 。 据信 , 人类在3万年前到1.5万年前左右 , 迁移至此 。 通过古气候模拟和遗传数据分析 , Sikora等人认为 , 至少有部分古代北西伯利亚人在LGM期间迁移至白令陆桥南部(图1) , 且他们正是美洲首批定居者(有时也被称为“第一批人类”)以及约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人群的共同祖先——作者将这个人群称为“古代古西伯利亚人” 。 东亚人群对古代古西伯利亚人贡献了75%的DNA , 对第一批人类贡献了63%的DNA 。 由此可见 , 这两支后代之间存在地理分隔 。 对此 , 作者认为他们是从2.4万年前左右开始分离的 。
图1|古代人类穿越白令陆桥的迁徙图 。 在末次盛冰期 , 名为白令陆桥的地区连接了西伯利亚和美洲 。 图中 , 白令陆桥为叠加在现代西伯利亚和北美位置上的浅蓝色部分 。 Sikora等人[4]分析了西伯利亚东北部古代个体遗骸的DNA数据 , 认为有一支他们称为“古代北西伯利亚人”的群体可能在末次盛冰期(从2.65万年前至1.9万年前)从西伯利亚迁至环境更宜居的地区 , 比如白令陆桥的南部(椭圆虚线位置) 。 作者假定这些个体是美洲首批定居者(即第一批人类)以及后来的西伯利亚人种群(即古代古西伯利亚人)的共同祖先 。 东亚人也对这两个种群的遗传起源有贡献 。 古代古西伯利亚人种群随后在整个西伯利亚扩张 , 而第一批人类也扩散至美洲 , 这两个种群预计在2.4万年前开始分散 。LGM之后 , 大陆桥的两边(包括其他地区)都出现了重大的环境和文化变化 。 在西伯利亚 , 考古证据显示当地人使用的工具技术发生了变化 , 这与当时猛犸象象牙的稀缺相呼应[8] 。 将这些考古证据与Sikora等人的遗传数据结合起来 , 可知古代古西伯利亚人种群的扩散 , 曾造成了种群和文化上的改变 。 在1.1万年前至4000年前左右 , 古代古西伯利亚人被一个名为“新西伯利亚人”的群体所取代 , 抑或与他们产生了基因交流(孕育了后代) 。同样是在LGM之后 , 第一批人类开始向南迁移[9,10] , 而其他种群仍留在了北方——Flegontov等人把研究目标对准了这些种群后来的历史 。 更具体地说 , 作者考察的是考古学上定义为不同文化的种群之间的关系 , 比如在约5000年前穿越美洲北极的古爱斯基摩人 , 以及800年前在扩散过程中可能取代了古爱斯基摩人的新爱斯基摩人(图2) 。 研究人员还考察了这些古代种群与讲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纳-德内语和其他语言的现代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 。
图2|古人种群从西伯利亚东北部向外迁移 , 并穿越美洲北极 。 Flegontov等人[5]分析了美洲北极的古代和现代个体的DNA 。 作者确定了一个古代西伯利亚人种群是古爱斯基摩人种群的祖先 , 这一种群在约5000年前从西伯利亚迁移至美洲和格陵兰 。 作者发现 , 古爱斯基摩人是现代以纳-德内语(居住在图中粉色区域)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现住在纳-德内地区周围)为母语人群的祖先之一 。Flegontov等人考察了48个古代个体和现代伊努皮亚特人(现居住在阿拉斯加北部)的基因组上的约124万个可变核苷酸位点 。 此前的研究[11]未能确定古爱斯基摩人是否与其他人类种群有过基因交流 。 Flegontov和同事的数据确定了古爱斯基摩人对新爱斯基摩人有基因贡献 , 因此可以说 , 古爱斯基摩人是现代爱斯基摩-阿留申语族以及纳-德内语族人群的祖先之一 。这两篇最新发表的论文都对古爱斯基摩人展开了深入分析和讨论 。 不同之处在于 , Sikora等人侧重于它们的西伯利亚祖先 , 而Flegontov等人更注重考察它们与后来出现的北美人种群之间的关系 。 通过鉴定 , Sikora等人确定了古爱斯基摩个体(包括一个住在格陵兰的Saqqaq个体)是古代古西伯利亚人和一支东亚支系的混血后代 。 Flegontov等人则将这一西伯利亚祖先称为“原始古爱斯基摩人”(Proto-Palaeo-Eskimo) 。 两篇论文还描述了古代人群在整个白令海峡相互交流以及迁回西伯利亚的证据 。 Sikora等人认为 , 古代古西伯利亚人对现代纳-德内语族人群具有基因贡献 , 但与Flegontov等人观点不同的是 , 他们认为这些DNA贡献来自西伯利亚祖先 , 而不是古爱斯基摩祖先 。两篇论文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 , 虽然两个团队分析的部分DNA样本来自同一处考古遗址 , 但尚无法区分这些样本是否来自同一个体——这也是考古材料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 对于考古学来说 , 一个通用的操作规范是鼓励科学家们提供最初发掘队员所使用的文物识别号 , 从而促进开展跨研究的对比和验证 。 这么做还有助于确保对考古遗址的破坏性取样可以得到适当调整 , 把对这些不可再生资源的伤害降至最低 。 这种操作规范还能保证古代人类的后裔也可以加入关于采样的讨论(Flegontov等人在论文中用实例证明 , 他们曾咨询了阿拉斯加群体的成员) 。两项研究不仅揭示了西伯利亚人种群和北美北部人种群在历史长河中曾发生过群内以及群间的复杂交流 , 同时也考察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 尤其是LGM时期的冰河时代气候如何迫使人类前往“庇护所”(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 , 之后随着冰川融化或气候变暖 , 他们的后代又开始向其它地区继续扩散 。 然而 , 对于最初占领Yana地区后的2万年 , 考古学家尚未找到任何人类基因数据 。 用考古学上的话来说 , 这是一段巨大的空白 。 今后 , 需要对这一时期的西伯利亚和白令陆桥人种群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 才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种群的遗传和文化多样性 。另一方面 , 确定这些庇护所在西伯利亚东北部的具体位置 , 以及这些地区的环境条件也很有必要 。 尤其重要的是 , 了解白令陆桥庇护所的人口结构 , 以及这一结构是否支持白令陆桥滞留(standstill)假说[12] 。 滞留假说认为第一批人类在LGM期间 , 即冰盖向南扩张之前曾被隔离 。到底经过几“波”迁移 , 人类才在美洲实现了定居?对于这一旷日持久的争论 , 最新论文给出的回答可能是只有两波:第一批人类以及古爱斯基摩人 。 如果真的是这样 , 这又如何解释部分亚马逊人群似乎与南岛语族人群(今分布在东南亚、大洋洲和马达加斯加)有相同的DNA[13,14]?白令陆桥庇护所的人群是否也有这一起源?最后 , 西伯利亚东北部和远北美洲的环境变化、人类迁移以及文化与遗传适应曾发生过哪些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两项最新研究将为我们对白令海峡周围的古代人类探索之路指明方向 。1.Nogués–Bravo, D., Rodríguez, J., Hortal, J., Batra, P. & Araújo, M. B. PLoS Biol. 6, e79 (2008).2.Pitulko, V., Pavlova, E. & Nikolskiy, P. Quat. Sci. Rev. 165, 127–148 (2017).3.Hoffecker, J. F., Elias, S. A., O’Rourke, D. H., Scott, G. R. & Bigelow, N. H. Evol. Anthropol. 25, 64–78 (2016).4.Sikora, M. et al. Nature570, 182–188 (2019)5.Flegontov, P. et al. Nature570, 236–240 (2019).6.Pitulko, V. V. et al. Science 351, 260–263 (2016).7.Hu, A. et al. Nature Geosci. 3, 118–121 (2010).8.Pitulko, V. V. & Nikolskiy, P. A. World Archaeol. 44, 21–42 (2012).9.Fagundes, N. J. R. et al. Am. J. Hum. Genet.82, 583–592 (2008).10.Goebel, T., Waters, M. R. & O’Rourke, D. H. Science319, 1497–1502 (2008).11.Raghavan, M. et al. Science345, 1255832 (2014).12.Tamm, E. et al. PloS ONE2, e829 (2007).13.Raghavan, M. et al. Science349, aab3884 (2015).14.Skoglund, P. et al. Nature525, 104–108 (2015).原文以The lineages of the first humans to reach northeastern Siberia and the Americas为标题发表在2019年6月5日的《自然》新闻与观点版块
推荐阅读
- 特朗普要走过去拍照,催泪弹“开路”先
- 总统要走过去拍照,催泪弹“开路”先!
- 走过了一个坎,才有下一个坎
- 汉人十大远古先祖的样貌新鲜出炉了!速来参照
- 我走过西安的街,看见苦等报复性消费光临的人
- 赵世平的诗歌:这就是生活
- 走过39个年头,香港电影金像奖就只剩情怀了?
- 长征走过五十年 长征火箭好样的!
- 【体坛扒客】孙杨一夜损失上亿!上诉恐成走过场,网友支招:转做污点证人吧!
- 赵世平的诗歌: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