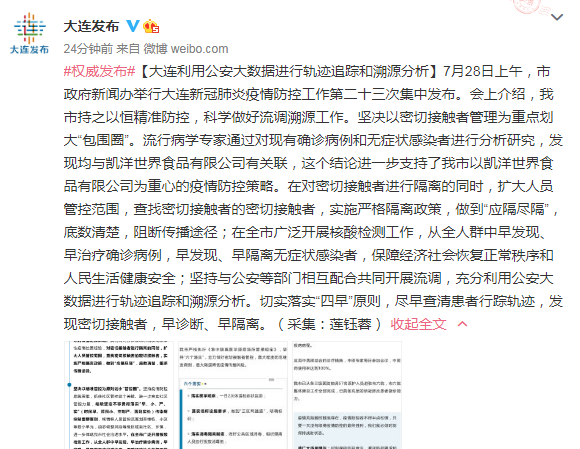看来,我还得写一篇文章说明一下。近40多年来,年龄或比我大、或比我小一些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出色的才华,趁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东风,像一部分抢得先机下海的经济界人士一样,早早地摆脱了原先贫困窘迫的处境,生活得自在潇洒,不少人混得风生水起,可谓意得志满。如同摆脱了贫困、走上小康生活之路的农民工群体一样,一代已无后顾之忧的知识分子群体,同样面临着“我们的灵魂在何处安放”的诘问。只要深入到每一个省、每一座大城市的文学艺术界中,就不难听到类似程步涛以及他周围一大帮人物的轶事和传奇,有的故事和情节、人物关系甚至比我已经写下的还要出人意料、扑朔迷离。
我这样说,不知是不是解答了有人读了《魂殇》之后感觉某人似曾相识的迷惑。
广而言之,岂止是农民工群体、经济企业界人士,一代知识分子在富裕以后,都存在一个人生观、价值观及精神慰藉的问题,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国人,都该在自己的内心自问一下:你的灵魂该在何处安放?
涉及人类灵魂的事物,很多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还有读者看完了《魂殇》,意犹未尽地追着我问:故事好像没有完,程步涛猝死的真相,到小说结尾都没有讲出一个所以然来。
还有年轻的读者一口气看完小说,捧着书来问我:你前面铺垫得这么多,总该给我们一一剥离解析吧?要不读完后心头欠欠的,总觉得不满足。
不过瘾啊。我身边的同伴看了这本新书,也直截了当地这么说。
记得40年前,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在发表和出版以后,也有不少读者,特别是和我年龄相仿、同样有知青经历的读者,不停地向我发问:“杜见春和柯碧舟后来怎么样了?他们回去以后,还应该有很多故事啊!”“哪怕生活在内地,或是回城之后,还有很多故事呢,哪有这么简简单单就结束了的事。”还有热情的读者,写好了《蹉跎岁月》的续集寄来,说是无论写《蹉跎岁月》之二,还是接着往下拍电视剧,这些故事情节都可以采用,就这么结尾太可惜了。
30年前,《孽债》出版之后,尤其是25年前改编为电视剧广为播出之后,希望知道五个孩子以后的故事声浪,一波高过一波,总是说就这么结束太可惜了。从普通老百姓、老知青,到高层的官员,都向我直截了当提出,应该为他们写个续集。
其实,从青少年时代起,我就是个热心的读者,可以说,读了一辈子。我读得很快,又很慢。整个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的两三个月,为了排除烦扰,我几乎白天黑夜都在读书。读得快是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新作、杰作确实很多,我得想方设法地一一浏览,学习,鉴别,看看这些比我年长、大多数比我年轻的作家们怎样选材,怎么写,怎么面对网络的冲击。读得慢是碰上了我觉得值得细细揣摩和品鉴的作品,反复地翻来覆去地读,真有爱不释手之感。
把话题拽回来,我要说的是,《魂殇》该写该交代的,在作品的进展过程中,我都写了。至于程步涛之死的谜团,我已做出了解读和破译。那么读者为何还会觉得没讲清楚,不过瘾呢?
我想这是阅读习惯使然。我们喜欢皆大欢喜的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读者才觉得心满意足。我们的很多故事都是这么结尾的。就如同有关部门破一个案子,历经艰辛曲折,最后终于把元凶逮捕法办了,大快人心地画上句号,归档。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会有比例甚少的一些“悬案”,挂在那里,被束之高阁,尘封在档案之中。多少年之后,处理积案时,会把它翻出来。还有些人和事,被我们以称为“冷处理”的方式,让时间和历史的烟尘蒙上一层面纱,逐渐地让世人淡忘。
就如同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某个引人注目的热点人物,某个引起街谈巷议、众说纷纭乃至争论不休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被人遗忘一样。这样类似的人和事,小至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大到轰动一座城乃至一个省,甚至惊动了国家和世界,都曾经有过,以后也仍旧还会发生。在我书写《魂殇》后记的前后,正是席卷人类和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弥散之时,关于病毒的源头,正争论得不亦乐乎。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年,影响了整个欧洲和世界的“西班牙流感”的起源,讲清楚了吗?查获元凶了吗?
推荐阅读
- 这群被公安工作“耽误”的灵魂画师
- 看多媒体互动展厅弘扬党建文化
- 希姆博尔斯卡
- 李白写下一首最孤独的诗,原来孤独不是寂寞,是灵魂深处的无奈
- 性能强悍的——鬼丸武士刀
- 带着“肉体”去探索,灵魂是要上当的,《老子》快乐不是享乐
- 陈建明用灵魂表情大意,将独特的色彩玩出新的高度
- 优雅格调的灵魂居所!
- 他是英国“灵魂画家”,跟画融为一体,所到之处全是画
- 鲁迅|孔乙己脱下长衫后,好似剥离了灵魂,那是作为封建文人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