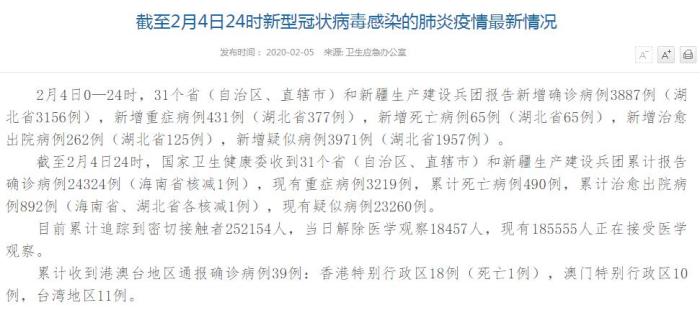高文彬|东京审判亲历者高文彬:生而逢时的淡泊者( 三 )
一根扁担
1979年初 , 人生中第二次重返上海时 , 从火车站走出的高文彬 , 脸晒得黢黑 , 肩背处因常年承担重物肿得老高 , 一根扁担挑着他的全部家当 。
女儿形容他当时的状态 , “被改造得彻底 , 和农民一模一样”——那时 , 高文彬已经56岁 , 他人生青壮年的时光都消耗在了苏北和江西的劳改农场 , 整整27年 。
在被卷入那起改变他人生走向的案件之前 , 他最新一份工作是在解放后的上海军管会外事处 。 1952年 , 在东吴大学的老师艾国藩被打成特务后 , 高文彬曾因工作事宜前去请教老师而受牵连 , 被控“泄露国家机密”判刑10年 。
一个常年和英文、律法打交道的知识分子每天要面对繁重无尽的体力劳动 。
有时 , 一天插秧要插一亩地 , 累到“晚上睡觉敲锣都敲不醒” 。 在鄱阳湖边修筑堤坝 , 用身体去挡住木板 , 泡在水里两个小时轮换一次 。
挑泥负重 , 肩膀和背部皮肤都磨出水泡 , 光着膀子在阳光下再晒到脱皮 。 休息时都不敢平躺 , 否则一转身凉席就能拉下一层皮 。 反复如此 , 他的背后来变得像“乌龟壳”一样粗糙 。
莫须有的罪名直接击垮了他的家庭 。 妻子与他分离 , 亲弟弟也和他划清界限 。 女儿高岚也因为父亲的关系 , 被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 , 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 。
他也有过最绝望的时刻 , 但从没想过终结自己的生命 。 后来在回忆中 , 他说当时的想法是 , “我没有做错什么 , 怎么会到这种地步”、“我要是死了 , 别人还以为我是畏罪自杀 , 一定有一天还我一个清白” 。
为了提高身体免疫力 , 他花钱从当地老乡那里买来别人不愿吃的黄鳝和泥鳅 , 丢进搪瓷缸里加点盐和水 , 烧火煮熟吃光 。
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 , 高文彬依然保持体面 。 他四十多年前的学生刘瑛 , 在一篇题为《永远的绅士》文章中 , 回忆了当时在江西一个半军事化农场子弟学校担任英文老师的高文彬:“那个年代 , 人们普遍鄙视穿着打扮 , 完全忽略个人卫生 , 而高老师永远把自己的头发三七开 , 梳得纹丝不乱;即便下田干活 , 也把裤脚、衣袖卷得整整齐齐 。 他总是穿一件干净的立领的确良衬衫 , 配一条有笔挺裤线的西装裤 , 夹着讲义 , 走上讲台 。”
回到上海后 , 不管来人是谁 , 大多知道拜访高先生需要遵守他的两条规矩:来之前先打电话告知 , 到家后必须留下吃饭 。 只要家里有外人 , 在铺着黄色木地板的家里他也一定会换上皮鞋 。
请客人喝咖啡 , 他会提前准备水果饼干、奶油蛋糕 。 要是大夏天 , 他还会让保姆在湿润的小毛巾上洒几滴花露水 , 说是能提神醒脑祛暑热 。
好几次 , 程兆奇邀请老先生出席东京审判相关活动 , 老爷子总是打扮得一丝不苟 。 他对自己着装的要求到了严格的程度 。 几十年来 , 他的西服和长裤都是在南京路一家老裁缝店里定做 。 有一次他到学校参加会议 , 车子开了一半才发现手表没戴 , 他要返回去取 。 同车的向隆万劝住了他 , 抵达会场后硬是去借了一块手表给他 , “其实他也不看时间 , 就是习惯了要戴着 。 ”
他无法理解女儿高岚为什么会喜欢穿过于随意的牛仔裤 , “怎么穿成这样子?不好不好 。 ”连保姆的外出形象他也顺带管理 。 去年9月18日 , 他去南京参加关于东京审判的巨幅油画开幕式 。 保姆吴元丽平常为了照顾他 , 常穿好走路的运动鞋 , 会议开始前换上了他特意交代的黑色高跟鞋 。
那根陪伴了他多年的黄棕色扁担最后被他带回了上海 , 1.5米的旧物像证据般保留在家中 。 竹片内侧 , 至今还能看到刻下的清晰工整的名字:文彬 。
他对于那段经历并没有过度埋怨或仇恨 。 “他是很积极的人 , 是抱着一定可以重见天日的信心坚持活下来的 。 ”他的一位朋友如是说 。
“费力不讨好”的事
就在《元照英美法词典》正式出版的2003年 , 题为《被遗忘30年的法学精英》一文 , 报道了这本“没有政府支持、缺少经济资助 , 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词典诞生之路和它背后的东吴老人们 。
推荐阅读
- 收入|全球亿万富豪财富总额达10.2万亿美元;东京市中心二手住宅8月环比上涨1.1%达538.8万元|Do早
- 中国新闻网|东京新增新冠确诊203例 日增感染数连续2天超200例
- 感染者|东京新增新冠确诊203例 日增感染数连续2天超200例
- 大阪钢巴|日职联:FC东京杯赛晋级状态稳定,大阪钢巴4连胜士气急速回升
- 乒乓球|大赛0的突破,陈梦8比0连胜王曼昱孙颖莎,为东京奥运增添砝码
- 消费者|职业打假索赔百万,法院审判结果为何反转再反转?
- 央视|职业打假索赔百万,法院审判结果为何反转再反转?
- 消费者 职业打假索赔百万,法院审判结果为何反转再反转?
- 央视新闻|职业打假索赔百万,法院审判结果为何反转再反转?
- 快了棒棒糖|80亿美元一分不能少!蓬佩奥抵达东京催款!考验菅义伟的时候到了